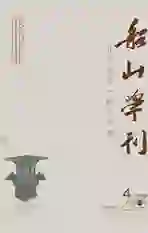论虞舜德法相济的治政理念对现代社会的借鉴
2018-10-29杨金砖
杨金砖
摘 要: 虞舜时代虽然离我们今天已相当遥远,但是他所开创的虞舜文化——即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社会规范,却如一只烛火,照亮了中华民族夏商以来的所有文化进程,尤其在国家治理与社会构建方面,其卓越贡献,至今仍值得我们悉心体会、继承弘扬。虞舜所倡导的德治不仅与西方的法治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其道德教化并不排斥法的惩罚。
关键词: 虞舜;德政;法治
《大学》开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告诉我们在一个人的修身、养性、格物、致知的过程中,“明德”“亲民”“至善”是我们最大的追求。虞舜之所以被儒家学派尊奉为中华道德文化的至圣,儒家学说的鼻祖,原因是虞舜在德政天下中的克己慎独与修齐治平,真正实现了“内圣外王”的道德修炼。他创设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路,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理论根基。
一、虞舜德治与西方法治的异曲同工
人类社会的发展,尽管其进程的途径千差万别,但是其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和终极世界的梦想却是一致的。
譬如: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希伯来人创作了《圣经》,出现了夏娃和亚当的传说,有了耶和华神的崇拜。认为亚当听从毒蛇的诱引去摘食了树上的禁果,于是便落下原罪[1]2 - 4。从而,人类必须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来赎洗身上的罪孽。但是直立的人却不甘心于匍匐大地的痛苦,于是便有了古希腊苏格拉底等一系列哲学家的反思,也就出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
《理想国》被学界称之为人类历史上西方社会最早的乌托邦。柏拉图认为:在理想国里统治者应该是最具哲学思辨能力的智者,并且能身体力行,学以致用,求诸实践。《理想国》里讨论的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正义”的追求。但是,何谓“正义”?诗人西蒙尼认为:“正义就是欠债还钱”,“正義就是给每个人一恰如其分的报答”。色拉叙马霍斯认为:“正义就是强者权利”,“正义是为了强者的利益服务,不正义是只对自己有好处”。苏格拉底在一系列的辩论中,最后指出:个人的正义要与城邦即国家的正义联系起来,而要构建一个我们所憧憬的理想国家,或者说城邦,那么这个国度或城邦的管理者和百姓必须具备四种美德:“正义、智慧、勇敢、节制”[2]。《理想国》是西方哲学思辨的发端,也是西方制度文明的滥觞。不过,在苏格拉底的心里,认为“理想国”的实现是非常渺茫的。[2]导言3
在西方文明里,语言是万能的,正如神通过语言创造万物一样,语言与逻辑发展到了极致。同时认为人心总是不可靠的,尤其是那些掌管权力的统治者,总想突破权力的边界去最大化的行使他手中的权力,而给天下百姓造成痛苦。于是,催生了他们法律制度的建立。即通过法律与制度对权力者的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以防范其权力滥用的可能。网上曾流传美国小布什总统的一段名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8]69尽管布什不过是政坛上的一位匆匆过客,但网上这段虚拟之言明白地揭示了法治社会的重要。
在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同样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第一个国家联邦,它不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法治联盟,而是建立在礼义基础上的道义联盟。在中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尚书》中[3]前言,其开篇的《尧典》里,引领我们走向光明的不是神,而是我们的道德人文始祖唐尧和虞舜。《尚书》的具体成书时间虽然没有定论,但其从《尧典》到《秦誓》,在时间维度上恰与《圣经·旧约》所述说的年代基本相当,而孔子、孟子所处的年代又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年代相差不远。尽管人世间没有神灵,但是惊奇的是东西方文明恰在历史的同一时间节点上绽放。在孔子的《论语》《礼记》等著作里,所体现的仁、义、礼、智、信五大品德,与苏格拉底提出的“正义、智慧、勇敢、节制”,无论是内涵或外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仁者无敌,仁者勇也。尤其是虞舜在与大禹的政治交接时,所提到“仁、智、勇”三大准则几乎与苏格拉底的思想如出一辙,英雄所见略同。但是,苏格拉底只是一位哲学家,一位通观全局的哲者,而不是一位政治家与王者,所以他无力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而虞舜却不一样,他不仅是一位圣人,更是一位把持权杖的王者,因此,在柏拉图为《理想国》的蓝图难以实现而苦闷时,虞舜的邦国早已走出伊甸园去建设自己的人间天堂。儒家至圣孔子称颂虞舜时代为“大同世界”。何谓“大同”?孔子在《礼运》里作了这样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4]513如此理想的社会图景,几乎与佛国的“天堂”和马克思所描绘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相媲美。
虞舜的大同世界是以“仁”为基础的,在部落与民族之间推行“仁政”。假若将百姓比喻成羊群,那么地方管理者就是州牧,假若将百姓视如子民,那么朝廷命官就是父母,无论是州牧,还是父母,都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与羊群一样善待天下的百姓。基于这样的思维,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国家管理模式——这就是圣贤政治。在圣贤政治里,仁政是其最大的追求。君王是替天行事,那么他的品行最高尚,才能最出众,胆识最超群。学而优则仕,士而优则王。这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后来的汉儒将孟子的“君轻民重”演绎成“君为臣纲”,彻底地将儒家文化中的“民之所本”导入到另一个极端——即“王者至上”,将刚刚萌芽的“人权天赋、人人平等”的法治思维扼杀在了行进途中。但是,对社会秩序的构建,对人际关系方面的理顺,虞舜的仁政则依然在发挥其独到的作用。因此,司马谈于《论六家要旨》中慨然赞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5]412 - 414可见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不可随意否认。
东西方思维的差别,导致了社会管理理念上的迥异,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其终极指向都是一样的,无论是虞舜的大同世界,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其目的都是希望构建一个理想社会。西方重视法治,法治的基础是要有“良法”可依,而“良法”的前提就是对人的尊重,对天地良心与自然规律的准确把握,这才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否则,背离百姓意愿与背离大众的意志的法规,只能是恶法陋规。而恶法陋规是永远也达不到法治的目的。
中国强调“仁德”,所谓仁者,即存天地之常理,化人心之私欲。仁德的前提就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对人格的坚守,对生命的怜悯与关注,对他人观点与意见的包容。这与法治思维中的“虽然不赞同你的观点,但却坚决维护你发表意见的权力”,可谓殊途同归,异曲同工。
二、虞舜的道德文化烛火洞明
毛泽东同志对战争胜负问题曾有过精辟地论述:“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其实,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也是一样,关键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尤其是那些执掌权力的少数中的关键,对历史进程的推动,其作用巨大。尧天舜日盛世的开创,显然与其选贤任能的用人制度和诚信至上的道德信仰是分不开的。
其实,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所以独以中国得以延续,而其它均已湮灭在历史进程的尘埃里,其原因就是对虞舜“仁政”文化的坚守。仁政如一湖碧波潋滟的江水,映照着神灵的天空,浸润着干涸的大地,也滋养着苦难百姓的心灵。“选贤任能”尽管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出于一种主观愿望,但是,客观现实的结果却给平头百姓提供了努力的平台与晋升的通道。通过举孝廉与科举考试的途径,将尽可能多的社会贤才凝聚到體制之内,让其成为服务社会的精英,而不是反叛社会的暴徒。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纵然在朝廷更替的剧烈动荡中,依然能保持其文化的延续与知识分子使命的纯洁,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奥妙所在。
虞舜的“仁政”是以“孝”为前提的,因为家是社会的最基本的组成单元,若普天之下都对父母兄长孝顺,那么整个社会就一定和谐稳定。中国有句古话:“百善孝为先,”此语出自清代著作《围炉夜话》,但从其源头可追溯到虞舜。从历史文献中的大量记载可以看出:虞舜生活在一个“父顽、母嚚、弟傲”的“狼”群似的家庭,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关怀与爱护,而且时时处于慌恐之中。因为一家人皆欲杀舜,使其整天在性命之忧的环境中艰难度日。但是于舜而言,他没有怨恨,而是更加谨慎笃孝。“顺而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6]628虞舜终以孝行感动天地,使危机四伏的家庭而渐渐变得和谐、和睦与友善,最后“以孝烝烝,乂不格奸”[4]216。虞舜因孝闻天下而被四岳长老举荐到了尧帝的身边,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君。虞舜被征用之后,又将对家人的孝演变成对天下的“仁”,于是,“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6]628显然,“仁”是社会和谐友善的基石。虞舜由“仁孝”而“仁政”,实现了家庭伦理的社会转换,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开明盛世,并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历史进程,每当风云际会,无不以尧舜为图景,去号召天下的志士以杀身立仁,维系社会的正义。
虞舜的“仁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他人的尊重。虞舜处理国家事务,从不独断专横,而是广开言路,听取众人意见,然后才进入决策与执行层面。虞舜的用人与处事,在《尚书》里有许多精到的记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3]7虞舜传位于禹时,对大禹告诫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 [3]18从这两段文字,足见虞舜对他人意见的尊重和吸纳。
二是遵照自然规律,发展农业生产,丰富百姓生活。虞舜深知人的生存需要是第一位的,它远比荣辱声名重要。教化虽然可以使人尚善,但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这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思维具有文化上的一致性。若衣食不足而空着肚子去说教是没有用的。正如《管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5]1虞舜作为先古帝君,深知衣食于百姓的重要。他于《南风歌》中唱道:“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为了百姓能过上一个丰衣足食的日子,虞舜依据天象,制定历数,然后任禹作司空,治理江河水土。命令弃为主管农业的官:“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 [3]11指导百姓依据时令气候播种五谷,发展生产,让百姓快速地富足起来。
三是注重制度建设,以宗礼为基础,以乐教为核心,推行新的社会规范。一个好的社会,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制度来维持。虞舜以宗庙社稷的祭祀为基础,建立礼仪制度,规范社会人群,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如命伯夷为秩宗:“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夷制定了礼仪制度,但制度过于刚性,百姓不一定乐于接受,于是,又命夔为乐官,以优美的音乐去柔抚人的心灵。“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3]12刚性的礼与柔性的乐双管齐下,刚柔相济,八音克谐,神人欢娱,因此,国家也就和谐通融。
三、虞舜的道德教化并不排斥法的惩治
中国自晚清开始,每次重大的思想博弈与理论之争,无一不是从立法立宪之争开始。但历经一百多年,我们制定了成千上万的律文条例,但是,我们依旧在人治的境地徘徊。习近平执政以来,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倡导“三严三实”,推行“群众路线”,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追求公平正义,以壮志断腕的勇气和胆识全面反腐,其目的就是要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增强法律意识。
法治的确是一个好东西,它要求我们人人讲规矩,讲原则,重契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实,这也是我们社会问题日积月累,无法排解而倒逼的结果。我们知道,国内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物质财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人的思想道德与法治理念并没有随之提升,反而社会矛盾日益突显。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发布的《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表明,自2000年以来,共发生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多起,其中多数事件是因平等主体间纠纷引发,官民矛盾占有一定比例。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府,为何出现如此吊诡问题?原因就是像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周永康之类身居高位的败类,阴阳两面,心无戒尺。不仅没有去践行党的政策与法规,而且设法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捞取个人的资本,贪婪成性,掌勺人从私分大锅饭,进而私占大饭锅,完全置天下人民于不顾,从而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如近些年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中,哪一起不让中央怒发冲冠,哪一件不令百姓齿寒心冷!
道德与法制的天平,如何得以保持平衡而不致倾斜,这的确是考量一个政府其执政能力与履职水平的不二法门。习近平总书记明察秋毫,高举“以法治国”的利剑,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害群之马,不论是“老虎”,还是“苍蝇”,一律零容忍。“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再次彰显了党的伟大与英明。
利不为民谋,权为己所用。特权腐败严重影响和败坏了党的形象。人心向背,不仅加速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更是祸及国家与政党的安危。为了防止我们的民族分崩离析,避免我们的国家再次出现“其兴也勃然,其亡也速然”的历史周期率,除了加强法治,也要求我们必须根植于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的基因图谱中寻找更精准的良药妙方。从而,我们也再一次回想到舜文化里的德法相济的治国思想。
建立法纪,惩治凶恶,树社会正气,这是一切社会的愿景与皈依。在虞舜时代,虽然还谈不上什么完善的法制社会,但“刑以惩恶”的律法思想早已形成,并在社会活动得以推广和应用。如《尚书·尧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7]10制定了五种刑罚,并在百姓中广泛宣讲,教人们遵守,不得触碰,“惟刑之恤哉”,体现了立法的仁慈与普法的深入。对于那些触碰法律底线的人,无论权有多重,位有多高,都照章惩处,决不姑息,从而也就保证了执法的公正公平。如四大凶族,在尧帝时代就已作恶多端,然因其势太张,当时尧帝不敢惩罚他们,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一等一的“大老虎”。但虞舜摄政后,为给天下以清纯太平,给百姓以正义廉明,则毫不犹豫地给四凶以最严厉的惩治。《尚书·尧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7]10这里,舜帝对四凶的惩处,能使四大凶族与天下百姓都感到心底诚服,也足以说明舜帝的立法、执法、用法水平的高超。虞舜是以仁为本体,以法为手段,仁者爱人,故也必为人所爱。
虞舜的法治思想建立在道德理念之上,凡是合理必然合法,凡是合法必须合理,理与法形如水乳,德与行光如日月,现乎于隐,显乎于微,行行止止,无不中节,这就是虞舜的高妙。对此,孔子赞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
诚然,一个好的法治社会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它除了需要建立起科学而符合人性的各类法典之外,还得不断地进行教化和宣传,以培养民众的法治意识。虞舜命皋陶管理司法,他对皋陶说:“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惟明克允”是司法公正的基础,也是司法扬善的基本要求。如何才能不折不扣地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这就需要道德方面的教化必须与日俱进。“志士不受嗟来之食,廉者不饮盗泉之水。”这是道德教化的结果。虞舜命“契”主管教育,其目标非常清楚,就是教育百姓遵守道德规范,树立良好品德,尊老爱幼,友善家人,和睦邻里。虞舜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即命令“契”用“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来教化百姓,使每一个人都能从内心深处去敬重这五种品德。不过,教化是一种引领,而不是一种强制,因此,虞舜提出必须“在宽”。
通过对虞舜治政理念的缕析,不难看出,只有扬善与惩恶相济,严法与尚德相协,教化与惩罚并用,法理与情理相融,才能真正地突显法治的作用与效果,这也正是我们要继承的舜文化的精髓与瑰宝。
【 参 考 文 献 】
[1] 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
[2] 柏拉图.理想国.吴献书,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3] 周秉钧,注译.尚书.长沙:岳麓书社,2001.
[4] 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长沙:岳麓书社.2002.
[5] 上海辞书出版社编.管子:牧民.诸子百家名篇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6] 万里.虞舜大典:古文献卷.刘范弟,辑录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9.
[7] 周秉钧,译注.白话尚书.长沙:岳麓书社,1990.
[8] 狄马.“笼子”是用什么制成的.发展.2013(4).
(编校:龙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