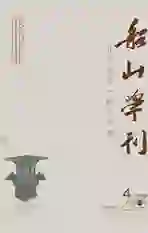中古佛典序跋的佛教史价值刍论
2018-10-29赵纪彬
赵纪彬
摘 要: 中古佛典序跋具有重要的佛教史价值,保存了印度早期佛教的因子,勾勒出佛教中国化的变迁、记录了佛典翻译与整理的底本,映射出统治者与佛教的关系,折射出佛教的发展程度,反映了佛教的態势,记载了佛教史实。中古佛典序跋对佛教史的记录、保存、还原、映射、反映、评判具有鲜明特色,一方面所承载的佛教史具有一定的广阔性,囊括了域内与域外,佛教史内部的各个要素以及与佛教史相关的多个层面, 另一方面承载佛教史的手段多样化,既有正面、直接记录,又有侧面折射。
关键词: 中古;佛典序跋;佛教史价值
序跋有时或涉及到书写对象所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作者的生平事迹,或对其书写对象的梳理,在此过程中无疑涉及到对历史的记载。序跋具有浓厚的历史因子,一方面对历史的记载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另一方面对历史的记载方式多样化。
作为序跋的一个子类,中古①佛典序跋相应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只不过它与佛教、佛典、佛事活动等密切相关,融进了大量的佛教史因子:印度早期佛教的某些风貌、佛教中国化变迁的痕迹、佛典翻译与整理底本的变化、统治者与佛教的关系、佛教的发展程度、佛教的态势、佛教史实。整体观之,中古佛典序跋对佛教史的记载方式较为多样化,所记载的范围涉及域外与域内两个层面。
一、保存印度早期佛教的因子
中古佛典序跋尽管在形式上源于我国,其内容则多与佛教、佛典等域外文化有关,其中不乏印度早期佛教。由于记载印度早期佛教的原始佛典,在我国翻译与整理时被保存下来。汉译佛典源于对域外佛典的翻译,二者的内容具有一致性,因此域外佛典中的印度早期佛教成分,在其汉译本佛典中得以呈现。含有印度早期佛教成分的汉译本佛典在被书写序文或跋文时,印度早期佛教的相关内容有时不可避免地被触及,对中古佛典序跋而言亦是如此。中古佛典序跋描述了佛陀讲经的情形,如康孟祥的《佛说兴起行经序》描述了如来因舍利弗问及十事宿缘,对众讲授的情形,“如来将五百罗汉,常以月十五日,于中说戒。因舍利弗,问佛十事宿缘。后以十五日时,将本弟子,说讫乃止,如是至九。往所以十问而九答者,以木枪之对人间偿之,欲示人宿缘不可逃避故也”[1]2 - 3,此描述与如来讲经的情形相一致,因为佛陀在讲经时,往往先有一人发问,然后由他为之作答,是他们之间的反复问答。再者,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描述了世尊宣讲《安般守意经》时所引起的反响:
世尊初欲说斯经时,大千震动,人天易色,三日安般,无能质者。于是世尊化为两身,一曰何等,二曰尊主,演于斯义出矣。大士、上人、六双、十二辈,靡不执行。[2]244
佛陀在为众讲说《安般守意经》时,三界为之震动、天人为之变色,他的身体一分为二,于是大士、上人、六双、十二辈均尊奉该佛典。世尊讲授佛典所引起的反响被视为佛典的流通品,有利于增强佛典的流传效果,然而其中不乏神异虚构。
中古佛典序跋记载了早期佛典的形成机制。阿难在佛陀的众多弟子中,记忆力最强、被誉为“多闻第一”,他在小乘佛教的第一次结集大会上背诵出《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增一阿含》《譬喻经》《法句经》等佛教典籍,释道安的《阴持入经序》对此有所记,“大弟子众深惧妙法混然废没,于是令迦叶集结,阿难所传,凡三藏焉”[2]248,从中暗示了早期佛典的形成机制。
中古佛典序跋对印度早期佛教的记载尽管微乎其微,其价值却不容忽视,一方面扩大了中古佛典序跋所书写的历史范围,鉴于多数中古序跋所记载的历史囿于域内,中古佛典序跋对印度早期佛教的记载则触及域外历史,这就扩大了自身所书写历史的范围。另一方面对中古佛教尤其是佛典的状况有所折射,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典序跋的题写对象多为域外佛典的汉译本,这就间接映射出当时域外佛典偏多,编纂于我国的佛典则相对较少的状况。再者,中古佛典序跋中的印度早期佛教因子的偏微,体现了其题写者的叙事策略,鉴于国人对印度早期佛教的陌生,其含量不宜过多,从而有利于佛典在我国的传播。
二、勾勒佛教中国化的变迁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要在我国具有广泛的受众则必须实现中国化,借助中国文化来扩大自身影响力。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具有阶段性差异,这在中古佛典序跋中具有鲜明反映。
佛教传入之初,依附于我国的神仙方术,附着于黄老思想,趋于道家化,黄老与浮屠并提,道家人物的一些属性被移植到佛家人物上,使其具有我国神仙的特性,“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覆刃不伤,在污不辱,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3]2,佛陀被赋予“神通”的属性,此乃其原始形象所未曾有之,是其中国化的产物,此情形在中古佛典序跋中也有所呈现,“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2]242,在该佛典序文中,佛陀被神仙化。不仅佛陀被神仙化,其他佛家人物也披上了神仙的外衣,以安世高最具代表性,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对此有所记:
有菩萨名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其为人也,博学多识,贯综神模,七正盈缩;风气吉凶,山崩地动;针脉诸术,睹色知病;鸟兽鸣啼,无音不照。怀二仪之弘仁,愍黎庶之顽暗,先挑其耳,却启其目,欲之视明听聪也。[2]244
在该佛典序文中,安世高能预知吉凶祸福、观色知病、识鸟兽鸣啼之音,其博学多识非常人所备,具有神异的特征。此类中古佛典序跋题写于佛教被道教化的环境之中,是对佛教中国化的真实记载。
佛教的中国化处于动态之中,它随着我国的社会文化、自身的实力等因素而变化。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实力有所提升,开始与我国文化互动,其中以与玄学的合流最具代表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般若学互相影响、吸收彼此,时之佛典序跋对此有所记,如道安法师的《鼻奈耶序》曰:“以斯邦人庄老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也。”[1]25般若学因玄学而得以广泛传播,玄学则因般若学更加兴盛,彰显出佛教与我国当时社会思潮的融合。
中古尤其是汉末魏晋南北佛典序跋真实勾勒了佛教中国化变迁的历程,客观记录了它的发展脉络,在勾勒的过程中彰显出特色。中古佛典序跋对中古各个历史阶段内佛教中国化的勾勒,映射出其题写者對佛教的关注。中古佛典序跋对佛教中国化的记载,与佛教中国化的同步,由此彰显出它的与时俱进。中古佛典序跋对佛教中国化的记载具有一定深度,往往超越佛教本身而触及我国的社会思潮、社会文化以及国人的思维方式等。
三、记录佛典翻译与整理的底本
中古尤其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记载了佛典翻译与整理过程中所依的底本,如支敏度的《合首楞严经记》曰:“敦煌菩萨支法护手执胡本,口出《首楞严三昧》,聂承远笔受。[2]271由该佛典序文可知,支法护在翻译与整理《首楞严三昧》时以胡本为底本。僧伽提婆在翻译与整理《阿毗昙心经》时以胡本为底本,鸠摩罗什法师在翻译与整理佛典时以胡本为底本,释慧远的《阿毗昙心序》与释僧叡的《大品经序》对此分别有所记。道慈法师的《中阿含经序》、未详作者的《首楞严经记后记》与《华严经记》等其他中古尤其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对佛典翻译与整理过程中,以胡本为底本的现象也多有记载。整体观之,隋唐佛典序跋对此问题鲜有论及,可能与当时佛典翻译与整理活动的成熟状态有关。
中古尤其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对佛典翻译与整理过程中所依底本的记录具有一定意义。一方面为认识佛典翻译与整理提供了重要线索。佛典翻译与整理是重要的佛事活动之一,所依底本又是该活动中必不可缺的要素之一,中古佛典序跋就此记录,有利于对该活动的认识。另一方面有利于解决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如佛教传入中土的路线。目前学界对佛教传入我国的路线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佛教直接由印度传入我国,另有学者则认为佛教并非直接由印度传入我国,如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认为“佛教之最初传入中国的边疆塔里木盆地一带”[4]607。中古佛典序跋对佛典在翻译与整理时,以胡本为底本的记载从侧面证明了佛教并非由印度直接传入中土,而是在西域胡化后传至,否则佛典在我国翻译与整理时就不会以胡本为底本,这就为厘清佛教传入我国的路线问题提供了一定启示。要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对佛典翻译与整理过程中所依底本的记录具有双重意义,不仅彰显出它的存史价值,而且为某些历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启发。
四、映射统治者与佛教的关系
佛教与历代统治者的关系较为微妙,在整体上表现为亲密或排斥。魏晋南北朝时期,某些统治者推行积极的佛教政策,组织甚至亲自参加佛事活动,对佛教极为尊奉,此现象在当时的佛典序跋中多有反映,如陆云公的《御讲般若经序》记录了梁武帝组织宣讲《御讲般若经序》时的情形,“皇太子智均悉达,德迈昙摩,舍三殿之俗娱,延二坐以问道。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亦咸发深心,并修净行,薰戒香以调善,服染衣而就列”[1]12,该佛典序文描述了梁武帝时的皇太子、宣成王及其他王侯宗室在听讲《御讲般若经》之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听讲者多达千余人,多为当时的官僚士大夫,其中包含诸多域外使者,“凡听众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书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虏使主崔长谦、使副阳休之及,外域杂使一千三百六十人”[1]12。陆云公的《御讲般若经序》对梁武帝萧衍组织宣讲《般若经序》的记载,映射出梁武帝萧衍对该佛典的尊奉之情,折射出他对佛教的积极态度。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对统治者尊奉佛事的记录,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出二者的亲密关系,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
观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题写者群体的构成成份可知,其中不乏当时上层统治者,如姚兴、萧衍、萧纲等,为佛典题写序文的行为映射出他们对相关佛典的积极态度,彰显出他们对佛事的崇奉,映射出他们与佛教的亲密关系。
隋唐佛典序跋对统治者与佛教的亲密关系也有所映射,武则天所作的《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暗示了她与佛教的亲密关系,曰:“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宝雨之文后及”[1]308。武则天的另一篇佛典序文——《大周新翻三藏圣教序》亦表达了她对佛教的崇奉,详情可参看该佛典序文的相关内容。
隋唐佛典序跋的题写者群体中不乏统治者,其中以武则天最为典型,她题写有《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大周新翻三藏圣教序》《新译大乘入楞伽经序》,李世民有《三藏圣教序》,李治有《圣记三藏经序》,李隆基有《大宝积经序》,李豫有《大唐新翻密严经序》《大唐新翻护国仁王般若经序》,李适有《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序》等。与汉末魏晋南北佛典题写者群体相比较而言,在隋唐时期,上层统治者的成份明显增加,此现象在某一层面上折射出佛教与统治者的亲密关系得以加强。
要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真实记录了当时上层统治者与佛教的亲密关系,具有多重意义。一方面为把握中古佛教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有益启发。纵观汉末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数百年间,佛教与上层统治者的关系以亲密为主流,佛教依附于上层统治者,上层统治者则利用佛教以维护自身的统治,正是二者的互相利用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因此中古佛典序跋就此记录为准确把握此时期佛教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有益启示。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古佛典序跋对佛教史的真实记载、在中古的数百年间,亲密成为佛教与上层统治者之间关系的主流,因此中古佛典序跋的相关记录较为真实客观,符合历史事实,彰显出它对历史的尊重以及真实记录。中古佛典序跋对上层统治者与佛教亲密关系的映射具有连续性,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在某程度上暗示了其题写者对佛教发展问题的充分关注,也是对佛教发展规律的总结,充分意识到上层统治者在佛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五、折射佛教的发展程度
佛典序跋能够在一定层面上折射出佛教的发展程度,可谓是佛教发展的“晴雨表”,因为它的数量、题写者群体、题写章法等要素与佛教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在汉末,佛典序跋在数量上微乎其微,仅有严佛调的《沙弥十慧章句序》、康孟详的《佛说兴起行经序》、牟融的《牟子理惑论序》等篇,题写者群体不够广泛、参与者寥寥无几并且多为域外僧人,章法不够成熟、篇幅短小、内容相对狭窄、艺术特色也不够鲜明,这与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尚短、发展尚不成熟等因素相关。
降至中古时期,佛典序跋的构成要素进一步发展。中古佛典序跋的数量有一定提升,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达178篇、隋唐时期有217篇,佛典序跋数量的增加则意味着佛典数量的上升,而佛典数量的上升又与佛教的深入发展密不可分。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群体进一步扩展,它的题写者主体由域外僧人逐步转变为域内僧人,同时它的题写者阶层呈现出扩大的倾向,由先前单一的僧人到最高统治者、官僚士大夫、居士、文人学者等。中古佛典序跋的技法显著提升,篇幅明显增加,内容涵盖面更为广泛,句式多为四言,讲说方式以譬喻为主,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中古佛典序跋构成要素的发展与此时期佛教的趋于成熟密不可分。
中古佛典序跋对佛教发展程度的折射有时更为细腻,不仅触及该时期内佛教的整体状况,而且关注每个阶段的具体状况。总体而论,佛教在中古时期整体上趋于繁盛,具体到每个阶段的情形则不尽相同,这一现象在中古佛典序跋中有所体现,从其数量上得以印证。由于魏太武帝推行消极的佛教政策,严重阻碍了佛教的发展,相关佛典序跋相应地偏微,题写于此时的佛典序跋寥寥无几。南朝的统治者大多推行积极的佛教政策,由此推动了佛教的发展,相关佛典序跋的数量明显提升。佛典序跋发展的不平衡性在隋唐时期亦有所呈现,如武则天尊崇佛教,无疑有利于佛教的发展,相关佛典序跋相应地丰富;唐武宗推行消极的佛教政策,导致佛教遭到毁灭性打击,相关佛典序跋随之偏少。一言以蔽之,中古佛典序跋的数量与佛教的发展程度在一定范围内呈正相关,前者对后者有一定映射。
中古佛典序跋在一定范围内折射出佛教的发展程度,因为它的构成要素与后者密切相关。中古佛典序跋以相关佛典为基础,在数量上与之正相关,而后者又与佛教的发展程度有一定关联,前者由此与佛教的发展程度建立起间接联系。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群体与佛教的发展程度密不可分,若佛教发展不够成熟,其影响力相对较弱,佛典序跋的题写群体相应薄弱。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章法与佛教的发展程度存在间接关联。佛教的深入发展必将对佛典的章法产生一定影响,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古佛典序跋的题写者,因为他们在题写序跋时必先诵阅相关佛典,无形中为之浸染,中古佛典序跋的章法由此与佛教的发展程度建立起间接关联。中古佛典序跋对当时之佛教发展程度的折射,是其存史价值的升华。
六、反映佛教的态势
何謂佛教的态势,即佛教在某一时期内的发展走向。佛教自传入中土,它的态势表现在哪些方面?汤用彤先生认为“自汉以来,佛教之大事,一为禅法,安世高译之最多,道安注释之甚勤。一为《般若》,支谶、竺叔兰译大小品,安公研讲之最久”[5]136,由此而知禅法与般若成为当时佛教的主流态势。
何谓禅法,今人唐思鹏认为“所观境 (五欲、五盖,甚或一切诸法),专注一趣,审谛观察,如实了知其过患相、功德相、杂染相、清净相、粗苦相、净妙相等,从而引生神通智慧现行,成办一切诸应所作,是名为禅”[6]12,禅是一种内心专注的状态,内心专注而没有任何意念,进而获得智慧、成办一切诸应所作。中古佛典序跋对禅法多有涉及,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阐释了禅法的内涵,“禅,弃也,弃十三亿秽念之意”[2]243,该佛典序文认为禅法则为弃、弃众秽,唯有如此方能内心专一。
除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之外,其他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对禅法亦有所论及,如释慧远的《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表达了对禅法的赞誉,概括了禅法的特色,指出修习禅法的裨益,阐释了禅法“五门”中的“四门”,指出佛大先修习禅法的行为。再如,僧叡法师的《关中出禅经序》亦大为赞许禅法,指出禅法的形成途径,记载了鸠摩罗什法师对禅学典籍的整理。最后,慧观法师的《修行地不净观经序》论及禅智的特色,初学禅法者指明修习途径。总而言之,中古尤其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含有丰富的禅法要素,概述禅法的要义及特色、指出修习的裨益及途径、记载与禅法相关典籍的编纂,由此映射出禅法在我国佛教界广泛盛行的态势,从而推动对我国佛教态势的认识。
何谓般若,它是般若波罗蜜多的略称,是大乘佛教中的佛、菩萨所具备的一种智慧,它既是大乘佛教修行所要达到的目的,又是观察一切事物的准则。般若类佛经大约产生于印度案达罗王朝中叶(约1世纪中叶),其中《小品般若》和《大品般若》在龙树时代(2或3世纪)已经开始流行,所谓“大品”“小品”是指两部《船若经》在篇幅上有大小长短之分,中心内容则基本相同。《小品般若经》在中土先后经过七次汉译:东汉竺佛朔译的《道行经》一卷,吴国康僧会译的《吴品经》五卷,吴国支谦译的《大明度无极经》四卷,西晋竺法护译的《新道行经》十卷,东晋祗多蜜译的《大智度经》四卷,前秦昙摩埤与竺佛念合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五卷,后秦鸠摩罗什法师译的《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大品般若经》在我国汉译的时间相对较晚,先后产生三个译本:西晋竺法护译的《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十五卷,西晋无罗叉与竺叔兰合译的《放光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后秦鸠摩罗什法师与僧睿法师等合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四十卷。观上述可知,般若类佛典在中土先后经过多次的翻译与整理,流传广泛。
中古尤其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广泛涉及般若学,从而映射出当时佛教态势的另一个层面。对般若多有赞誉,如释僧叡的《小品经序》称颂《般若波罗蜜经》是菩萨成佛的最佳途径,“《般若波罗蜜经》者,穷理尽性之格言,菩萨成佛之弘轨也”[2]297。再如,支道林的《大小品对比要抄序》对般若也大为赞誉,“夫《般若波罗蜜》者,众妙之渊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来之照功”[2]298。再者,为般若类佛典书写对象的序跋极为丰富,僧叡法师有三篇,除上文所提及的《小品经序》外、还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释论序》及《大品经序》,道安法师的《道行般若经序》及《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 慧远法师的《大智论抄序》,智昕法师的《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序》,萧衍的《注解大品序》,法虔法师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记》等,由此彰显出中古佛典序跋对般若的广泛关注。
由上可知,中古尤其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对禅法及般若均有广泛涉及,从中反映出中古佛教的态势,因而具有多个层面的价值。一方面为认识中古佛教的整体风貌提供了一定帮助。佛教态势实际上是佛教主流形态及其整体风貌的一个构成层面,是某一阶段内佛教的风向标,佛教在某一阶段内的主要发展走势,中古佛典序跋就此记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对当时我国佛教整体风貌的认识,体现出它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有助于对中古佛教发展规律的归纳,由于佛教的发展态势受多个因素影响、往往呈现出阶段性变化,若将中古佛典序跋中的相关记录加以汇集则构成了佛教的发展脉络,进而有利于归纳佛教的发展规律,这是它的延伸意义之所在。体现出中古佛典序跋承载佛教历史手段的多样化,中古佛典序跋不仅从正面记录佛教史,而且从侧面反映佛教史。要而言之,中古尤其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佛典序跋在映射中古佛教发展态势的过程中,形成鲜明特色,形成自身的历史价值。
七、记载佛教史实
中古佛典序跋记载了一些与佛教相关的事或人,保存了一些佛教史实,由此被赋予存史功能。中古佛典序跋对当时重要的佛事活动——佛典的汉译与整理极为关注,详细记载了该活动的各个要素,如时间、地点、参与者等,力图真实再现该活动的风貌,如未详作者的《道行经后记》记载了《道行经》被汉译与整理的全过程: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译者月支菩萨支谶,时待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正光二年九月十五日,洛阳城西菩萨寺中沙门佛大写之。 [2]264
该佛典序文记载了《道行经》汉译与整理的起讫译时间、汉译者、汉译地点、书写者等要素。昙林法师的《毗耶娑问经译记》详细记载了《毗耶娑问经》翻译与整理的整个过程,其组织者为魏尚书令仪同高公,起因是“愍诸错习、示其归则”、即有感《毗耶娑问经》的舛误,地点是魏尚书令仪同高公之宅,参与者为昙林、瞿昙流支,起译在“兴和四年岁次壬戌,月建在甲,朔次乙丑”,讫译则在“建初辛巳甲午”,详情可参看该佛典序跋的相关内容。要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详细记载了佛典翻译与整理的过程,由此拓宽了相关史料的保存途径。
中古佛典序跋记载了佛教史上的某一重大事件。在佛教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个别历史事件多为中古佛典序跋所记,如关于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未详作者的《四十二章经序》对此有记: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于今不绝也。[2]242
此记载具有一定历史价值,为解决佛教传入中土的时间问题提供了宝贵材料,令人遗憾的是该佛典序文的题写时间、题写者信息均未详记,著名佛教学者汤用彤先生认为它可能早于《牟子理惑论》,“牟子《理惑论》作于汉末,《四十二章经序》出世或更早”[5]18。若汤先生的观点成立,《牟子理惑论》的“永平求法说”则袭自于《四十二章经序》,故该佛典序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载具有开创意义,为后人所承袭。反之,若该佛典序文的“永平求法说”则承袭于《牟子理惑论》,由此彰显出该佛典序文所记内容的真实性,不能因题写时间及题写者的模糊性而否定它的历史价值。
玄奘西游之事为敬播的《大唐西域记序》、李治的《圣记三藏经序》、释颜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序》等隋唐佛典序跋所详细记载,详情可参看相关佛典序跋内容。
中古佛典序跋不仅记录佛教史实而且加以评述,在尊重佛教史实的基础上,对某一问题加以评判,由此成为其题写者表达观点的工具,如释宝唱的《比丘尼传序》对比丘尼之始这一问题有所论断,“比丘尼之兴,发源于爱道”[7]1,该佛典序文认为比丘尼始于爱道,这一论断具有一定科学性。在原始佛教僧团中,起初并没有比丘尼,比丘尼始于佛陀的姨母爱道,《瞿昙弥经》《四分律》卷四十八、《五分律》卷下、《中本起经》卷下、《中阿含经》卷二十八、《大爱道比丘尼经》卷上、《毗尼母经》卷一等佛典均有相关记载。相关情节如下:佛陀的姨母摩诃波阇波提憍昙弥(汉译爱道)听佛陀讲法后而萌发出家为尼的意念,遂率五百女子至佛陀的住所请求出家,却遭到拒绝,如此三次均被回绝,她们着“法衣颜色憔悴而不悦”,在佛陀住所外面悲戚。阿难就此询问佛陀,世尊曰:“今使母人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法地清净梵行大道不得久兴盛。”[8]1经过阿难的多次请求,佛陀最终应允此事,前提是她们必须遵守八敬法,爱道答应佛陀的要求而出家为尼,因此释宝唱的《比丘尼传序》的论述具有一定可信度。
释宝唱的《比丘尼传序》认为我国比丘尼始于净检,“像法东流,净捡为首”[7]1,净捡之所以更为接近真正意义上的比丘尼,源自她意识到佛教戒律的重要性,因为她在出家之初就进行了受戒。由于当时我国尚无比丘尼,所以净检不得不“从和上受十戒”,后来她又上戒坛受戒,因此净捡是我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比丘尼。
中古佛典序跋保存了大量的佛教史实,或關注佛教史上的某一类事件、或重点关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个别事件,并且在此基础上加以评述,间接体现出保存佛教史的功能,因而具有一定意义。一是保存了佛教史,中古佛典序跋无论是对佛教史实的记载还是评述,均是对佛教史的真实记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史料。二是对佛教史实记录的完整性,中古佛典序跋既记载了佛教史上的某一类事件又关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个别事件,体现出点与面的结合,做到了宏观概述与微观关注的有机统一。三是对佛教史实的客观评判,中古佛典序跋不仅充当佛教史实的客观记录者、亦做裁判者,在尊重佛教史实的基础上对之加以评判,重在厘清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考。要而言之,中古佛典序跋对佛教史实做到尊重、真实记录、客观评判,是弥足珍贵的佛教史料。
【 参 考 文 献 】
[1] 许明.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2] 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
[3] 释僧祐.弘明集//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社,1990.
[4]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唐思鹏.禅法要义.佛教文化,2005(1).
[7] 释宝唱.比丘尼传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
[8] 译者失传.大爱道比丘尼经//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社,1990.
(编校:马延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