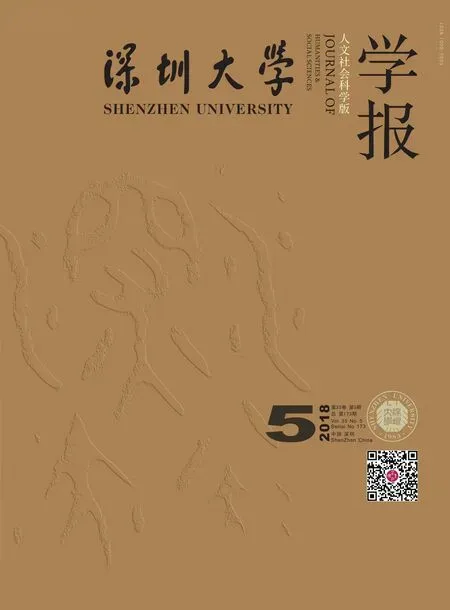超大城市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2018-10-29黄造玉
李 升,黄造玉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北京 100124)
一、引 言
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推进,流动老人成为城市中重要的社会群体。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户籍不在当地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60岁以上人口数量达到934.4万人,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相比,5年间流动老年人口增加了87.1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5.79%[1]。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指出,至2015年流动老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比例已达7.2%,整体上呈现增长态势,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成为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而无论是照顾子孙晚辈,还是养老就业,健康是流动的重要前提,尤其是在迈向老龄化及流动化社会的过程中,流动老人的健康状况无疑成为当前及今后都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已有研究从不同学科及不同视角对老年人口的健康问题展开了讨论,并指出了超大城市流动老人的流动和生活特征,强调了流动老人健康生活的重要性[2],但对超大城市流动老人健康问题的实证研究依然有限。从流动选择的角度来看,流动老人的流入地选择不仅与自身或家庭因素相关,也与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联系,因为其关联了能够保障并维持健康的生活条件。因而流动老人无论是出于自身需求抑或家庭需求,“北上广深”这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超大城市自然成为其重要的流入地选择。尽管超大城市的社会保障等生活条件良好,但由于流动老人的“非本地”特征,依然会面临诸多生活难题。对于城市而言,流动老人数量的增长给流入城市的基础公共设施、社会管理服务和医疗保障制度等社会支持系统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和挑战,尤其是对于“北上广深”这样公共资源紧张的超大城市来说,往往容易形成流动老人的健康需求与资源保障供给之间的矛盾。因此,对“北上广深”超大城市的流动老人健康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对老人健康问题的研究中,除医学意义上的客观健康(身体健康)状况分析之外,主观健康(健康自评)状况是重要的分析视角。主观健康状况是个体基于对健康的认知,综合多种个人或社会因素对自身健康状况做出的评价[3][4]。若主观健康状况表现为积极正向的认知评价,则有助于个体形成积极正向的心理及行为。因此,主观健康状况已经成为衡量老年人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5][6]。那么,流入到超大城市的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如何?又有哪些影响因素可能与之关联?本文将根据国家卫计委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北上广深”超大城市的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做出实证性分析。
二、文献与理论研究
在对流动老人健康的关联因素研究中,除去由身体引发的医学解释因素以外,主要可分为两个层面的分析路径。一是将流动老人作为流动人口的构成部分,分析人口流动因素与健康的关系,主要包括流动动机、流入地类型、流入地社会支持等维度。二是将流动老人作为老年人口的构成部分,分析老年人的自身特征因素与健康的关系,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及生活方式等维度。
在人口流动因素与健康关联的讨论方面,最典型的理论命题是“健康移民假说”,该假说认为,具备必要健康条件的人往往更易迁移,且健康状况较好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长期留在流入地,强调健康状况一定程度上直接关联了人口流动的动机与决策[7][8]。也就是说,当流动人口带有明确的流动动机或决策时,更容易认同自己处于健康状态,也更容易使自身处于流动状态。同时,因流动而导致的生活场域的转换也可能是影响健康的不确定因素,即从一个生活地区流动至另一个生活地区,地区间的差异性程度会影响到流动者的健康状态。有研究指出,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存在地区差异,不同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也会不同[9]。此外,流动过程中的关系网络对流动老人的健康支持也是重要的讨论内容。有研究指出,在流入地获得的来自家庭、亲友、组织机构等的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的健康有积极影响[10][11];还有研究指出在家庭结构方面,有配偶的老年人的健康程度要高于未婚者、离婚者和丧偶者[12],即家庭化迁移可能对流动老人的健康状况产生积极影响。
在自身特征因素与健康关联的讨论方面,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紧密相关,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13]。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是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指标,高收入会对健康状况产生正向效应[14],即当不同收入水平的人们被问到对自己健康状态的判断时,高收入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是好的[15],而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的健康状况也会越好[16]。对这一关联的主要解释是,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更容易获得健康的生活方式及更多的健康资源与健康知识支持等。社会经济地位关联健康的理论命题同样适用于老年人群体,已有的对老年人健康的研究指出,在客观的身体健康状况会影响主观健康评价之外,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的健康影响同样显著,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好[17][18]。此外,与社会经济地位关联的其他特征因素指标,如年龄、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等都会对流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19]。
整体而言,由于流动老人群体包含了“流动”与“老年”的双重特征,因此与流动老人健康关联的影响因素既包含了人口流动因素,也包含了自身特征因素,对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的分析就需要综合性的考虑。基于已有研究及现实经验,可以将影响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的因素概括为基本属性因素、流动因素、社会支持因素、经济状况因素及客观健康因素等多个维度,这些维度构成了本文实证研究的基本框架。本研究将通过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北上广深”超大城市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验证。
三、数据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将“流动老人”界定为在调查时点年龄为60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流动”是指调查样本所在地点区别于调查对象户籍所在地的情况。接受调查的流动家庭中,半边户(即夫妻一方为户籍人口,另一方为流动人口)不在调查对象之列。从调查数据中选取的流入地为“北上广深”的流动老人共6600人,其中,流入地为北京的有3040人,流入地为上海的有3008人,流入地为广州的有116人,流入地为深圳的有436人。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状况,对应于问卷中受访者对“身体健康状况”的认知判断,对该问题的回答有4类:“健康”、“基本健康”、“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和“生活不能自理”,分别编码为1至4。根据对以往相关研究理论的分析,将可能对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产生影响的因素分为5类:(1)基本属性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户籍类型;(2)流动因素,包括流动原因、流动时间和流入地区;(3)社会支持因素,包括本地朋友数量和婚姻状况;(4)经济状况因素,包括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平均月收入和家庭平均月支出;(5)客观健康因素,包括是否参加体检(过去一年,是否参加过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心组织的免费健康体检,不包括因病做的检查)和是否有慢性病 (是否患有医生确诊的高血压或糖尿病等)。变量的具体操作化与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调查数据显示出“北上广深”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总体良好,受访流动老人中,认为身体属于健康的比例达到95.8%,生活不能自理者比例小。流动老人身体状况总体良好的另一个表现是在过去的一年中,患有医生诊断需要住院的病/伤流动老人比例仅为5.8%。这一定程度上与“六普”数据结果相一致,即中国老年人健康状况存在地区差异,北京、上海和广东的老年人健康状况相对良好[8],这表明超大城市的生活水平条件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具体看不同影响因素下的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表现,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表1 “北上广深”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描述统计结果(变量描述性分析结果)
第一,在基本属性因素方面,从比例上来看,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非农业户籍的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更好。60-69岁的流动老人中,有57.7%认为自己健康,80岁以上的流动老人中认为自己健康的比例下降至34.1%。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流动老人中,身体健康的流动老人比例为94.5%,生活不能自理的流动老人比例为0.5%,而在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大本及以上的流动老人中,身体健康的流动老人比例达到98.4%,不存在生活不能自理的流动老人。第二,在流动因素方面,因为务工经商、照顾子女和照顾孙辈而流动的老人主观健康状况最好。流动原因为治病的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相对较差,其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流动老人占30.0%。第三,在社会支持因素方面,本地朋友数量越多的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相对越好,朋友数量在10人以上的流动老人中有99.1%的比例认为自己健康或基本健康。在婚姻状况上,未婚和离婚的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的分布差异较大。相对来说,已婚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状况较好,其中3.4%认为自己不健康,而丧偶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状况较差,其中10.3%认为自己不健康。第四,在经济状况因素方面,主要经济来源为劳动收入和储蓄及理财的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表现较好,这与流动原因也呈现出一定的对应关系。第五,在客观健康因素方面,参加体检以及没有慢性病的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明显整体较好,从两者交互的结果来看,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状况与客观健康状况并不能完全对应。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分析模型
由于作为因变量的主观健康状况包含了对健康认知评价的4个有序类别,因此研究选择使用有序logistics回归模型,将基本属性、流动因素、社会支持、经济状况和客观健康5类因素纳入回归模型,用以检验不同维度影响因素对主观健康状况的解释贡献。从表2的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同一变量的不同类别中,至少有一项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即所有纳入模型的变量均对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状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表2 “北上广深”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有序回归模型
(二)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影响因素
1.基本属性因素与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状况关联密切。模型结果显示,男性、年龄在60-69岁以及非农业户籍的流动老人更可能对自己的健康形成正向的评价。在此方面,用相同数据对上海市流动老人自评健康状况的分析也显示出了相似的结果,即年龄较低、非农业户籍的流动老人自评健康情况相对较好[18],这表明超大城市中流动老人的健康状况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受教育程度对于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的影响方向则是不清晰的,相比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流动老人,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较好的可能性更大,而其它的受教育程度影响效应并不清晰。这与已有研究中“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健康”的观点并不一致[5],一定程度上也表明超大城市流动老人的流动因素可能会对自身特征因素的效应起到弱化作用。
2.流动因素对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评价具有显著影响。模型结果显示,在流入地的时间越长,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自评较差的可能性越大。一般而言,流动老人最初是带着健康状态进行迁移的,超大城市的流动老人更多是需要照顾晚辈及务工经商等[2],因此需要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而随着在流入地生活时间的延长,不同生活场域的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其健康状况。流动原因的分析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与流动原因为“其他”的流动老人相比,因为务工经商、照顾子女和照顾孙辈而流动的老人主观健康状况更好的可能性较大,这与上文中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也是相一致的。在流入地差异上,与在广州和深圳的流动老人相比,在北京的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状况较低的可能性更大。从数据反映的情况来看,因为治病而流动的老人其流入地最主要为北京,而在广州和深圳有更大比例的老人因务工经商而流动,从事务工经商的流动老人更容易形成正向的主观健康评价,这与广东地区整体上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具有一致性表现[20]。
3.社会支持越多的流动老人越易形成积极正向的主观健康评价。模型结果显示,与本地朋友数量在10人以上的流动老人相比,朋友数量相对较少的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较差的可能性更大,而本地朋友越多的流动老人其主观健康状况有更大的可能性较好。在婚姻状况上,与已婚的流动老人相比,未婚的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较差的发生比更高。一方面流动老人退出工作领域后,原有的因业缘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弱化,另一方面流动老人流动之后生活空间发生改变,与原居住地的亲戚朋友等联系减少,因而在流入地的流动老人需要重构其社会网络关系,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获得社会支持。可以推测,流动老人处于相对完整的家庭结构中,并在流入地的朋友数量越多,越容易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其情感、社交及日常生活等需求越有可能得到满足,也就越容易保持良好的主观健康状态。这与已有研究的观点是一致的,即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心理情感因素在主观健康评价中的积极效应是明显的,积极的生活态度与群际交往情感上的愉悦在老年人自评健康中起到了正向作用[21],家庭成员或夫妻间的相互支持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保证,对老年人的健康自评起到了基础性的积极影响[11][12]。
4.经济状况因素对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评价具有显著影响。模型结果显示,家庭月收入对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状况有所贡献,即家庭经济收入越高的流动老人,越易形成积极的主观健康评价,这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关联效应,与前述已有研究的观点一致。与经济收入相比,家庭月支出对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的影响效应方向则相反,即生活支出越高的流动老人,越不容易形成正向的主观健康评价。对于流动老人而言,生活支出越多,可能意味着生活中需要解决或满足的需求越多(如疾病花费等),这会对其主观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在主要经济来源的影响上,与主要经济来源是“其他”的流动老人相比,经济来源是离退休金/养老金及家庭其他成员支持的流动老人主观健康状况较差的可能性更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依靠劳动就业等方式获得经济来源的流动老人更易认为自身是健康的。
5.客观健康因素与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状况关联密切。模型结果显示,锻炼时间的增长对主观健康状况有正向的影响,常参加体检以及没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流动老人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健康的。这无论是与已有研究结果抑或现实经验都是相一致的,客观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流动老人会更多地参加锻炼,对自身健康重视的老人也会更积极地参加体检。对流动老人而言,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生理上的身体健康都会对其主观健康状况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此方面,对全国65岁以上老人的抽样调查分析也显示出同样的结果[5]。流动老人生活环境的改变,在流入地的客观健康状态维持有助于形成积极正向的主观健康评价,因而在流入地实现良性融合并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显得更为重要。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超大城市中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状况整体呈现积极正向的良好状态,其主观健康状况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在基本属性因素影响方面,男性、年龄在60-69岁以及非农业户籍的流动老人的主观健康评价较好。在流动因素影响方面,流入时间越短、持有照顾晚辈及务工经商等明确决策、流入地在广深的流动老人更易形成良好的主观健康评价。在社会支持因素影响方面,已婚有配偶、在流入地朋友多的流动老人主观健康评价较好。在经济状况因素影响方面,家庭收入高的流动老人更易对自身形成积极正向的健康认知,而生活支出大的流动老人则不易形成正向的主观健康评价。在客观健康因素影响方面,锻炼时间长、常参加社区体检、没有慢性病的流动老人更易形成正向的主观健康评价。
对比于不同时期、针对不同老人群体的调查分析结果,可以基本得出一个稳定性结论,即在基础性的家庭经济支持以外,客观维度的健康身体状况及健康生活方式、主观维度的良性社会关系网络及情感支持等,都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群体的健康自评水平,这些影响因素带有较强的超出个体之外的“社会性”特征,这对于转换社会生活环境的流动老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带有“社会性”特征的因素往往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而是需要在社会制度的设计框架中共同履行功能。如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对医疗保险的参与能够提高子女对其经济供养的概率,带来“养儿防老”和“社会养老”的协同效应[11],从而使家庭经济支持和社会医疗保障对老年人的健康自评产生积极的正向效应;在城市社会融入方面,有研究表明与社区中老人的交往有助于促进随迁老人的城市社会融入[22],在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制度设计中,推动流动老人的社区融入,构建流动老人的本地社会交往生活圈,既能够丰富老人需求的情感支持,又能够引导老人转向立足本地的健康生活方式,从而促使流动老人形成积极正向的主观健康评价。
由于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优越性,“北上广深”超大城市对老年人口仍有持续吸引力,在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仍需关注流动老人这一日趋庞大的群体的健康状况及其复杂的社会影响因素。由于流动老人的健康关联了人口流动及个体特征等多维因素,在改善流动老人健康状况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与本地老人不同的难题,这就需要在个体关注、家庭关注、社会关注、政策关注等多个层面重视流动老人群体,也需要在理论及政策讨论方面开展更广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需要考虑影响流动老人健康的“社会性”因素,将“流动的”健康问题“在地化”,以此满足流动老人对生活健康的需求,切实提升其在流入地的生活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