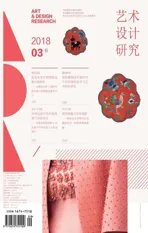清代及民国时期汉族道教服饰造型与纹饰释读
——以武当山正一道、全真道教派法衣为例
2018-10-19王鸿博崔荣荣
夏 添 王鸿博 崔荣荣
因践行“暂借衣服,随机设教”①,道教斋醮科仪中高功身着的法衣工艺精湛、形制简约、纹饰规整,是对道教宗法教义及审美价值的基本体现。对于道教服饰,姜生以史料、道教经典为基础探讨了两汉及魏晋南北朝的道教服饰伦理思想;②孙齐认为道教法服制度的兴起、普及与确立预示着道观制度的兴起、普及、确立;③田诚阳道长对道教服饰源流及类别、形制进行了梳理;④蔡林波简析了道教常服中道巾的源流;⑤学界对清代及民国时期道教法衣的研究缺乏立足存世实物的考析。本文以武当博物馆、北京白云观、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及私人收藏的20件清代、民国时期的道教法衣为基础,进行形制、结构、色彩、纹饰方面的比较分析,试图解析清代及民国时期道教法衣的造型、纹饰特征,挖掘其蕴含的宗教文化内涵。
一、清代道教服饰源流
秦汉以降,道教服饰形制、色彩随朝代兴替与道教发展而变迁。至南北朝,陆修静《陆先生道门科略》根据五斗米道的教阶制度将道教衣冠制度进行了统一,并指出道教法服与世俗朝服一致,具“别贵贱、昭品秩”的功能;⑥唐代张万福《三洞法服科戒文》又对道教服饰的等级进行了七阶细分;明初,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称:“古者衣冠, 皆黄帝之时衣冠也。自后赵武灵王改为胡服, 而中国稍有变者, 至隋炀帝东巡便为畋猎, 尽为胡服。独道士之衣冠尚存, 故曰有黄冠之称。”⑦关于明代道教常服、法服,有研究者直引中华书局校点本《明史》记载,据考,其文本有断句疏漏,正误应为“洪武十五年定,道士,常服青,法服、朝服皆赤,道官亦如之。惟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绿纹饰金。”⑧《大明会典》《三才图会》均有相同记载。⑨
清代道教常服直接承袭了宋、明常服形制,仅有细微变化。如图1示出故宫博物院藏宋代、清代皇帝“道装像”,虽朝代不同,但是道教常服形制未见更异。其中图1(a)宋代绢本设色《听琴图》画轴中宋徽宗戴道冠、服宽袖褐色道袍、褐色下裳、腰束玄色腰带垂至下摆,袖缘、门襟缘、底摆缘均镶玄色边饰,服饰色彩浑厚而不失清雅;图1(b)、(c)为清代绢本设色《雍正帝行乐图·道装像》《胤禛道装双圆一气图像》,一像绘雍正皇帝蹲身崖顶,口中念词、左手持舞塵尾,右手合拈作印,身侧海水波涛中一龙踊跃而出;另一像绘其于松下屈腿而坐,正与一道士交谈。两幅图中雍正皇帝均外穿黄道袍、内着素裳、腰系蓝绦、足蹬红履,头顶上道冠色彩略异。雍正皇帝道袍门襟镶边较短,仅至腰。
虽然雍正皇帝对待道教较为宽容,但是清代历任统治者均信奉黄教,对释道采取贬抑政策,道教在清廷遭遇冷落与抑制。据《清稗类钞》载:“清康熙丁未(1667年)七月,礼部统计释道,僧共一十一万二百九十二名,道士共二万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姑共八千六百一十五名。”⑩僧尼总数近六倍于道士人数。据《大清会典》记载,康熙壬子(1672年)准“僧道,除袈裟法衣外,服用与民同”。[11]清廷基于前朝之经验教训及民间爆发的数次白莲教起义等,对于道教是在严格防范和限制条件下利用。[12]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强制僧侣、道士弃用佛教、道教常服改换民间服饰,以抑制释道二教的发展。康熙丙寅(1685年),虽颁旨“照所袭衔名给与(张继宗)诰命。”却补述“一切僧道,不可过于优崇,致令妄为,尔等识之。”[13]明代以道士担任的太常寺乐官的定例亦被打破,乾隆谕旨廷臣“释、道二氏异乐,不宜用之。乃令道士别业,别选儒士为乐官。”[14]康熙、雍正虽偶有修缮道观并赐道士法服等权宜之举,但是整体来看清代道教发展仍日渐衰微。至民国,道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联系彻底中断,其发展更多地依靠自力更生与民间崇信,汉族民间道教服饰随之呈现出明显的“大众化”、“世俗化”趋势。

图1:故宫博物院藏宋代、清代皇帝道装像三幅(局部)

图2:清代道教科仪场景
二、清代及民国武当山正一道、全真道教派法衣形制与色彩
明代帝王对宗教信仰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得重方术的正一道贵盛一时。[15]明成祖朱棣基于政治需求异常重视武当道教,命正一天师直接掌管武当山各个宫观。因循明制,清代武当道教中正一道长期居主导地位,在清初龙门派传入时,仍是这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龙门派实力逐步增长,渐次超过正一而上之。[16]至清末,武当山九宫八观在咸丰前为“三山符箓派”与嗣汉天师府联系在一起,咸丰六年爆发了高二先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以武当山为战场,战争中诸宫倾圮。全真龙门派十三代传人杨来旺到武当山后,修复诸宫并传龙门派于各宫观、庵堂,正一道与全真道两大道派融合、共存。[17]故而武当道教既具全真派特色,亦擅长于正一道派的斋醮祈禳、炼丹、驱邪等。[18]
近代传统道袍有大褂、得罗、戒衣、法衣(天仙洞衣)、花衣(班衣)、衲衣六种。[19]北宋道书《玉音法事》记载宋真宗时《披戴颂》的有关规定,道士所穿法服包括:“云履”“星冠”“道裙”“云袖”“羽服”“帔”“朝简”七部分;[20]其中“羽服”应指鹤氅法服。“披鹤氅以朝真,戴星冠而礼斗”是道教法服准绳,清代武当山正一道、全真道高功在道教科仪(祈福禳灾、祈晴祷雨、超度亡生等)中穿着法衣与花衣,均为鹤氅样式,花衣纹饰较法衣少。清代道教法服的色彩承袭了明代道士、道官“法服、朝服皆赤”的传统,并反映于存世实物及明清笔记、小说记载之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几乎在所有论述教戒的道经中都有明确的压抑性、限制性的规定,且诸多道教经典记载道教禁戒之一即“不得身着五彩”,[21]但是这种禁戒更多地贯彻于质朴的道教常服之中,法衣即名“天仙洞衣”(明朱权称云洞衣系寇谦之所制),必然要凭借精湛的织绣技艺与丰富的纹饰符号以彰显其作为道教科仪中人神交通的重要媒介。

表1:存世道教法服款式与色彩(部分)

图3:《吴全节十四像并赞图卷》之“朝元像”
将清代史料与道教科仪图像、传世法衣实物结合,能客观地考察法衣的形制、色彩、纹饰特征。图2(a)示出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藏清代《金瓶梅》“黄真人发牒荐亡”丝质彩版画(1700年) ,38.5×31cm;图2(c)为美国亚瑟·萨克勒画廊藏清代焦秉贞绘《宫廷道教科仪》丝质彩版画(1723~1726年) ,358×157cm。图2(a)刻画的是世情小说中民间道教度亡法事场景,图2(b)放大示出“黄真人”所服“大红金云白百鹤法氅”——刺绣白鹤纹饰的氅服衣长及踝、衣身宽博、敞袖,袖缘、底摆缘均镶皂边,图中高功、经师、乐师均外穿绛色法衣、经衣,内着白色下裳;图2(c)刻画的是清廷建醮场景:法官娄近垣亦服绛红色法衣、袖缘镶皂边,立于三层高台之上。一名清廷官员头戴凉帽、身着补服,跪于法官身侧,台下经师、乐师服绛色、青色经衣,各司其位。两图中高功法衣的形制、色彩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元代陈芝田绘《吴全节十四像并赞图卷》(图3)刻画元代法官吴全节的法服形象一致。据画中题字:“延佑五年(元代,1318年)戊午夏,奉旨建大醮于上京,作朝元像。”可证其服饰为宫廷斋醮科仪用法衣。综观清代存世道士画像与实物法衣色彩(表1),可知清代道教法师在科仪中多穿用绛红色绣花法衣。
道教法衣结构符合中华服饰“十字型、整一性、平面化”的特征。法衣主要特征为:直领、直身、平敞袖、底摆略收、摆缘呈圆弧状。款式为鹤氅法衣与窄袖对襟袍,鹤氅法衣平面结构呈“矩形”、对襟袍平面结构呈“十字型”,衣长随身,通常衣身横向宽度大于纵向长度,面料以绸、缎、纱为主,里料采用与面料异色的棉、麻衬布,门襟系一字直扣与襻带结合的闭合形式。周身加刺绣,领缘、底缘加边饰。图4黑底绣花法衣的刺绣工艺与纹饰风格较粗犷、张扬,不似清廷赐服(江南三织造制)工艺精致、细腻,该法衣应为民间匠人制作。
清代武当道教鹤氅法衣的色彩与武当山奉祀神祇所象征的易学“五行、五色”相符。武当博物馆藏一件黑底绣花法衣(图4),系清代高功举行道教科仪时穿用的上衣,长140厘米,宽183厘米,对襟、直领、广袖,黑色缎料上以捻金线刺绣盘金龙纹。法衣为黑金二色,其“黑色”服色依循武当山奉祀神祇真武大帝“披发、跣足、皂袍”的形象设计而成。《淮南子.天文训》载:“北方,水也。”武当山为玄武道场,主北,五行中北方属水,尚黑,故而武当此件法衣从玄武之色。[22]明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冠服制度章》卷六载:“鹤氅,凡道士皆用,其色不拘,有道德者,以皂为之,其寻常道士不敢用。”可见鹤氅法服不拘用色,而唯独皂色(黑色)鹤氅仅为有道德者服用,自成祖始,明代统治者因对“玄武”的崇奉进而尊尚“水德-皂色”服色。笔者在考察法衣实物过程中发现图4法衣的金线多处脱散、破损,龙、云、蝙蝠纹饰显得凌乱,亟待修缮。

图4:武当博物馆藏黑底绣花法衣

图5:武当博物馆藏红底绿(蓝)边绣花法衣

图6:武当博物馆藏绛红色江崖海水团龙法衣
与清代黑底绣花法衣相比,武当山民国时期的红底绿(蓝)边绣花法衣的形制并无二至,衣身长短相差无几,仅纹饰方面有所区别:黑底绣花法衣底摆有边饰,红底绿(蓝)边绣花法衣则在袖缘、门襟、底摆等部位饰蓝色缎料。如图5所示该法衣长138厘米,宽182厘米,直领广袖,周身用五色丝线刺绣“紫霄宫”、“新大胜会”字样及郁罗箫台、八卦、星宿、凤、云、团鹤、菊花、牡丹、江崖海水等纹样。清代及民国时期汉族民间道教法衣常于衣服里料上书写、刺绣法服所属宫观名称以及该法服制作者的姓名(便于法服的使用、保存以及法服破损时寻找原制作者织补),但是宫观与法会的名称同时刺绣在法衣后领处(重要位置)则实属罕见,“紫霄宫”为武当山明代存续至今较为完整的道教宫观,此件法衣系该宫观“新大胜会”所置。

图7:纸质刺绣“五老冠”及丝缎质刺绣“五佛冠”
《尚书·益稷》载:“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23]在法衣上用“五色”丝线刺绣“五彩”纹饰,蕴涵了深刻的吉利与祥瑞含义,武当山民国时期的法衣在纹饰方面比清代法衣更丰富,在满足信众世俗功利愿望的驱动下装饰了大量的吉祥图案。图6示出民国时期武当道教绛红色江崖海水团龙法衣,其形制借鉴了宋代汉族民间传统对襟褂,长136厘米,宽155厘米,重0.9千克,直领、对襟、接袖、衣身前短后长、周身刺绣有云、龙、江崖海水、牡丹等纹饰。
清代武当道教首服也反映着当时宗教信仰中“佛道融合”趋势。道士通常戴五岳冠、星冠、偃月冠、三台冠、莲花冠、五老冠等。图7(a)示出武当山道教协会藏清代道教“五老冠”,长42.5厘米、宽20.5厘米,系武当道教“铁罐施食”科仪中高功所戴。纸质“五老冠”上刺绣神祇为道教仪式中代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的天尊,即东极宫中救苦天尊、南极朱陵度命天尊、西极黄华荡形天尊、北极玉眸炼质天尊、中极九幽拔罪天尊。图7(b)、(c)、(d)示出清代佛教“五佛冠”,纹饰较武当“五老冠”复杂,采用了拉锁子、平绣、钉金绣等多种装饰手法。其形制与道教“五老冠”相仿,仅冠叶上刺绣的五方神祇、符号(梵文)不同。据袁瑾考证,道教“铁罐施食”与佛教“瑜伽焰口”的施食时间相同、仪式的坛场设置相似,是道教、佛教融合的一个鲜明的现象。[24]道教“铁罐施食”科仪中“五老冠”与莲花冠共用,佛教“瑜伽焰口”仪轨中“五佛冠”与毗卢帽并举,这种首服“类似性”易致使观者对道教与佛教的“服饰符号”形成趋同化解读。
三、武当山道教法衣纹饰与寓意
道教法服中的纹饰符号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清代及民国道教法衣纹饰精美,一方面在纹饰构图中反映了道教“天圆地方”的宇宙图景观,另一方面于织绣中融入了大量的大众化、世俗化的民间吉祥图案,直接借用纹饰符号的象征寓意来表达法服的威仪、华丽、神秘。如詹石窗先生所言:“作为一种精神现象,道教符号体系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不论是道教的语言符号还是道教的非语言符号都是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辐射下形成的。”[25]
首先,通过观察、比较、归纳道教存世法衣纹饰特征,发现存世法衣的后身纹饰远较前身华丽、复杂。究其原因有三:一则因为法师在斋醮科仪中演示禹步(图8(a)所示)的腾挪、转身等动作中必然展示服饰背面。如云梦秦简《日书》、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均记载,楚地巫医以禹步为舞,以北斗七星的位置行步转折可聚七星之气,故又称“步罡踏斗”。葛洪 《抱朴子.内篇.仙药》[26]与 《云笈七签》卷六十一《服五方灵气法》[27]于“禹步”的步法作了详尽的阐释。图8(b)示出苏州玄妙观正一道派科仪中的“二十八星宿”步法,法师行仪时持圭踏遍四方星宿,多须转腾;[28]二则因为在仪式空间中,法师、经师们通常面对法坛,同跪同起,观仪者位于法师后方,或跪、或立,因此观仪者的视线极易落在法师背部(图9),在受众的长期视觉停留点(服饰背面)构制更为系统、完整的道教符号能更有效地传递宗教思想感情。三则法衣“前简后繁、前疏后密”的纹饰布局一方面强调了均衡、统一的形式美感,另一方面凸显了道家易学中“阴阳”对比、调和的哲学思想。

图8:“禹步”与“步罡踏斗”简图

图9:武当山道教科仪场景

图10: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清代鹤氅法衣与对襟法袍“方、圆”构形

图11:武当博物馆藏绛红色江崖海水团龙法衣纹饰结构(笔者绘制)
其次,法衣纹饰多于后身呈现“满饰”状态,并且纹饰位置的经营多遵循“天圆地方”的章法。法衣纹饰的构制规则既反映了“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又表明了法衣制作者与服用者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在《文子》《庄子》《淮南子》等道家典籍中对于“天圆地方”的记载也颇为常见。此外,湖北省博物馆藏一件罕见的东汉道教文物“神仙人物釉陶匣”:其端面刻画手持“规”的女娲及手持“矩”的伏羲,匣两侧刻画两对羽人(持规)、神仙(持角)、力士。此匣集合了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羽人、飞天、乌鹊、鹿蹻、不死药等战国晚期至东汉时期的大多数神仙符号。[29]由此可见,“规矩、方圆”概念经诸子百家相互融合之后已成为重要的道教符号。清代道教法衣的平面结构与纹饰经营位置中所遵循的“规矩、方圆”结构如图10所示。图10(a)为清代缎质绣神祇鹤氅法衣,位于衣身纵横中轴线相交处的三清尊神居位最高,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四大元帅等共350尊神祇均从上到下分班排列,井然有序,神祇身侧原刺有名号,后经穿用磨损所剩无几。图10(b)为清代石青缎八卦仙鹤纹对襟法袍,基础八卦纹饰沿服饰后中轴心“太极”旋转,并呈“米字形”均匀分布。基础八卦纹与莲花、如意、双鱼、蝙蝠、金钱、石榴、寿桃、瓜瓞绵延等吉祥纹样组成团纹,隙地填仙鹤衔灵芝、红蝙蝠(洪福)、多头云纹。此袍在太极、八卦符号构成的“米字形”宇宙框架中包容象征世俗美好愿景的各式吉祥纹样,从而构成了一幅完整、稳定、丰富的清代道教服饰图景。
武当博物馆藏道教法衣纹饰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龙纹为核心纹样。例如清代黑底绣花法衣与民国绛红色江崖海水团龙法衣(图11),均以正龙与团龙为后中心主纹,辅以海水纹、江崖海水牡丹纹为下摆纹饰,散点分布的云纹、蝙蝠纹点缀于主纹间隙之中;另一种是以郁罗箫台、日、月、二十八星宿组成核心纹样。这种纹饰构形也是绝大多数存世法衣的纹饰形式。如图12所示,红底绿(蓝)边绣花法衣矩形前片中双凤纹样对称分布在“圆”骨骼的两侧,矩形后片二十八星宿围合的“内圆”之中是郁罗箫台、双龙蟠柱、北斗七星、南斗六星,上悬三清宫阙、“右”日(金乌)“左”月(玉兔)及“紫霄宫”、“新大胜会”字样;第二层“外圆”以一正龙、四行龙、双鹤衔灵芝、寿桃、五岳真形图及道教符箓围合;“外圆”下方的“立水”与“平水”纹样之间以五彩丝线等距刺绣三朵牡丹花,并与底摆“双龙抢珠”纹饰构成第三个“圆”。清及民国时期武当道教法衣强调的龙纹主题既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皇权崇拜心理相合,又是对先秦道教传统“四象”、“龙蹻”符号的继承与发扬。清代及民国时期汉族民间服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审美取向也充分贯彻于武当道教法衣辅助纹饰中。明、清传统龙袍、官服底摆的江崖海水纹以及祈求“福、寿”的仙鹤衔灵芝、蝙蝠、寿桃(福寿双全)等辅助性纹样的组合使用将道教服饰的神圣性与世俗性、宗教性与艺术性在“天圆地方”的构型中融合一体。
笔者以武当山正一道、全真道教派法衣的纹饰结构为基础,具体考察20件清代及民国时期的道教法衣纹饰构形细节(表2),概括出以下五点法服纹饰特征:
第一,“四象”中“青龙、白虎”常装饰于门襟垂带处。法衣门襟敞开,仅用直扣、襻带于胸前系合,前门襟双垂带上饰“左青龙、右白虎”纹样,与道教宫观山门处常列青龙、白虎二神像镇守之例暗合,如明姚宗仪《常熟私志.舒寺观篇》载:“致道观山门二大神,左为青龙
孟章神君,右为白虎监兵神君。”另据观察,不同法衣前身的“青龙、白虎”及后肩的“日、月”左、右位置常常互换,多因从法衣制作者与穿用者视角观察前身图案的左、右位置颠倒所致,后身“日、月”二纹的位置互换应是对清代帝服“左肩
日、右肩月”固定章纹位置的借鉴、避忌所致。此外,朱雀、玄武、龙、凤、蟒、麒麟、仙鹤、蝙蝠等动物纹常呈“双数”对称组合(双龙抢珠、龙凤呈祥),或与辅助性植物、器物、文字纹饰相互组合(如暗八仙、灵芝、如意、仙草、金钱、寿桃、缠枝花、万字纹,寿字纹等)以构成具吉祥寓意的团花、二方连续、角隅图案。
第二,太极、郁罗箫台、日月、北斗七星、南斗六星、二十八星宿、五岳真形图常呈圆形分布。太极、郁罗箫台居后身中心位置,日月悬于上方,北斗、南斗分列左右,二十八星宿环绕郁罗箫台,五岳真形图则拱列于底弧。据明代《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载:“黄帝见天人,冠金芙蓉冠,有俯仰于上,衣金星斗云霞之法服……帝始体其像,以制法服,为道家祀天之服。”法衣中的日月纹饰与明清宫廷服饰中的日月纹饰一致,常作“三足金乌”、“玉兔捣药”之形。星斗因形圆、色金的特征,常用盘金、钉金绣制成金色团纹,正圆的星斗纹彼此连缀呈“点状线”结构,环绕于郁罗箫台周围。郁罗箫台又名玉京山,《云笈七签》卷二一引《玉京山经》称:“玉京山冠于八方诸大罗天,列世比地之枢上中央矣……”,法衣织绣纹饰以郁罗箫台为核心的构图程式贯彻了道教包罗万象、兼容并蓄的宇宙图景。

图12:武当博物馆藏红底绿(蓝)边绣花法衣纹饰结构(笔者绘制)
第三,道教经典符号“八卦”的六十四卦象常用作“点状线”沿法衣四周镶边装饰,从而形成矩形框架将各种具象、抽象的纹饰符号藏纳其中。因为在古人的心目中,八卦往往代表了整个宇宙,具有无限包容性,因之便能产生丰富的符号语言效应。[30]值得注意的是,法衣底摆部位刺绣的缘饰极易磨损以至于丝线脱落、散佚,但是相较于缠枝花卉、仙鹤、蝙蝠等形、色复杂的纹饰,“六爻”卦象纹饰构型简洁易于织补,制作者能迅速修缮法衣边缘破损纹饰,同理,构型简洁的“线状”回纹也常装饰于法衣袖口缘、领缘、底摆缘,集装饰性、功能性于一身的镶边细节体现了民间匠人节俭意识与“备物致用”的造物思想。
第四,道教神仙谱系虽复杂但是出现在法衣纹饰中时仍循章法。正如卿希泰先生批驳道教神仙“杂乱无章论”时指出:“道教诸神并非杂陈无序,而是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整合,并且形成系统。”[31]清代及民国道教神祇纹饰法衣分两类:其一,当法衣上的道教神祇数量较多时(超过300尊)按照道教神仙谱序以三清尊神为中轴,沿法衣后中心从上到下、从中间到两边排列,观者可从神祇站位、身后有无“背光”及神祇所着冠、服式样、色彩推断天神、地祇、人仙之属;其二,清代及民国时期八仙常以暗八仙(法器)形态出现在汉族民间服饰上,绝少有直接刺绣仙人图像的。但是道教法衣却常常装饰缂丝、刺绣八仙像——以圆形“开光”式样构图,八位仙人及其代表性的法器置于圆形“开光”内(也有二尊仙人组合于同一圆中),并按照“圆形”骨骼均衡地装饰在法衣之上。

表2:存世道教法服纹饰(部分)
第五,清代及民国时期道教经典教义发展几近停滞,道教符咒禁忌、去病禳灾、祈晴止雨等方术,都成了人们信仰中实际的需求。[32]故而法衣纹饰内容除沿袭道教传统“养怡长生”主题之外,受汉族民间世俗、功利文化与“佛道融合”趋势影响,出现了大量融汇、杂糅的衍生符号。如明清龙袍、官服中的江崖海水纹、十二章纹,祈求加官进爵的平升三级(瓶中三戟)图案,佛教八宝纹等随着清代至民国道教的衰落而趋于泛滥,以民国时期道教法衣为甚。清末至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许多似是而非的鹤氅法袍。例如:李雨来先生藏的2件清末鹤氅法袍中既有五岳真形图又有佛八宝纹、满文,据其推测应为满、蒙民族使用;罗德岛设计学院博物馆藏编号为55.242的清末缂丝法袍(该馆错标为“道教法衣”)采用“平缂加画”的工艺制成,纹饰中的仙鹤、三爪蟒、麒麟均呈现出典型的清晚期风格,氅衣后身虽有三清宫阙、郁罗箫台(“四层塔”式样不符合规制)、门襟垂带饰二龙纹、且后身满饰“十八罗汉”、五岳真形图走形、北斗与南斗均列“七星”、二十八星宿缺数,种种“佛道混杂”的纹饰均与道教法衣遵循的法则相悖;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一件编号为58.146的清代鹤氅法袍(该馆错标为“道教法衣”)除“鹤”之外则全然是佛教纹饰:蓝底缎质绣仙鹤、缠枝牡丹,后身绣佛教八宝纹,门襟垂带饰二龙纹(不符合“左青龙、右白虎”规制)。另有多件民国时期的民间佛教法袍全然模仿了道教鹤氅法衣的结构、纹饰,仅将“郁罗箫台”换成佛教神祇而已,这些法袍已失却道教之“根本”,均不属道教法衣范畴。
四、结 语
清代及民国时期武当山正一道、全真道教派法衣乃道教法衣之集大成者,现为道教传道、宣扬、修行之通行用服。既承袭了汉民族因满清入关以来遭受毁灭的衣冠文化,又在道教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哲学思想与民俗文化的融合,使之作为布道及祭祀载体在宗教仪式中具有独特的专有性和神秘性。道教法衣作为宗教工具直接承担与民众的视觉交流,因而向其植入特殊的纹饰图样以体现道教教义中的宗教观、宇宙观、世界观以及生死观,为道家思想宗教化、道教传播世俗化之直观媒介。因此,挖掘及梳理道教法衣形制与纹饰源流进而分析其蕴藏的文化及宗教意义,利于对汉族服饰文化的理解与传承,也可尝试性的解读历史进程中道家思想和道教教义之变迁及其在法衣中的世俗化呈现。
注释:
①《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第229页。
②姜生著:《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伦理论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5年,第175页。
③孙齐:《中古道教法服制度的成立》,《文史》,2016年第4期,第69-94页。
④田诚阳:《道教的服饰 (一)》,《中国道教》,1994年第1期,第40-41页。
⑤蔡林波、杨蓉:《早期道巾源流辑考》,《中国道教》,2015年第1期,第58-61页。
⑥同②,第175页。
⑦同④,第40页。
⑧东方:《〈明史·僧道服〉正误二则》,《史学月刊》,1991年第4期,第34-34页。
⑨[明]王圻、王思羲撰:《三才图会(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52页。
⑩[清]徐珂撰:《清稗类钞·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39页。
[11]参见清档:[清]清会典/康熙朝/大清会典一/卷之四十八/[禮部]/[儀制淸吏司]/冠服/冠服通例/4/8
[12]卿希泰著:《中国道教史: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4页。
[13]参见清档:[清]清实录/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十一/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至八月/9/35
[14]同⑩,第1956页。
[15]潘显一、李裴、申喜萍等著:《道教美学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年,第17页。
[16]同[12],第4页。
[17]王光德、杨立志著:《武当道教史略》,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
[18]唐大潮、石衍丰:《明王朝与武当道教》,《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10页。
[19]田诚阳:《道教的服饰 (二 )》,《中国道教》,1994年第2期,第32页。
[20]张振谦:《北宋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现象论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第96页。
[21]同②,第174页。
[22]湖北省博物馆编:《道生万物——楚地道教文物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77页。
[23]李学勤著:《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24]袁瑾著:《佛教、道教视野下的焰口施食仪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75页。
[25]詹石窗:《道教符号刍议》,《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34页。
[26]王明撰:《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9页。
[27]同[22],第176页。
[28]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研究组编:《苏州道教艺术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29]同[22],第18页。
[30]同[25],第39页。
[31]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32]同[15],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