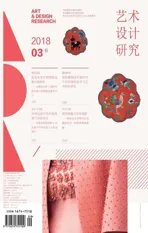明代戒指的样式、用途及文化考析
2018-10-19邓莉丽张泽玥
邓莉丽 张泽玥
“戒指”又称“指环”、“约指”、“指镯”、“指钏”等,“戒指”一词的普遍使用是从明代开始。明代都卬 《三余赘笔》:“金世俗用金银为环,至于妇人指间,谓之戒指。”①又顾起元 《客座赘语·女饰》:“金玉追炼约于指间曰戒指。”②目前考古发现的明代戒指,不仅在数量上较前代大幅度增加,样式也更加丰富,其用途也更加多元化。
一、明代戒指的样式
1、金镶宝戒指
金镶宝戒指是明代流行的戒指样式,明代金镶宝戒指具体又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戒面单颗宝石镶嵌,这种类型较为常见,如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膺绪墓出土的嵌绿松石金戒指③(图1),戒面突起呈椭圆形,金托内嵌一颗绿松石,托周围饰联珠纹; 第二种为戒面两颗宝石镶嵌,这种样式一般镶宝石的托为葫芦形,湖北蕲春县蕲州镇明墓出土的一枚金镶宝戒指即是一例④,该戒指戒面作葫芦造型,上下各嵌一颗宝石,明代梁庄王墓也出土有相同样式的金镶宝戒指⑤;第三种为戒面三颗宝石镶嵌,上海李惠利中学墓发现的两对金镶宝戒指⑥,戒面的三颗宝石一横排列,中间者最大,两颗较小的宝石对称分布于左右两侧,江西刘娘井明墓也发现与此样式相同的金镶宝戒指⑦。
2、马镫形戒指
马镫形戒指也是明代流行的样式,这种戒指戒面高出于戒指圈,戒面有一定的弧度,形似马镫。马镫戒指因为戒面与戒指圈之间有一个略弯的转折,在明代又称作“古折戒指”。与普通的圆圈形戒指相比,马镫戒指戒身大且分量重,戴起来便能凸显富贵之气。明代马镫戒指发现较多,如浙江余杭塘栖超山明墓出土的金马镫戒指⑧(图2),上海明代太学生顾叙墓出土的白玉马镫戒指⑨,江苏常州花园底明代白氏家族墓出土的一枚银马镫戒指⑩(图3),明昭勇将军戴贤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一对蔓草纹马镫戒指[11]等。
3、几何形戒面戒指
这类戒指戒面以及圆形、椭圆形及长方形为主,戒面一般略微高出戒指圈,也可以看作是马镫形戒指的延伸款。如梁庄王墓出土的金法戒[12](图4),戒面为长方形,錾刻一“回”字。上海宛平南路三品官员夫妇墓女穴室出土的两对金戒指[13](图5),一对戒面为圆形,一对戒面为长方形。南京江宁谷里出土的两枚金戒指[14],一枚戒面为椭圆形,另一枚为长方形,上面浅刻灵芝纹。南京丁墙村出土的一对金戒指[15],戒面长方形,两端收成尖角,一件饰挑柴的樵夫和耕田的农夫,一件饰垂钓的渔夫和勤读的书生,合为“耕读渔樵”,纹样为浅浮雕效果。南京西善桥明墓出土的一对金戒指[16],戒指圈至戒面渐宽,戒面为长方形,上浅刻鹭鸶莲纹,同墓出土的另一对金戒指[17],戒面为圆形,其上镂空圆钱形图案(图6)。
4、翻面戒指
这一类的戒指戒面中心有轴,用以翻转。上海李惠利中学明墓女穴室出土的一枚金戒指[18],戒面做成委角方形,边框与芯子分制以活轴相连,芯子的一面饰一个“安”字,另一面饰“秋胡戏妻”纹样(图7)。江苏太仓明王忬墓出土的一枚金戒指[19],戒面为蜀葵花形,花心设活轴,一面焊“忍”字,另一面焊“耐”字(图8)。上海顾东川夫人棺内出土的四枚金翻面戒指[20],戒面亦为委角方形,内心为长方形,一面分别印有“万”、“寿”、“同”、“福”四个字,一面分别为“福”、“山”、“海”、“攸”四个字。
5、花卉及动物造型戒指
这一类戒指戒面以各类花卉或动物造型呈现,主要有蜀葵花、菊花、蟾蜍、狮子、鸳鸯等造型。上海潘允徵原配赵氏墓出土的一对金戒指[21],戒面作蜀葵花型,一枚花芯刻“松”字,另一枚则刻“柏”字。南京马群明墓出土的一枚金戒指[22],戒面錾刻一朵扁菊,花芯下端镂空作菊叶状。明登州府同知李新斋夫人木棺出土的一对白玉戒[23],戒面为一只圆雕白玉蟾蜍(图9)。萧山水漾坞明墓出土一枚鎏金蟾蜍纹乌银戒指,戒面锤鍱半立体像生蟾蜍[24]。陕西博物馆收藏的一枚明代金戒指,戒面为一只立体金伏狮[25],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也出土有四件立体伏狮纹戒指[26],同墓还出土有两件立体鸳鸯纹戒指。
6、其他样式
南京中华门外邓府山出土的一对金戒指[27],戒面为盾形,其上錾刻竹节纹(图10)。上海李惠利中学墓女穴室出土的一对金戒指[28],联珠纹环,两端锤鍱錾刻成龙首。江西益庄王夫妇合葬墓王妃万氏棺出土的四枚金戒指[29](图11),戒指捶压成扁细条状,有两个扁平的圆面相对为饰。南京江宁殷巷沐叡墓出土的玉韘[30],为圆形,一端延长呈角状,上有一道凸弦纹(图12)。江西明代乐安昭定王朱奠垒暨妃宋氏合葬墓出土两件玉扳指[31],一件为扁圆形,一件为圆形。
二、明代戒指的用途
1、男女定情定婚的信物

图1:嵌绿松石金戒指

图2:金马镫戒指

图3:银马镫戒指
明代以戒指作为定情或定婚信物已是普遍现象,明代男女婚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封建礼教的约束,需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男女双方还是具备一定的选择权利,通常在婚事确定之前,先要相亲,相亲由男方掌握着决定权,同意后则留下戒指等物,若亲事由父母长辈做主,男方也需往女方家送些礼物定亲,又叫做“插定” 。 《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七回写春梅吩咐媒婆薛嫂带上礼物:“往葛员外家插定女儿,带戒指儿。”《金瓶梅词话》与《醒世姻缘传》中分别有好几处关于定情、定亲或相亲场景的描写,里面所涉及的物件大都包括戒指,具体见表1。

图4:金法戒

图5:长方形、圆形戒面金戒指

图6:钱纹金戒指
明代关于王室贵族的婚礼礼仪的文献,如《明史》《明会典》中所记载的纳彩、纳征礼物中虽没有戒指,但从明代王室贵族墓室戒指的发现情况来看,王妃墓室尤其是帝王王妃合葬墓中屡有金或金镶宝戒指发现。如明梁庄王朱瞻垍与其继妃魏氏合葬墓出土金镶宝戒指三枚[32],与其一起被发现的还有玉叶组佩、金钑花钏等物。 《明会典》卷六十六记载明代亲王婚礼纳征礼物中就包括“玉谷圭”、“金钑花钏”[33]等物件。可以设想,戒指也是王室贵族婚嫁财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作为夫妻信物或纪念之物用于陪葬。
定婚戒指一般为男方送与女方,但如果是用于定情,也可以是女方送给男方,《三刻拍案惊奇》第五回中写一妇人看上役缉耿埴:“将手上两个戒指,把袖中红绸汗巾裹了,向耿埴头上‘扑’地打去。”[34]明代冯梦龙《挂枝儿》里也写道:“这几般表记儿送与哥哥作念……戒指儿戒游手,荷包儿谨浪言。”[35]封建礼教主张“男女授受不亲”,只有手通常暴露在外,是最易接触的身体部位。“戒指儿戒游手”应是指戴上戒指,就能时刻提醒所戴之人要戒除与其他异性的身体接触。同一个物件,由“指环”、“指镯”到“戒指”名称的词义转换来看,以“戒指”一词作为男女定情订婚信物,在词义的传达上也更为贴切具体。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用于定婚戒指的数量较多,少则一对,多则六个以上,又以四个为多。如上表中“定婚礼物明细”一栏六处有五处戒指的数目都是四个,从出土实物看,四只戒指成套出土的案例也有不少,如江西刘娘井明墓[36]、顾叙夫妇合葬墓女棺[37]出土的金镶宝戒指均为四只,宛平南路三品官员夫妇墓女棺出土有两对金戒指(图5)。至于戒指的样式,应该是有多种,根据个人喜好和财力来定制,一般来说,以金镶宝戒指、金质戒指为多,定婚戒指的佩戴也以女性为主。
2、祝寿祈福、个人明志及身份象征
明代戒指的纹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求吉祈福的祥瑞纹饰,这一类主要有寓意夫妻恩爱的纹饰,如“鹭鸶莲花纹”、“鸳鸯纹”等,除此,又以祝寿题材为代表。明代祝寿之风盛行,祝寿题材的纹饰被大量应用于各类器物,戒指也不除外。如上海顾东川夫人棺内出土的四枚金翻面戒指所印之字,就包含了长寿、有福之意。瑞兔纹、灵芝纹及蟾蜍纹等戒指也都含有祥瑞长寿的寓意,如浙江王世琦墓出土的四枚金戒指[38],其中两枚饰瑞兔望月纹,两枚饰灵芝纹。瑞兔与长寿相连,主要源于“嫦娥奔月”、“瑞兔捣药”的神话故事,故事中瑞兔不分昼夜地为神仙们捣制长生不老之药。蟾蜍纹戒指的设计构思与明代流行的群仙祝寿故事也有联系,内府演出本《群仙祝寿》杂剧,刘海蟾祝寿的供献便是“金钱一串、金蟾一个”[39]。这类饰有祝寿题材纹饰的戒指或是为寿礼而专门打制,且多为家里晚辈给长辈祝寿时准备的礼物。明代剧本《明珠记》第十回中便写道:“明日是俺舅娘生日,买些金珠首饰上寿。”[40]
第二类为个性化纹样设计,用于表达个人身份或表明个人的志向与信仰。前者如李惠利中学明墓出土的金翻面戒指(图7),戒指图案便是根据佩戴者身份专门设计的,“戒指图案亦可寓意为‘妻’。而另一面的一个‘安’字,也不妨解作与妻对应的‘安人’之意。”[41]“安人”是对六品命妇的尊称。后者如耕读渔樵纹戒指,“耕读渔樵”是明清时期流行的装饰纹样,描绘俗世生活,又被文人士大夫们用来表达退隐之后,对田园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的人生境界的向往之情。再如明王忬墓出土的“忍”、“耐”字纹翻面戒指(图8),也是用来表达王忬崇尚“百忍”之道的儒者风范的个人志向。另外明乐安昭定王朱奠墓出土的两枚玉扳指,形制与清代扳指几乎一致,应为清代扳指的先声,这种玉扳指实际使用功能已经削弱,演变为贵族男子佩戴的标志物。
3、作为财物赠送他人,用于请托或感谢
金银戒指、镶宝戒指自然也可以当做财物,用于请托办事或作为礼物答谢。《醒世姻缘传》第十四回载晁大舍请典史办事送的财物除了银子又:“一个坛内安上了一副五两重的手镯,一个坛里放上每个一钱二分的金戒指十个,使红绒系成一处。”[42]又同书第七十一回写道:“童奶奶从袖中取出一个月白绫汗巾……说道:‘这个汗巾儿里边有付小金丁香儿,两个银戒指,烦爷替我捎给奶奶,也见我感激爷的意思。’”[43]又明代小说《石点头》第四回写方氏为了和孙三郎幽会:“先把两个银戒指赏着春来,教他观风做脚,防守门户。”[44]
4、宗教用戒指
明梁庄王墓出土的金法戒(图4),是明代戒指中特殊的一例,该戒指出自“法器匣”内,应为法器。金法戒与一般戒指相较,含金量较高,梁庄王墓出土的其它三只金镶宝戒指,含金量为79.16%~83.14%[45],而金法戒含金量高达91.75%,重达18.7克。金质佛教用具含金量通常比日用品或装饰品要高,因为佛教认为在黄金中加入其他元素会降低黄金的纯度,这样一来黄金发出的天然金光就会黯淡,从而会亵渎神灵。金法戒在做法事时具体使用方式应有多种,如可以作为装饰品,巴卧·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噶玛噶仓》中描写16世纪初法王的装扮便是“右耳饰一白莲耳坠、下身右角悬挂孔雀之羽毛,其上示现它处不见之纯金指环。” 这里金指环是装饰在孔雀羽毛之上,同时也强调了该指环为“它处不见之纯金”,金法戒也可作为供物,同书中描述法王吩咐绘画一天镜像时说:“坛城周围被白云覆盖,其前方为八吉祥瑞……虎皮上方为会供物、弓箭、轮宝、金刚戒指等。”[46]南京象山东晋墓出土一枚金刚戒指,与梁庄王墓金法戒造型十分相似,经学者考证,这枚金刚指环即来自佛教发源地印度。[47]
除了法戒,另外还有一些戒指从纹饰上看,与佛教也有关联,如常州花园底明代白氏墓出土的刻有“心”、“存”二字银马镫戒指(图3),结合同墓发现的鎏金银观音立像、坐佛像来看,墓主生前为信佛之人,此银戒所刻文字或与墓主生前宗教信仰相关。再如金卧狮戒指,狮子本为佛教象征物之一,如文殊菩萨坐骑便是狮子,狮子座也被运用在药师佛、宝生如来、大日如来所化现的应身上。
三、明代戒指源流及文化背景
1、推崇复古、提倡汉风的服饰制度
明朝是汉族建立的王朝,朱元璋出身农家,这一点与汉太祖刘邦相似,锐意复古是明朝治国政策的特征之一,在制定服饰制度时,朱元璋也要求“礼官及诸儒臣稽考古制以闻”[48]。明代戒指的某些样式可追溯至汉代,最典型的便是玉韘,韘是套于右手拇指上用于钩弦护指的工具。我国目前最早的玉韘发现于商代,汉代是玉韘较为流行的时期,不过由唐至元,却几乎没有玉韘的发现。沐叡墓出土的玉韘形制与江苏省常州市出土的西汉初期玉韘[49]十分相似,另江西益庄王王妃万氏棺出土的金戒指(图11)与吉林大安渔场秦汉时期墓地出土的一枚铜戒指[50]的形制也十分相似,而该类型戒指在唐代至元代这一期间也没有被发现过。由此可见,在明代服饰推崇复古、提倡汉风的情形下,由唐至元某些消失的戒指样式在明代又重新出现了。
2、中西亚、东南亚等地戒指文化的渗透

图7:“安”字、“秋胡戏妻”纹翻面金戒指

图9:蟾蜍纹白玉戒

图10:竹节纹盾形金戒指
蒙元时期,中东和中亚穆斯林便开始大举迁居黄河和长江流域,西方珠宝和阿拉伯宝石学开始在中国流行。我国宋末元初戒指镶宝之风已经开始兴盛,不过此时镶宝戒指还未成为戒指样式的主流,直到明代才蔚然成风。明代金镶宝戒指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与外来戒指文化的深入渗透有直接关系,明代的外交政策是主张“不征”,明朝与中西亚、东南亚等国家长期保持着朝贡、贸易往来的友好关系,各种金镶宝戒指、金戒指通过朝贡、贸易的途径传入中国。如《西洋朝贡典录》记载的满剌加国的贡物中就有“金厢戒指”,浡泥国、锡兰等国家贡物中也都有“金戒指”。除此,明代戒指上刻印文字的方式或也是受到西方戒指文化的影响。戒指在西方最早作图章之用,图章戒指戒面一般刻有象征个人身份或权利的文字或纹样。如5世纪时波斯的一枚印章戒指[51](图13),方形的戒面中心阴刻一个弹琴的人,左边及右下角各有一动物,四周刻印意思为“加冕圣人约翰印章”的希腊文字。虽然目前没有文献资料直接证明明代从中西亚、东南亚等国家输入的戒指中有印章戒指,但是在当时频繁的政治经济贸易往来中,外来戒指文化无疑会对明代戒指的设计产生影响。

图8:“忍”、“耐”字纹翻面金戒指

图11:椭圆面对饰金戒指

图12:玉韘
3、农耕与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再次交融
明代虽然是汉族建立的政权,但在其之前的元朝却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各民族服饰的相互影响,在元代颇为明显,以至于明代中原服饰风俗中还保留有一些游牧民族服饰因子。如宋元之前发现的戒指多为单只或一对出现,明代的戒指却多为四只以上出现,多时甚至带满双手十根手指。上海宛平南路三品官夫人墓,出土的六只白玉戒指与四只金戒指,发现时戴满女墓主十指[52],这样的喜好或许是受到了游牧民族服饰习惯的影响。游牧民族往往在首饰的妆扮上喜好繁多,如辽代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的墓主人陈国公主十指戴金戒指十一枚(有一指上两枚套叠在一起)[53]。明代的盾形戒指、立体动物造型的金戒指,在游牧民族的戒指中也可找到其源头。内蒙古包头市出土的一枚北魏时期嵌松石立羊形金戒指
[54],戒面焊接昂首盘角立羊造型。内蒙古通辽市出土的蟾蜍形金戒指[55](图14),戒面呈盾形,水晶戒面为一立体蟾蜍。再看明代流行的马镫形戒指,从社会环境来看,农耕地区对马作为交通、生产和战争工具的依赖程度远不如北方草原地区,对于马镫的认识度与熟悉度自然也不如游牧民族,将游牧民族具有代表性的生活用具用于汉族地区日用装饰品设计,反映了两者文化的相互交融。
4、藏传密教的影响
明代前半期宫廷藏密活动频繁,梁庄王墓金法戒为藏传密教法器。作为法器的戒指由唐至明较为罕见,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有一枚鎏金银戒指[56](图15)或也是作为密教法器。有学者认为,法门寺地宫原为唐代密教道场[57],密教Mandala翻译为曼荼罗,“Mandala之本意为圆的、圆形的、环状的, 如太阳、月亮、球体、戒指、车轮等圆形物体。”[58]梁庄王墓金法戒与法门寺鎏金银戒指看,均为铸制成器,没有豁口,为标准的圆环,与Mandala 之本意相吻合。戒指也是密教庄严具的一种,收于《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缘部》唐武则天制《方广大庄严经》卷四载:“五百释种大臣亦各奉为菩萨造庄严具。所谓指环首饰。宝颈耳珰……”
明代戒指的设计除了受以上几点因素影响,也与当时本土审美文化、民俗文化有很大关系。首先明代首饰崇尚金玉珠宝为贵、华丽厚重为美的奢侈之风,其次是各类吉祥纹样在明代也日趋成熟,而明代新兴的小说、话本及戏曲也为戒指设计提供了新的构思来源。
四、一点设想:戒指作为婚姻信物与古印度梵剧、佛教传播的关系

图13:波斯图章戒指

图14:辽代蟾蜍纹盾形金戒指

图15:唐代鎏金银戒指
戒指在我国作为正式的婚姻信物出现开始于南宋,尤其在民间更为流行。吴自牧《梦梁录》卷二〇记载的聘礼“三金”中的“金鋜”便是指金戒指。这一现象应该和宋元杂剧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联系,与文字传播相比,说唱的形式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所接受,传播面也更为广泛,宋元杂剧中有很多关于戒指作为爱情、婚姻信物的剧情。如明洪楩辑录的宋元及明初话本小说及《清平山堂话本》中话本《戒指儿记》,便是以一枚金镶宝戒指为线索,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串联起来,元代关汉卿《望江亭中秋切鲙》第三折中也写道:“(正旦云)这个是金牌?衙内见爱我,与我打戒指儿罢。再有什么?”而宋元杂剧受佛教故事、古印度梵剧影响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沙恭达罗》是著名的印度梵语古典文学作品,由古代印度作家迦利陀娑所写,根据季羡林先生考证,迦利陀娑“大概生于350 年到472 年之间”。 《沙恭达罗》讲述了女主人公沙恭达罗与国王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并结为夫妻,国王回京时留下刻有自己姓名的戒指作为信物给沙恭达罗,而她与国王“重圆” 的关键因素是国王见到了信物——戒指。目前关于印度梵剧传入我国的具体时间尚无定论,不过有学者研究表明传入时间应早于南宋,“加之《弥勒会见记》剧本在新疆的被发现、《沙恭达罗》剧本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被发现, 可以说, 梵剧在南宋戏文产生之前被国人所知是确凿无疑的。”[59]另外也有学者认为,“约在13 世纪时,迦利陀娑的著名诗作《云使》( Meghaduta) 就被译成藏文,收入大藏经《丹珠尔》中。有人甚至提出,至今传唱不衰的八大传统藏戏之一的《苏吉尼玛》,有可能是根据迦梨陀沙的《沙恭达罗》写的。”[60]在古代,中国佛教僧侣为了翻译与诵读佛经,首先要学习梵文,并通过讲经说文的形式推广佛教故事。如唐代高僧义净就在东天竺的南界耽摩立底居住一年有余,师从僧人大乘灯学习梵语,其译著《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三写净饭王之子与耶输陀罗的婚事也是凭借指环得到确定。古印度与结婚戒指相关的佛经故事及梵剧故事产生时间大概相当于我国的魏晋至唐代初期,其传播需要一段时间,至南宋时,通过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及藏传佛教已流播到中土各地,并被大部分人所熟知和接受,其故事情节又被宋元戏曲、说唱艺人所借鉴,从而进一步得到推广,至明代,戒指已经成为民间男女定情定婚的常用之物。因此可以推断,我国以戒指作为定情定婚信物现象的产生,与佛教文化在我国的普及发展有着内在联系,不过,二者发生直接关联的时间节点论证还需进一步的文献资料丰富与挖掘。
结语
明代戒指丰富的样式、精巧的工艺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美轮美奂的视觉审美体验,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多彩的明人生活画卷。戒指在明代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常见的装饰品,除此,还有很多实际的用途,它是定情定婚的信物,在人际交往中也可以作财物或礼物赠送,它又是贵族及士大夫们明志、表达身份的象征物,并承载着人们美好的生活愿望,在宗教活动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明代部分戒指的样式可追溯至汉魏时期,外来文化、游牧民族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之间的融汇贯通,对明代戒指样式、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戒指在我国作为婚姻信物的出现,与佛教僧侣对佛经故事及印度梵剧故事在我国的推广传播也有着密切的关联。
注释:
①都卬:《三余赘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②顾起元:《客座赘语》,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③[14][15][16][22][27][30]南京市博物馆:《金与玉——公元14-17世纪中国贵族首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第58-60页。
④[25][54][55]南京博物院:《金色中国——中国古代金器大展》,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395-398页。
⑤[12][32]湖北省博物馆:《梁庄王墓——郑和时代的瑰宝》,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7年,第64、95页.
⑥⑨[13][18][20][21][23][28][37][52]何继英:《上海明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第60页,第129页,第163页,第62页,第106页,第117页,第163页,第61页,第128页。
⑦[36]小屯:《刘娘井明墓的清理》,《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第56页。
⑧[41]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92页,第91页。
⑩唐星良:《江苏常州花园底明代白氏家族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6期,第46页。
[11]彭适凡、李科友:《明昭勇将军戴贤夫妇合葬墓》,《考古》,1984年第10期,第929页。
[17]南京博物院:《明朝首饰冠服》,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
[19]太仓博物馆:《太仓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
[24]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水漾坞明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2016年第3期,第36页。
[26]张才俊:《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文物》,1989年第7期,第32页。
[29][31]江西省博物馆:《江西明代藩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27、21页。
[33]申时行:《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4]陆人龙:《三刻拍案惊奇》,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47页。
[35]冯梦龙:《冯梦龙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22页。
[38]裘樟松、王方平:《王士琦世系生平及其墓葬器物》,《东方博物》,2004年第2期,第107页。
[39]扬之水:《繁华到底——明藩王墓出土金银首饰丛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8期,第84页。
[40]陆采:《明珠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6页。
[42][43]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12、557页 。
[44]天然痴叟:《石点头》,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45]梁柱:《梁庄王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
[46]周润年:《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二十六),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52页。
[47]罗宗真:《试谈南京出土东晋玻璃杯和金刚指环的来源》,《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00期,第66页。
[48]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实录》,北京:中华书局, 2016年,第 677页。
[49]徐丽华:《常州博物馆50周年典藏丛书·玉器画像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50]吉林省博物馆文物队:《吉林大安渔场古代墓地》,《考古》,1975年第6期,第361页。
[51]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Jewellery:Through 7000 Years.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n Ltd, 1976,P247.
[53]张郁:《辽陈国公主夫妇殡葬服饰小记》,《文物》,1987年第11期,第27页。
[5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彩版一七四。
[57]《法门寺地宫原是唐代密教道场》,《中国宗教》,1995年第1期,第29页。
[58]侯慧明:《论密教早期之曼荼罗法》,《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3期,第30页。
[59]康保成:《“戏场”:从印度到中国——兼说汉译佛经中的梵剧史料》,《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1期,第53页。
[60]贾华:《试析印度古典戏剧〈沙恭达罗〉及其藏译本》,《西藏研究》,2013年第6期,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