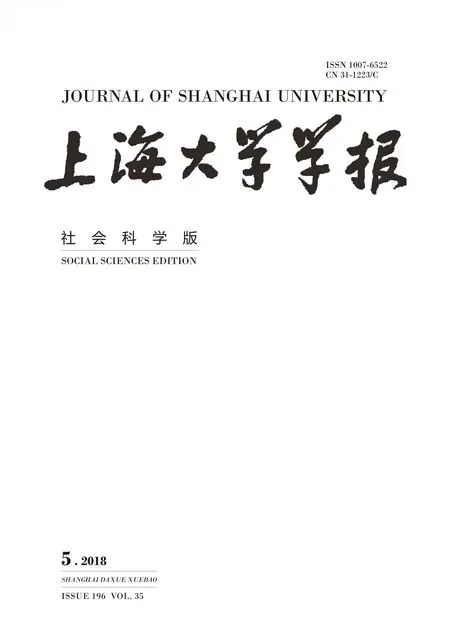英国的库尔德斯坦政策探析(1915-1922)
2018-10-09郭长刚,杜东辉
郭 长 刚, 杜 东 辉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一、英国中东战略中的库尔德斯坦地区
近代以来,为遏制俄罗斯帝国的南下扩张,英国的中东政策一直致力于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一战”初期,虽然英国联合法国和俄国试图说服奥斯曼帝国保持中立,但在“亲德派”的影响下,奥斯曼帝国政府最终选择加入同盟国一方,并于1914年11月初对俄不宣而战。随后,俄、英、法相继对奥斯曼帝国宣战。
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给英国通向印度的海上航线造成巨大的威胁。①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逐渐丧失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印度的防御,成为英国海外战略的重点。为此,英国在1902年成立“帝国防御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se),以保障海外殖民地的安全。英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中东战略。1915年3月8日,阿斯奎斯(H. H. Asquith)首相任命了一个由外交部、殖民部、印度事务部、战争部、海军部等部门官员组成的德邦森委员会(de Bunsen Committee),旨在明确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定位。委员会的主席为外交次长助理莫里斯·德邦森(Maurice de Bunsen),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为委员会书记。当时英国在中东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保住西线战场,促使俄国坚持与德国作战,英国已经满足其对海峡地区和伊斯坦布尔的领土要求,“近东均势”被打破,全面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将在所难免;法国要求得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西里西亚地区(Cilicia),这又对英国控制的埃及和苏伊士运河造成潜在的威胁。因此,英国在保障其利益前提下,还必须协调自己与法、俄盟友之间的多重矛盾。
从4月中旬到5月底,德邦森委员会共举行了13次会议,并于6月30日提交了题为《英国在土耳其和亚洲之急需》(BritainDesideratainTurkeyandAsia)的报告。[1]该报告着重强调了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两河流域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达的灌溉农业可为帝国提供大量的谷物;处于英国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政府可以抵制俄国向波斯湾方向的扩张;这一地区对于保障通向印度航线的安全具有重要军事意义。该报告还系统地阐释了解决奥斯曼领土问题的四种方案:(1)瓜分;(2)划分势力范围;(3)维持奥斯曼帝国独立;(4)使奥斯曼帝国地方分权化。在阐述瓜分方案时,委员会特别关注了南库尔德斯坦即摩苏尔维拉亚特②维拉亚特,一般译作“省”,是晚期奥斯曼帝国的一级行政区划,下辖若干次级行政区划桑加克(Sanjak)。据1899年的奥斯曼帝国地图,摩苏尔维拉亚特下辖摩苏尔、基尔库克和苏莱曼尼亚三个桑加克,大体包含现代南库尔德斯坦地区,在英国外交文献中摩苏尔和南库尔德斯坦经常混用。的战略定位。虽然南库尔德斯坦拥有重要的石油资源,且对保障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安全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但是,报告认为,这一地区既是法国感兴趣的地区,也与俄国的势力范围接壤,维持大量的军事存在将是维系英国对其持久统治的必然选择。这无疑将会为本已不堪重负的帝国防御增加负担。因此,报告建议将法国可能要求的乌米亚湖(Lake Urmia)以西的库尔德斯坦地区(摩苏尔北部)嵌入英俄势力范围之间,充当英俄之间的缓冲区。与此同时,该报告还建议英国在地中海东海岸寻求一个可容纳海军舰队且能与巴格达用铁路相连的港口,并把巴勒斯坦的海法(Haifa)作为最佳选择。①1915年3月,在同意将海峡交给俄国后,英国决策者已经考虑在地中海东岸寻求一个港口作为“补偿”,赫伯特·基奇纳(陆军大臣)和温斯顿·丘吉尔(海军大臣)都建议选择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即今土耳其东南的伊斯肯德伦港)。但是德邦森报告认为,英国如果占领亚历山大勒塔,将把法国的势力范围分割为两半,势必激起法国的强烈反对。德邦森报告书旨在回答“如果战争获胜,英国如何处理中东事务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这一核心问题,它第一次将南库尔德斯坦地区纳入英国中东战略的整体考虑之中。
战争初期,英国还密切关注着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这不单是基于阿拉伯军队在战争爆发后日益凸显的军事价值的考量,还由于策动作为“圣地”保护者的阿拉伯人发动反奥斯曼帝国的起义将会打击奥斯曼帝国。为鼓动阿拉伯人起义,1915年10月,代表英国政府的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Sir Arthur Henry McMahon)以书信形式向麦加的阿拉伯民族运动领导人谢里夫·侯赛因(Sharif Husain)作出阿拉伯人在战后获得独立的许诺,两者就具体疆界划分达成初步共识。[2]47-56英国又不得不平衡法国和阿拉伯人之间互有冲突的领土诉求。11月,英法正式举行中东问题谈判。由于法国代表乔治斯·皮科(Georges Picot)坚持得到“大叙利亚”地区,拒绝在阿拉伯人独立问题上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但是随着德意志帝国战略西移,法国无暇东顾,不得不改变对阿拉伯人的强硬态度。新一轮的英法谈判在12月份开始,赛克斯接替亚瑟·尼克尔森(Arthur Nicolson)出任英国代表。与之前的立场不同,法国主张直接控制地中海沿岸和黎巴嫩地区,间接统治由阿拉伯人统治下的叙利亚内陆部分,作为“补偿”,南库尔德斯坦部分地区应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3]713这一提议既与英国建立战略缓冲区的打算不谋而合,也为英国得到海法提供了交换条件,从而消除了双方谈判的最大障碍。1916年2月初,英法两国政府先后通过了赛克斯和皮科起草的备忘录草案。
俄国的支持显然是解决奥斯曼领土问题的前提条件,英法对此心照不宣。1916年3月10日,英法两国驻俄大使同俄外交大臣举行会谈,俄国明显对法国势力向南库尔德斯坦的延伸不满,因其不希望在南下波斯湾的道路上多出一个障碍。3月17日,俄国外交大臣向英法提出修改势力范围的备忘录:比特利斯通道和乌米亚湖地带应划归俄国,作为补偿,瑟瓦斯-哈尔普特-基沙勒之间小亚细亚领土将让给法国。4月26日,法、俄根据俄国的备忘录对其势力范围边界做出微小的调整。[4]65-8
到1916年6月1日,英国、法国、俄国之间完成照会互换,经过反复磋商后的《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Agreement)最终完成,确立了三者在近东地区的势力划分:(1)俄国得到亚美尼亚和北库尔德斯坦地区,包括埃尔祖鲁姆(Erzurum)、特拉布宗(Trabzon)、凡城(Van)、比特利斯(Bitlis)等地;(2)法国得到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沿海地区、安纳托利亚东南沿海的西里西亚和阿达纳(Adana)以及毗邻俄国势力范围的内陆地区——艾因塔布(Aintab)、乌尔法(Urfa)、马尔丁(Mardin)、锡瓦斯(Sivas)和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3)英国得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城市海法和阿卡(Acre);(4)在英法的直接占领区之间的地带,南北分为所谓的“区域B”和“区域A”,分别由英国和法国间接统治;(5)巴勒斯坦国际共管;(6)亚历山大勒塔为自由港。[2]60-64
英国无疑是战时中东政治版图划分的最大赢家:通过国际共管巴勒斯坦以及直接控制海法和阿卡,英国把法国的势力范围限制在巴勒斯坦以北地区,防止其对埃及和苏伊士运河造成威胁;通过将法国势力延伸到摩苏尔地区,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俄国的势力范围之间制造出一个法国势力的楔子,如大卫·弗罗姆金所说:“法国的中东就像中国的长城,它将保护英国的中东免于受北部野蛮的俄国人的侵袭。”[5]这样,英国在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前成功地构建起新的防御地带,确立了在中东地区的优势地位。
英国主导的战时多边协定虽未提及库尔德人的权利问题,但库尔德斯坦已处于被瓜分状态:北库尔德斯坦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小扎卜河(Little Zab River)以南的库尔德斯坦将处于英国的间接统治;西库尔德斯坦和处于英法势力范围之间的摩苏尔地区将分别是法国的直接和间接统治区域。虽然“一战”期间英国已经与一些库尔德贵族建立了联系,但尚难说这时的英国存在一个定义清晰的库尔德斯坦政策,这主要体现为:(1)与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问题相比,英国既没有把库尔德人当成一个需要单独考虑的独立群体,也没有将库尔德斯坦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或族群区域来考虑;(2)英国对库尔德斯坦的关注主要基于战略考虑,即通过牺牲库尔德人的利益和引进法国的介入,将其作为英国中东防御的重要一环,为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提供安全屏障。
二、从军事占领到《色佛尔条约》的签订
1918年10月30日,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在“阿伽门农号”战舰上签订《蒙德罗斯停战协定》(ArmisticeofMudros)。然而就在同一天,英印联军第18师团接到占领摩苏尔的指令,并在一周内占领了《赛克斯-皮科协定》划给法国的摩苏尔地区。[6]对于英国的这一突然举动,现代学者多从石油动机加以解释。然而根据战时协定,法国只得到摩苏尔北部地区,英国则保留了当时已知的主要潜在产油区——基尔库克(Kirkuk)、提克里特(Tikrit)、图兹胡尔马图(TuzHhurmatu)和基夫里(Kifri),这也解释了为何克里蒙梭在随后的谈判中会轻易放弃摩苏尔。[3]715其实,英国这一举动固然有其经济动因,但主要还是基于战略考虑:十月革命后,俄国势力暂时退出中东地区,英国不再需要引进法国的介入来对抗俄国;军事上,控制俯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的库尔德山区地带,将会为南部平原提供重要的安全屏障。
由于英军面临着军力不足和行政官员的缺乏等现实困难,维持与占该地区人口多数的库尔德人的友好态度,对于维护局势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占领当局在摩苏尔地区实行有限的地方自治。1918年12月1日,作为美索不达米亚最高行政长官的阿诺德·威尔森上校(Arnold Wilson)任命谢赫·马哈茂德·巴尔金吉(Sheikh Mahmud Barzinji)为苏莱曼尼亚库尔德自治政府的行政官。但两者在自治政府的自治范围和统治方式上存在根本矛盾。1919年5月22日,马哈茂德逮捕了苏莱曼尼亚地区所有的英国行政和军事官员,宣布库尔德斯坦独立。威尔森立即采取军事行动镇压叛乱。6月,马哈茂德被捕,后被流放到印度。[7]157
然而吊诡的是,从占领当局在南库尔德斯坦所施行的实际政策来看,英国似乎并不支持库尔德人的自治愿望。既然如此,为何英国主导的《色佛尔条约》又不否定在包括摩苏尔在内的库尔德斯坦建立库尔德民族自治政府的提议?原因在于,“一战”造成的国际环境的骤变使得伦敦政府和占领当局之间就美索不达米亚和南库尔德斯坦地区的统治策略存在严重分歧:一方面,主要来自于英印联军的美索不达米亚官员认为,“管理伊拉克就是实行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方式”,他们基于“印度经验”倾向于采取直接统治,不相信当地人的自我治理能力;[8]另一方面,战后“民族自决”原则开始成为具有高度正当性的国际规范,英国传统的殖民统治策略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1918年1月,美国威尔逊总统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提出“十四点原则”,其中第12条提到的“土耳其统治下的其他民族有无可置疑生命安全和自主发展的绝对自由的机会”,[4]130给中东民族解放运动以巨大鼓舞。1918年11月7日,迫于《赛克斯-皮科协定》被苏俄公布后引起的舆论压力,英法发表宣言,称它们对奥斯曼帝国作战的目的是完全和最终解放受土耳其人压迫的弱小民族,并许诺要建立基于当地居民自由选择的政府。[2]112其实,英法宣言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打消当地居民对潜在的新兴压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忧虑。但以威尔森为首的巴格达占领当局显然没能领会这种国内和国际舆论气候的新变化,坚持用传统的帝国主义统治经验管理美索不达米亚。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在占领初期并未形成一致的统治政策,这使得威尔森及其来自印度的下属得以在占领区依其印度经验施加统治。“由于缺少民政官员,所有这些官员及其助手都是从英军(英印联军)中征募而来,这或许能解释他们在南库尔德斯坦事务上的僵化政策。”[9]因此,威尔森在南库尔德斯坦的政策只具有“实验”的性质,反映的只是他本人及英印官员的看法,而非伦敦政府决策层的意见。
镇压马哈茂德叛乱后,库尔德人的自治愿望并未完全消失,他们在北部山区的叛乱活动,使英国稳定局势的努力频繁受挫。此时,伦敦已经开始考虑放弃直接统治方案,因为管理一个骚动不断的南库尔德斯坦将会给英国本已严峻的财政形势雪上添霜。1920年4月13日,来自外交部、殖民部、空军部和印度事务部的长官召开联席会议,以扶持一个处于英国保护下的库尔德自治政府来作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缓冲区”,这与威尔森的直接统治策略相比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此次会议批准了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的关于延迟一年解决摩苏尔问题的建议草案。该草案成为后来《色佛尔条约》有关库尔德自治方案的第62、63和64条。[10]57
与战时瓜分库尔德斯坦的政策相比,这一时期英国开始将“库尔德人之多数的土地”作整体的考虑。英国支持库尔德人的民族自治诉求,既是对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的被动回应,也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游说的结果。②战后初期,多位库尔德民族运动领导人曾与英国有过接触。1919年1月,由流放的苏拉娅·巴德尔汗领导的位于开罗的“库尔德独立委员会”呼吁英国帮助其建立库尔德斯坦国家,见David Ma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Kurds, P.122;库尔德进步协会和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赛义德·阿卜杜拉·卡迪尔(Seid Abdul Kadir)在会见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外交官员时,“请求”英国政府采取与库尔德人民志向一致的政策,并建议英国用库尔德人阻挡土耳其民族运动和布尔什维克的发展,见Memorandum by Mr. Ryan, 4 December 1919, FO.406/41/163681/No.2271。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一政策契合了英国在减少财政和军事投入的前提下,抵制土耳其和苏俄的渗透进而保障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安全的现实需要。然而,当时与协约国签订条约的奥斯曼苏丹政府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即使在伊斯坦布尔它也缺少足够的支持。与此相反,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显示其巨大的潜力,而《色佛尔条约》基本上无视它的发展。
三、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与英土摩苏尔之争
1919年,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处在濒临被肢解的境地。4月29日,意大利军队在安塔利亚登陆,占领了协约国战时秘密划定给其的地区。5月15日,英国支持的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登陆,并持续向东推进,意欲恢复其昔日东正教帝国的荣耀。愤怒的土耳其人在凯末尔帕夏领导下奋起抗争。5月19日,凯末尔在黑海沿岸的萨姆松(Samsun)登陆,这一天被认为是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7月,由东安纳托利亚护权协会发起的埃尔祖鲁姆大会召开,并通过《埃尔祖鲁姆宣言》。1920年1月20日,在民族主义者的游说和压力下,奥斯曼帝国新议会在伊斯坦布尔开幕。两周后,议会通过了《国民公约》(National Pact),从而确立了关于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基本要求。
民族革命战争的首要目标是保障安纳托利亚的领土完整,粉碎希腊和意大利的入侵,结束协约国的占领,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在这一首要前提下,民族主义者采取了灵活的民族政策。根据《埃尔祖鲁姆宣言》,安纳托利亚东部各省(包括库尔德人聚居的迪亚巴克尔、凡城和比特利斯等地)是奥斯曼共同体(Ottoman Community)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居住在这片土地的所有伊斯兰族群是真正的兄弟,他们富有相互牺牲之情,并尊重彼此的社会环境”,“我们真正的兄弟与我们的宗教和种族一致,不可能分离”。[11]81920年1月28日,奥斯曼帝国议会通过的《国民公约》则宣称,“阿拉伯多数”所居住的领土,应由全民公投决定其命运,而“所有奥斯曼穆斯林之多数居住的土地(无论是在停战线之内还是之外),这些人在宗教、种族和目标上是统一的,充满了相互关爱之情,要准备个人的牺牲……绝不承认任何事实上的或法理上的分裂”。[12]1920年4月24日,凯末尔在大国民议会的演讲进一步指出:“每一个居住在祖国边界内的穆斯林群体有其独特的环境、习俗和种族特性……自然,这些还没被详细阐述,因为时机未到。当我们的生存得到保障时,这些问题将会在兄弟之间得到解决。”[11]11-2
无论是《埃尔祖鲁姆宣言》还是《国民公约》,凯末尔主义者从中阐发的民族理论都充满了模糊和歧义:一方面,库尔德人被认为是一个种族或族群;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所有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又都属于一个民族,是“真正的兄弟”。这种措辞的模糊反映了凯末尔及其追随者旨在实现更大范围的民族动员的现实需要。通过强调“手足情谊”“伊斯兰教”“奥斯曼”等这些仍然微存的血缘、宗教和政治认同纽带,并许诺以地方自治权利,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将北库尔德斯坦四分五裂的库尔德部落(虽然不是全部)拉拢到自己一边。①凯末尔在独立战争期间曾数次表达过对库尔德地方自治的支持。如1920年他在给尼哈特帕夏(Nihat Pasha)的指令中提到:“我们的政策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建立大量自治机构……关于库尔德人居住的区域,我们认为建立地方政府是国内外政策的需要。(民族自决原则)是一个世界公认的原则,我们也接受这一原则。库尔德人逐渐完成地方政府的组建后,他们的领导人和贵族将会以此名义赢得我们的支持。”见Andrew Mango, Atatürk and the Kurd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99年第4期第13页。例如,在埃尔祖鲁姆,凯末尔成功组建了由库尔德和阿拉伯部落组成的伊斯兰军(Quvva-I-Islamie),扩大了民族主义者的势力。[13]凯末尔在北库尔德斯坦的成功,意味着《色佛尔条约》规定的库尔德自治方案在这一地区实行的希望渺茫。
同时,凯末尔对英国的库尔德斯坦自治方案保持着高度警惕。1919年6月11日,在给迪亚巴克尔库尔德贵族的电报中,他提醒库尔德人,英国炮制的库尔德斯坦独立计划是为亚美尼亚人的利益服务的,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应为祖国领土完整而奋斗。7月,他又乐观地宣称,在英国保护下的库尔德斯坦独立方案已经被“摧毁”。[11]6-8此外,凯末尔还关注着爱德华·诺埃尔少校(Major Edward Noel)②诺埃尔既是英国情报员也是库尔德人专家,战后受威尔森的委派负责监管库尔德事务。由于他对库尔德人的民族志向抱有同情并支持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经常被英国的中东官僚称为“劳伦斯第二”或“库尔德的劳伦斯”,见Michael M. Gunte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Kurds, Oxford: The Scarecrow Press, 2004: 149-150。在马拉迪亚(Malatya)与库尔德部落的秘密接触,并阻止了诺埃尔对锡瓦斯会议(Sivas Congress)的破坏计划。[7]128-9英国在北库尔德斯坦的微弱影响逐渐消弭于凯末尔主义者的民族动员。
如果说英国还能以超然的态度对待北库尔德斯坦的土耳其民族运动,在南库尔德斯坦它却不能置身事外。不管是“奥斯曼穆斯林多数的土地”,还是1918年10月30日停战线,土耳其人的领土诉求都包含了摩苏尔地区。1921年6月,一股土耳其士兵来到摩苏尔东北部的拉尼耶(Ranya),意欲策动库尔德部落的叛乱,削弱英国在南库尔德斯坦的统治地位。尽管有英国空军的轰炸,土耳其士兵还是顽强地在里万杜兹(Rawanduz)坚守到年底。①关于英国空军(RAF)在委任统治时期的作用,见Peter Sluglett, Britain in Iraq: Contriving King and Country, London: I. B. Tauris, 2007: 184-92。1922年7月,受土耳其支持的阿里·沙菲克(Ali Shafiq)上校来到里万杜兹,明确声明其使命是重新征服摩苏尔维拉亚特。他的军队驻扎在贾兹拉(Jazira),得到很多地方部落的支持,以致土耳其军队占领拉尼耶时没有遇到太多的反抗。[7]1419月初,英国和其他非库尔德行政人员乘飞机撤出苏莱曼尼亚,政权交给由库尔德人组成的委员会,局势陷入混乱。这时的英国在南库尔德斯坦几乎没有军队可供调遣。与此同时,库尔德民族主义者要求英国释放马哈茂德的政治运动正在苏莱曼尼亚形成,并扩散到哈莱卜克(Halabja)、基夫里和基尔库克等周围地区。虽然高级专员帕西·考克斯(Percy Cox)②1920年10月,帕西·考克斯取代威尔森成为英国驻美索不达米亚的高级专员。反对,殖民部还是决定利用不断上涨的库尔德民族情感,抵挡土耳其人的煽动和渗透。马哈茂德再次充当了英国实现局势稳定的工具,但他很快再次失势。
到1922年9月,安纳托利亚的失地已被全部收复,随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进入伊斯坦布尔城。这时的民族派已经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一支强大力量,英国不得不正视一个新土耳其的崛起。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对英国的库尔德斯坦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1)库尔德民族自治的地理空间被压缩到英国占领的南库尔德斯坦地区,英国不得不重新考虑伊拉克北部边界安全问题,并寻求保障南部平原安全的替代方案;(2)英土和谈势在必行,双方对摩苏尔地区的争夺转移到谈判桌上。库尔德民族自治问题逐渐让位于英国托管的伊拉克和土耳其之间的领土和边界问题,而前者则沦落为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
四、英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与库尔德自治方案的流产
1920年6月,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的阿拉伯人叛乱事件以及由此而给美国造成的巨额军费支出,致使英国的中东政策在国内遭到严厉的批评。伦敦政府意识到有必要结束其中东决策长期以来在外交部、印度事务部和战争部之间的分歧。年底,劳合·乔治首相最终决定在殖民部里创造一个单独部门——中东局(Middle East Department)——来掌管英属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决策权。1921年起,丘吉尔出任殖民大臣。自此,美索不达米亚事务的决策重心由寇松主持的外交部转移到丘吉尔领导的殖民部。
1921年3月12日,由丘吉尔主持的开罗会议开幕,出席会议的中东事务官员多达40人,由政治、军事和财政三个委员会分组讨论相关事宜,主要议题包括: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前景、减少军费开支、费萨尔(Faisal)出任伊拉克国王等问题。在南库尔德斯坦政治定位上,考克斯和丘吉尔产生了较大分歧。考克斯主张将南库尔德斯坦并入伊拉克,其理由为:凯末尔在北库尔德斯坦的胜利使得《色佛尔条约》关于库尔德自治的条款不再具有实施的可能性;南库尔德斯坦在经济上的落后使得库尔德人(苏莱曼尼亚的库尔德人除外)愿意并入伊拉克政府。[14]154与其相反,丘吉尔认为忽略库尔德人的民族情感将会给英国的撤军计划带来麻烦。在3月16日发给劳合·乔治首相的电报中,丘吉尔提出了相对完整的库尔德斯坦政策,即维护现状,避免将库尔德人纳入阿拉伯人的统治之下,直到库尔德人的代议机构做出选择。①Mr. Churchill to the Prime Minister, Foreign Office, 1921, FO.406/46/E4211/533/65。劳合·乔治批准了丘吉尔的建议,并提醒他“必须预料到安卡拉政府策动南库尔德人与北部同胞合作的企图,这种合作试图将南库尔德斯坦并入安纳托利亚政府”。②Prime Minister to Mr. Churchill, London: Foreign Office, March 22, 1921, FO.406/46/E4211/533/65。当开罗会议结束时,7位就库尔德问题表决的政治官员中的4位,即丘吉尔、休伯特·扬少校(Major Hubert Young)、爱德华·诺埃尔和劳伦斯(T. E. Lawrence)支持分离的南库尔德斯坦方案。[14]155
开罗会议明确表示,作为决策机关的中东局决定把南库尔德斯坦作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战略缓冲区,这一决定基于如下考虑:(1)如果将南部阿拉伯人的统治强加在库尔德人身上,可能导致政局动荡;(2)库尔德人的反抗很可能导致凯末尔主义者与库尔德人联合起来对抗英国,这意味着英国不得不重新部署军事力量以确保美索不达米亚的安全,而加快撤军以减少财政支出是近期的核心目标;(3)丘吉尔希望英国官员能训练库尔德人部队使其具有防卫能力,以替代英国部队;(4)建立库尔德自治政府必然会激励库尔德民族情感,这会促使库尔德人与英国合作。三个月后,丘吉尔在议会下院的演讲重申了他在南库尔德斯坦问题上的立场:“考克斯将会在伊拉克和库尔德斯坦扮演不同的角色……我相信,在他的影响下,南库尔德斯坦和伊拉克的关系将更加密切,但同时我想清楚地表明:正如它本来的状态,我们正在库尔德斯坦实践一个地方自治原则……南库尔德斯坦将被作为一个商业区(commercial area)来管理,其部落领袖不会被置于新成立的阿拉伯政府之下,而是直接对高级专员负责,直到我们期待的局势稳定和大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为止……库尔德军队将会成为阻挡凯末尔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渗透的最有价值的壁垒。如果我们将其置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之下,后果将是灾难性的。”[15]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一个惊人的政策逆转:中东局和丘吉尔的政策被拒绝,考克斯的方案获得支持”。[10]59这种逆转发生的原因有二:
其一,开罗会议虽然支持分离的南库尔德斯坦方案,但是它并没有立即明确指示委任政府执行这一决策,因为此时殖民部的精力正聚焦于伊拉克国家的创建和费萨尔王子出任伊拉克国王及其权力的限定等问题。这使得考克斯可以继续实行其“并入”方案。为了表明费萨尔是伊拉克人民主动选择的国王而非英国的傀儡,“国王选举”在1921年7月底举行。在考克斯策划下,南库尔德斯坦地区(苏莱曼尼亚除外)也纳入到这次选举之中。在其回忆录中,时任埃尔比勒(Arbil)政治官员助理的华莱士·里昂(Wallace Lyon)描述了这次选举是如何在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的:“一个绝密电报指示我们要尽其所能说服人们选择费萨尔……我那时是一个年轻军官,习惯于毫无异议地执行命令,且对政治谋划毫无经验。部落首领和城市长者聚在一起,询问相关事宜,他们不愿投票并询问有无其他候选人,我不得不承认没有……(他们问)如果不投票英国是否会恼怒?是否会派军镇压?我说我不知道,但推测他们会有点失望。”[16]虽然很多库尔德人拒绝支持费萨尔,但在英国的操纵下,费萨尔还是不可思议地获得了96%的支持率。对考克斯而言,这次选举是证明其方案可行性的最佳时机,也是他将南库尔德斯坦并入伊拉克迈出的重要一步。
其二,英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使得库尔德民族自治的政治空间丧失殆尽,这是根本原因。1921-1922年,英国的中东政策逐渐处于孤立地位,并遭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批评。1921年2月26日,苏俄与波斯签订条约,废除沙俄在波斯取得的特权,作为回报,苏俄得到在战争条件下越境打击敌人的许可。[2]90-43月16日,安卡拉的土耳其民族政府与苏俄签订《莫斯科条约》,苏俄正式承认民族主义者的领土要求,并为其提供武器和财政援助。[2]250-31921年底,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三个高加索共和国被置于苏俄的影响下。苏俄这一系列战略安排使“英国战后在这一地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险些付诸东流”。[17]10月20日,作为英国盟友的法国与安卡拉政府单独签订《安卡拉条约》①又称《富兰克林-布里翁条约》(Franklin-Bouillon Agreement),由法国外交官亨利·富兰克林-布里翁(Henry Franklin-Bouillon)与安卡拉的土耳其外交部长约瑟夫·凯末尔贝伊(Yusuf Kemal Bey)签订。,结束了法国与凯末尔政府的敌对状态,这表明英法矛盾开始公开化。同时,希腊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使英国借助希腊军队迫使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承认和接受《色佛尔条约》的愿望成为泡影。到1922年9月初,为时3年的希土战争以希腊的失败而告终,劳合·乔治的中东政策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面对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指责,他被迫于10月19日辞职,博纳·劳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赢得大选。
英国政局的变动对其库尔德斯坦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首先,1922年10月24日,维克多·卡文迪许(Victor Cavendish)取代丘吉尔成为新任殖民大臣,与后者相比,他缺乏处理中东事务的经验,英国的中东政策将不可避免更多地受到负责“委任统治”的高级专员的影响;其次,新内阁继续致力于缩减英国在伊拉克的防卫和行政支出,在短时间里创造一个能够保障其领土安全的伊拉克政府成为英伊当局急需完成的任务,民族异质性的考虑退居次要地位;最后,新政府开始改变劳合·乔治的亲希腊、敌视土耳其民族政府的政策。凯末尔的成功使英国意识到对土合约的实现是保障伊拉克安全,抑制苏俄的南下扩张,进而维护英国的波斯湾利益的必然选择。为安抚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英国不得不放弃谋求库尔德斯坦独立的计划,以消除凯末尔对英国肢解土耳其的忧虑。作为回报,土耳其则要加入国际联盟以实现对苏俄的孤立。在英国对外政策层面上,库尔德人的政治命运和利益诉求被排挤到英国中东政策的边缘位置,沦为大国利益之争的棋子。在1922年洛桑谈判期间,为争取库尔德人的支持,英土双方虽都口头强调将保障库尔德人的权利,但也都心照不宣地闭口不谈库尔德民族自治问题。至此,库尔德民族自治的政治空间完全丧失。
结语
作为战后新的中东秩序的主要策划者,英国的库尔德斯坦政策影响深远。巴黎和会确立的中东政治版图,本质上体现了以英法为主的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需要。然而,民族主义这股世界性潮流已经成为塑造中东社会的另一股决定性的力量,经过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那些曾经被列强许以空头支票的弱小民族大都逐渐取得了自治和独立地位。但是,库尔德民族自治问题却被永久性地搁置了下来,并由此产生了至今仍困扰中东社会稳定的“库尔德人问题”。“一战”期间及战后,无论是伊斯坦布尔的库尔德民族主义领导人,还是像谢赫·马哈茂德这样的地方实力派,都曾试图将其自治和独立愿望寄托于英国的帮助。英国决策层内部也确实存在过想要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建立“库尔德斯坦国”的方案,只是随着英国中东地缘战略定位的调整,这一方案最终不了了之。综合来看,英国最终忽视库尔德人的自治和独立诉求,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英国在库尔德斯坦的利益与其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利益相比,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无论是《赛克斯-皮科协定》对库尔德斯坦的瓜分,还是《色佛尔条约》对库尔德民族自治的支持,英国的首要目标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战略缓冲区,以防止土耳其或苏俄的南下扩张。当库尔德人不能承担这一角色时,英国即果断将其舍弃。
第二,凯末尔主义者的胜利压缩了库尔德民族自治的政治和地理空间。对脱胎于濒临肢解境地的土耳其民族政府而言,西方大国瓜分奥斯曼的噩梦恍在昨日,它不可能允许东南边界出现一个处于英国影响下的且对其稳定构成巨大威胁的库尔德自治实体。对土合约的迫切需要,则使英国选择牺牲库尔德人的利益来安抚土耳其民族主义者。
其三,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虚弱性也是同等重要的原因。根植于复杂的历史传统,库尔德人的身分内部存在着部族、语言、宗教和地域的严重分裂。宗教或部落领袖主导的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权力机构严重阻碍了大规模社会动员的实现。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为实现其民族志向不得不转而依靠大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