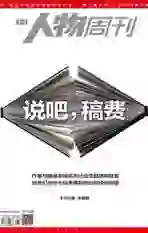职业
2018-09-25
心理援助热线接线员一根电话线的营救
当被问到陌生人的生死与自己的关系时,王磊找不到合适的答案,她想了很久,说出“慈悲之心”这个词,立刻又觉得不合适,“这个词太重了”
文 / 李雨
“我手上有200颗安眠药,跟你讲完,我就吞下去,”第一次接到高危来电的魏华林深吸了一口气,用左脚使劲蹬了几下地;“我想喝敌敌畏自杀,”刚入职三个月的王磊听到这话,心里“咚咚咚”直打鼓;“明天九点,我就拿罐汽油去死,”已经工作了四年的谌冬娣仍有点紧张地搓了搓手……
他们是广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心理援助热线组的接线员。魏华林因不满足于在中学当心理老师;王磊因中学时被校园霸凌而对心理学产生兴趣;谌冬娣因崇拜港剧《刑事侦缉档案4》中宣萱饰演的临床心理专家……本来毫无联系的三个人一同走进了这间心理援助热线室。
从2007年成立至今,热线组共接过12万多例来电,其中高危来电(来电者有自杀倾向或正在实施自杀行为)占4%左右,死亡是这群接线员日常要面对的问题。
根据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首份全球预防自杀报告,世界上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据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统计,中国2012到2015年的平均自杀率为6.75/10万,农村高于城市,男性高于女性,老年人群高于年轻人群。
2002年,加拿大人费立鹏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开通了中国第一条自杀干预热线。五年后,作为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26家心理援助热线试点单位之一的广州市心理援助热线开通。这条热线面向全国,有六台座机,九名接线员分三班轮流值班,保证24小时在线,全年无休。
没有答案
8月19日晚上10点,广州惠爱医院只有心理援助热线室还亮着灯。推开热线室的门,25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左墙挂着钟,右墙上靠着一个装满心理学书籍的柜子,往里走是六张办公桌,每张桌上配备一台电脑和电话机,接线员自由选择座机。
王磊今天值C班(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她把包和外套扔在靠近门口的小沙发上,随后按开惯用的二号线座机。接着她和B班(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同事对接,拿到纸质版通话记录,翻阅上一个班的记录,还没来得及把包和外套收拾进休息室,“铃铃铃”,电话来了。响了两声,王磊接通电话,她瞅了一眼电脑屏幕——10时12分,工作正式开始。
第一个来电的是一位高三女生,这次考试没达到目标分数,心里难受。“我该怎么办?”王磊没有正面回答,先是安慰了她,接着讲了跳高的故事——跳高是每次只提升一点高度,而不是一蹴而就。最后,她问女生是否知道达不到目标的原因。得到的答案是沉迷看小说,内心抗拒学习。
这样的琐碎日常占据了咨询来电的九成多。有的来电者按下这串号码,就想从接线员那里获得解决办法。怎么还清债务?怎么追回女朋友?离不离婚?辞不辞职?……接线员都没有标准答案。事实上,接线员最大的作用就是成为树洞,充当一个倾听和陪伴的陌生人角色,协助来电者找到答案。硬是要接线员说出一套方法论的话,他们只能用另一种方式重述一遍安慰的话。得不到答案,来电者会质问:“打给你有什么用?”
夜晚,是人们感情最脆弱的时候。有时来电量会比白天高出20%。这一夜,王磊接了19个电话,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心理问题:青春期的少女很努力学习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同;职场人士抱怨老板理所当然地给他增加大量工作;欠债者无力偿还债务;失眠者难以入睡……其中有个咨询来电长达75分钟,是个高危来电(普通的心理咨询一般控制在30分钟之内,危急来电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
将近凌晨5点,一个女孩来电。这一天,她丢失了手机但得不到处理,愤懑情绪爆发。她告诉王磊,天亮之后她就要自杀,还要伤人。
王磊预估还有阻止悲剧发生的时间。她先耐心倾听来电者的事,再使用共情技术,“我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她转述对方的话表示理解。以往成功率极高的办法这次不奏效了,女孩不肯松口。半个小时过去,王磊无计可施,只好直白地告诉女孩“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女孩仍无动于衷。
“你的名字是?”这是王磊最坏的打算了。遇到危急情况,接线员会尽可能问出来电者的名字和位置,以便报警。
突然,她留意到系统显示这个名字曾打过一个危急来电,接线员正是王磊。“我这边看到八个月前你给我们打过电话,接听的也是我,真是一种美好的缘分。”出乎意料,这种缘分打破了僵局,成功地在悬崖边拉住了女孩。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任何时候有自杀的想法,都先打给我?”
“你放心,这两天不会有事的。”
类似的对话发生在每一次高危来电中。接线员会尽最大的努力让来电者作出承诺——活下去。
但很多时候,一根电话线的力量太微薄了。
王磊记得,热线组的小组长魏华林常常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去年,一名广东高校的女大学生因母亲有精神病史而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像母亲一样疯掉,久之患上抑郁症。给心理援助热线打来电话时,她正坐在11楼的窗台。接線员努力和女孩建立了信任关系,她甚至答应接线员挂了电话会先离开窗台,和家人联系。不料,半个小时后,女孩来电告别,接线员还没来得及问清发生什么事,电话就挂断了。接线员报了警。因为属于高危来电,热线组隔天会进行电话回访。第二天,女孩的死讯传来,男接线员忍不住哭了。
魏华林希望接线员能认清这份工作的有限性,也能克服这种无力感。
接线员不是警察,也不是医生,挽救这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人靠的只是一根电话线,他们的办法是努力帮助来电者寻找身边的资源,比如父母,比如朋友。让万念俱灰的来电者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关心、惦念着他们。但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实在走投无路,还遭亲友抛弃。
“那怎么办呢?”
“告诉他,还有我。”有时,接线员是绝望之人最后的资源。
当被问到陌生人的生死与自己的关系时,王磊找不到合适的答案,她想了很久,说出“慈悲之心”这个词,立刻又觉得不合适,“这个词太重了。”
接完这通高危来电之后,终于消停了一会。早晨7点40分左右,电话又响了。王磊太累了,她礼貌地告知对方自己快要下班了,如果对方不介意,可以8点后再打来。7点55分,她循例出门打开中心门口的LED灯,嘀咕了句:“好饿!”
质疑、隐瞒、骚扰
在这个岗位上,误解和质疑是常有的事。这群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接线员,常常会接到四五十岁的人来电咨询家庭矛盾问题。对方听到接线员年轻的声音,会质疑能否帮到他们。前几年,魏华林遇到过一个有此顾虑的五十多岁已婚女性。魏华林和对方解释:“我从事这工作快十年了,可能会遇到跟你类似的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尝试聊一下。”但是遇上执意要换人的,接线员也会尊重。
从接通电话的第一刻起,接线员就努力和对方建立信任,并以最大的善意对待对方的故事,但这种善意和信赖有时会被利用。谌冬娣遇到过欠债者隐瞒自己的恶行,一昧抱怨别人向自己追债;也遇到过咨询恋爱的男子一昧把责任推给女方;甚至有一对夫妻分别打来电话,将同一个故事讲述了两个版本,妻子抱怨丈夫不顾家,丈夫抱怨妻子给他太大压力。实际上,谌冬娣能理解大多数的来电者。“大部分人在叙述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偏向自己。”
若来电者自身实在存在很大的矛盾,接线员也会提醒他,这是心理学上的面质技术。几年前,魏华林接到过一个电话,有个四川女孩因父母离异,责怪父亲不管自己,闹自杀。但魏华林了解到女孩的父亲因为担心,24小时守着她,连出门买包烟,都小跑着去。魏华林再与女孩通话时,便试探性地问她:“我可能有些疑问,你刚说……,现在又说……。”
包容小谎言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包容与自己完全对立的观点。王磊记得,她刚入职时曾接过一个女性的电话,对方一句“女人都是下贱的”把她惹急了,她辩驳了几句,刺激了对方的情绪。之后,她反省了很久。如今,她觉得就算无法理解对方,至少保持中立。
心理援助热线有一个评分系统,若是来电者评了“不满意”,热线组会有专门的人打电话询问原因。接线员的好评率一般达90%以上。王磊上个月被评了两次“不满意”,来自同一个人。
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因找不到工作和女朋友,他觉得自己很失败,便拨通了援助热线。因为好几次都是王磊接听,他便缠着王磊,向她要微信,还要求她做他的女朋友。王磊不同意。他一气之下就给王磊打了“不满意”。一周之后,因为王磊在咨询时间超过30分钟后提醒了他。男子又来了气,再次打了“不满意”。
但王磊不介意。热线组鼓励建立固定的咨询关系,如果来电者希望每次咨询的都是同一名接线员,可以询问接线员的工号,但不能要私人联系方式。不与来电者建立咨询之外的关系,这是对双方的保护。刚入行两三个月的时候,王磊曾被一个来电者威胁,如果她不给微信,对方就自杀。王磊妥协了,最后对方没加她微信,但她为此担心了一整晚。如今,王磊面对这种情况有招了,她会反问对方“谁才应该对你的生命负责?”
除了这种情况,接线员还很容易面临来电者的骚扰,甚至是性骚扰。目前,性骚扰在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性骚扰和咨询性问题的边界更是模糊。所以性骚扰来电也常常困扰着接线员。有的来电者会以咨询性问题为借口,详细地描述性爱场景,甚至使用很多淫秽的词语,更有甚者在电话的另一头发出怪异的声音。
魏华林记得,她曾接过一个三十多岁女性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详细地描述自己如何被外甥偷窥、挑逗,边说还边发出怪异的叫声。当魏华林尝试引导她找问题时,她又马上把话题拉回描述细节上,以此获得性快感。从前面对这些性骚扰的来电,魏华林会脸红、尴尬。后来,她接触了更多关于性方面的心理知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觉得这是性的一种释放方式。这么一想,她又自我安慰到,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性骚扰来电。
现在魏华林会教新人,遇到这样的骚扰电话可以装作听不懂,不满足对方的欲望;有男同事在的話可以直接把电话转给他们。挂断电话之后,接线员有权在系统上限制这个号码的来电。
两大忌讳
魏华林是热线组资历最深的接线员,从热线开通起就加入了热线组。2015年,她转为行政岗位,管理整个热线组,新人都会称她为师姐。王磊理解,都是学心理学的,算是同门。
魏华林日常主要负责招新、培训等行政工作,有时也会在一线接听。在招聘当中,魏华林倾向于有心理专业背景的科班生。目前,九名接线员中有七个是学心理学专业的,两名是有精神科专业背景的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
这支接线队伍从成立至今招聘过不少于十次。最新的一轮招聘预计在9月中旬进行,魏华林已经收到十几份简历。但受到人力成本的限制,队伍的人数仍控制在10个以内。面对每天高峰时的上百通来电,显然是不足的。
据魏华林称:现在电话的接通率只有50%,很多时候来电者会遇到被占线打不通的情况。这种情况让她忧心,因为永远不知道被占线的会不会是高危来电。所以她会尽量要求接线员控制咨询的时间,并每个月组织一次培训,小组内的成员分享自己印象深刻的案例,借此提升整体的专业技能。
魏华林总结出接线员的两大忌讳,一是将心理咨询和思想道德教育混为一谈,二是用自己的世界观去看待别人的事情。
魏华林举了个反面例子,一个接线员对一个家境优越却想自杀的女孩说,“你怎么能自杀,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这是不专业的。接线员要以中立的态度面对来电者,不应用道德标准去衡量、批判他们的行为。从前,魏华林当初中心理老师,常常会有班主任让她帮忙辅导一些学习不认真的早恋的孩子,事后班主任会干预她的咨询,她觉得一来会暴露学生的隐私,二来自己成了一个道德教育的角色。
在热线室里,接线员会遇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就算在电视剧里也鲜少上演的事情,鲜活地在现实中发生,但接线员不会站在道德的高处指责他们,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帮助他们减轻痛苦。
有的人在生活中向别人倾诉,常常会收到一句“这都是小事”。但这句话不会在热线室里出现,在这群接线员眼里,来电者的事都不是小事。他们清楚大多数时候,促成自杀都是经年累月积压的情绪,死亡不是最痛苦的,日常的琐碎才最折磨人。
王磊遇到过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女孩因和姐姐争论一道考试题目而难受。“我认为我是对的,姐姐认为她是对的,我该怎么办?我好难受。”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传到王磊耳边。王磊没有把这当作一桩小事,她耐心地引导小女孩明白这道题的答案明日就会公布,今天不要为此难受。
抑郁症是自杀的最大危险因素,但很多人不了解抑郁症。接线员常常充当科普员。这样的科普有时候不被理解。王磊就遇到过一个语气很横的母亲,一口咬定王磊是骗子,让儿子别相信她。
当然,成功的例子也不在少数。魏华林就收到过一封来自一个重度抑郁女孩的母亲的感谢信;20日的凌晨,王磊也接到一个家长打来电话了解孩子抑郁症的病情;而抑郁症患者家人的感谢电话也时常响起……
平时,C班最忙的是晚上10点到凌晨三四点,之后的电话没那么多,接线员可以在连接着热线室的大概四平方米的休息室里休息。
以前王磊值夜班想休息的时候,会把热线转到休息室门外的座机上。她睡在双架床的下铺,袜子也不脱就躺上床,一旦电话响了,她就能迅速起来,跑出去接听。但她很难睡踏实,老“幻听”电话响了。后来,她累了干脆趴在桌上休息。
我问王磊在医院值夜班怕不怕?她说自己胆子很肥。
前段时间医院电路出了问题,频繁停电。有一次,她值C班正接着电话,突然停电了,整个热线室一片漆黑,她仍旧镇定自若。
“你不慌吗?”
“慌什么?电话还通着呢。”
(感谢南方日报黄锦辉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