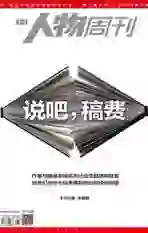一部高分纪录片的艰难上映
2018-09-25熊方萍
熊方萍
《最后的棒棒》上映第二天,体重170余斤的导演何苦立言,“票房过100万,我直播头顶开瓶。票房过1000万,我表演胸口碎大石。”半个月过去,看来直播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截至8月31日中午12点,《最后的棒棒》票房仅93万人民币。
票房爆冷,口碑不佳,这并非何苦最担心的。眼下他愤怒的是团队人员跟丢了棒棒后续记录的主线人物黄师傅。“气得我直骂他们没长脑子,现在我上哪去找?”黄师傅非片中的老黄,他年届73,在理发店与何苦相识,是何苦继续追踪记录棒棒群体的重要线索。“老人家当时在染黑头发,我觉得奇怪就和他摆了几句龙门阵。他说染黑了显得年轻点,太老了别个不敢找你爬坡上坎。”
李白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描绘过川渝地区险恶崎岖的地势,脚夫于是有了立足之地。距离《蜀道难》写成后的1200多年,火遍全国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在1996年为这一职业进行了全国性的重新命名——棒棒。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山城棒棒军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约四十万人。导演束一德以电视剧的形式记录了棒棒的鼎盛时期,退役军人何苦则用纪录片抓住了棒棒没落的尾巴。
纪录片有三个版本,分别是13集剧版(获得豆瓣九千多网友打出的9.7高分),117分钟短片版(于2016年获得首届金树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短片奖),以及最近上映的99分钟院线版(豆瓣评分6.4)。三个版本内容基本一致,主要记录了六个棒棒的日常,分别是何苦、老黄、老甘、大石、老杭和何南。除了何苦,其余五人在90年代投身棒棒行业。但随着院线版上映,观众的质疑从何苦的棒棒身份蔓延到影片主题。
“大寒过后,一定立春”
不论此前是否看过13集剧版,院线版主题都是让观众最不买账的地方。剧版主要记录快要消失的山城棒棒军生存状态,而院线版则通过记录棒棒的生活来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
“片子最早完成于2015年,离现在三四年了,增加一些反映当下的片段能缩小一点距离感。出于这个考虑,在剪辑院线版时我改变了创作思路。”何苦前后换了四个编导,才剪出现在的院线版,然而新创作思路下的主题却招来更多质疑。
不少豆瓣评论提到“主题靠强行升华、改善靠摆拍、生拗主旋律”等令人不适的观影体验,但何苦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质疑的主要是这两年补拍的镜头和最后的解释。老黄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有了很大改善,农村确实在变好,勤劳善良的人确实过着越来越好的生活。我只是如实记录。不信你看好吃懒做的何南,他的生活还是一团糟。再说所谓的强行升华主题,老黄等人生活改善、农村生活好起来的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有目共睹,你说是不是?”
同样的质疑也发生在半年前。今年3月,何苦带着117分钟的短片版走进中国传媒大学。放映和交流结束后,《极地》监制张雅欣教授对何苦说,“我们的学生在这方面非常挑剔,不过现场看来,同学们对你的作品很认可。”
这种认可并非平铺直叙。交流期间同学提出同样的质疑——出于何种原因在结尾新增了棒棒离开自力巷以后的生活?倔强、自尊心强的老甘回到农村,享受低保,村干部上门劝说他搬去敬老院;迟钝木讷的老杭病得厉害,回到农村老家养起蜜蜂,日子清闲,一年能挣两万块;大石家重新蒸蒸日上;老黄一家还清房贷还买了新车;除了依旧指望着靠赌博翻身的何南,片中几位棒棒师傅的生活在离开重庆城区后得到明显改善。
对于90后来说,新增的结尾带着显而易见的主旋律色彩。有人低声讨论,这是不是和導演二十几年军旅生涯中所接受的思想教育有关。其间也夹杂着另一种猜测——大概是为了过审,13集剧版都没这部分。随着电影上映,质疑被迅速放大。
何苦与团队不止一次做过回应。有团队成员表示,大寒过后,一定立春,但这个春来得不够温暖,也不够有理有据,这是重新补充修改的直接原因。另外棒棒师傅的生活是有起色了,但起色从何而来?片子里没有给出交待。
“片子过审非常顺利。当时拿过去,有工作人员说你这部片子早就该拿过来了。”何苦说,过审顺利得让自己吃惊,他原以为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他们不应该被文化生活拒之千里
何苦幼年的梦想是当棒棒,因为棒棒的办公地点在重庆城里。彼时重庆对何苦的意义和今天北京对小镇少年的意义颇为相似。在决定转业去当棒棒前,他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里面提到这样一个童年片段:“重庆应该是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重庆人不应该和我们一样也要撒尿。九岁那年,远房堂弟因治疗皮肤病去了一趟重庆。回来之后病虽未好,但全村的孩子都很崇拜他,因为他是去过重庆的人了。我甚至为有这样一个堂弟而自豪了好一阵子。”
少年何苦不是不知梦想为何物,用他的话说,“不晓得同学们争先恐后要当的科学家是干啥的。”至少家中惟一的课外读物《万县日报》并没有提供过任何相关解释。即便改革开放四十年以后的现在,偏远地区的文化生活依旧贫乏得抬眼就能看到尽头。
“好多纪录片是拍给文化人看的,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有相对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温饱之余能想到去关注别人。”何苦认为,豆瓣网友是这类观众的典型代表,现在的文化产品市场也主要在为这些人服务。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支配下,那些数目更为庞大、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观众很自然地被忽略、遗忘在一旁。
“不是说普通观众没有一颗关心别人生活的心,而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局限,他们的视野只能够到这里,他们能看懂的只有这么多。豆瓣网友给我打多少分我不在意,这些最普通的观众能不能看到、能不能看懂才是我在意的。”2015年3月,与编导詹艳合作剪完剧版第一集时,何苦对詹艳说,“你拿回去给阿姨(詹艳的母亲)看看,如果阿姨觉得好看,还想看,我们就按这个方向往下剪。”
一年多时间,拍摄素材累计超过5个T,何苦先用20天回顾,写成20万字同名纪实文学,再以此为大纲,同詹艳连续工作半年,剪辑成380分钟剧版,切分成13集。按照约定,何苦的第一批审片人是老黄等主要人物和他们的家人。“拍摄之初我承诺了,如果最后作品呈现出来,有不合适不真实的地方,我直接删相应的素材。”
看完13集,他们没有对内容提出异议。令何苦最为感触的是老黄的女儿黄梅,“一边看一边哭,哭到站不起来。问她原因,她说知道爸爸辛苦,但从来不知道爸爸这么辛苦。”何苦又从13集中挑出三集,邀请来第二批审片人——50位棒棒师傅。“一是想知道他们认可不认可我呈现出来的棒棒生活,二是想知道他们能不能看懂,能不能看进去。”第二次“审片会”的效果也喜人,棒棒师傅看得津津有味,何苦的信心加了码。
院线版推出后,宣发方拨给何苦5万块活动经费,带着这笔钱,他开着一辆上年纪的长安车下了乡。“目前走了黔西南地区的20个乡村。条件比较简陋,和农村的坝坝电影一个样子。这会儿刚好是暑假要开学嘛,村里老人小孩都来了。”
何苦带去下乡的不只是电影,还有送给小朋友的文具,送给孤寡老人米面油。有人质疑这和他之前请棒棒师傅团年的做法一样,公益作秀,变相搞宣传。“片子排片率非常低,仅靠院线上映很难让普通观众看到,特别是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何苦继而问道,“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媒体报道总是片面塑造留守儿童如何缺乏关爱,给这些孩子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比起自己,爸爸妈妈更爱钱。但其实不是,他们的父母就和棒棒一样,都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没得选。我希望孩子们看完这部片子能对父母的不容易多一些了解,也不要因为觉得爸爸妈妈爱赚钱不陪在自己身边,就在成长过程中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同时我也希望老人看了能更理解自己的儿女,对外出务工的子女少一些抱怨。这些青年人不是说不想在家,撂下孩子就跑城里去逍遥自在了,是实际生存情况不允许。”
何苦觉得大多数纪录片是在致力于让生活得更好的人去了解生活得不那么好的人,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和讲述,让普通大众彼此之间增进了解、打破隔膜,更勇敢地生活。“他们非常普通,没有多少文化,甚至有的是文盲,但他们不应该被文化生活拒之千里。”
好像撞到了新出路
对比剧版得到的盛赞,院线版豆瓣评分稳定在6.4,出乎何苦和发行方的意料。“发行团队和我参考了13集剧版的评分和其他指标,觉得院线版应该能拿到8分左右。我也不想回应什么,不管是骂我骂片子的声音,还是肯定的声音,只要是善意的,我都接受。这个作品完都完成了,下一个作品注意吸取经验和教训更重要。”
继《最后的棒棒》之后,何苦确实完成了一部尚未和观众见面的纪录片——《我的城管是兄弟》。“拍摄和后期剪辑早就完工了,但照目前(观众对《最后的棒棒》院线版骂声一片)来看,我实在没有勇气把它拿出来。”
话锋随后转向严肃,媒体关于“城管的报道基本都很负面,导致大部分人都觉得城管等于坏人,冷漠得很。但大部分人对真实世界并没有什么了解,偏见就是这么来的。这个社会充满誤解,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只要有误解存在,那我做的事就有价值。”
何苦极度自信,同时对融入主流半信半疑。面对满屏差评,他仍斩钉截铁地说,“我敢叫这个板,全天下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拍得了棒棒题材的纪录片。没有力气就融入不了这个群体,没有才华就驾驭不住细节。我也敢说这是目前为止全中国最好笑的纪录片。虽然讲的是底层人民的生活,但你能看见他们身上的幽默达观,无出其右。”
虽然如坐针毡,他还是想方设法找到差评里四五位专业影评人的联系方式,发出请教的邀请。只不过局面让人有些难为情,回应他的只有一个。何苦有些局促地说,“回应我的这位影评人很真诚,跟他交流我学到很多。”
已经开学,票房要有所起色基本不可能,这部高分背书的纪录片似乎已经走进传播的死胡同。再联系何苦时,他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有四五家中学联系我,希望我把片子带过去给孩子们上开学第一课。我感觉好像撞到了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