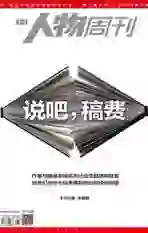萨拉热窝没有枪声
2018-09-25镜子周建平
镜子 周建平
“像是在亚洲!”
公共汽车刚从塞尔维亚南部的塔拉公园驶入波黑境内,各式各样的山就连绵不绝地倾轧过来,有时是平缓的高山草甸,有时则是垂直耸立的悬崖峭壁。天正下雨,窗玻璃上弥漫着一层浅浅的水汽。我望向窗外,看见零零散散的牛羊正在山谷间吃草,一些安在山头的房屋正摇摇欲坠。和西欧那种悠长、舒缓、讲究中产阶级情调的乡村完全不同,波黑的山水充满了一种粗粝、狂野的质感,甚至还有一点和生存搏斗的意味。所以在去往首都萨拉热窝的路上,我相当恍惚:这怎么可能是在欧洲呢?
在很多老派的欧美人眼中,遥远的巴尔干半岛确实就是神秘的东方了。1908年曾游历过这一地区的女作家弗兰西丝·金斯利·哈钦森在听到“达尔马提亚”(现位于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相邻的克罗地亚)就曾惊呼“那地方简直就是另一个星球”!她在名为《1908慢行巴尔干》的书里这样写道:“名字里透着一股奇怪的魔力!听着这么遥远,像是在亚洲!我兴奋地想象着旅途上的景象,高山要塞、天然港口、奇形怪状的建筑还有原始人!”
现在信息发达、交通便利,不会有人再说想看到“奇形怪状的建筑还有原始人”这样的幼稚话,但她却真切表达出了110年前巴尔干半岛在欧洲的边缘感。当然很快,这种边缘感就随着一次刺杀彻底消失了。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暗杀了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霍泰克。一个月后,以此次暗杀事件为导火索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后100年,萨拉热窝经过漫长的南斯拉夫时期和惨烈的波黑战争,彻底变成了一座不太轻松的城市。
地图上的一条虚线
萨拉热窝四面环山,橙黄色的屋顶像倾泻而下的瀑布,一直从半山腰绵延到山脚。如果乘客没有特地要求,贝尔格莱德开来的汽车一般会直接穿过城市,到达距离市中心八公里的汽车东站。除了站前有一个简陋的报刊亭,这里破败得就像人迹罕至的郊区。马路边的花坛里是干燥的泥土,四周的房屋是灰扑扑的、苏联式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离线的谷歌地图显示,这里属于波黑塞族共和国——往北100米,地图上有一条虚线将波黑联邦和波黑共和国分割開。我内心雀跃,以为马上要经历穿越铁丝网一类的刺激运动了,可没料到当我站在那条虚线上时,那里却只有普通的马路、普通的树。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个国名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这个国家是由这两部分构成的。但实际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只是地理概念,真实的波黑被分成了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政治实体。前者控制波黑51%的领土,首都为萨拉热窝,后者控制余下的49%,法定首都是东萨拉热窝,实际首都则是西北部弗尓巴斯河左岸的巴尼亚卢卡。这是《代顿和平协议》的结果——1995年11月21日,时任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草签了波黑和平协议,12月14日,这份协议在巴黎正式生效。在这之前,波黑经历了二战结束后欧洲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萨拉热窝则经历了一场现代战争史上时间最长的城市包围战。四年时间里,将近20万人死亡,200万人四处流离。
就在离那条虚线不远处,我发现了一个朴素的公交车站,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停着两三辆大铁皮盒子一般的汽车。我早就做好了当地人听不懂英语的准备,指着市中心最有名的教堂图片刚想开口,司机就用流利的英语给了我肯定的回答,并说到拉丁桥那站下车后,再走几百米就能到目的地。波黑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消费却并不便宜,公交车单程的价格就得1.8马克(合人民币7.2元)。一路上开得七拐八拐,站与站之间间隔很短,来往客流量却不小。
大概40分钟后,我到达了市中心的拉丁桥。桥这头是一个小型公园,那边则是人头攒动的古城。绿色的米里亚茨河穿行而过,初夏的岸边尽是葱茏的树和掩映其间的白色野花。游客三三两两在桥上拍照,也有不少人驻足在桥边的1978-1918萨拉热窝博物馆门口。100年前发生在这个街角的一次暗杀改变了20世纪的走向,100年后这里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景点。
“为什么会如此钟情于萨拉热窝呢?”在塞尔维亚南部旅行时,我曾问一个波兰青年。他来自另一座历史名城克拉科夫,每年夏天都会到萨拉热窝住几天。“萨拉热窝太多姿多彩了!它的城市形态是杂糅的、文化是交织的,不像很多欧洲城市充满了一种稳定的、安逸的无聊。”他回答。
萨拉热窝确实是躁动的。所在地区一直被称为“欧洲火药桶”;老城区充满古代波斯风情,市场、街道都始建于十五六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时期,初来者看到满街穆斯林很容易怀疑自己穿越到了伊朗;而就在离信徒众多的格兹·胡色雷·贝格清真寺大约200米的新城区,又同时矗立着波黑最大的天主教堂——圣心主教座堂。
“你能在萨拉热窝看到不同的宗教建筑、不同的信仰,也能看到纯粹的山城风光……总之,这是一个微缩版的世界。”我刚到古城中心的一家青旅办好入住,前台人员就拿出城市地图介绍。她热情地问:“你想看什么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这座城市的渊源,已经因年代久远而变成尽人皆知但也仅限于此的历史掌故,因此我更感兴趣的是20年前的波黑内战。战争和萨拉热窝的记忆相伴相生,改变了它的城市格局、人口分布、历史情境以及我们提到它时的种种语态,当然,最直接的是,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很多人没有再长大
很多人死于1992年至1996年。
萨拉热窝古城周围的山坡上,分散着大大小小的墓园。每一个墓碑都很相似,白色,刻着名字和生卒年月。墓园没有明确的入口和出口,也不像东方国家那么讲究风水、讲究避讳。它们就镶嵌在依山而建的居民区之间,有些甚至就在马路旁的花坛之间。
有一天雨过天晴,我从古城对面的山上望过去,那些橘黄色屋顶中间或出现的白色,就像一片尚未埋葬的骸骨;而当我走近那堆墓碑,那重重叠叠的影子又像一些无从辨别的生命。当天不是什么特殊节日,依然有很多穆斯林在祭拜,有的拿着鲜花,有的拿着水果。
自从1980年代南斯拉夫各民族矛盾激化以来,独立就成为了主题。1991年,波黑境内的三个主要民族穆斯林、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在是否独立、独立后是建立中央集权国家还是松散的联邦制国家等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1992年3月,波黑战争爆发。4月5日,反对独立的塞尔维亚族共和国军队和南斯拉夫人民军包围了萨拉热窝。此后一直到1996年2月29日,这座城市的居民就一直和物资匮乏、饥饿、不长眼睛的子弹相搏斗。
“我们从啤酒厂接水,一路都是无止尽的炮弹、射击……接着就是受伤和死亡的消息……”
“漫长的、寒冷的夜,然后是更寒冷的夜。就好像身处一个失落的世界,时间完全停止了。我希望这种日子永不再来。”
“当我闭上眼睛回溯记忆,往事就像电影胶片一样展开……枪炮的气息、孤独、寒冷、饥馑……战争是魔鬼!”
“战争中是没有童年的。它消失在你辨别炮弹和步枪口径的时候。”
我在萨拉热窝战争童年博物馆(War Childhood Museum)的一本书上看到了这些句子。它们都是战争亲历者的口述,内战发生时,他们大多才六七岁。
这个博物馆位于古城北部,在中文版本的旅游网站上几乎无迹可寻,展览形式也更接近个体故事的诉说——每一个展出的玻璃盒子里都放着一件我们如今看来十分平常的物品,有时候是一本笔记本,有时候是一只玩具熊,有时候是被压扁的牛奶盒,有时候甚至只是一张糖纸。每件物品外的白色纸板上,当年的战争儿童们都简短描述着自己和展出物品之间的故事,并且标注了姓名和出生时间。
创建者Jasminko Halilovic介绍,他起先的想法是做一本书,向成长于波黑内战的年轻人征集160个战争记忆故事。而在编辑过程中,他意识到这种经验分享的重要性,于是就启动了博物馆筹建计划。据他估计,战争中有七万未成年人生活在萨拉热窝,其中有1000人通过这项计划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在他们的叙述中,“食物”“水”“饥饿”“绝望”是最常见的词,“希望”则经常是跟在“我”之后的假设。故事中经常有人死亡或者失踪,因此穿梭在一件吊着的灰色儿童大衣、一个陈旧皮箱和一只黄色小熊之间时,身处和平年代的人很容易被巨大的情感力量淹没。
“在战争初期、手榴弹刚刚开始在城里乱飞、我们开始跑到地下室里时,我的妹妹妮娜(音译)开始写战爭日记。她想要一本带锁的真正的日记,但书店都关门了,父母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本子。所以一直到1995年,妈妈从工作的地方给她带回一本笔记本,她才真的开始写。她这样写道:‘太糟糕了!你们为什么要扼杀我们的灵魂?有只为爱而存在的事物吗?为和平,为游戏,为快乐……但是,我不会诅咒你们,因为你们也是那些热爱和平和快乐的孩子的父亲。1995年8月27日,在参加完一次舞蹈比赛后的隔天,妮娜受伤。不久后,她在医院去世,年仅12岁。她是萨拉热窝围城时最后那批被枪炮杀死的小孩。”
“这个我决定捐给博物馆的芭比娃娃,是我拥有的唯一一个战争纪念品。战争发生时我太小了,记不得很多,但关于这个娃娃的事一直被家人提及。我三岁时,我妈妈决定抱着我穿过希望隧道从外婆所在的萨拉热窝市区回到我们居住的哈拉什尼察(萨拉热窝郊区,穆斯林聚居地)。那是一个寒冷的下雪的冬天,但我妈妈就穿着非常单薄的鞋子。当我们到达潮湿阴暗的希望隧道时,一个士兵给了她一件非常珍贵的东西——一双防水的靴子!而当我们离开希望隧道时,我瞥见一个男人手里正抱着这芭比娃娃,我一下子就哭了,我太想要它了。妈妈太希望我开心了,就用她脚上的新靴子换了这芭比娃娃。我们回到哈拉什尼察后,妈妈就把我留在家里,独自去找柴火和水了。我利用这个空隙,剪掉了娃娃的长发,这让妈妈非常失望和伤心。”
……
这些故事都不复杂,有的残酷,有的温情,有的只是鸡毛蒜皮的琐碎叙述,有的甚至让人难以理解。只是当一场大规模战争被具化为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它就好像保存了不可磨灭的情感证据。在进入这个封闭的、安静的故事盒子之前,工作人员曾有个例行公事的询问:“你是如何知道我们博物馆的呢?你为什么想来呢?”
“我和这些孩子是同龄人,但波黑战争离中国太远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工作人员笑着点点头说:“我也是同龄人。”
那天从博物馆出来,我又继续往山上走。傍晚的黄堡是观看萨拉热窝最好的地方,云层有些厚,阳光时有时无。我坐下点了一杯波斯尼亚咖啡。因为咖啡太苦,店家搭配了一块白色的、指甲盖大小的方糖。我问他:“这个方糖,是在喝之前还是之后吃呢?”
“As you want(你想怎样就怎样)。”他说。
“共离开,尘俗万千,荒谬立场”
第二天中午,我就去了希望隧道。那里距离市区10公里,是目前萨拉热窝最热门的旅游景点。因为交通不便,大多数人会花费30马克(约合人民币120元)在市区参加一个半日游的旅行团。但我不想把这种探访变成一种纯粹的游览,所以执拗地坐了50分钟公共汽车,然后顶着下午1点火热的太阳在郊区走了2.5公里。
途中,汽车经过了一个现在看来有些破败的体育场。通过谷歌地图得知,这里就是1984年冬奥会的举办地。在关于萨拉热窝的旅游介绍中,这个景点都在其列。那是这座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人口增长,工业繁荣。到1991年战争前夕,有超过50万居民生活在这里——这个数字在1995年减少了36%。一部分人死在了萨拉热窝,一部分人则是穿过希望隧道逃离了被包围的城市——逃离的结局有些也并不好。
那些人在逃离时,是以为围城外面就是自由,还是只想着拼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概率呢?
我走在并不宽阔的、没有树荫的乡间马路上,周围连一辆车都没有。我想起了1994年由美国、加拿大和德国共同制作的纪录片《萨拉热窝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当时,两个来自不同族裔但青梅竹马的恋人相约在1993年5月19日逃离萨拉热窝,战争双方也在这一天协议停火。但未料,刚到市中心的Vrbanja桥时,两人就中弹身亡了。当时一位美国记者正在附近,拍下了二人倒下的瞬间。后来香港歌手郑秀文还唱过一首同名歌曲:“恋情从无要分宗教,从无惧枪炮,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恋。是对青春好情人,某天相依倒地上,共离开,尘俗万千,荒谬立场。”
事实上,从1800年前匈奴西进、欧洲民族大遷移,萨拉热窝就开始了各民族混居的历史。尤其是14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塞尔维亚地区,并对当地人强制伊斯兰化以来,这里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和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身处同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认同和对国家前途的考量。事后看,很难说这场战争在当时必然发生,也很难执果索因地说独立一定具有正义性。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在内战中围城和屠杀一定是不人道的。
2003年1月,塞族共和国军第一司令官斯坦尼斯拉夫·加利奇因为对萨拉热窝的包围和恐怖袭击,被前南斯拉夫国际战犯法庭判处反人道罪,并处无期徒刑。四年以后,他的接替者米洛舍维奇则因第二次马尔加雷虐杀和包围萨拉热窝被判处33年有期徒刑。
在当时这座如同地狱的城市,希望隧道是唯一能和外界接触的渠道。这里和机场相连,食物、军用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都通过它运输。隧道全长800米,现在对游客开放25米。景点另外附有一个小型博物馆和几间10平方米的影像室,除了一两个私人导游正在介绍历史,其余人都保持着相当一致的缄默。博物馆一楼最深的一个房间里,挂着士兵们的军服、箱子和几支仿制的步枪。房屋低矮,光线暗淡,衣物上又落了灰,如果不是另一个游客突然进来,我简直怀疑飘荡进了另一个时空——这种感觉在几分钟之后再次来临,就在我钻进那并不漫长也不黑暗的一小节希望隧道里时。我听到不远处有飞机起落的轰鸣声,我想如果回到二十多年前的话,这声音到底意味着轰炸还是新鲜的物资呢?
我钻回地面,机翼正好掠过头顶。夕阳正在远山铺陈开来,照在隧道旁边的铁丝网和绿色的田野上。我在影音室旁边的自动贩卖机买了一瓶饮料,坐在院子的木椅上休息时,震动和沮丧同时控制了我。在萨拉热窝住几天,根本不可能了解这个地方的全貌,就连这种野心本身都显得可笑;可萨拉热窝又好像具有一种历史无处不在的力量,让你时时刻刻体会着它生死存亡时的悲喜。它保存了很多细节和证据,可这不朽本身就是不幸的。
我看着络绎不绝前来参观的游客和他们钻出地道时释然的表情,突然想起了战争童年博物馆书中一个叫《我的姐姐正在画迪士尼英雄》的故事,作者是出生于1983年的Selma。
“我的姐姐艾达(音译)是在战争一开始就画了这些画的。我们住在市医院附近,周围是炮弹经常袭击的目标。因为外出很危险,所以我们经常在屋里或者地下室里玩。她手上经常捧着书和一些画笔。她喜欢画画,也很有天赋。要知道在油灯下诞生真正伟大的作品是非常罕见的!有时候她会给朋友们写信,但那更像是一种日记。在她写下这些信并过完17岁生日不久,一个相对和平的夜晚,我们的门被敲开了。我们当时独自在家,父亲在和人下棋,母亲在外工作。是我姐姐的一个朋友。一天之前她们吵架了,她是想来和好的。我姐姐站在门外空地上,我在厨房里,很快我就会加入她们。突然之间,震天的爆炸声让整个屋子剧烈地摇晃起来,一切都被蒙上了灰尘。我听到了吼叫,那是我父亲的声音。我坐在地上根本没法移动。后来我父亲疯了一样冲进来,抓起毯子就跑。我再也没有见过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