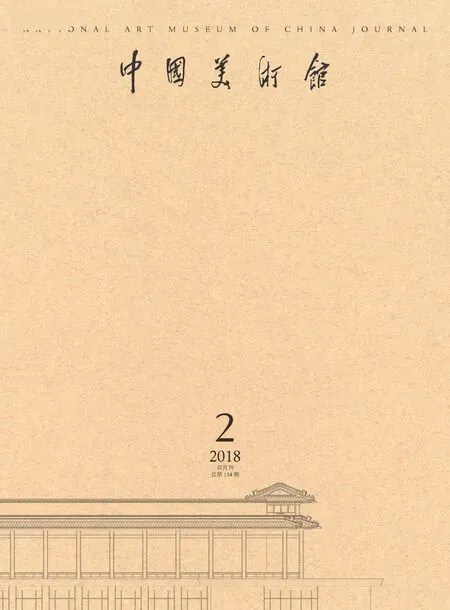论袁江绘画中的西方因素
2018-09-22王汉
王 汉
本文在清初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背景下来讨论袁江绘画的西方因素。文章考察了袁江绘画中向远处消失的大路、有明暗的房屋、乌云以及向后收拢的楼阁侧面线条这四种对象,并将这四个方面与大致同时期的西方绘画作比较,指出袁江绘画曾受到西画的影响,但袁江对西画的吸收是“润物细无声”式的。
一、引言
公元17世纪和18世纪,西方基督教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也带来了许多绘画作品和绘画技巧,形成了中国美术历史上又一波的中西文化交流之潮。在这波文化交流之潮下,许多西方绘画的因素流入中国。
袁江的山水画以工细严谨著称,至今仍为人所称道。“袁江,字文涛,江都人,善山水、楼阁,中年得无名氏所临古人画稿,遂大进。宪庙召入祗候。”这是史书记载中年代较早、比较详备的一种,见于张庚的《国朝画征续录》,后来的记载均承此说,大同小异。我们今天赞叹于袁江精湛的画艺,按张庚的说法因得古人之法,但按当时的社会情境来看,袁江绘画应该与西洋画有一定的关系。换句话说,袁江绘画风格的形成不仅得益于中国古代传统,还得益于一些西洋画的养分滋润。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1916年即指出:“袁派参考西洋画的写生手法,在山水画中形成了新的写实画派。”近年,王春立在《永远开放的中国美术》一文亦提到袁江之画受西画影响。可惜的是他们的叙述极略,不知据何以立论,直观感觉为多。因此本文试用形式分析的方法,将袁江山水与西洋绘画相比较,找出其中的相似之处,并将这种相似之处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空间中去考察。由于有关袁江文献资料非常稀少,我们无法从文字材料上对袁江绘画受西洋画法影响这一观点加以明确阐述,因此我们只能说袁江绘画中具有西洋绘画的因素。
二、袁江山水画中的西画因素
(一)向远处消失的大路
作于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的《东园图》卷(见图1),现藏上海博物馆。图卷长370.8厘米,高59.8厘米,绢本设色。这是一幅极其写实的画卷。此写实有两层含义:其一,画面上的景物形象、空间刻画逼真,使人身临其境。其二,对照张云章的《扬州东园记》,画中园林建筑布景与实际几无差异。卞孝萱在《袁江〈东园图〉考》一文中所引的诗文是为了进一步说,文献上所记载的清扬州府江都县东郊甪里村乔氏东园,与袁江所绘《东园图》,景物完全相同。再将袁图与《重修扬州府志》卷首《舆图》《江都甘泉四境图》对照一下,还可以看出,袁江《东园图》上环绕的流水,就是《江都四境图》上回环曲折的河渠,袁图上耸立的两塔,就是《江都四境图》上的文峰塔和三汊河塔。地理环境也是完全符合的。
这种高度的写实性本身就异于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理念。明初王履《华山图》提出“庶免马首之络”,指出了以往中国山水画的一个缺限——中国山水画在五代宋初尽管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但很少有对某一特定山水进行写实性描写的作品。王履本人努力践行自己的观念,写出了形象上肖似的华山,然而他却并没有因此受到后世画家们的重视。
画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画卷右段的河边的一条大路。从画面的下方开始到画面上方结束,划出一个大大的“3”字形,几乎贯穿整个上下画幅。大路“自近而远,由大及小”,渐渐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具有强烈的纵深感以及真实存在于地平面上的空间延续感。翻检以往中国山水画,除去晚明以来,这样的“路”是从未见过的。
画面纵深感大致是通过这样几个方法形成的:1.大路自身的造型。大路前宽后窄,到了远处路宽急剧变小;同时“3”字形路的两个弧,下方的弧跨度极大,弧度极小,而上方的弧跨度极小,弧度极大,对比强烈;大路坡石的大小和繁简程度也对前后空间距离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2.大路上的人马车。在大路上出现三组人车马,近景、中景、远景中各一组,各组大小呈现为前大后小,变化明显,这样前后变化明显的行旅之人在宋元中国画中很难见到。3.房屋树木。中景房屋树木与远景房屋树木的大小对比强烈,形成前后的空间感,特别是远景树木,从肉眼可辨的有形树木至莫可分辨的墨点,营造出特别深远的空间。这种方法在宋元传统的中国画中经常见到,然而对比如此鲜明且创造出极深远的空间形式却没有。4.田畦。大路左侧被分割的块块田畦随着路的伸展近大而远小,也对大路的空间纵深感的营造起着辅助作用。田畦的母题在中国画比较常见,然而明中期的传统与此不同。
这些方法在焦秉贞的《耕织图》(见图18)中有比较明显的应用痕迹。图中的田间小路,虽然与前述“3”字有一点儿差距,但是其空间纵深感极强,与袁江《东园图》效果非常相似。前景树木与远景树木或农具等物体大小的强烈对比加深了这种纵深感。最重要的是两幅画都出现了对田畦的描述,焦秉贞的田畦,其大小在空间中依次变小,直至远方,袁江与焦氏的处理方式类似。应该说袁江技法中对透视法的理解不像焦氏那样深,也没有焦氏那样严谨。然而有差别的是《耕织图》的视点低,而《东园图》的视点高。在这一点上,《东园图》更接近西方年代略早的《法兰克堡景观》图。
苏立文在《明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的反应》一文指出,1610年利玛窦去世以前,南京与南昌的传教士们向中国参观者展示了他们图书馆中的许多优秀图书。例如,纳达尔关于基督生平的《福音历史图集》(安特卫普,1593年),上边的插图是根据威廉克斯与德·澳斯作品复制的,利氏写道,由于这部书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他觉得有必要为北京传教团再要一部。他给著名的出版家与印刷家程大约4幅版画,程大约将这些画编入他的设计概述书中,用以装饰造型墨块。勿庸置疑,吸引程氏的是新颖的艺术形式,它们远胜于适合主题的需要。他还将奥特利乌斯十分精致的对褶地图集《世界舆图集》的一个复本以及布朗与霍根堡的《世界城镇图集》的最初几卷带到北京,当他收到普朗坦的多卷本《皇家圣经》(1568—1572)已是1604年了。在传教团图书馆至少有5种关于欧洲建筑学方面的图书,包括两本维特鲁威与一本帕拉第奥的书,中国的学者与画家们在17世纪初的20年里可能看到过。
高居翰在《气势撼人—— 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一书中将张宏、吴彬的绘画与《世界城镇图集》(在高氏的书中此书名《全球城色》)中的版画相互对照,其中有许多惊人的相似点,高居翰认为晚明绘画中有许多西方绘画的因素。

图2 袁江 《东园图》 局部

图3 《法兰克堡景观》 铜版画

图4 《法兰克堡景观》 局部

图5 《堪本西斯城景观》 铜版画
我们循着高居翰的目光来审视袁江与《世界城镇图集》中的版画,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首先看《法兰克堡景观》(图3、图4),画中的大河与《东园图》(图2)中路的形状有惊人的相似性,都呈“3”字形,在画面中的位置相似,制造的景深错觉相似,利用河里(袁江画中则是路)中景与远景中物体的大小对比暗示了空间伸展的方法相似。
再来比较《堪本西斯城景观》(图5)与《东园图》(图1、图2),渐远渐窄的桥梁与随之而变小的人马车,制造空间错觉的方法与《东园图》无异。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堪本西斯城景观》画中远处地平线上的教堂尖塔堪比于《东园图》远处突出于地平线上的寺塔。
所不同的是袁江在远景处理上更多运用中国的方法,用云雾来虚化远景,使得地平线附近的景物看上去若有若无,不像西方画家那样明晰。

图6 《landshut城景观》 铜版画
附带说明的是,袁江的绘画,特别是在他的后期绘画中,有一个重要的要素——连续一贯的视平线的存在,这个特征在《东园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东园图》长370.8厘米,高59.8厘米,在这样长卷式的绘画中呈现左右一贯连续的地平线,这在传统山水画中,难得一见。
总体而言,袁江《东园图》的空间纵深感与两幅西方版画是非常类似的,但却在中国传统绘画中难觅其踪——除了同样受西方绘画影响的晚明部分画家。
(二)有明暗的房屋
西方绘画相对于中国绘画来说,一个最主要的区别性特征是用明暗来造型。利玛窦指出,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吾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
此处说的是肖像,在山水画中,山石也用明暗来表现立体感,表现受光与背光,然而这些明暗的施用,有时只是区别前后的石块。在建筑绘画中,中国的传统绘画基本不施明暗,更多是使用线条来表明建筑的结构和空间。
在袁江的绘画中出现几处用明暗来表现的建筑,而且明暗的施用均按建筑的转折结构。例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山水楼阁图》之六《山庄秋稔》(图7)。
《山水楼阁图》,十二条屏,绢本设色,每幅高188.7厘米,宽46.4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第6幅为《山庄秋稔》,图中部的房屋左侧墙壁暗而右侧墙壁明,明暗分别处正是左右墙壁的转折线。这样的明暗布局,使得这座房屋极具立体感和光影感。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在《阿房宫图》(图8)中。阿房宫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条屏,绢本,设色,纵193.5厘米,横658厘米。其中有一个主要楼阁台基明显与传统画法不同。台基洁白无瑕,然而左侧台基则显阴暗,且阴暗转折处恰是正侧面的结构转折线,不知袁江在此处为何这样处理转折线左右的台基,其中有一点不可忽视——西方绘画的影响。

图7 袁江 《山水楼阁图》局部 中国画188.7cm×46.4cm 1723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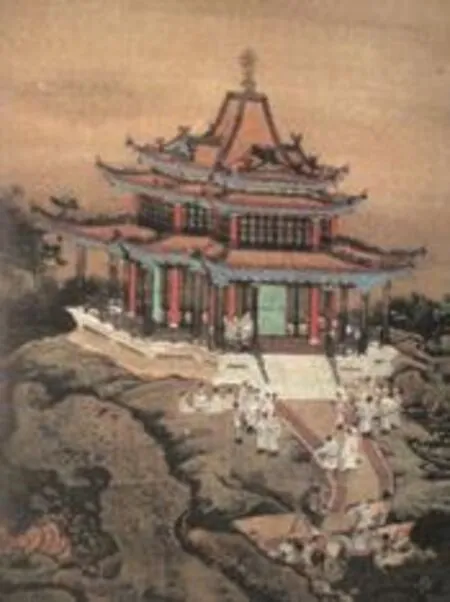
图8 袁江 《阿房宫图》 中国画193.5cm×65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9 袁江 《山水人物图》局部 中国画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0 袁江 《关山夜月图》局部 中国画126.5cm×160.4cm 1720 上海博物馆藏
其他如:中国国家博物院藏《山水人物图》(图9)其中一幅,右下门边墙的转折非常明显,正面白,侧面则略施阴影,立体感强。上海博物馆藏《关山夜月图》中关隘上的房屋大约也是如此(图10)。需要多提一点儿的是,关隘左上与右下的山石有来自右上方的光照射的感觉,山石的右上方有些被提亮的感觉。
具有明暗法西洋绘画传入较早,1519年,利玛窦来华携来宗教题材的铜版画,即“宝象图”“圣母怀抱圣婴”等图4幅,赠与当时的制墨大师程大约。后来程氏将四幅铜版画以木版摹刻收入《程氏墨苑》,其雕刻技法已能表现出富有明暗凹凸、形象生动逼真的西洋铜版画风格。
1713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北京受康熙指派主持铜版雕版印刷《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图11),这是一部具有明暗和西方透视法的作品。在《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的第1幅《西岭晨霞》中,水面上的建筑基座,有明显的明暗效果,有明显的明暗交界,左侧的台基暗,而右侧的台基更亮一些。图9是其中的《延薰山馆》图。房屋使用明暗法绘制,效果特别明显,光感极强。

图11 马国贤(意大利) 《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之二》 铜版画
袁江是否曾经看到过《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现在没有非常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是袁江是进入过宫廷的,这在张庚的《国朝画征续录》中有明确记载。因此袁江有很大可能接触到这批画作。
(三)山水画中的乌云
在袁江的《春雷起蛰图》(图12)、《春雷起蛰龙图》(图14)和《山水楼阁图》十二屏之二《山雨欲来风满楼》(图13)中,袁江都非常写实地描绘了远方空中的乌云。
就我个人的视野来看,这样的母题在以前的山水画中很少见过。传统中的云基本为白云,多用墨色烘染或用线勾勒。在描绘“风雨如晦”主题的山水画中,清之前的画家多用墨色烘染出风雨中昏暗的氛围,再加上斜侧的线来表现风雨的动感。袁江也曾在几个图画中展示这样的技法(见图15《重阳风雨图》)。

图12 袁江 《春雷起蛰图》中国画 153cm×51cm天津美术学院藏

图13 袁江 《山水楼阁图十二屏之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画 188.7cm×46.4cm 1723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14 袁江 《春雷起蛰龙图》中国画 134cm×50cm 1723中国美术馆藏

图15 袁江 《重阳风雨图》中国画 63cm×28cm中国美术馆藏

图16 《春雷起蛰龙图》局部与《landshut城景观》图对比

图17 《沉香亭图》局部
如果看看明末西方传教士带来的铜版画——《landshut城景观》,图中上方云层密布,作者应该描绘的是白云,然而由于其使用了明暗法来描绘云层的立体感,云层下方色彩阴暗。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乌云。当然袁江更有可能接触的是上面提到的马国贤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还是刚才那幅《西岭晨霞》图中,画面左上方飘着白云,当然被读解为乌云亦无不可。袁江可能见过这幅画,激发了他的灵感,在山水画中去表现乌云翻滚的场景。
另外,对比《春雷起蛰龙图》,乌云的大体形态与《landshut城景观》 (图16)相似——呈大开口的“U”形,云层下方明亮的天空。甚至整个远景布置似乎都来自该铜版画——左边的山坡,坡后的房屋和高耸的尖塔,向远处伸展的地面,最远处的山峰。
(四)向后收拢的楼阁侧面线条
大约在康熙庚子年(公元1720年)后,袁江绘画中的楼阁出现一个并不显著的变化——建筑侧面的结构线呈向后方收拢的趋势。在我所收集到的有具体纪年在康熙庚子后且有方形楼阁的绘画中几乎都有此特征。参见图17《沉香亭图》分析图。A4—A6线条呈向右上方聚合之势,但A1-A4间依然相互平行,A6与A7两线向屋前方收拢,与透视法恰恰相反。这是袁江大多数有透视现象楼阁的特征。
尽管这种前大后小的收缩画法在唐代的墓室壁画就已经出现,在经过宋元的继承和发展后,到明代很少见到这样的处理方式。例如,史载袁江早年学仇英,仇英的很多界画作品以及更加大众通俗的书本插图版画中,许多建筑侧面的结构线都是平行的。是什么原因促使袁江对建筑侧面的线条做出这样的处理?此处当然会有两种解释,一是受传统影响,历史文献记载中的袁江“中年得无名氏所临古人画稿,遂大进”。另一个解释则是袁江很可能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或启发。高居翰和苏立文已经证实晚明绘画是受到了西方绘画的影响。到了清初,这样的影响有更多的例证。
焦秉贞,山东济宁人,康熙时官钦天监五官正。善绘事,祗候内廷。所画花卉精妙绝伦,其山水、人物、楼观之位置,自近而远,自大而小,不爽毫发,系采西洋画法。“其位置之自近而远,由大及小,不爽毫毛,盖西洋法也”,康熙中祗候内廷。焦秉贞奉诏绘画制《耕织图》46幅,初印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这是宫廷版画中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本子。自康熙三十五年本后,《耕织图》出现了多种版本,本刻本、绘本、石刻本、墨本、石印本均行于世。在《耕织图》中(图18),房屋的侧面线条明显地向地平线消失,造成比较强烈的空间感和真实感。嘉庆《扬州府志》载: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圣祖仁皇帝巡游江南,过扬州,御赐《耕织图》一部。”可见其时在扬州应该可以见到《耕织图》。
马国贤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也是一个西方透视法的学习范本,铜版画中很多建筑,都采用了西方透视法。
年希尧分别在公元1729年和1735年两次出版《视学》,图解说明西方透视法。他在1735年的序中说:“予究心于此者三十年矣。”这说明,大约在1705年,他就已经开始这方面学问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说,在1705年左右,有关西洋透视的方法已经在社会上传播,并引起年希尧的关注。

图18 焦秉贞绘,朱圭刻 《耕织图》 木刻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
除此而外,上文所引苏立文的论文中提到:“在传教团图书馆至少有五种关于欧洲建筑学方面的图书,包括两本维特鲁威与一本帕拉第奥的书,中国的学者与画家们在17世纪初的二十年里可能看到过。”
三、结论
我们通过上面四个因素来推测袁江的画作应该受到西洋画法的影响。1710年的《东园图》显示,袁江已经接触并运用西洋画法,但是他在楼阁描绘法上依然沿袭过去形成的习惯。利用明暗制造的光影效果可能曾经引起袁江的兴趣,他将这种方法应用在部分建筑的绘画中。在山水画的天空中描绘乌云似乎是袁江的独创,但是这一创造灵感应该来自于西方绘画,特别是各种版画中对天空云彩的处理。大约在1720年左右,袁江画楼阁时故意将楼阁檐口线与台基线向后收拢,不再如前面所绘的那样平行,因此我们推测袁江此时决定在楼阁画中加入一些透视法的因素,来改进他的楼阁画。
当然,袁江在态度上是审慎且稳健的,并没有过多地或过明显地采用西洋技法,而是润物细无声地让西洋技法融入其原本的传统技法之中,保持其前后风格的大致统一。这种学习和应用外来技术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