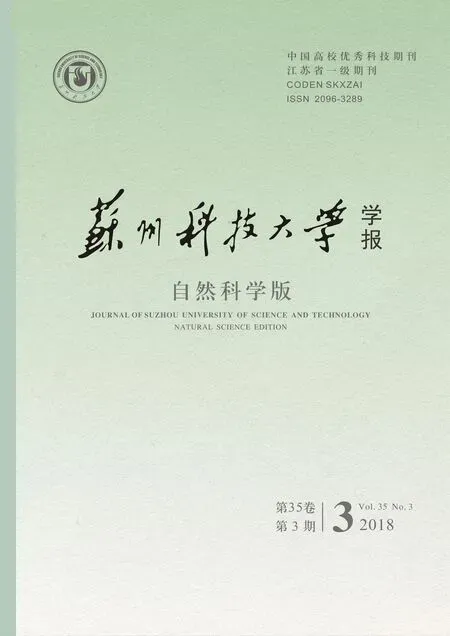基于地域性维度的苏州生态城市建设策略
2018-09-20伍燕南
伍燕南,王 跃
(苏州科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随着气候变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及城市自身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等问题的日趋加重,生态城市作为缓解和破除城市化发展中生态危机的重要对策[1],是未来城市建设的方向,这已成为当前的普遍共识。我国自提出 “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以来,已经有超过90%的地级市将“低碳生态城市”作为建设目标,跨越省、城镇群、城市、社区等不同空间层级的各类生态示范区实践也不断加强[2]。然而,由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生态城市的建设常留于表面形式,表现为对生态城市量化指标的追求,而缺乏对生态城市质的精心设计,由此造成生态城市数据生态化,实际不生态或不完全生态,生态面貌相似,缺乏特色等问题,而这种“不生态”、“无特色”将成为未来城市持续发展的软肋。因此,必须因地制宜,构建富有地域特色的生态城市,以提升城市的品质,增强城市的竞争力。
1 苏州生态城市建设的地域性优势
1.1 优越的自然生态本底
1.1.1 气候生物资源
苏州地处中亚热带北缘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均温15.7℃,1月均温2.5℃,7月均温28℃,全年日照时数1 800 h。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1 100 mm。良好的气候环境为动植物的生存提供了基础,据不完全统计,苏州中心城区约有植物778种,隶属于145科466属,主要有藻类和苔藓植物等低等植物,以及包括被子植物、裸子植物、蕨类植物在内的高等植物[3],其中本地植物616种;动物主要有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等,其中留居、旅经或在苏州地区进行繁殖的鸟类有173种,约占全国鸟类的14.6%。各类林草地、农田郁郁葱葱,并建有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穹窿山自然保护区、七子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森林保护区,为苏州生态城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基础条件。
1.1.2 山水资源
苏州市区地势低平,平均海拔高度3~4 m,但在其中心城区西部与太湖之间却串珠状地分布着一系列低山丘陵,大阳山、天平山、灵岩山、邓尉山、渔洋山、穹隆山、凤凰山、七子山、楞枷山等高耸逶迤,宛如一条绿色项链,狮山、何山、天池山、旺山等则低缓俏丽,宛如一个个翡翠珍珠,共同装点着坦荡的平原。而 “缘水而起,因水而兴”的苏州,水更是自不待言,西依太湖,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护城河环绕古城,古城内“一环三纵三横”的河道骨架及众多支流纵横交错,河网密度高达2.45 km/km2,被誉为“水城”,古城周边则围绕着阳澄湖、金鸡湖、独墅湖、石湖等湖泊(如图1所示)。在城市范围内如此密集地分布着山水资源是不可多得的,也是苏州最具特色的自然生态优势。

图1 苏州自然生态本底图
1.2 深厚的人文生态遗存
1.2.1 源于自然的城市空间格局
苏州城被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称赞为“鬼斧神工”,建城伊始即遵循着“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理念,从选址、城市格局到道路、建筑,无不体现着自然的影响力,最终打造出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城址未移、自南宋以来城市布局未大变、双棋盘格局和“小桥·流水·人家”风貌沿袭至今的历史文化名城 ,环境优美,尺度宜人,可谓“设计结合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典范。
1.2.2 高于自然的园林文化
从春秋时期的“姑苏台”到明、清时期的私家园林,苏州造园艺术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园林艺术的代表,利用山水、生物等自然元素构筑良性的人居环境,为当今留下了丰富的遗存,如今遍布苏城的80多个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园林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着这种“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思想,并成为改善城市生态的重要载体。
同时,这种造园思想也渗入到现代城市建设中,叠山理水、苏式盆景等园林技法外延至城市绿化、水系的打造上,至2017年,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已达37.46%,绿化覆盖率42.2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52 m2,整个苏州已然成为一个大型的园林,正可谓“我居城市中,疑身在园林”,园林艺术的高度发展大大提高了苏州城的生态美学水平。
2 苏州生态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
2.1 城市生态基底破碎
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州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对土地的需求急剧增加,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剧烈,大量水体、林地及农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如图2所示),原生态基底变得较为破碎,据测算,苏州生境破碎度指数年增加达16.2%[4],以至于当前虽有一定量的生态用地,但其生态效益则下降较大。

图2 苏州市城市建设用地变化
2.2 城市生态空间质量退化
在山水、林地遭吞食、侵占的同时,其质量也在不断退化。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监管的不到位,城市生产与生活污水大量排放、垃圾沿河湖堆置,致使水体污染,水质下降,相关研究表明,苏州大部分湿地景观健康状况一般,特别是金鸡湖、尹山湖等,靠近开发强度较高的城区中心,退化较严重[5],而大阳山、凤凰山、城郊农田等也在早期的开山取石、毁林开地及现代旅游、房地产开发中遭受很大破坏,山体破碎,林田毁坏,虽然当前在不断加大城市绿地的建设,然而,这种人工化的林地,特别是“见缝插针”式的小绿斑更多的只是量上的弥补和一种视觉效果,而在质上,由于生物种类的缺乏、层次结构的单一、空间结构的不合理,难以发挥显著的生态效益,其地域特色就更难以显现。
2.3 城市小气候异化
苏州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人口大量增加,建筑物和道路增多,使城区气温显著升高,虽然有研究表明,近10年来热岛效应呈现波动减弱[6],但温度仍较高,极端天气也较频发。2017年6~9月平均气温27.5℃,为历史同期次高值,比常年同期偏高1.5℃,特别是7月平均气温达31.9℃,创历史同期新高,高温日数异常偏多,达33 d,持续时间长、强度强,成为史上仅次于2013年的炎热夏季。同期,降水量则比常年偏多24%,而7月降水量仅73.8 mm,为1995年以来最少值,降水变率较大,有38 d出现短时强降水,46 d出现强对流天气。可以预测,随着城市建设的进一步推进,这种小气候异化现象将可能继续加强。
2.4 城市空间尺度打破
近年来,苏州城市建设规模持续扩大,2016年,苏州市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458.06 km2,人口551.0万人,分别较上年增长0.63%和0.32%,城市用地规模弹性系数达到1.97,高于1.12的较合理水平[7],表明城市空间扩张速度快于人口城市化速度,而与此同时,苏州作为江苏省发展最快速的城市,在城市化发展速度与生态环境水平整体趋于协调的发展状态下[8],仍存在一定的城市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的问题。而建设过程中,虽然苏州古城在建设中实行了限高政策,加上成片的黑顶、白墙建筑,依然能感觉到老城的气息,但由于河道填埋、道路拓宽,那种宜人的空间尺度只能在一些历史街区、风貌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同时,由于古城外围高层建筑集聚,一方面使古城成为“洼地”,与周边各区高低对峙,缺乏过渡(如图3所示),另一方面由于布局缺乏统筹,影响城市景观和视觉走廊的通透性,亦或一些特色建筑被掩盖,亦或一些自然山体、河湖美丽的轮廓线被打破,甚至使城市天际线显得零乱(如图4所示)。

图3 苏州古城区至东部园区的建筑

图4 苏州西部高新区建筑与自然山体背景
3 苏州地域性生态城市建设策略
“河湖密布,山林环绕”是苏州自然生态的根本,“传统格局,园林风貌”是苏州自然生态的延伸,这是苏州最重要的生态特质,针对苏州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受到威胁和破坏的传统生态环境,应本着积极保护、不断完善的生态原则,探寻适合自身特点的思路和方法,凸显传统环境优势,构建富有山水型个性的和谐生态城市。
3.1 加强城市“三维”空间控制性建设
城市空间发展与建设是当前城市山水、田林等原生态用地被占、生态格局和生态环境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又是城市发展所必须的,甚至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标志,如何平衡城市空间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关系,是苏州生态城市建设要关注的重点。
3.1.1 城市平面空间发展控制
在城市平面空间发展上,苏州应转变目前外延式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严格管理对城市形态稳定有较大影响的开发区、新城等的布局和建设[9]。根据当前苏州城市总体规划,着重在现有的城市区域范围内,加强古城核心区及周边高新区、园区、相城、吴中、吴江五组团的集聚发展(如图5所示),通过合理分工布局、紧凑开发,打造各具特色的、功能齐全的区域中心,提升土地的集约和节约化利用效率,从而降低对土地资源,特别是对山水自然生态空间的占用。
3.1.2 城市垂直空间建设控制
在城市垂直空间尺度建设上,苏州在保持原有宜人的自然、人文风貌基础上,同样需要在垂直空间方向拉伸,以高效利用土地,将被解放出来的城市空间还原于自然与城市农业,同时,可以有效节约耕地,尽量保留下原有的地貌及优良植被,为动植物打造生态通道,这也是紧凑型城市的发展路径。但在纵向发展的同时,苏州需要将古城与周边各区进行综合、长远规划,以中心古城与外围山体高度为出发点,以人民路、干将路城市主轴线为中心,形成合理的空间过渡,避免盲目追求高、大、新,以构建良好的人文生态。
3.2 强化城市“山水”生态保护性开发
3.2.1 城市生态敏感区保护
事实上,苏州历次城市规划都贯穿了保护的理念,1986年为保护苏州古城,提出另辟新区发展,至1996年形成“东园西区,一体两翼”的思路,2006年进一步提出“四角山水”的规划格局。然而,面对发展的需求,生态范围常常一次次被突破,保护性规划形同虚设,如西北角三角嘴湿地周边基本被城镇无序扩张的建设用地封堵,其中又以环保标准和生产效率很低的乡镇企业为主[10],严重破坏了湿地环境。因此,必须进一步将具有地域特色的大阳山、灵岩山、凤凰山、穹窿山等山地丘陵,太湖、三角嘴、阳澄湖、金鸡湖、独墅湖等湖泊湿地区,京杭运河、胥江等骨干河流以及苏州古城和陆巷、杨湾、木渎、光福古镇等生态敏感区域设置为生态控制区(如图6所示),严加保护,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并根据各自特点划定一定范围的缓冲区或过渡区,进行限制性发展,如西部山体周边及滨水区应严格控制高层建筑和破坏性的发展。同时,对一些小型地貌、水体、特色建筑区域运用“反规划”理论,在未明确其发展方向时采取先保存后开发的策略,以保护原生态的环境,为其地域性、生态化发展奠定基础。

图5 苏州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示意图

图6 苏州生态敏感区保护图
3.2.2 城市水特色空间文化拓展
水是体现苏州城市活力与魅力的最重要元素,当前,苏州不断加强古城河道的综合整治,以恢复水城特色,取得明显成效,与此同时,可进一步加强环城河外河道的利用,这里河网众多,且河道长、宽,可利用其连接古城区与外部湖泊或景区,甚至可以发展成“水上公共或旅游交通”,一方面将河湖贯通成网,从而为增强生态效益、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稳定的生态格局提供基础,另一方面这里空间广阔,可以通过挖掘和丰富其文化、景观内涵,使其成为苏州特色水生态文化的展示区。当前,可着力打造三条线路:东线——以胥江连通太湖与古城区,其起点是胥门,终点是胥口伍公祠,途径胥口、木渎古镇及灵岩景区,沿途分布许多古遗;北线——以山塘河连通虎丘与古城区,其一端是“吴中第一胜景”的虎丘,一端是“曾经红尘中最繁华”的金阊之地,此处吴风浓郁,河路并行,相辅相成;西线——葑门塘连接金鸡湖、独墅湖与古城区等,可展现传统古城与现代化园区的和谐共生(如图7所示)。此外,还可发展外塘河、横塘河分别连接阳澄湖、石湖与古城区等。由此将苏州的“假山假水城中园”拓展为“真山真水园中城”,彰显水城的特色魅力。
3.3 促进城市绿地系统网络化构建
城市绿地是城市的“净化器”,也是生态城市表达的最直接、最重要方式。与一般绿化不同,生态城市的绿化不应该只是简单的植物栽种,而是要通过绿化促进生物多样性乃至“区域生物圈”的形成[11]。
3.3.1 绿网模式
根据苏州的主导风向,可依托西部山地及周边水体等成片开敞式绿楔,将外围较大型绿色开敞空间从西、西北、东北、东南等方向引入城区,以弥补古城区绿量不足的问题,同时依托环古城河、河网及道路等将城区内的古典及现代园林绿地等与这些生态绿地沟通,最终形成以太湖为依托,以绿楔为骨干,以绿廊为纽带,以城市公园为核心,以街头绿地、广场、小游园、单位附属绿地为节点的多核均布的网状布局模式(如图8所示),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降低城市大气污染,推动生态城市的建设。

图7 苏州水系统空间构建图

图8 苏州绿地生态网络构建图
3.3.2 绿廊串联
目前,苏州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2.25%,不乏生物生存的场所,山地、河湖、湿地、公园都是其集聚空间,但“孤岛”式为主的分布特点,常常阻碍植物群落的连通,更是切断了动物的行走,因此,需要进行整合,构建起相互联系的绿色网络,增强其生态功能。依据苏州现有的山体、河流等自然廊道及道路等人工廊道,核心构建“一环三纵两横”的绿色廊道体系。
一环:即环古城河绿廊,利用环古城河的自然贯通性,两岸构建一定宽度的连续绿带,同时串联起沿线的桂花公园、盘门、百花洲、糖坊湾、原苏州动物园等大型绿地及众多小游园。
三纵:西部为“山绿廊”,依托西部原生态山体走势,在封山育林、山体复绿的基础上,在山体之间辅以各类人工林带,从而形成连通阳山、天平-灵岩山、穹窿山、凤凰-七子山、上方山的山体林带。中部为“水绿廊”,依托京杭大运河自然连通性的优势,通过打造沿河绿化,拓展其生态功能。东部为“路绿廊”,依托东环路、东环高架城市主干道,充分利用地面空间,发展较大尺度的绿廊,发挥更大的生物保护作用。
两横:均依托交通干道,南侧为绕城高速,北侧为高铁沿线,打造沿线绿廊,并向西延伸与西部山地林带衔接,形成更为完整的“绿链”,让苏州的生态多样性在“自然力”的作用下逐渐恢复起来。
3.3.3 绿斑溶解
长期以来,城市绿地的设计多为刚性边界,尤其是公园、古典园林、附属绿地等多有围墙将其与外界隔断,即使是广场等绿斑,也常常以道路、大面积硬质铺装等与周边环境分离,其生态作用受到极大限制,因此,唯有弱化边界的分割与限定作用,甚至打破空间界限,才能使仅有的“自然”空间环境发挥更大的生态效益。对于公园,尽量取消封闭型边界,多采用绿篱等渗透型边界,使其更好地融入生活;对于附属绿地,在场地无法开放的情况下,可利用栅栏等柔性边界设计,或丰富墙面立体绿化,形成较为自然的衔接,而对于大尺度的广场和小尺度的游园等,则要做到硬质空间与软质空间相互渗透,避免生硬,从而化解人工与自然的冲突。
4 结语
生态城市的建设涉及内容广泛,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动态过程,要综合考虑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城市发展方向和周边自然人文环境等因素,加强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走富有地域性的绿色之路,才能真正地持续与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