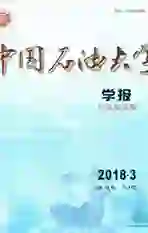吕祖谦的文道观及其文章创作成就
2018-09-17许和亚
许和亚
摘要:吕祖谦的文章创作取得“衔华佩实”的成就,原因是他在北宋以来文道分裂与对立的时代背景下,主动致力于弥合文道之裂,形成了“融会理文”的文道观;并在“中原文献之传”的学术渊源与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将这一文道观落实到具体的创作中。吕祖谦的文道观及其文章创作不仅属于文学的范畴,而且是其学术的一种表现形态和重要层面,在宋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吕祖谦;文道观;文章创作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3-0082-05
南宋乾道、淳熙年问,吕祖谦是与张栻、朱熹齐名的理学大家,其开创的“吕学”,南宋中期以后与“朱学”“陆学”鼎足而立,各擅胜场。在传统的文学史观念和叙述中,理学家秉持“作文害道”的文道观,这种文道观统摄下的文学创作普遍具有以语录为文的弊病,极大地损害了诗文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对宋代及以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其实,由于学术体系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南宋理学家的文道观又是各有差异的。吕祖谦虽不以文自名,但在当时却是享有盛誉的文章家,这要回到南宋中期具体的历史脉络中考察,揭示其独具内涵的文道观和文章创作成就,而这又与吕祖谦个人的学术渊源和知识结构紧密相关。本文从以下三个互为关联、相辅相成的层面展开论述。
一、融会理文的文道观
吴子良说:“自元祜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会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实。”自北宋元祐年间至南宋,以二程为代表的“道学之儒”和以苏轼兄弟为代表的“文章之士”之间的文道之争一直绵延不绝,矛盾不断升级,甚至分化为彼此对峙的两大阵营,最终酿成“理与文分为二”,也即文、道分离的割裂局面。道学与文学这种紧张关系的形成肇端于程颐,他从道的纯粹性、严肃性立场出发,提出“作文害道”,认为应该摒斥文学,专心于道学修养之中。至元祐时期,道学与文学的这种对立和排斥,演变成士大夫之间在政治甚至人格上的相互攻讦与交恶,尤以蜀、洛两党为甚。至南宋中期,朱熹对“苏学”讨伐的力度和深度皆前所未有。罗大经说:“朱文公云:‘二苏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倾危变幻之习。又云:‘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谓此文公二十八字弹文也。自程苏相攻,其徒各右其师。……文公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朱熹对“苏学”的讨伐是其创构与张扬“新道统”的必然路径,同时也与其秉持的道主宰文、“文便是道”的文道观紧密相关: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日:“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
在朱熹看来,苏轼之所以“文自文而道自道”,就是因为“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向身上做工夫”,即“持敬”功夫,“敬”是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所在,而苏轼却要“打破这‘敬字”,自然遭致朱熹的批驳,并指责“文章之士”创作的“文人之文”“大本都差”。钱穆先生说:“轻薄艺文,实为宋代理学家通病。惟朱子无其失。其所悬文道合一之论,当可悬为理学、文学双方所共赴之标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朱熹所持的“文道合一”之论建立在以道为根本、文为枝叶的文道观之上,在一定程度上以抹杀乃至牺牲文的审美性、艺术性为代价;同时,就其不遗余力地排击苏轼等“文人之文”而言,确是有失公允的。
朱熹对“苏学”的讨伐,导致文道关系愈加恶化,呂祖谦正是在这种文道分裂与对立的时代背景下致力于融会“理”“文”之裂的,并对南宋中后期的程洵、叶适、魏了翁等人皆有重要的启示。朱熹的内弟程洵便“初敬慕苏氏之议论,复谓程、苏之道同”,尽管朱熹与之“辨难数千百言”,但最终程洵还是走向“合苏、程为一家”的融合之路。刘壎说:“闻之云卧先生(吴汝式)曰:‘近时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欧苏之裂。”陈元晋在评述魏了翁的学术追求时赞扬道:“潜心大业,会同蜀洛,上通洙泗之一源;凌厉庄骚,下掩渊云之众作。”所谓“会同蜀洛”,也即会同以苏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与以二程兄弟为代表的洛学。以上诸人的这种尝试与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揭橥了南宋理学士大夫已敏锐觉察到理与文也即道学与文学在当下出现了分裂与对立,并严重影响到了理与文的正常关系,这种冲突和分裂与儒家素来倡导的“有德者必有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文道合一观念是背道而驰的。这种融会理文、弥合文道之裂的努力,是对以往错误地严分道学与文学之界而加剧文道之裂行为的自我反省和拨乱反正,无论在思想史上抑或文学史上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淳熙四年(1177)冬,吕祖谦奉旨开始编纂北宋一代诗文总集《宋文鉴》,叶适指出此书“大抵欲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而不以区区虚文为主”。作为理学家的吕祖谦,对于文有很高的期待,“文之时用,大矣哉。观乎天文以察乎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文者,殆非绘章雕句者之为也”。吕祖谦所看重的“文”,是那些可以“察乎时变”“化成天下”的有“时用”的文章,即以是否有益于治道、有补于世教为判定的标准。他认为“文士虽为人所爱,而亦为人所薄,若唐之王、杨、卢、骆,虽有文采,终为人所薄者,以其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后人仰之,莫不肃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经》之文亦然。”本于正、发以正,文质兼备的“《六经》之文”正是吕祖谦对于文章的终极追求。正如叶适指出的:“吕氏所次二千余篇,……人主之职,以道出治,形而为文,尧、舜、禹、汤是也。若所好者文,由文合道,则必深明统纪,洞见本末。”治道需要“形而为文”,同时“由文合道,则必深明统纪,洞见本末”,这是个辩证统一的过程。文与道并非割裂的关系,而是统一的整体,两者彼此依存、互相交融,一旦将任何一方抽离出来,文字便陷入沦坏的境地。
鉴于北宋以来文道分裂乃至对立的局面,吕祖谦在文章创作中,以及通过编纂《宋文鉴》自觉以融会理文、统合文道为己任,这不仅是其文学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层面,在其一生的学术轨迹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说“以道出治,形而为文”是吕祖谦融会理文的途径和方式,那么“由文合道,则必深明统纪,洞见本末”,则是吕祖谦融会理文的指向和目标,其终极目的在于达至文道合一、文质彬彬的至善之境。而这种融会理文的文道观的形成,建立在吕祖谦对文道内涵自我体认的基础之上。同时,这种融会与吕祖谦“中原文献之传”的学术渊源与知识结构紧密相关。
二、“中原文献之传”的学术渊源与知识结构
吕祖俭为其兄吕祖谦所作《圹记》云:“公之问学术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参贯融液,无所偏滞。”其实,吕氏家学与“中原文献之传”的这种关系,不仅是吕氏兄弟的自我认同,而且是当时乃至后来学者的共识。朱熹说吕祖谦“矧涵濡于先训,绍文献于厥家”,巩丰云其师“文献绍家学,刻意稽虞、唐”,后来的《宋史》与《宋元学案》皆承此说,有“中原文献之传”的吕学遂与朱学、陆学相区别,成为南宋理学的重要支派之一。
对于何为“中原文献之传”,吕祖谦曾说:“昔我伯祖西垣公(吕本中)躬受中原文献之传……嵩、洛、关、辅诸儒之源流靡不讲,庆历、元祐群叟之本末靡不咨。以广大为心,而陋专门之暖姝;以践履为实,而刊繁文之枝叶。”吕祖谦早年闻林之奇得吕本中之传,故师事于林之奇,因此“中原文献之传”复归于吕氏。吕祖谦又从刘勉之、胡宪、汪应辰、张九成诸人学,参稽众家,汇归于一,故“中原文献之传”于吕祖谦处集大成。而“中原文献之传”也即如吕祖谦所指出的镕铸北宋一代性理、经制、文史为一炉,以及“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的学术蕲向,同时也显示出吕氏学术强大的包容性与融合力。正因为这一学术渊源,故吕祖谦标注《三苏文集》,编选《古文关键》,编纂《宋文鉴》,展现了其重视文的一面;同时又以理学家的身份与朱熹合作编著理学文选《近思录》。这既是吕祖谦“中原文献之传”在学术、文学层面的具体践行,同时也标示了其融会理文的文道观的思想渊源。
综观宋代士人,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也鲜明地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之学”的丰富内涵:同时,宋代士人在具体的学问取径上又各有不同的侧重。在南宋中期诸多理学家之中,吕祖谦对历史的关注与用心是其他人所不能及的,这也遭致好友朱熹的批评,说他“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其实,吕祖谦并非如朱熹所说的那样重史轻经,他是经史并重的,这也是南宋中期浙东学人的共同学术取向。元代彭飞在《历代制度详说原序》中说:
自性理之说兴,世之学者歧道学、政事为两途,孰知程、朱所以上接孔、孟者,岂皆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紫阳夫子浙学功利之论,其意盖有所指,永嘉诸君子未免致疵议焉。东莱先生以中原文献之旧,岿然为渡江后大宗。紫阳唱道东南,先生实羽翼之,故凡性命道德之源,讲之已洽,而先生尤潜心于史学,似欲合永嘉、紫阳而一之也。
吕祖谦“欲合永嘉、紫阳而一之”,也即融合性理之学与浙东史学于一身,扭转“道学、政事为两途”这一分裂局面,弥合程朱性理之学与永嘉经制之学的分歧。体现在文章创作上,即如朱彝尊所说的,宋代“有儒林之文,有理学之文。儒林之文,本乎学问意见,考据探索,足以发扬志识,而经制之业出其中焉。理学之文,本乎穷理致知,明体达用,足以开来继往,而道统之传出其中焉”。在文章创作中,吕祖谦致力于合“儒林之文”与“理学之文”为一,形成了其文章既有经制之业,又有道学性理之传的显著特色,是其融会理文的文道观与“中原文献之传”的外在表现形态。
吕祖谦学术的终极追求是以“成己成物”为目标的“合内外之道”,“内即是理,外即是事”,其所谓的“道”是内与外的结合,也即“理”与“事”的交融。其实,“中原文献之传”从根本上来说立足点在史学,因此吕氏家学尤重“前言往行”。在吕祖谦看来,“大抵忠厚悖笃之风衰,缘前言往行断绝:今之学者所以浇薄,缘先王长者之说不闻”。吕祖谦“中原文献之传”的学术渊源,以及对“前言往行”的关注,使他在知识结构上相对于同时代的“文章之士”和“道学之儒”多了一个史的面相,这也使他的学术多了一层史的底色。
吕祖谦并未因对史的重视而忽视经和不讲义理,他认为作为“前言往行”的史与作为“德”的义理两者之间并非彼此独立,义理可以考验史之是非,史反过来可以订正义理之得失,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作为“中原文献之传”的集大成者,呂祖谦在潜心经史之学的同时“欲合永嘉、紫阳而一之”,而且重视文的功能和作用,反映在文道观上便是致力于融会理文,体现在知识结构上即汇合程朱性理之学与浙东史学、事功之学为一体。这也决定了吕祖谦在创作实践中致力于融合“儒林之文”与“理学之文”为一,最终形成其文章“衔华佩实”的创作成就和艺术境界。
三、“衔华佩实”的创作实践
清四库馆臣评价吕祖谦的文章创作说:“其文词闳肆辨博,凌厉无前,……祖谦于《诗》、《书》、《春秋》皆多究古义,于十七史皆有《详节》。故词多根柢,不涉游谈。所撰《文章关键》,于体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诸体虽豪迈骏发,而不失作者典型,亦无语录为文之习。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指出了吕祖谦文章既“词多根柢”又“豪迈骏发”的特征,这两者的统一即“衔华佩实”的创作成就和艺术境界。
对于南宋理学士大夫而言,得君行道、恢复故疆的关键在于正人主之心,因此吕祖谦力倡孝宗兴复圣道,留意于圣学。其《乾道六年轮对劄子》云:“陛下所当留意者,夫岂铅椠传注之问哉!宅心制事,祗畏兢业,顺帝之则,是圣学也;亲贤远佞,陟降废置,好恶不偏,是圣学也;规摹审定,图始虑终,不躁不挠,是圣学也。”所言圣学内容皆本之经史,遣词造句皆有根柢,全文体物至察,义理无偏,其不为虚文、切于治道之心,可谓至矣。《淳熙四年轮对劄子》委婉指出孝宗“独运万机”之实、之失,认为“厥今虏势陆梁而国仇未雪,民力殚尽而邦本未宁,法度具存而穿穴蠹蚀,实百弊俱极之时”,只有“治道体统,上下内外不相陵夺而后安”。同时“考古而验今”,对“国朝治体”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总结:“以宽大忠厚建立规摹,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为“远过前代者”:“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盛相望而干略未优”,为“视前代犹未备者”。最后根据“仇耻之未复,版图之未归”的严峻现实,建言孝宗“今日治体其视前代未备者,固当激厉而振起;其远过前代者,尤当爱护而扶持”。全文深得孟子论辩艺术之精髓,欲抑先扬,委曲动人,“其言和缓,不致蹙迫”,可谓最得“开悟人主之道”。行文结合自身为学之特点,步步着实,有理有据:全文布局有法,语言整饬,议论风发,高蹈卓绝。其如清人张坦让所言:“其文也,如匣灯帷剑,浑金璞玉。髫时读其遗编,恍见洙泗支流,而一种静穆之致,使人仿佛兴起。”道出了吕祖谦文章“豪迈骏发”又不失婉曲微讽、中正无偏的浑厚静穆之致。对于文章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吕祖谦强调“言语足以动人,文章足以耸众,不正则反为害”。因此他认为:“屈原有爱君之心固是善,惜乎其发之不以正,自愤怨激切中来。……若孟子则初无此心,其言语始终和缓,皆出于正,此屈原、孟子所以分。”表现在文章创作实践中,也即如韩漉所说的“吕伯恭拳拳家国,有温柔敦厚之教”。这正是我们理解吕祖谦文章创作的重要出发点和立足点。
不仅像《轮对劄子》这样的奏议文,其他如表、奏状、启、策等文体亦是吕祖谦所擅长的。乾道六年(1170),吕祖谦为张栻作《乞免丁钱奏状》,运用列数据的方法将丁钱之利害说得分明,通过前后、左右对比展现严州百姓因苛捐杂税而生活困顿、民不聊生的严酷现状,文章说理深婉,有温柔敦厚之气,深得曾巩《救灾议》“说利害体”的为文之法。同年作的《馆职策》,开篇说“治道有大原。不本其源,徒欲以力抹斯世,君子许其志,不许其学。天下之事,要不可以力为也”。文章反复论辩贾谊“序天下之事,所先者外忧,所后者内治,于为治之大原,似未深讲也”。姚崇“不务格其君之心,而以力邀之”,“埒之于宜,则非匹矣”。行文气脉、论辩技法明显受苏轼策文的影响,故黄震说此文“词锋横出,读之起人意”,也即四库馆臣所说的“文词闳肆辨博,凌厉无前”的风格特征。再如《代宰臣以下贺车驾幸秘书省表》《中两科谢主司启》等表、启类文章,大都纯正宏深、文敏而丽,得词臣之体,“为一时著作之冠”。凡此皆展现了吕祖谦文章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与兼容性。
此外,在文体上,吕祖谦的创作并不止于以上列举的几种文体,而是众体兼备,如记、序、题跋、传、祭文、墓志诸体,皆为其所擅长。据文集所收,吕祖谦所作祭文二十余篇、墓志铭四十余篇,在文集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其祭文大都声情并茂,将人物的描述置于特定的历史场域中。《祭汪端明文》言汪应辰处于“南渡群贤皆在之时,而北方余论未衰之际,款门墙而遍历,跻堂奥而独诣。合诸老之规摹,而融其异同;总一代之统纪,而揽其精粹”。同时指出汪应辰“少而论和,既不诡随于小人之党:晚而议战,复不苟同于君子之徒”的独立人格。吕祖谦的墓志文创作虽大多为应酬之作,但篇篇有法度,又不失灵活变化,往往能够在体制上推陈出新。如《薛常州墓志铭》,文章法度井然,如实详细记载墓主生平言行,其立朝之大节、崇高之人格不言自明。全文以议论收尾,将薛季宣置于前后相连的历史序列之中,给予其恰当的历史定位和评价。陈亮称此文“布置有统,纪载有法,精粗本末,一般说去”。其他如《大梁张君墓志铭》《金华汪仲仪母王氏墓志铭》《刑邦用墓志铭》皆开篇议论,先声夺人,以史笔为文,将笔下人物置于南渡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来考察,以墓主之身份、经历展现时代的风云变幻,让人在无限感慨中反省过往的历史。《题伯祖紫薇翁与曾信道手简后》,追忆吕氏家族与江西的关系及盛衰,展现了自北宋以来的历史画面,故黄震称此文“历叙曲折处,极可观,有关世变”。《东莱公家传》通过对吕好问一生事迹的记述,展现了两宋之际纷繁复杂的历史变迁。文章于靖康之难后吕好问立身大节、出处本末辩白尤力,语言剀切详明,行文井然有法,记载翔实可信。
吕祖谦的散文创作,在文章体裁上可谓兼备众体,在艺术风格上也呈现多样化的格局。《白鹿洞书院记》为吕祖谦记体文中的名篇,朱熹评此文“辞约义正,三复叹仰”,程千帆先生评价此文“风格详整,极有义法,颇能显示出吕文的特色”。《秀州陆宣公祠堂记》《重修钓台记》皆行文有法,议论平正,气度冲和。其他如《游金华赤松山记》《入越录》《入闽录》等皆为游记文,清新隽逸,随笔点染,情境宛然,与柳宗元、苏轼的游记文风格相近。凡此皆可看出吕祖谦文章创作的多元化格局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特征。
综观吕祖谦的文章创作,既众体兼备,又风格多样,多元会通,可谓“衔华佩实”。其文章“豪迈骏发”的一面与融会苏轼文风密切相關。吕祖谦对“抑扬驰骤开阖之妙”的苏文尤其赞赏不已。同时,吕祖谦的文章大多有为而作,不为虚文,且在经史义理上用力尤深,故其文词皆有根柢,多温柔敦厚之教。
四、结论
吕祖谦虽致力于融会理文,但在南宋中期学派意识渐趋膨胀的情境下,实难从整个理学与文学领域,弥合自北宋以来文道之间的分裂与对立。与此同时,吕祖谦融会理文的文道观及其文章创作实践,均为吕氏学术思想的具体体现;换言之,无论其文道观,还是奏状、表、启、祭文、墓志、序、题跋、记、传等文,不仅属于文学的范畴,同时也是其学术的重要层面。在学术层面上,吕祖谦以其“中原文献之传”的学术渊源和知识结构为基础,试图融会北宋以来的文道之裂:在文学层面上,吕祖谦的文道观及其文章创作具有鲜明的“贵用”蕲向,他强调文章要有补于世教、有益于治道,虽以韩、柳、欧、曾、苏等为文章学习的典范,在文章作法与技巧上取得较大的成就,但在题材内容和审美功能等方面,却难以与“文章之士”创作的“文人之文”相媲美。
不过,从“中原文献之传”的学术理念及其倡导的文章贵“时用”、有为而作的价值取向来看,吕祖谦融会理文的文道观及其文章创作实践,无疑取得了很高的成绩,这无论对南宋理学格局的形成,抑或宋文的发展皆有重要的贡献。吕祖谦融会理文的文道观,通过“中原文献之传”的学术渊源与知识结构,将其落实到具体的文章创作之中,形成了“衔华佩实”的创作成就和艺境。这种创作路径的形成,虽然属于其学术思想的表现形态,但在宋文的发展历程中却别具一格,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包括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等人在内的整个浙东学人的文章观念和创作路径,并形成一个文章创作流派,在两宋散文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吴子良将吕祖谦放在历代文章发展的历史序列之中,指出“南渡之文以吕、叶倡”,并揭示出吕祖谦融会理文的文道观。这在自北宋以来文道分裂乃至对立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纠偏归正、统合文理之功,对于南宋文坛中兴局面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和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