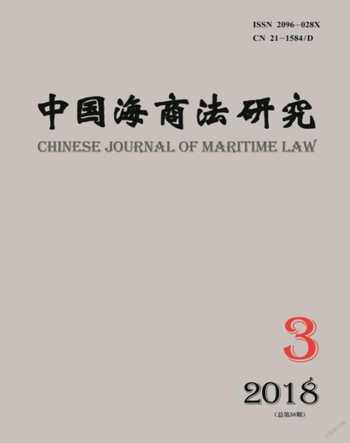《海商法》下收货人提货权利义务之辨
2018-09-10陈琳琳
陈琳琳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第86条将收货人在卸货港的提货行为绝对义务化,使得包括该条文以及第42条、第44条、第71条、第78条、第79条、第80条在内的法律条文间,存在着概念范围模糊、条文冲突的法律形式逻辑问题,也与《海商法》设置提单等制度的法律目的相背离。因此,在法律条文上进一步明确卸货港提货为收货人的权利,修正收货人提货权在《海商法》中的条文表达,将有助于提升《海商法》法律形式逻辑的严密性,并促进《海商法》立法目的和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海商法》;收货人;卸货港;提货权
中图分类号:DF961.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18)03001105
Identification of the right and obligation of the consignee to take delivery under CMC
CHEN Linlin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Abstract:Article 86 of the Maritime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MC) imposes on the consignee an absolute obligation to take delivery at the port of discharge and this causes some legal problems between Article 86 and Aarticles 42, 44, 71, 78, 79, 80. There exist logic issues of legal forms such as vague conceptual scope and conflicts of provisions and this deviates from the legal purpose of setting up the system of bills of lading in the CMC. In view of the abov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at the right to take delivery at the discharge port vests in the consignee and modify the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consignees right to take delivery in the CMC, so as to help improve the rigorousness of formal logic of the CMC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and value of the CMC.
Key words:CMC;consignee;port of discharge;right to take delivery
在国际货物买卖中,买方通常被要求承担及时提货的义务。但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因涉及相关单证或权利的转让,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收货人是否有权或有义务提取货物,往往取决于特殊的法律语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第86条在条文表达上似乎体现的是将收貨人的提货行为绝对义务化,即不管是卸货港无人提货亦或是收货人拒绝提货、迟延提货,收货人都需要向承运人承担由此产生的卸货港费用①。这与《海商法》第42条对收货人的定义以及涵摄于该法第44条、第71条、第78条、第79条、第80条等条文中的规范,存在法律形式逻辑上的冲突和对法律实质目的的背离问题。
一、《海商法》形式逻辑上收货人提货绝对义务的否定
(一)收货人范围模糊对提货绝对义务的否定
国际上对收货人的概念没有统一的规范。英美法下提单持有人与收货人被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主要适用于提单法而非海上货物运输法。其中收货人的适用范围较窄,主要适用于未签发提单的情况,而提单持有人主要适用于可转让提单,但不包括通过承运人签发提单而取得提单的托运人。[1]《汉堡规则》仅规定收货人,没有规定提单持有人。《海商法》同时采用收货人和提单持有人两个概念,将收货人与提单持有人作为并列概念进行规定。但由于《海商法》没有定义何为提单持有人,仅定义收货人为有权提取货物的人,而提单具有一定的物权凭证功能,因此就概念范围而言,提单持有人也可能作为《海商法》下的收货人。
当提单持有人作为收货人,《海商法》第86条规定的收货人提货义务也同样适用于提单持有人。从提单的功能价值角度看,流通性是空白提单和指示提单的价值所在,应为实践活动所遵循和体现。在海上货物运输过程中,提单可能一直处于流转状态,提单持有人在向承运人出示提单并主张提货前,承运人无法知晓提单持有人的确切身份。据此,如果将目的港提货规定为收货人的提货义务,似乎难以与提单的性质和功能相契合。
从提单概念范围的角度看,记名提单与指示提单、空白提单同属于提单的概念范畴。因此,除非法律条文明确限定“提单”所指向的范畴,否则“提单”概念的使用应涵盖记名提单、指示提单和空白提单,相应的规范作用也应同等约束不同类型的提单。这就说明,《海商法》第86条提货义务规定是否具有法律形式逻辑上的周延性,需要进一步考证《海商法》关于“提单”概念的规定。
《海商法》第71条规定:“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这一规定源自《汉堡规则》第1条第7款的规定,但又有所区别
。《汉堡规则》第1条第7款分为前后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提单概念做出界定,明确了提单的三种功能,即可作为合同证明、货物收据以及提货凭证,而第二部分紧接第一部分,进一步阐述凭单交付货物是指“应按记名人的指示交付、或者按指示交付、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亦即《汉堡规则》排除记名提单的适用,因此这一条款里的提单功能无法指向提单的全部范畴,更确切地说,提单作为提货凭证的功能在《汉堡规则》下只适用于指示提单和空白提单。[2]《海商法》第71条在借鉴《汉堡规则》的这一条款时,忽视了对提单功能指涉范畴的限制。
在《海商法》下,关于记名提单是否需要凭单交付货物的问题曾一度存在争议。记名提单不同于空白提单和指示提单,记名提单明确记载了收货人,一般情况下,承运人在卸货港进行货物交接时,只要收货人能证明其身份,承运人即可向其交付货物,是否出示提单显得不再重要。然而,《海商法》第71条明确规定提单是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凭证,且由于该条文没有限定提单的种类,因此这里所指涉的提单范畴自然应该包括记名提单。即在签发记名提单的情况下承运人也应该凭单交付货物。这一点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支持。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有限公司”案时,明确了即使是记名提单也需凭单交付货物①
。由此可见,即使在理论上强调记名提单凭单交付货物的必要性不再显著,现有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仍严格遵循凭单交付货物的原则。
海上货物运输并不必然涉及到提单的签发,即使不签发提单,海上货物运输也得以完成。例如,在航运实务中,为快速交付货物、节省相关费用等,常由承运人签发海运单。[3]相较于提单,海运单同样具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货物收据作用,但不具有可转让性,不是货权的证明或凭证。基于此,海运单被认为无法适用《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因为《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第1条明确规定,运输合同仅仅指提单或类似的权利凭证所包含的运输合同,海运单既非提单亦非权利凭证,自然无法适用《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4]但依据《海商法》第44条的规定,提单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并不穷尽所有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商法》第四章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范,同样适用于除提单外其他运输单证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依据《海商法》第80条的规定,当“承运人签发提单以外的单证用以证明收到待运货物的,此项单证即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承运人接收该单证所列货物的初步证据。承运人签发的此类单证不得转让”。海运单应属于该条文所说的“提单以外的单证”。因此,《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适用于海运单。《海商法》下的收货人包括海运单收货人。
海运单下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否依据海运单上的记载确定是有疑义的。因为《海商法》并没有拟制“海运单关系”,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法定“海运单关系”。虽然收货人与托运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但两个合同是各自独立的。海运单下的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缺少必要的法律关系基础。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09条规定收货人负有及时提货的义务,被普遍认为有利于促进交易目的的实现,进而为多数人所称赞。[5]但这并不当然地证成《海商法》第86条的合理性。因为将建立在合同关系基础上的收货人提货义务直接适用于没有合同关系基础的收货人和承运人之间是不恰当的。为补正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基础,1990年《海运单统一规则》规定,托运人为收货人的代理人,其与承运人订立的合同也代表着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运输合同的订立。同时规定,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海运单确定。
这实际上是通过托运人的代理行为,在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建立约定的“海运单关系”。在此基础上,倘若将卸货港的提货规定为收货人的义务,尚有其合理之处。由此亦可见,除非《海商法》效仿1990年《海运单统一规则》创设类似的法定“海运单关系”,构建起承运人与收货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基础,否则《海商法》第86条规定的卸货港提货义务不应用于规制一般海运单下的收货人。
(二)法律条文冲突对提货绝对义务的否定
从法律文意解释的角度看,《海商法》第42条将收货人定义为有权提取货物的人,就说明提货是收货人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以该条的意思表达代入《海商法》第86条,可以发现只有在迟延提货时,收货人才有义务承担因此产生的卸货港费用,因为既然提货是收货人的民事权利,收货人就可随意处置这一权利,包括放弃行使权利等。第86条将不提取货物或拒绝提取货物设置为收货人承担卸货港费用的责任前提,无疑与第42条的规定冲突。
二、《海商法》法律目的意义上收货人提货权利的必要
运输合同由承托双方签订,提单也是承运人先签发给托运人再转让至收货人(收货人与托运人不是同一人时),收货人没有参与此过程,其意思表示欠缺,需要在提单关系中为其提供法律保护。据此,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绝非“义务先导、权利附随”,而应该是“权利先导、义务附随”或是“权利义务同步”。
(一)“权利义务同步”之弊
认为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是“权利义务同步”模式的,其理论根源主要在于将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提单关系认定为是运输合同关系的转换。也即,这种观点肯定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提单关系为法定的提单关系,但认为提单上记载的权利义务是由运输合同上的权利义务转让而来,提单从托运人转让至收货人时,提单上记载的权利义务就转让至收货人,收货人对提单上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致使托运人在运输合同中对应的权利义务处于暂时搁置状态。收货人不行使和履行提单上记载的权利义务,这些权利义务就会重新归置于托运人,由托运人最终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此观点虽然肯定提单所确立的法定关系,但没有将提单关系完全独立于运输合同关系,没有很好地体现提单突破运输合同相对性的价值所在,甚至于虚置提单制度。将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认定为是运输合同中权利义务的转换,完全排除了收货人、承运人以及托运人为运输活动当事人的共时性。即收货人只是托运人在卸货港的法定替代人,转让提单就是转让或转移卸货港的提货权利义务。此时的提货既是收货人的权利也是收货人的义务。因为在运输合同中,交付货物是承运人的义务,但协助这一义务的履行却是托运人的义务,同时基于对货物的所有权,提货也是托运人的权利。换言之,托运人即使放弃主张货物的所有权,协助承运人完成交付义务仍然是托运人的义务。这对于托运人而言,没有不公平之虞,因为运输合同的订立是其意思自治的成果。但对于收货人而言,等同于为其设定了法定义务,即使事实上收貨人没有行使任何权利。显然,这背离了提单突破运输合同相对性的实质目的。而且,这一观点也无法解释银行作为收货人时的实践问题。银行持有提单看重的是提单的担保价值,提货对于银行而言根本不是其目的所在,让银行承担提单下的义务并不合理。[6]
(二)“权利先导、义务附随”之利
认为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权利先导、义务附随”,一方面在于肯定当托运人与收货人不是同一人时,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法定的提单关系,另一方面在于明确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由提单上的记载确定的,即使这些权利义务从其终极根源上看是来自运输合同,但是与运输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各自独立。所谓“权利先导”是指提单主要在于赋予收货人提单权利,即提货权和损失赔偿请求权。“义务附随”是指收货人在行使提货权或损失赔偿请求权后需要承担的包括卸货港费用在内的相关义务。“权利先导、义务附随”,强调的是收货人的提单权利,只有提单权利的行使才能导向相关义务的承担,符合提单突破运输合同相对性的价值追求。
这一主张的理论根源在于,虽然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初始状态的确是运输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但经承运人签发提单的单方诺成行为后,这些权利义务即为法定的权利义务。[7]交付货物是承运人在运输合同下必须履行的义务,提单中的权利义务规定是承运人对其交货义务履行的预设,而承运人签发提单的单方诺成行为决定了“行使权利才承担义务”是这一预设的必然要求。因此,提货权是收货人基于提单关系享有的必然和不附条件的权利。这一权利不以其他义务的履行为前提,但其行使能够导向相关义务的履行。如,收货人行使提货权向承运人提取货物,但由于迟延提货产生相关的卸货港费用,对此收货人需要向承运人承担费用补偿。实际上,相关的国际公约已有类似的规定,如《鹿特丹规则》第57条、第58条规定,当且仅当提单持有人行使运输单证项下权利时,义务才转移至提单持有人。《1992年英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第2条、第3条的规定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权利先导、义务附随”同样适用于银行为提单持有人的情况,银行可以充分利用提单的担保价值,同时不用被逼迫去提取货物。此外,“权利先导、义务附随”也解决了“权利义务同步”中权利义务转换受托运人最低义务和原权限制的问题。“权利义务同步”的前提是运输合同中托运人的权利义务具有可转让性,如果存在托运人的最低义务和原权限制,相关的权利义务就无法转换为提单中的权利义务。[8]这也是“权利义务同步”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质疑。“权利先导、义务附随”很好地规避了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法定的,并独立于运输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托运人的最低义务和原权限制不影响收货人的权利义务。
以海运单方式交付货物是为了实现货物的快速交付。法律没有像规定提单关系那样,确定“海运单关系”,一则在于没有必要,因为采用海运单方式交付货物往往是对凭提单交付货物的替代,法律没有必要另行设置一种法定法律关系替代已有的法律关系;二则在于,不存在“海运单关系”并不意味着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反致到运输合同关系或买卖合同关系中,或说无需直接以运输合同或买卖合同规范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大多数国家并不承认“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承托双方之间的运输合同无法拘束收货人之类的第三方。[9]简言之,海运单下的收货人,其之所以愿意作为此类收货人的主要目的是快速取得货物,因此提取货物理应是收货人的权利。
三、提货行为的权利应然属性及其在《海商法》中条文表达的修正
(一)提货行为的权利应然属性
提货行为实现其权利属性的应然状态是为提货权反射的利益提供最大保护。这决定了提货权在由实然状态转向应然状态的过程中,法律应尽可能地肯定有利于这一转变的责任配置。
具体而言,法律应该明确规定何为提货行为,以及何种提货行为是不可逆转的且必然导向义务的承担。例如,单纯主张提货但没有采取行动、以提单或其他运输单证换取提货单以及事实上进行货物的提取等是否为提货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如何等。显然,事实上进行货物提取活动的是提货行为,且如果期间存在迟延提货的事实,收货人就需要对迟延提货造成的卸货港费用承担赔偿责任。然而,单纯主张提货的行为和换取提货单的行为似乎不能完全被认定为是不可逆转的权利行使,并必然导致义务的承担。原因在于,单纯主张提货或换取提货单的行为不代表此时的收货人就是最终的收货人。尤其对于单纯主张提货而没有实际行动的收货人而言,如果一主张提货就必然启动义务规制,将在很大程度上阻滞提单的流转,对收货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如,在The Berge Sisar案①
中,收货人在向承运人主张提货后,但在提货前的货物检验中发现货物不符合要求,于是拒绝提货,并将货物转卖给新的买方,货物最终为新的买方所提取。由于该批货物为化学品,腐蚀性较强,船体因此受损,承运人为此向一系列的主体提出索赔请求。其中,承运人对收货人的诉请理由是,依据《1992年英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的规定,收货人提出过提货请求就已行使了权利,实际提取货物成为收货人的义务,因此应当承担相关的责任。英国上诉院的法官虽然存在意见不合,但大多数认为,收货人主张过提货不是不可逆转的权利行使,其随后的提单转让已经构成对权利行使的阻却,因此收货人不承担提取货物的义务和相关责任。
不完全肯定单纯主张提货或换取提货单为提货权的行使,进而否定对应的义务履行要求,似乎过于
保护收货人的利益。但实际上这一做法在保障收货人提货权的权利属性时,也遵循了公平原则,因为如果出现收货人仅单纯主张提货或换取提货单而未实际提取货物的情况,承运人可以行使无人提货时的货物处置权,而不影响其运输合同义务的履行。
(二)提货行为权利属性在《海商法》中条文表达的修正
修正提货行为权利属性在《海商法》条文中的表达,应该包括对所涉法律条文的形式逻辑修正,以及提升法律条文实现其目的的现实可能性。这一过程中需要梳理的《海商法》条文包括第42条、第44条、第71条、第78条、第79条、第80条、第86条。上述条文中,除第42条是非规范性条文外,其他皆为规范性条文。第42条是个定义性非规范性条文,对包括收货人在内的其他概念作出了界定。第42条规定收货人是有权提取货物的人,这一定义太过简单,没有区分不同运输合同情况下的收货人,对后续其他条文的理解适用造成不利的影响。在修订这一条文时,应该保留提货属于权利的规定,在此基础上明确收货人提货请求权的依据,将提单、海运单等其他运输单证证明的海上运输合同都包括其中,并明确区分收货人与提单持有人,规定只有提单持有人向承运人行使提单上的权利时,提单持有人才转换为收货人。此外,应该排除托运人的代理人作为收货人的情况。强调提货行为的权利属性在于保障与之对应的合法利益,当托运人的代理人为提取货物的主体时,其相关合法利益依据运输合同就足以保障。在区分收货人与提单持有人的基础上,明确收货人的范畴涵盖海运单下的收货人,使得海运单下的收貨人得以依据第42条行使提货请求权。如此规定,一方面既可以在法律形式逻辑上协调第42条和第44条、第80条的规定,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法律实质目的上以明确海运单下的收货人提货权利的方式,肯定和保障海运单作为区别于提单之外的特殊单证的实践效用。
规范性条文的修订应以修正后的第42条为基础,协调和减少条文间的交叉和冲突。修正第71条、第78条和第79条在于明确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法定债权债务关系,即收货人是基于提单关系向承运人行使提货权。此项提货权是法定的提货请求权,不以特定义务的履行为前提。因此,提单持有人向承运人行使提单中的权利时即转化为收货人。
第86条是关于提货行为权利属性的集中表达。第86条中的“无人提货”一词容易引起歧义,因为不论是收货人不明还是拒绝提货都应该属于“无人提货”,但该条文将“无人提货”与“拒绝提货”并列规定,就存在表述不准确的问题。此外,仔细审视
第86条的迟延提货规定就可以发现,第86条事实上也肯定了提货是收货人的权利,即收货人迟延提货是收货人行使了提货权,但因权利的迟延行使给承运人造成损失,因此应由收货人承担相关的费用。因此,在修改条文时,需要删除现有第86条中“无人提货”和“拒绝提货”两个前置条件,保留关于收货人迟延行使提货权的义务规制。
如此规定,既保留了第86条在适用于记名提单收货人时的合理性规范作用,也避免了在提单的概念范畴内,割裂记名提单与指示提单和空白提单,在法律形式逻辑上使第86条与第71条、第78条、第79条相协调,在法律实质目的上肯定收货人提货的权利属性,并明确不当行使该权利所对应的义务。
参考文献:
[1]
谷浩.论收货人及其权利、义务和责任[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1,12(1):241254.
[2]郝家英.《海商法》71条相关问题分析[M]//赖梁盟.当代法学论坛(2008年第4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103.
[3]司玉琢.海商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90.
[4]TETLEY W.Marine cargo claims[M].3rd ed.Montreal:International Shipping Publication,1988:944.
[5]蒋跃川,朱作贤,杨轶.论收货人是否有必须提货的义务[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6,16(1):2535.
[6]陳宪民.论无单放货的法律问题[J].河北法学,2006,24(4):68.
[JP2][7]李天生.提单对海运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及其解释——基于提单权利性质学说的研究视域[J].东南学术,2012(6):211217.[JP]
[8]刘萍.对“提单非合同观点”的质疑[J].法学,2008(11):137143.
[9]姚新超.“电放”货物的风险及海运单的应用[J].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21(3):1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