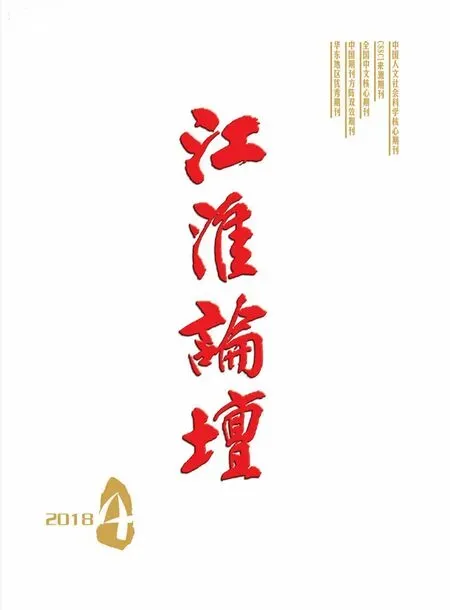讼卦中的诉讼观念及问题
——以匜铭文为参照
2018-08-24刘严
刘 严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 100872)

一、讼卦中的诉讼观念
先引讼卦文本于下: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九五,讼,元吉。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裭之。
关于讼卦所论的内容,古今注家均认为是争讼之事,其中反映的诉讼观念包括下面四点:
第一,诉讼的成因:诉讼双方的诚信被阻塞而无法实现。卦辞中的“有孚窒惕”即是此意。
第二,对待诉讼的态度:诉讼是危险之事,因此应追求无讼。卦辞认为“中吉,终凶,不利涉大川”,意思是说涉身诉讼亦应及时中止才能获吉,如果坚持争讼到底,必会导致凶险的后果,即以诉讼之事如同大川一样危险,不宜轻易涉入。爻辞对这一观念也反复提及,初六“不永所事”,即是中止当前的争讼状态,所以最终可以获吉。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强调回到原来不争讼的状态而保持不变,则能够在争讼这一危险之事中免凶而获吉。九二“不克讼,归而逋”,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无论将“不克讼”解作主观的“不能讼”,还是客观的“不胜讼”,“归”与“复”指的是放弃诉讼或改变争讼心态,恢复到原本“无讼”的状态。这些都体现了对无讼的追求。
第三,实现无讼的方式:一是卑不抗尊。六三可以免凶获吉的原因在于“食旧德”,而“食旧德”的最核心内容即是“或从王事,无成”,意为顺从王意而帮助成就其事,不应夸耀自己的作用。强调对王的谦顺,实际就是下对上的绝对服从。九二、九四两爻一般理解为争讼的双方,二者同为“不克讼”,“归”与“复”的实现方式也相类,但结果却有明显区别。九二是“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意为保留只有三百户人口的领地,暗含着缩小领地的意思,这样仅获“无眚”;九四则不但没有损失而且获“吉”。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二与四这两个爻位所代表的现实社会的政治层次不同。初六虽然“不永所事”,但依然不能避免“小有言”的现实损伤,即遭遇言语中伤。在这种情况下,爻辞仍然将其归结为“终吉”,可见初六之损伤并不在对其吉凶判定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体现了对其本身利益的漠视,而导致这一认识的原因,与初六最居下位有关。由初、二、四这三爻综合来看,讼卦有着明显的在争讼中单方保护居上位者利益的观念,强调了对尊卑秩序的维护。
二是贱讼和追求无讼。上九爻辞“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裭之”,意思是争讼到底,胜诉一方可能会因胜诉而获利,如“鞶带”等荣誉性质赏赐;但这种因胜诉而所获之利,终究会被迅速剥夺,不能长久持有。这里对于不可以胜诉为荣的强调,一方面与上文所说的无讼追求有关,但更多的可能还是希望通过培植这一观念来避免为获利益尊荣而滥讼,在后一层面上,即是实现无讼的手段。
第四,对理诉讼者的要求:中正之德。卦辞“利见大人”中的“大人”,多被认为是中正处理诉讼的人,故“利见大人”既含有对理讼者德行的要求,同时又带有期盼在诉讼过程中遇到中正理讼者的意味。九五爻辞“讼,元吉”,也是在探讨理讼者应具备的德行。从爻象言,此卦只有九五同时得位得中,即以阳爻居阳位,为得位,第五爻为上卦三爻之中爻,为得中;此外九五还居讼卦第五爻,位尊。这决定或要求九五尊者有中正的本质,且与卦辞中的“大人”相呼应。具有中正之德的大人作为理讼者,诉讼便能得到公正的处理。这些反映了对理讼者的道德期盼和要求。
二、匜铭文中的诉讼观念及与讼卦相合之处


对于铭文的解读局部还存在不同意见,其中有两点与本文所论关系较密,因此先略作说明。



李学勤、刘海年和刘翔诸先生认为五夫指司盟、证盟之人。《周礼·秋官司寇》中有“司盟,掌盟载之法”,所论证盟;“司约,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亦是对司盟人员的规定,均与“五夫”相类。在五祀卫鼎与卫盉中都有五个执政大臣参与诉讼的例子。据此而论,将“五夫”理解为司盟、证盟之人更接近史实。
时王的出现昭示了案件处理的合法性;“五夫”是司盟、证盟之五人,并非五个奴隶。据此将该案件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析别如下:

牧牛的罪名:与自己的官长争讼,“似乎不论情节曲直,牧牛已犯以下犯上之罪”。 至于牧牛与师的争讼因何而起,铭文未见,说明其未被纳入审理此案的视野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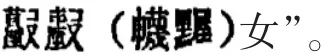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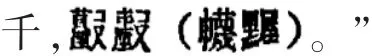
将讼卦与铭文对勘可以看出,二者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一致认识:
第一,赞扬理讼者的德行。铭文中作为案件审理者的伯阳父,数次减轻或命牧牛赎买自己应受的处罚,表现了理讼者不以严刑处理诉讼案件的质量。这彰显了“大人”的宽容之德,说明理讼者运用刑罚时的慎重。但,用刑慎重并不能支持其处理案件的方式是合理的。
第二,无讼的追求。牧牛因讼受罚的遭遇,正是没有及时中止诉讼而得祸的例证,这与讼卦卦辞“中吉,终凶”一致。可见,争讼要及早中止,否则将有灾祸,地位低下一方更应注意。此次案件判决命令牧牛发誓,如再与其师争讼,即获处罚,并列出具体的惩处措施;而且上面分析中已经指出,由铭文可以推知牧牛此前曾经立过与此内容类似的誓言。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图终止牧牛的以下犯上,表现伯阳父与时王对诉讼极力惩处,追求无讼的治理效果以保证统治稳固。
第三,卑不抗尊和权力至上。牧牛两次誓言都是以不与其师争讼为核心内容,而这也是此次案件判决中处罚牧牛的唯一罪名。只要牧牛顺从判决和自己的誓言,改变以往与上级诉讼的态度,遵守卑者无条件顺从尊者的原则,就不会得到灾祸,体现了对牧牛以下犯上的极力惩处。对牧牛的惩罚和命令牧牛所立的誓言,均未提及相应的法律依据 (在当时社会状况下或为普遍现象),且整个案件中并未涉及对师的丝毫约束,这些体现了区别对待尊卑的倾向。
第四,对于个体诚信的关注。对牧牛诉讼权利的剥夺和对尊卑秩序的维护,都是通过立誓的形式来保障,而且在牧牛已经违背誓言的情形下,依然要求其再次立誓,并没有给出新的操作可能。这体现了对无讼的追求还是寄望于卑下者自觉遵守誓言,反映了对于诚信的倚重。
三、讼卦中诉讼观念的问题

根据前文分析大体而论,讼卦的诉讼观念在理论建构上还存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首先,盲目追求无讼,混淆追求的目标和追求手段。讼卦的无讼目标,值得追求。讼卦中无讼理想,或是在社会治理良好的基础上实现的,《史记·周本纪》有载: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
虞、芮人受周文王治下民风皆谦让的感召,主动放弃诉讼。在讼卦的设置中,对九五中正处理诉讼的要求和上九不要以胜诉为荣耀的劝戒,亦表现出实现无讼需要妥善处理诉讼。这表明,讼卦承认诉讼的存在,亦强调只有中正处理诉讼才能得吉。可见无讼应是国家治理达到一定水平的自然结果,并非如九二、九四区别对待尊卑以压制卑下者诉讼的方式实现无讼。从铭文案例中牧牛起誓的内容来看,只要师状告牧牛,牧牛就要受到惩罚。以刑罚恐吓的方式,强制牧牛无条件服从其师,实质是通过剥夺牧牛诉讼的权利,选择性地抑制诉讼的产生,稳定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实现形式上的无讼。
此外,讼卦将诚信受阻视为争讼的起因。按照这种认识思路而言,只要保障诚信就能实现避免争讼的结果。铭文案件中判定牧牛状告其师有罪的根据在于他违背所立誓言。表面看来,这正是通过推重诚信来追求无讼,但铭文中的诚信只是针对是否遵守誓言而论,至于誓言内容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却未予讨论。这意味着这种诚信的起点有可能即是不合理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此处的诚信也就只能提供一个事实判断,而失去了其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的效力。
以上这些问题实际上将无讼的追求目标混淆为实现手段,为怠政或谋私提供空间。这很大程度上是讼卦中无讼观念的内涵不明晰导致的。

讼卦九五之吉与铭文中时王与伯阳父处理牧牛案件的方式,及其逼迫牧牛签署永不与其上司诉讼否则处以严刑的誓言,都反映了上层权力的无限性及随意性,与讼卦对理讼者“中正”的要求有距离。瞿同祖先生对此有深刻揭露:“贵族为了适合其彻底统治的要求,不但把握住统治的工具,并且设法垄断法律,使法律成为不公开。……他的命令就是法律,不容人怀疑,更不容人质问,人民完全在他的操纵中。 ”“清官”、“圣王”等称谓,均凸显儒家忠孝核心观念下对君主、官员道德自律的想象,这只是“体现了民众的政治理想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政治幻想”,难以实现,且为人治提供土壤。“利见大人”与九五的“讼,吉”,包含着对在位者的绝对信任和毫无限制,亦是“人治”的表现。
再次,区别对待尊卑、抑制诉讼,意在维护尊者的权力。讼卦九二与九五的差异反映了九五权力的绝对化,九二、九四的区别则反映了区别对待尊卑。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归复的状态不同。 九二言“归而逋”,“逋,亡也;亡,逃也”。 九二“逃”归,与此相较,九四“复即命”较为从容。其二,结果不同。九二“无眚”,“眚”引申为过误;九四“吉”。 从反方向而言,九二如继续诉讼则“眚”,结果有确定性;九四如有违背,结果是“不吉”,其弹性较大。其三,实现结果的条件不同。九二“无眚”,需主客观两条件具备,即主观“归而逋”,客观“其邑人三百户”;九四只要主观“复”、“安贞”便得“吉”。二者所以有此差异,只因居位不同。铭文中,师和牧牛亦因地位不同而受区别对待。后世对诉讼者有更多批判,称之“意怀险恶,性又刚健”,“不守本分、不知义理,专要争强争弱之人”,这是用道德言语告诫和教化人民;而人民盲目信奉“清官”,却很少提及限制官员权力和争取平等。可见,讼卦本身的贱讼、尊卑不抗、盲目信服九五,都具有教化意义且影响深远。
这些不足的实质是,讼卦中凡是对尊者的期盼和要求,在铭文中均未实现;对卑者的要求以及违背要求即凶的后果设定,在铭文中却完全实现。讼卦得以落实及未能落实的部分,在西周的诉讼案例中一目了然。若为整个社会良好发展计,在维持卑者不滥讼尊者的情况下,当反思如何落实理讼者公平对待不同地位的人,从案件本身着手,弄清是非曲直,依法裁决,最终完成无讼的社会建设。
然而后世传统注疏者,并未因西周诉讼中就存在的现实问题,指出讼卦解读中存在不足,进而提出诉求以保证理讼者的中正、诉讼者的平等地位和处理案件的公平以完善经典。历代注家根据讼卦九二的《象传》“自下讼上,患至掇也”,在不论是非的前提下,弘扬卑不抗尊。荀爽言“下与上争,即取祸害,如拾掇小物而不失也”,孔颖达言“自下讼上,悖逆之道,故祸患来至,若手自拾掇其物,言患必来也”,程颐言“自下而讼其上,义乖势屈,祸患之至,犹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来之德言“自下而讼上,义乖势屈,祸患犹拾而自取”。即,不论对错,以下讼上,卑者必遭灾祸。
这是传统注疏家在经典注疏中传承和维护尊卑之防,并以之教化百姓,进而维护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明证,也是儒生掩盖社会不公、粉饰太平的重要表现。周光庆先生认为语出先秦儒家、至两汉而盛行的“政令教化”,“是(教化者)根据统治者的意愿,以安定和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为己任”,有潜在保守性且可能发展为反动性,难以推进社会进步。由此观之,此言不虚。尼采对知识阶层推行的教化有更激烈的批判:“它(教会和上层社会推行的灵魂教化)使各种各样的弱者和受压抑者能够进行高超的自我欺骗,使他们能够把软弱解释为自由,把软弱的这种或那种表现解释为功绩。”让弱者通过教化,把自己的无能当做善良、把卑贱的怯懦理解为谦卑、把向仇恨对象的屈服称为顺从。周光庆和尼采所言或有激进,但他们对古代文化及传统观念的批判不无道理,即在弘扬讼卦之前,需要做系统研究和批判。
总之,讼卦中强调理讼者公正、不能以胜诉为荣、慎重对待诉讼和致力于追求无讼的太平世界等观念,如今仍有意义,这是经典传承的必要和优势;但是讼卦隐含着尊卑区别对待、盲目信任权威和毫无约束权力设置等解读的空间和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世的司法不公、尊卑差等提供观念支撑和理论依据。可见,讼卦中显而易见的优势值得发扬,而其隐晦、复杂、严重的问题,更值得发现、批判和纠正,这样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任何文化都是立体的存在,并非取其阳就能舍弃其阴,即简单选择经典对当代有积极意义的名词进行弘扬,恐难达到预期效果,还可能导致糟粕泛起。所以,弘扬传统文化,首先做的是研究传统文化,进入其系统内部去观照,并探究其在历史中起到的作用。唯有如此,才可能有效甄别哪些内容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现代人的需求,哪些需要批判继承,哪些需要彻底废弃。这是传统文化复兴面临的重大课题。
注释:
(1)按:爻位不同,境遇不同,这体现古人因时、因势制宜的智慧。但其中亦包含不同时势的人,应被区别对待。这种思想与中国的古代阶层社会有着复杂关系。
(2)李学勤认为牧牛是职官名,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殷周金文集成 (第二册) [M].北京:中华书局,2007:1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