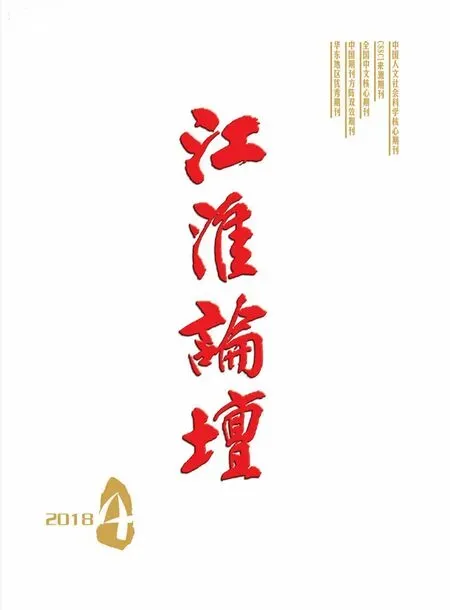重新审视美学学科与中国美学问题*
2018-11-12古风
古 风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2)
从20世纪初王国维等人引进美学到现在,100多年来美学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显学。目前,在全球化语境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由自强到自信,正在稳健地走向世界。美学研究遇到了百年难逢的好时机。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尤其是一些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诸如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学科边界、中国美学以及与世界美学的关系等等,都是我们要重新思考和研究的。
一、从柏拉图美学重新出发
267年来,美学学科由德国到欧洲,再从西方到东方,已蔚为大观,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科。但是,鲍姆加登在创立“Aesthetik”学科为美学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将美学研究引入一个狭隘的玄学误区。因此,迄今为止在美学学科的性质及研究对象等基本问题上,人们的看法还不全面,也没有达成一致,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诸如美学的学科定位、美学的研究对象、美学的基本范畴、美感的心理结构、审美活动、审美经验、美与丑、美学与艺术理论的关系、审美与道德的关系、审美与功利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几乎都需要重新反思。这些问题如不解决,不仅会影响美学研究的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各国之间的美学交流和对话。因此,本文想为解决这些问题寻找一个新的立根点,这就是:我们应该放弃“鲍姆加登式”的美学,因为“感性学”并不是“美学”,“感觉”也不能等同于“美感”。关于“感觉”和“感性”的研究,应该归入“心理学”而不是“美学”;我们也应该放弃“黑格尔式”的美学,因为“艺术哲学”也不是“美学”,“艺术”也不能等同于“美”的全部内容。关于“艺术”的研究,应该交给“艺术学”而不是“美学”。所以,我们应该回到“柏拉图式”的美学上来,即以人类的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使“美学”成为名副其实的“以美为对象的学问”。在这一点上,我们绝不能再将美学研究禁锢在“Aesthetics”的名称之内了!也绝不能再将美学的研究对象束缚在“艺术”的范围之内了!我们一定要从德国人设计的“美学圈套”中走出来!
为什么我们要回到柏拉图?或者从柏拉图美学重新出发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想把“美学”从“感性学”特别是从“艺术哲学”中解放出来;二是因为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谈论审美问题的集大成者和总结者,也是谈论审美问题最集中并最早试图建构美学学科的人。他对于审美问题的思考和实际贡献比鲍姆加登要大一些。具体说来,柏拉图对于美学的贡献有如下几个方面:
1.审美对象:
人类:人、小姐、我、你、身体、动作
宗教:神
社会:人生、饮食、色欲、制度、习俗、幸福
文化:知识、学问、颜色、演说
艺术:图画、雕刻、音乐、诗文、故事、竖琴、乐器
器物:汤罐、汤匙、器皿、商船、战船、黄金、象牙、石头
动物:母马、公鸡、野鸡、猴子
2.审美范畴:
美、丑、善、真、味、香、悲剧、喜剧
快感、视觉快感、听觉快感、痛感、滑稽、笑
形体美、心灵美、外表美、实际美
美的东西、生活方式的美、美的形体、形式美
美本身、美的本质
3.审美问题:
什么是美? 美是什么? 什么是丑?
什么东西是美的? 美本身是什么?
美的定义问题 美与善的关系问题
美与真的关系问题 美与快感的关系问题
痛感与快感问题 悲剧与喜剧问题
美与爱的关系问题 美与色欲的关系问题
具体美与抽象美 部分美与全体美
相对美与绝对美 美与时间问题
4.审美方法:
由具体到一般的逻辑演绎法
由形下到形上的逻辑演绎法
5.审美体系:
个别的美的事物→一个美形体→两个美形体→全体的美形体→美的行为制度→美的学问知识→美的本体
6.审美学问:
以美为对象的学问。
这些内容主要来源于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篇》《会饮篇》《斐利布斯篇》等。但是,值得指出:这些美学思想不一定都是属于柏拉图个人的,而是属于柏拉图那个时代的,如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还有之前的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等人,或者说属于古希腊的。只是由于这些内容取自柏拉图的著作,因而柏拉图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所以也可以看作是属于柏拉图的。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那样:“柏拉图在他的对话里,并没有亲自出来说话,而只是介绍苏格拉底和一些别的人作为谈话者,在这些人中我们常常弄不清楚那一位真正代表柏拉图自己的意见。”“柏拉图把他的思想纯粹放在他人的口里说出来,他自己决不出台,因而充分避免了一切肯定、独断、说教的作风。我们看不见他作为一个叙述的主体出现……就对话中所叙述的内容来说,哪一部分属于苏格拉底,哪一部分属于柏拉图,那是用不着多去研究的。我们很可以确定地说,从柏拉图的对话里我们完全能够认识他的体系。”“在柏拉图的对话里,他的哲学是十分明白地表达出来了的。”所以,本文就将这些看作是柏拉图对于美学的贡献。
与鲍姆加登美学立根感性、康德美学排斥功利和黑格尔美学忽视自然等相比,柏拉图美学的学术视野要开阔得多。它既古老,又很现代。因为现代美学研究的许多问题几乎都可以在柏拉图那里找到出处。尤其令人惊喜的是,他在《会饮篇》中,不仅提出了建立“以美为对象的学问”,而且还精心设计了“审美体系”框架和美学学科的模型。此后西方美学2300多年的发展,基本上都没有超出柏拉图美学的范围。因此,柏拉图才是西方美学真正的奠基者和美学之父。所以,我很赞赏法国学者于斯曼的说法。他认为,“美学在苏格拉底回答希庇阿斯(见《大希庇阿斯》)美不是一千零一种对象所具有的特殊属性之日就诞生了。”柏拉图美学“几乎是以后所有美学的序言。”因为,对于美学学科来说,这些内容无疑是最具有开创性的。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指出过。所以,我们重新审视柏拉图美学,就是想通过它了解古希腊学者使用过哪些美学话语,提出和思考了哪些美学问题,运用了哪些美学研究的方法等。至于他们的美学观点正确与否,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因此,我们回到柏拉图,就是要回归“以美为对象的学问”,即回归到名副其实的“美学”,把被鲍姆加登、康德和黑格尔等歪曲了的和遮蔽了的东西重新寻找回来,恢复“美学”的真面目。美学研究应从柏拉图美学重新出发。
二、中国有没有美学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美学。鲍桑葵说,中国“没有关于美的思辨理论”。 这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美学。还有人认为,中国现代美学是“西方美学在中国”,不是真正的中国美学。这是说中国现代没有美学。总之,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美学。
那么,中国有没有美学呢?
众所周知,“美学”是德国人的发明,鲍姆加登为其命名,康德和黑格尔完善了其理论体系。如果按照发明权来说,只能是德国有美学,其他国家没有美学。但是,在欧洲人的观念中似乎不是这样,因为他们认为除了德国以外,法国有美学,英国有美学,意大利有美学,甚至连年轻的美国也有美学。那么,为什么就不承认中国有美学呢?因为,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与中国一样,也不具有“美学”的发明权!如果按照“美学”学科诞生的时间来说,应该是1750年以后有美学,而1750年之前没有美学。但是,在欧洲人看来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古希腊有美学,古罗马有美学,文艺复兴时期有美学。尽管当时有人认为,“在中世纪, 美学是不存在的”,“中世纪没有美学”。 然而,吉尔伯特和库恩还是在其《美学史》中写了一章“中世纪美学”。这就等于说,欧洲古代有美学。那么,为什么就不承认中国古代有美学呢?因为,事实上欧洲各国古代与中国古代一样,是没有美学的。那又为什么说它有美学呢?鲍桑葵给出的理由是:欧洲古代虽然没有“美学”学科,但却有“美学事实”。认为,“美学事实的存在却要比‘美学’一词早得多。 ”由此可见,鲍桑葵在评判欧洲和中国有没有美学时,分别采用了“美学事实”和“思辨理论”的双重标准。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难道说中国古代就不存在“美学事实”吗?显然不是这样。
我认为,西方学者之所以形成“中国没有美学”的错误观点,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欧洲中心论”的偏见。鲍桑葵把中国没有美学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同进步种族的生活相隔绝”。正如托马斯·门罗所批评的那样,鲍桑葵的看法是“狭隘和荒谬”的。二是对于中国美学缺乏了解。尽管也有一些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审美文化的著作很早就传播到了欧洲各国,但只是局限于汉学家的小圈子内。对于广大的欧洲各国读者来说,由于受“欧洲中心论”和意识形态等局限,也可能只是知道一点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如鲍桑葵就曾坦言谈论中国美学“确实不在我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到现在100多年过去了,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多少。如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韦尔施在他的著作《重构美学》中译本序言中说,该书所谈的审美经验“大都是欧美的”,由于“手边没有中国的第一手材料”,所以没有谈到中国。很显然,这是他的托词。其实,他没有谈论中国美学是观念问题,而不是材料问题。只要他想写中国的审美经验,手边没有材料,还可以到图书馆里去找,甚至想尽一切办法去找。但是,在我国学者的美学论著中,如果完全不用欧美国家的材料,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状况100年来都是如此。可见这与我国读者和学者对于西方各国文学、艺术和美学了解的广博、细致和深入程度,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事实上,审美是人类的一种本质力量。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会有审美活动发生,就会形成审美观念和审美思想,也就会有美学。因此,德国有美学,法国有美学,美国有美学,中国也有美学。我们不妨以西方美学为参照来论证这个问题。我认为,如果美学是柏拉图式的关于“美”的学问,中国有美学,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关于“美”的谈论比比皆是;如果美学是鲍姆加登式的“感性学”,中国有美学,因为中国具有最看重“感性”的审美文化传统;如果美学是黑格尔式的“艺术哲学”,中国有美学,因为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灿烂的艺术和最丰富的艺术理论。总之,中国有美学,西方有什么类型的美学,中国也有什么类型的美学。这倒不是要讨好西方,才用“西方的标准”来谈中国美学;而是要向西方证明,中国美学是存在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看是否有没有“美学”名称的存在,这不是标准。建立美学学科是必然的,至于这个学科用什么名称则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鲍姆加登在创立这个学科时就先后用过“诗的哲学”、“广义的逻辑学”、“美科学”和“美学(Aesthetics)”等。 尽管后来“美学(Aesthetics)”的名称约定俗成了,但是却一直受到西方学界的质疑。至于将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艺术”的范围之内,看作“艺术哲学”,也是大成问题的。这一点早就受到西方明智人士的批评。德国美学家玛克斯·德索认为,美学的“定义过于狭隘”,不能够容纳不断出现的新艺术现象。因此,他尝试着在“美学”之外,建立一个被名为“一般艺术科学”的新学科。法国和美国的美学家也认为,美学的传统定义过于狭隘。但是,他们不同意德索的“双名说”,而是仍采用“美学”的名称,只是对其定义作了“较新的和较广义的解释。 ”甚至有更极端的观点,如法国学者保尔·瓦雷利对于 “美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质疑。认为,艺术不是科学,因而对于艺术进行科学研究只能加速艺术的消亡。所以,他说:“美学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如果美学能够存在,艺术将因它而消亡。 ”
因此,中国有没有美学,倒不在乎看它有没有“美学”名称,而是正如鲍桑葵所说,要看它有没有“美学事实”。那么,什么是鲍氏所说的“美学事实”呢?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指人类的审美活动,包括审美创造、审美鉴赏和审美理论的活动。为了节省篇幅,我只以“锦绣”为例来说明中国的美学事实。从审美创造看,“锦绣”是中华民族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它分为“锦”和“绣”两大类,前者用“织”的方法,后者用“刺”的方法,材料都是染成各种色彩的丝。由于材料稀缺和工艺复杂,早期只是贵族的专用品。同时,也作为国家礼品用于外交活动。于是“锦绣”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符号。随着对外贸易,还形成了“地球人”都知道的“丝绸之路”。在传承至今的“锦绣”之中,不仅承载着中国数千年的宗教、政治、军事、经济、风俗、文化和外交等信息,而且还浓缩着5000年中国文明史;从审美鉴赏看,“锦绣”很早就成为人们的观赏品。它色彩斑斓,花纹繁多,图案丰富,最具有视觉冲击力。因此,在上古文献记载和先秦诸子的著作中,都将“锦绣”看作最美的事物。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现代。《辞源》说:“锦为美物,因以喻鲜艳华美。”后来,“锦绣”演变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大凡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绘画书法等,都成为它所表现的对象,甚至形成了粤绣、苏绣、蜀绣和湘绣等不同地方风格的艺术流派。就以小小的绣品“荷包”来说,它历史悠久,品类繁多,成为不同地方和民族青年男女的定情物,流传着许许多多的《绣荷包》民歌。它承载着风俗、爱情和艺术,也表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从审美理论看,在古老的《尚书》和《考工记》等众多文献中,就有关于“锦绣”审美经验的记载。这些审美经验深入人心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审美模式。即以“锦绣”为审美参照物,来谈论其他事物的美,形成了诸如锦石、绣壤、锦鱼、锦鸡、绣眼鸟、锦绣山河等审美话语。近几年,我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锦绣与文学关系十分密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审美批评。这些审美经验经过长期的积累,出现了诸如丁佩的《云间丁氏绣谱》、沈寿的《雪宦绣谱》、朱启钤的《丝绣笔记》和杨世骥的《湘绣史稿》等审美理论著作。总之,这些就是中国人关于“锦绣”的美学事实,或者说是“锦绣美学”。但是,这只是中国人千千万万“美学事实”中的一件。因此,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证明中国古代是有美学的。
多年以来,外国同行大多认为,中国现代美学只是西方美学的“翻版”,是西方美学“在中国”的一种表现形式,因而中国现代没有美学(也有一些中国学者附和这种说法)。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看法。100多年来,中国学者对于美学研究的高度关注、积极参与和刻苦探索,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在这100多年之间,中国现代美学研究出现了三个高潮:即20世纪初至30年代,主要是西方美学的引进和美学知识的普及,以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吕瀓等人为代表;50至60年代,主要是建设中国新美学的思想统一和理论准备,以朱光潜、蔡仪、李泽厚、吕荧、高尔泰等人为代表;80年代至今,是中国美学全面发展和繁荣时期,以宗白华、李泽厚、王朝闻、刘纲纪、蒋孔阳、叶朗、周来祥等人为代表。从1980年以来,全国和部分省、市都成立了美学学会,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还设立了美学研究机构,主办了《美学》《中国美学》《外国美学》《美学年鉴》《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文艺美学研究》《美学思想》《审美文化丛刊》和《美与时代》等刊物。这100多年来,中国有多少人研究过美学?翻译了多少篇(部)外国美学著作?撰写了多少篇(部)中国美学著作?成立了多少个美学研究机构和组织?召开过多少次美学会议?这些几乎是一笔笔很难精确统计的数字。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创立自己的美学学说,诸如王国维的“境界说”、梁启超的“趣味说”、蔡元培的“美育说”、宗白华的“艺境说”、朱光潜的“主客统一说”、蔡仪的“典型说”、高尔泰的“自由说”、李泽厚的“实践说”、蒋孔阳的“创造说”、周来祥的“和谐说”、叶朗的“意象说”等等。真可谓是学说纷纭,气象万千,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总之,中国现代美学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是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将在另一文中论述),形成了“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鲜明特色。这一点在世界美学研究格局中是独一无二的。怎么能说中国现代没有美学呢?
三、中国美学正在走向世界
20世纪,美学学科从西方到东方,向世界各国传播。前50年,欧洲是世界美学的中心,各国美学基本上是在西方古典传统美学的范围内发展;“二战”以后,特别是后50年,世界美学的中心由欧洲向美国转移。当今世界各国美学研究发展状况虽然不平衡,但却表现出共同的趋向,即逐渐偏离了传统美学的方向,走上了“泛美学”、“反美学”(或者说是“丑美学”)和“非美学”(法国学者阿兰·巴迪欧提出的概念)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
从宏观上看,各国美学研究首先是运用美学学科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对于各自国家的审美经验进行了全面而有深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是,其缺陷是西方学者国别意识比较严重,知己而不知彼,学术视野过分狭窄。这从他们的论著中所引证的资料就可以得到证明。据统计:德国学者德索的《美学与艺术理论》重点引用德国的资料,共265人/291次;美国学者朗菲德的《审美态度》重点引用美国的资料,共27人/56次;法国学者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重点引用法国的资料,共178人/590次。因此,这些学者的美学研究“都带着自己的国别背景,德国的以德国为主,法国的以法国为主,英美的以英美为主。 ”这种状况由来已久,早在 1956年,托马斯·门罗就指出了这种现象:“美国美学家仍然倾向于主要引用美国人的作品,而英国学者只引用英国人的作品,法国学者只引用法国人的,德国学者则只引用德国人的。”他批评说这是“孤立主义”的表现。这说明了西方学者在美学研究上是保守的和狭隘的。但是,更加保守和狭隘的是,德索、朗菲德和杜夫海纳等西方学者对于东方美学的忽视,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于埃及、印度、中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美学文献一次也没有引用。这与他们的先人黑格尔等人相比就差得远了。归根到底,其主要原因还是“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在作祟。
因此,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不了解中国美学,而且也不情愿去了解中国美学。正如德国学者卜松山所说:“在西方国家,同样也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由于我们长期处于强国地位,以至我们已经不会对其他的文化给予充分的重视了,我们没有看到去理解或者学习这些文化的必要性。”这与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美学的热情和研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中西美学要真正地交流和对话,中国美学要真正地走向世界,仅仅靠我们学习、理解和研究西方美学是不够的,也需要西方学者理解和研究中国美学。现在,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美学并不了解,也不理解,甚至还有很多误解。譬如他们“一谈起中国美学,以为只有‘道’”。因此,我们需要理解。早在1934年,林语堂就说过,“中国曾经被人极大地误解过……在被理解与被称作伟大之间,中国宁愿选择前者。”我们现在的心情亦如此。
那么,有多少外国学者对于中国美学能够真正的理解呢?据我所知,大概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诸如日本的笠原仲二通过对汉字的考证和分析来探寻中国古代人的审美意识,法国的雅克·马利坦对于中国艺术美学特点的深入分析,美国的托马斯·门罗对于中国美学家陆机、刘勰、谢赫和蔡元培、朱光潜、蔡仪等人的了解,德国的顾彬对于中国美学“意境”范畴的理解和卜松山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现状的批评等。从这些人的论著看,他们对于中国美学的了解还是十分有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已经迈开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992年,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卜松山译)被译成德文出版;1995年,布洛克与朱立元合作,编辑出版了《当代中国美学》论文集英文本;1999年,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被译成韩文出版;2010年,李泽厚的美学论著被收入《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世界美学大会也逐渐重视对于中国美学的研究。1998年9月,在卢布尔雅那召开的第14届世界美学大会上,有立陶宛学者L.波希凯蒂的《中国审美本质的两个基本范式:道与仁》、日本学者笠原明子的《从中国早期绘画中所看到的身体观念》和田中英道的《“气韵生动”的美学——与西洋艺术理论的比较研究》等论文。2001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15届世界美学大会上,设立了“中国美学”专题。2007年7月,在安卡拉召开的第17届世界美学大会上,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在题为《艺术与宗教》的主题发言中,引用了不少中国古代美学的文献和概念。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积极参加世界美学大会,发出了中国的声音。中国在国际美学界的地位也逐步在提高。2006年6月,国际美学协会执委会在成都召开了理事会。同年10月,在天津召开了第4届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201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2013年7月,在波兰南部克拉科夫召开的第19届世界美学大会上,有25位中国学者参加会议,著名学者高建平当选为国际美学协会主席,还有多位中国学者先后成为国际美学协会执委。总之,这些对于西方美学来说或许并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中国美学来说却是迈开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当然,我们十分清楚:中国美学要真正走向世界,路途还很遥远。这不仅要靠我们中国学者的努力,也需要世界各国学者来共同参与。现在已经具备的有利条件是: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美学、近代美学和现代美学有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我们对于西方美学的研究已有百年的积累,既知中又知西。如果再加强外语学习,提高外语水平,我们就能够将中国美学“原汁原味”地翻译出去,在国际美学界真正树立起中国美学的形象。同时,我们也希望西方学者重视中国美学,研究中国美学。如果借用明代小说批评家叶昼的话说:“东人要修西方,西人要修东土。 ”中国美学只有在中西学者、中外学者的互动合作中,才能够真正地走向世界!
但是,中国美学走向世界还不是我们研究美学的最终目标。那么,我们研究美学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我认为,从学术方面来看,有三点:一是“各美其美”,研究中国美学,建立中国美学体系;二是“美人之美”,尊重和学习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审美经验和美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三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研究人类共同的审美经验,总结人类共同的审美规律,建构世界美学体系。因此,世界美学既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和而不同”的一面,又有“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的一面,是两者的统一。从实践方面来看,有四点:一是美化自我,包括内在美化与外在美化,提升自己的人格,完善自己的形象;二是美化社会,包括美化社会秩序和美化社会生活,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创造优美的社会生活;三是美化环境,包括美化自然环境和美化社会环境,创造平衡、整洁和美观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四是美化艺术,纠正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发展中的偏差,克服各种“艺术恶作剧”的弊病,创造真正的审美的艺术。因此,美学所具有的功能,是哲学、伦理学和艺术学所无法取代的。
注释:
(1)柏拉图《会饮篇》,朱光潜编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页。这里只是想把“美学”从“感性学”特别是从“艺术哲学”中解放出来,并不是要倒退到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上去。最近,美国学者玛丽·马泽斯尔也提出了相类似的观点。她认为,美学应该“回到传统,认为美学探讨美的概念”,见玛丽·马泽斯尔《美与批评家的判断:重绘美学》,收入彼得·基维主编《美学指南》,彭锋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2)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3)朱光潜先生认为,“所谓‘以美为对象的学问’,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美学,这里‘美’与‘真’同义,所以它就是哲学。”(《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我对此有不同看法。因为,根据上下文语境看,论者所说的是“美”的问题,而不是“真”的问题。所以,柏拉图虽然没有用“美学”这个词,但实际上说的就是“美学”,而不是“哲学”。
(4)鲍桑葵《美学史》对于柏拉图美学提出一些有价值的理解和分析,但评价不是很高。吉尔伯特和库恩的《美学史》对于柏拉图美学的评价有错误,甚至有自相矛盾之处。譬如说:“柏拉图的著作与其说是美学著作,不如说是反美学的著作。”“柏拉图除了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之外,似乎在美学方面什么也没有建立。”(《美学史》上卷,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73—74页)他们所关注的是柏拉图对于“艺术”的论述,而不是对于“美”的论述。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者对于柏拉图美学的评价多偏低。因此,我认为,应该对柏拉图美学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
(5)德国学者卜松山认为,“中文的‘美学’这一字眼,是合乎将美学看作是一种关于美的理论的西方主流美学的意思的。”见[德]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刘慧儒、张国刚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页。
(6)参见[德]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刘慧儒、张国刚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页;周来祥《新中国美学50年》,《文史哲》,2000年第4期。
(7)我16年前,就对于这个问题有过论述。请参阅古风《意境与当代审美》,《思想战线》,2001年第6期。
(8)如黑格尔说:“Asthetik这个名称不恰当,说得更精确一点,很肤浅。”(《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在上世纪20年代的德国和40年代的美国,对于“美学”名称的合理性都有过质疑。(参见[美]托马斯·门罗《走向科学的美学》,石天曙、滕守尧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15—219页)
(9)参见古风《丝织锦绣与文学审美关系初探》,《文学评论》,2007年第 2期;古风《“以锦喻文”现象与中国文学审美批评》,《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0)共有三种《中国美学》不定期刊物,先后由首都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主办。
(11)关于世界各国的美学研究状况,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1.[德]沃尔夫哈特·亨克曼《二十世纪德国美学状况》,周然毅译,《社会科学家》,1999年第2 期;2.[法]雷蒙·巴耶《二十世纪的法国美学》,刘韵涵译,《美学译文》,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版;3.[美]托马斯·门罗《美学在美国的最新发展》,见其论著 《走向科学的美学》,石天曙、滕守尧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 175—187 页;4.[美]彼得·基维《导言:今日之美学》,见其主编的《美学指南》,彭锋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5.李心峰《回顾历史,开辟新境——日本美学近况》,《文艺研究》,2000 年第 2 期;6.邱紫华《20 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历史反思》,《文艺研究》,1999年第6期。7.艾士薇《非美学:对传统美学的反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23日,第5版。
(12)参见[日]笠原仲二《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魏常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法]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刘有元、罗选民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美]托马斯·门罗《东方美学》,欧建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德]沃尔夫冈·顾彬《审美意识在中国的兴起》,王祖哲译,《中国美学》,2004年第 2期;[德]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刘慧儒、张国刚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
(13)资料来源如下:王小明《第十四届国际美学大会综述》,《文史哲》1999年第2期;《中华美学学会通讯》,2007年第2期;高建平等《从国际美学大会到中国当代艺术》,《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6期;《中华美学学会通讯》,2007年第1期;《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讯》,2013年第1期。
(14)叶昼的《西游记》评语,引自宋俭等编注《奇书四评》,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
(15)这是1990年费孝通在其八十岁生日欢叙会上提出的观点,引自刘俐俐《“美人之美”为宗旨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的几个论域》,《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