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你与故乡之间缺一个奈保尔
2018-08-03张艺芳
文_张艺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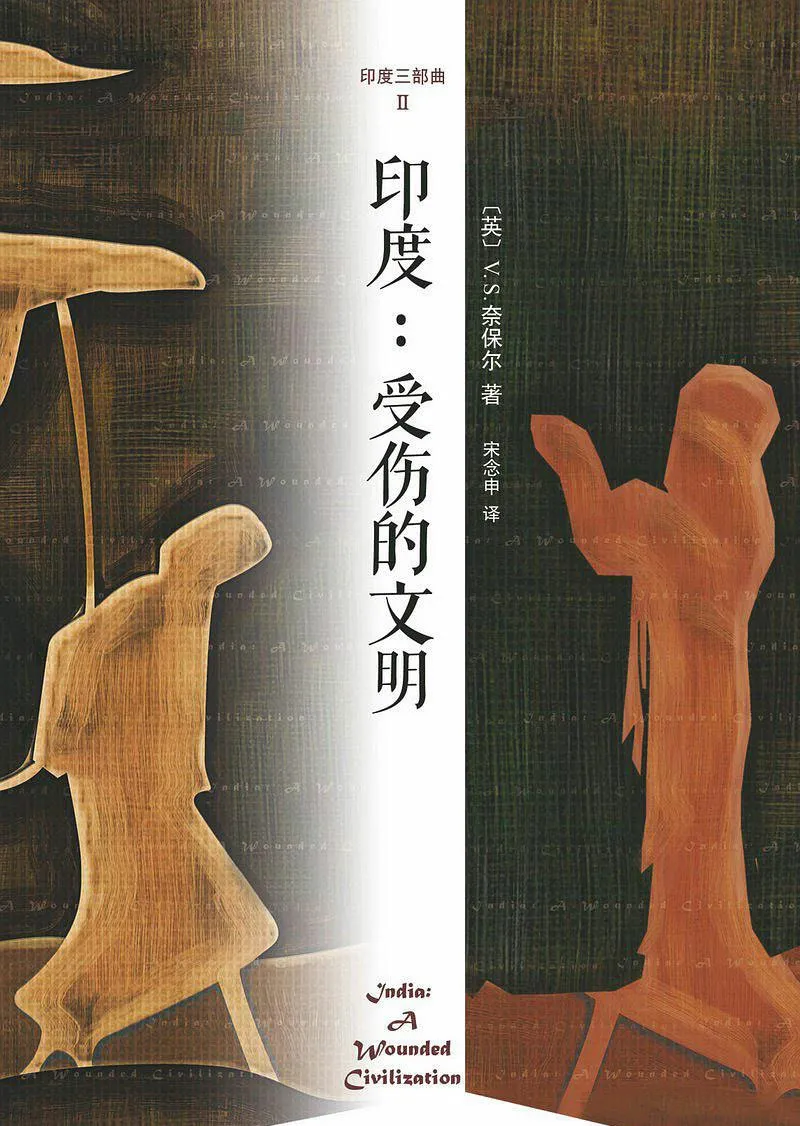
8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奈保尔去世。奈保尔的颁奖辞是:奈保尔的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人们从被压抑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奈保尔之所以需要中国读者反复阅读,因为他笔下的故乡——印度,与中国有着太多相似的经历。同为文明古国之一,社会中残存着传统文化和信念的遗留,社会在“旧”的传统观念与“新”的经济时代的摩擦中前进。
作为社会观察家的奈保尔,三次以火车慢游的方式游走故乡。1964年,第一次返回故乡,记忆中的印度早已不在。祖父的传奇故事依然在家乡流传: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前往英国特立尼达小镇,养家糊口,期间还回国为亲眷赎回田产,是一个印度婆罗门家族的成功移民实例。
奈保尔看到的是一个在探索民主政体、五年经济计划中的印度:肮脏、贫穷,种姓阶级制度让人们世世代代活在自己的身份中,低贱种姓做着脏累的工作,码头的车夫,似乎正是印度的“骆驼祥子”。
从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印度人——公务员、厨子、向导、酒店管理者、锡克人身上,他思考和分析甘地的社会改革,以及失败的成因,分析印度教和种姓阶级制度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他亲眼看到公务员低效的办事风格,堆积如山的政府文件,繁冗的办事流程,而他们成为公务员,竟然只是因为——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公务员体系腐败不堪,收受贿赂,本来的惠民工程也因为工人吃回扣大打折扣。
十三年之后,当他第二次来到印度,眼见城市化进程中的孟买,修建好的高级住宅楼被围在低矮的工人棚户区中间,市政却无法使市民达成是否为工人划地修建居住区的一致意见。他愤慨地写下: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种姓和位置,每个群体都生活在远古时代便划定的各自的区域之内,贱民和拾荒者住在村子尽头。残酷已经不具含义,它就是生活本身。
因而当他看到衣着整洁、身材秀美的印度人,便忍不住感叹:肮脏腐乱、视人命如草芥的印度,竟也能产生出这么多相貌堂堂、温文儒雅的人物。印度制造出太多人口,结果却弃绝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
站在维查耶纳伽尔宽阔的庙前大道上,这个在侵略和战争中、在废墟之上不断重建的城市,他开始反思印度停滞不前的原因——史书历数着战争、征伐和劫掠,却没有关注智识的枯竭,更没有留意这个国家的智识生活是怎样的——这个国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还是在遥远的过去完成的。印度的危机不只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大的危机在于一个受伤的古老文明最终承认了它的缺陷,却又没有前进的智识途径。
他意识到从文明古国到现代世界所需经历的种种问题,田园牧歌已不可能,现代世界亦不能滑稽模仿,寻找文化上的动力,通过智识途径让古老文明焕发生机,是奈保尔所能想到的。
第三次来到印度,已是1990年,奈保尔认为:眼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指引了一条更真实、更普遍的道路。这也正是他进行长途旅行、展开系列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他曾向读者抱怨:狄更斯之后,这群(英国)作家越来越不愿意探索自己的心灵。而印度小说家那拉扬对民族性的剖析,又不能让他信服。他看到社会发展中、小富即安的印度民众,叹息他们对探索“人类可能性”缺乏兴趣。
当今的中国,也一度接受着这样的审视目光。外国的写作者同样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充满好奇,何伟在中国读者中因《寻路中国》《江城》《奇石》《甲骨文》等书知名。何伟谈道,“中国就像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他写到北京的四合院以及院子里围绕厕所展开的社区文化,他跟随自由探险者和考古爱好者调研长城,试图解释长城在中国文化中的符号意义。
外国作者对中国社会的非虚构描写,除开作者的幽默,在嘻嘻哈哈大笑一番之后,也正像看到照到不同侧面的镜子。对于印度,奈保尔是个异乡人,他的视角和价值观都是英国式的,敏锐,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对于中国,如想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样需要一个全景式的社会观察,推动智识的进步。
近些年,国际教育火热,留学越趋低龄化,中国亦将成为他们回不去的故乡。多年之后,我们希望,那面镜子不仅仅出自一个异乡人,也出自一个真正了解本国文化的人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