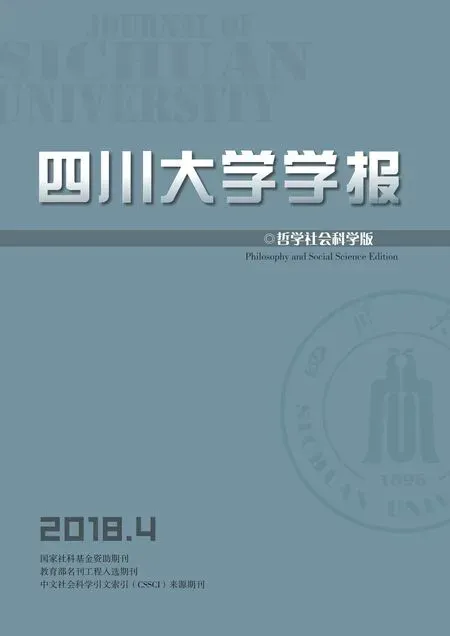艺术作品中的隐匿性“大地”
2018-08-03
“在海德格尔之前,哲学中没有大地的问题。”*Nijhoff, Earth and Go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artin Heidegger, Netherlands: The Hague, 1961, p.33.“大地(Die Erde)”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哲思语词,主要出现于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等文中,其他带有些许思想意味的“大地”阐述,更多时候出现在那些文学意味强烈的对尼采作品以及荷尔德林的诗进行分析的文章中。这个隐匿性的“大地”概念在海德格尔思想中期分析“艺术”时出现,并不是随意的安排,在这个概念中“隐藏着当海德格尔沉思艺术时在他的思想的路上所采取的决定性的步骤。”*奥托·珀格勒:《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宋祖良译,台北:仰哲出版社,1995年,第225页。奥托主要是针对海德格尔思想发生转折的相关情形做出了这一论断。
一、艺术作品的本源之“大地”
《艺术作品的本源》是由1935年至1936年间海德格尔几次关于艺术的演讲整理而成,尽管该文对“美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作者本意却是“克服美学”,同时克服对象性的“是者”之理解的。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所包含的对“是者”的基本态度,关涉到艺术以及作品的本质基础。*Martin Heidegger, GA65, S.503-504. 值得注意的是,克服美学的任务这一说法出现在《哲学论稿》中,但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并没有明确提过。因此,他以“艺术”为名的追问是行进在对真之本质与“是”之本质的追问道路上的。*参见Martin Heidegger, GA 5, Holzwege,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77, S.73. 如Dreyfus所言,海德格尔并非注意到艺术之特殊性的第一人,黑格尔、尼采、瓦格纳早已对此话题有所涉及。但他认为第一个基于“是”之意义而探究是态学上的艺术的人,就是海德格尔。Hubert L. Dreyfus, “Heidegger's Ontology of Art,” in Dreyfus Hubert L. and Wrathall Mark A, eds., A Companion To Heidegg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p.411.虽然将“艺术”与“真”关联起来,海德格尔并非第一人,自古希腊起,就有对艺术与真之关系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最初是诗人提出“诗”可否表现真相或揭示事物之真,随之引发了哲学家们的思考。到了中世纪,艺术与真的关系问题依旧未能达成一致,但对艺术之真的内涵有了更为清晰的界定,即它表现在艺术与现实的符合、与创作者意念的符合以及作品的内在一致性方面。这也就是说,是在符合论的真之理解基础上进行的艺术与真的认识。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351页。近代以康德与席勒为代表的德国美学传统则在艺术与真的关系问题上持肯定态度,即艺术是具有解放力量与救赎功能的。但海德格尔对“真”的独特理解,以及引入“大地”概念来解释“艺术”与“真”之间关系的做法,在哲学史与美学史中都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在直接分析“大地”之前,需先了解海德格尔对“真”所持的独特看法。

“艺术”通常作为“艺术作品”出现,当问到“艺术作品是什么?”时,指出《蒙娜丽莎的微笑》所画的是一个微笑的女人,或者杜尚的作品《喷泉》就是一个“便池”,大概无法说这种答案“错了”,但这样的回答与“艺术作品”的本质毫无相干。且不谈各种后现代艺术中毫无艺术作品实体的行为艺术等等,即使面对实存着的某个作品,当下的我们通常所鉴定的也不是作品本身,而是创作者的身份,鉴定人所作的工作与其说是与“艺术”有关,还不如说是与科学鉴定或者考古之类的专业相关。除了考证作者的身份来确定作品的方式之外,还有针对“艺术作品本身”的各种“客观精确”的标准:对绘画作品中的色彩进行光谱分析;对雕塑作品与模特原型的量化核实;或者对音调音色的数据整理。虽然它们的方法与根据都不统一,但一致的是,“艺术”本身在这些方法中不仅没有得到展现,其本质反倒在精确的数据中涣散失效。但这类精准分析的失效似乎在表明,艺术作品本身在“庇护”着什么不被揭开,艺术作品的本质似乎天生就是“遮蔽”的。那么,艺术的“庇护”“遮蔽”的本性到底来自哪里?展示着自身的艺术作品所不展示的又是什么呢?海德格尔将这些问题集中到了“大地”这个特殊的概念之上。
严格说来,“大地”并不是一个单独出现的概念,而是在与“世界”概念形成的“世界-大地”整体概念中的一方。而“世界”概念在海德格尔早期著作中就已经是一个核心概念,如《是与时》中“在-世界-中-是”的此是所关涉的“世界”,它构成一种境域,这种境域是此是所关注的投射的开端。更早的作品中,如弗莱堡时期在分析“体验”时所使用的“世界着(weltet)”的表达,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依旧可见,但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含义本身已经发生变化,以及海德格尔对“世界”动词化的处理并没有发生在“大地”这里。还可以明显看到的一点是,“世界”概念前始终是不定冠词,即“一个(某个)世界”,而“大地”则是紧跟在定冠词后,即“这片大地”。很显然,这些语法现象并不是海德格尔的任意而为,全篇文章对动词和冠词的一致性处理所暗含的是这两个概念本身所携带的深意。
从这两个概念的出场例证开始分析。演讲主题为“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对“世界”与“大地”的阐释则在对艺术作品的分析中,侧重阐释“世界”的作品是以“鞋”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在海德格尔对传统的物之所是观念逐一进行批判性梳理后,他试图通过艺术作品来“直接描绘”一物,因此他选择了梵高的作品“第255号”。*《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也曾讨论过梵高以“鞋”为主题的作品。但从原文看,《形而上学导论》中的鞋(Bauernschuhe)是属于“农夫”的,而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却是“农妇”的鞋(Bäuerinschuhe)。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5页。另,在与海德格尔的通信中,美国学者梅耶·夏皮罗指出,这段描述所涉及的梵高作品第255号并非是“农鞋”,而是梵高自己在城市所穿的鞋。这一度成为诟病海德格尔擅长“暴力解释”的引证。梅耶·夏皮罗:《描绘个人物品的静物画——关于海德格尔和梵高的札记》,丁宁译,《世界艺术》2000年第3期。
而在此之前的作品《是与时》中,海德格尔对用具物之所是的分析,是通过区分“上手性”与“现成性”,得到“牵连整体”,再从这种牵连整体的“何所牵”以及最终了结之处的方向,走到了“在-世界-中”的“此是”,进而显示出了用具物之所是就是其有用性。但在“艺术作品的本源”系列演讲中,他则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本源分析,将用具之所是的“有用性”进行了理解上的推进。在梵高的画布上,鞋之所是显现出了“有用性”的根植之处:“可靠性(Verläßlichkeit)”。
有用性只是作为可靠性的本质后果漂浮在可靠性中的,真正“按照物的不同方式和范围把一切物聚集于一体”*Martin Heidegger, GA5, S.20.参见海德格尔:《林中路(修订本)》,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7页。的则是可靠性。因此,用具之所是只有在可靠性之中才被真正把握。有用性的物之所是发生在使用中,而真正的用具之所是,则发生在一副绘画作品中。它不是说明书中的那种透视结构说明图,也不是描绘鞋具各部分细节的展示图,而是一双皮靴静置在画框中的某一角度的写真。但就是这样一幅连年代背景都模糊处理的画作,却让鞋的主人每日的随意穿脱,与亲密用物建立的信任,及其整个生活世界都在此铺陈开来。这种使用与信任没有在画面上直接显示,作品中甚至没有主人与使用场所的描绘,仅只有鞋。鞋具之所是不在制鞋匠人的工艺制作中,也没有出现在主人穿鞋行走的使用中,画作的静谧中突获的用物之灵动,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艺术品中,有着什么直接从作品本身中冲出,这种冲出不仅不依赖于物,反倒是物在之中得到了显露;不仅不被造于人,反倒是人在之中得到了位置。在这里,鞋具的原材料、使用者和制造者,作品的创作者和欣赏者都在一定的意义上以缺席的方式表达着自身,但实际上并不可见。在这样的呈现中,艺术作品不再是提供某种审美体验的客体,而是凭借着某种自立而属于它的世界,并涌现在它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中。只有当这个世界崩塌,它才会沦为某种僵死的作品,成为体验中被打量和计算的对象。不过,有死往往意味着生,艺术作品正是因为能够使“是者”走入其所是的光亮之中,获得某种活耀的恒定,它也可能僵死在体验与交易中。这种艺术作品的发生标志就在于,“是者”之真在艺术作品中自行设置。但这里所谓艺术与真的关联,并非描摹的栩栩如生之“真”。由于对“真”与“世界”“设置”等的领会,我们惯常滞留在字面之上,因此对这里所说的“是者之真自行设置入作品”感到异常困惑。
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说的“设置”是指“带向持立”,借用梵高的画作来说明,“设置”则意味着那双鞋在艺术作品中走进了它的“是”之光亮中。但这种设置的光亮并非纯粹的亮光,即它不会只是单向度地敞开一切,而是同时庇护着某种被疏朗和遮蔽所形容的东西。而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使物显示其所是,恰恰并非它栩栩如生地画出了某物的各个细节,使其置于某种纯粹的亮光之下,看到物与作品的符合一致,而是因为在这种庇护中,在光亮的荫蔽之处发生了真,用具所关涉的世界涌现在这件作品中了。
“世界”在这里显然不是我们日常表达的“世界”,可以联系到《是与时》中“在-世界-中-是”的世界,但又不完全相同。如果说《是与时》中的世界需要等到“此是”的出场才能被领会,那么“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的“世界”,则需要等到与之成对的“大地(Erde)”出现才能被把握,海德格尔将它的出场安排在对一座希腊神庙的描绘中。

在海德格尔的描述中,“大地”自身现身为庇护者的某种涌现,其他涌现者将“大地”作为各自返身隐匿的地方。世界着的“世界”则涌现着,作品的真之开启就在这种涌现中呈现。这里所谓的世界的开启与大地的隐匿,发生在一座建筑作品中。这座神庙建筑甚至不一定供奉着神的肖像,但它却“使神本身现身在场,因此它就是神本身。”*Martin Heidegger, GA5, S.29.参见海德格尔:《林中路(修订本)》,第25页。即它作为一件艺术作品也发生着梵高画作中所发生的“解蔽”,真在此自行设置入作品。但神庙的“设置”表现为一种“建立”,神就在这种作品的建立中现身在场,“把在指引尺度意义上的公正性开启出来。”*Martin Heidegger, GA5, S.30.参见海德格尔:《林中路(修订本)》,第26页。这种作品之为作品,其所建立的就是一个世界,并在其自身的遮蔽中守持这个世界。
贯彻海德格尔对“世界”的理解,艺术作品建立的世界“世界着”,人隶属于这个世界,而一般纯然物与动物落入的只是“环境”。即只有人能够逗留于“是者”的敞开领域中,拥有着我们的世界。画作所呈现的用具,以可靠性敞现了农妇的世界,农时、作物、辛劳与喜乐都在这种世界着的发生中聚集着;神庙作为神的现身,建立了一个世界,为万物的广袤设置空间、开放敞开领域之自由。这些艺术作品“张开了世界之敞开领域”,*Martin Heidegger, GA5, S.31.参见海德格尔:《林中路(修订本)》,第27页。并制造了让万物得以回溯自身的大地。
海德格尔强调,世界与大地正是在对立的争执之中,才互相进入各自本质的自我确立。两者互不可缺地置于作品所呈现的真之发生中:自行锁闭的大地在世界自行公开的敞开状态中进入敞开领域,在计算大地时所不能获得的种种揭示与穿透,在作品所敞开的世界中现出真身。在与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相遇中,你所遭遇的绝非质料,而直接就是这件作品本身,但质料也绝没有消失,而是作为其本身出现在由作品所敞开的世界之中。这种既出现又有所隐匿的特殊出场,正是万物不被耗损地真实自我显现的原因所在,即大地所代表的自我遮蔽使得万物不单纯是被消耗的物,而是涌现着、被庇护着,从世界中显现又匿于大地之中的物本身。
由此,海德格尔认为作品之所是的两个基本特征就是“建立一个世界”与“制造大地”,它们共处在作品所是的统一体中,于争执中确认自身与对方。因此也可以说,艺术作品就是这样的世界与大地之间争执的保持者,而正是这种争执的亲密性实现,使得艺术作品获其本质,即“是者之真”在作品之所是中发生了。世界和大地特质迥异地统一在作品之中,它们在艺术作品的独特静谧之中暗潮汹涌地争执着。作品发起、保持并实现这斗争,使之不仅不会消解在作品中,反而作为统一体被保存,这种统一来源于世界和大地的同一根据,也即这斗争所争取的“是者”整体的无蔽状态——真。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进一步加深了对“无蔽之真”的理解,他将物之无蔽的出现,指向了“疏朗(Lichtung)”这一概念,即由于进入和离开这种“疏朗”,物才得以无蔽。这种“疏朗”是一种特殊场所,它存在于“是者”整体中间,物之无蔽性在这个场所中被揭示而变得为人所知。在海德格尔的分析中,“是者”能作为“是者”而“是”,只有当它进入和出离这种疏朗的光亮领域之际才能实现;人作为“是者”,也只能在疏朗中才能获其位置,并遭遇非人的“是者”,即发生与物的交道。“由于这种疏朗,是者才在确定和不确定的程度上是无蔽的”。*Martin Heidegger, GA5, S.40.参见海德格尔:《林中路(修订本)》,第34页。译文有改动。
而隐匿的“大地”所强调的则是在“疏朗”中,“是者”也总是有所抑制,保持着某种遮蔽状态。也就是说,“是者”进入其中的疏朗,既是无蔽也是遮蔽。海德格尔在此区分了两种遮蔽的方式:一种为“拒绝的遮蔽”,即“是者”虽然有所显现,但显示的不是自身而是它物;另一种则是“伪装的遮蔽”,即“是者”以假象的方式显示自身。“更确切地说,疏朗仅作为这种双重遮蔽发生”,*Martin Heidegger, GA5, S.41.参见海德格尔:《林中路(修订本)》,第35页。译文有改动。海德格尔的这种说法是要强调“无蔽”并非一种特征,也不是某种现存状态,而是囊括着对峙的生发,“疏朗”与“遮蔽”的对峙是相较于“世界-大地”争执的“源始争执(Urstreit)”。因此,真之本质的无蔽是被某种源始本质的否定贯彻的,这种双重遮蔽的否定,就属于作为无蔽的真之本质。*Martin Heidegger, GA5, S.41.即海德格尔在“论真之本质”中已经表达过的说法,真在本质上就是非真。
艺术作品中所呈现的是世界与大地之间的争执,其所成就的乃“是者之真”;而更为本质的争执则是真之本质中疏朗与遮蔽之间的“原始争执”,这种原始争执要争得的则是敞开中心,即“是之真”。两种“真”的差异作为海德格尔对“是态学差异”思考的深化,所表达的是:疏朗发生在此,世界和大地也属于这种敞开领域,包括时间-空间本身这种可以使“在场现身”发生的争执区域也归属于这种本有的原始争执之中。*Martin Heidegger, GA65, S.260-261.因此,当“真”作为疏朗与遮蔽的原始争执发生之时,作为敞现者的世界决断地建基于大地之上,大地则作为锁闭者而通过世界显现。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争执,就是这种“真”根本性的发生方式之一。*Martin Heidegger, GA5, S.42.相对于《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的分类,海德格尔在这里将“本质性的牺牲”与“思想者的追问”合并称为“思想性的牺牲”;并不再提“邻近于是者中最具是之特性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并列举出的“用具制作”与“技术”。分类的变化暗含着他对真之发生的理解的微妙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指示出其本人在中晚期的关注话题“技术”及“思想”。梵高的画作中所发生的“真”,使“是者”整体在鞋具之所是的敞开中,即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中进入无蔽状态;希腊神庙所发生的“真”,使“是者”整体在诸神面前进入无蔽,并保持在这种状态中。艺术作品中的“真”不是“真实”意义上的真,而是无蔽状态本身在与“是者”整体的关涉中的发生,亦即本源意义上的“本有(Ereignis)”。自行遮蔽的物之所是在艺术作品中获得亮光,并将这种亮光嵌入作品而形成“美”,而这种美就是作为无蔽的真成其本质的一种方法。*Martin Heidegger, GA5, S.43.
二、隐匿性的大地之“隐匿”
从以上分析足以看到,隐匿性的“大地”概念在海德格尔思想之路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除了显示海德格尔对“是”与“真”理解的深入,其自身还可能隐匿了一些海德格尔并未直接点明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关于“大地”概念的来源与外部相关因素
伽达默尔(Gadamer)认为海德格尔的“大地”概念源自诗人荷尔德林(Hölderlin),这个词的真正故乡可能是诗歌的世界。*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邓安庆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462-463页。虽词语源自诗歌,但是态学上的意义则与海德格尔自身思想的发展相关。伽达默尔对“大地”概念在是态学上的意义上引入的正当性分析,将在后文分析。学者特拉夫尼(Trawny)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海德格尔的“大地”概念无疑受到荷尔德林诗歌的决定性影响,这位诗人对“地基”“土地”“天空之下”等特性的语词赋予深刻的寓意,这些寓意都可以关联到人所赖以生存的“大地”这一重要词语。
学者巴姆巴赫(Bambach)同样也将这个概念的来源与荷尔德林联系了起来,但他对这种联系的分析,显然没有止步于诗歌的世界。“海德格尔在哲学上对荷尔德林的关注,毋宁说总是政治性的……他试图通过一种编码过的论说……来实施他的政治规划……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为了政治的目的而对一位诗人进行的神话化。”*查尔斯·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张志和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362页。除了巴姆巴赫,还有很多学者对“大地”进行过政治性的解读。学者博尔特就认为,当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发挥“大地”这个概念时,他所意指的乃是“此是”的一种“维度”,且只有在与“文化”或“世界”的争执中才能被揭示。这种意义上的“大地”与当时的党派词汇“土地(Boden)”有一定的关联。博尔特:《海德格尔的秘密抵抗-超越斗争与权力》,赵卫国译,载刘小枫、陈少明编:《海德格尔的政治时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86页。国内学者彭富春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彭富春:《哲学与美学问题——一种无原则的批判》,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1-172页。但需注意的是,这种政治性解读的目的并不在于寻找某种“过失”和“证据”,而只是提供了直面海德格尔思想的一种方式。笔者对相关资料的参考也只是在这种方式的启发下,试图丰富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大地”。“大地”概念的政治色彩在巴姆巴赫看来还不仅仅体现在对荷尔德林诗词的“编码”使用中,他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大地”所携带的政治性。
在巴姆巴赫的分析中,“大地”隐匿的政治涵义往往体现在海德格尔使用的相关词群中,即除了大地外,还有“土地(Boden)”“扎根状态/原生性(Bodenständigkeit)”“土壤(Land)”“根(Wurzel)”及“无根”等等一些在他看来或多或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党派色彩的词汇。因此,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之前,1924年的夏季课程中“扎根状态”这个表达,已经有了“大地”概念的部分雏形。当海德格尔宣布要赢回活跃在希腊的扎根状态与原生性时,他所指的是一种扎根于地基或土壤的状态,它与当时学院派的“动荡性”不同,其所提供的乃是持久和坚固性。*查尔斯·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第46页。巴姆巴赫将这种“扎根”在魏玛年代的背景下理解为,针对德国文化无根状态的某种“革命之根”。人们需要扎根的就是“这片大地”,而非不确定的“某一片”。这种磐石性的“大地”作为建立“一个世界”的承载者,在它的坚固持久之上,才能开启出历史的种种可能性。*艺术作为这种意义上的历史性世界建立者,基于“这片大地”而建立出各异的“某个世界”。海德格尔认为作为创建的艺术最早发生在古希腊的世界,随之是中世纪和近现代的世界。其中的每一次转换都展现了某种新的本质性世界,每一次的建立都发生了是者之无蔽。海德格尔:《林中路(修订本)》,第56页。伽达默尔曾在阐释“审美的时间性”时,通过分析“节日”来进行过阐释。这里的“同一片大地”与“不同的世界”也有类似的情况,即对于一年一度的节日而言,每一年都是同一个节日,但它绝非单纯地重复。虽然有着历史性的改变,但它仍然是经历着这些演变的同一个节日庆典。尤为重要的是,只有在变化与重返的过程发生中,“节日”以及“世界”才能真正是其所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60-161页。
“扎根状态”这个表达还有另一个来源,巴姆巴赫认为海德格尔以不同于约克(Yorck)的方式继承了他对现代欧洲“无根状态”的批判。这种继承中体现了“大地”概念的另一雏形。海德格尔在《是与时》第73-77节中对此是所进行的历史性解读,体现了扎根状态与此是之本真性之间的本质关联。此是“时间性”地“绽出”,不是仅扎根于“过去”或传统中,而是在“过去”“当下”以及“将来”的统一中,在对“将来”的筹划中不断地将种种可能性“生存”出来。这也就是说,历史作为一种可能性的视域是指向将来的。因此,“原生性”所指的不是仅仅扎根于“过去”或“传统”的土壤,而是意指某种“隐蔽的”“未知的”“地下性的(chthonic)”事物。这种事物的意义则需要与隐藏和遮蔽状态进行某种本质性对峙才能获得。而隐匿性的“大地”作为“遮蔽”,在此意义上就成为了塑造个人命运与民族天命的一种本源。即命运与天命都不是现成的,而是由传统发送到某共同体的种种历史可能性,在本质性的争执或对峙中,世界得以建立。*查尔斯·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第46-50页。
《艺术作品的本源》中隐匿性的“大地”与真之“遮蔽”的关联,巴姆巴赫同样在“扎根状态”中找到了类似的联系。“扎根状态”曾作为大战前夕的一个文化口号,成为德国青年运动“本真性”词汇的一个部分,意图反对无根的生存方式与都市性,突显与自然风土更根源的关联。“大地”与“世界”的“争执”在巴姆巴赫的分析中,则是受到了奥拖(Otto)在《希腊诸神》中所描述的新的荷马诸神与古老的地下诸神之间的冲突的启发。*查尔斯·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第91-92页。荷马诸神取代地下诸神的情形,就是柏拉图的“真之本质”取代了“遮蔽-去蔽”之真的情形。
虽然巴姆巴赫并不认为海德格尔的“大地”与纳粹农业部长的“血与土”直接相关,但他坚持憎恨种族主义的海德格尔依旧在他的“大地”中流露了清晰的政治意图,在相关的修辞中为国家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辩护。*查尔斯·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第103页。类似的判断与论证,在整本书中随处可见。除了这里提到的“扎根状态”与“大地”以外,巴姆巴赫将“大地”与“民族”相联系的分析,政治性的程度更甚。对于这种论证,笔者认为务必保持审慎的态度,避免先入为主地强行解释。
学者张志扬认为海德格尔的“大地”概念与海德格尔曾关注过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有关,该悲剧中对“大地-冥府”的说法与“大地”的幽暗、隐匿特质相似。*张志扬:《偶在论的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6页。巴姆巴赫则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悲剧中克瑞翁与安提戈涅的冲突体现在两种不同的“大地”理解上,前者将“大地”理解为政治意义上的空间性“领土”,而后者则将之视为诸神居留、安葬死者的“故乡”。*类似两种大地理解的对峙,还出现在海德格尔有关希腊人与罗马人对大地理解的论述中。他认为希腊人将“大地”理解为“在-中间”,即在遮蔽的“地下”与光亮的“地上”之间;而罗马人则将“大地”理解为不同于“海洋”、用来建筑的领土。Martin Heidegger, GA54, S.88-89.
海德格尔显然是在安提戈涅的角度来把握“大地”的,它体现了人与本源的某种本质关联,从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的分析还能进一步看到,克瑞翁象征了某种笛卡尔式、技术的本质所意指的形象,这种代表着人类主体性的“无根性”形象与隐匿性的“大地”所指向的“无蔽-遮蔽”之争是绝缘的。*查尔斯·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第244-245页。主体性姿态对“真”的赢获,乃是在以“集置”为特征的技术世界中,通过将主体与客体都强行解蔽为持存物而完成的。这种强制性解蔽不仅无视“大地”的遮蔽维度,甚至连“解蔽”本身也一同被忽略了。*Martin Heidegger,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S.30-31.而安提戈涅对“大地”的看法、对安葬的理解、以及在冥府的遭遇,则都显示了“大地”隐匿的本源性与神圣性。她与克瑞翁的抗争在某种程度上所隐喻的是,民族需要通过恢复与大地的源初关联,以抵抗克瑞翁所象征的“无根性”。在海德格尔对《安提戈涅》的阐释中,还值得注意的是对“无家可归(Unheimlich)”*这个词乃是海德格尔对希腊表达“δεικα”的翻译,该词的字面含义是阴森、可怕、难以名状的。但从海德格尔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到,它显然已经负载了超出字面的涵义。在《是与时》中对“畏”进行阐释时就已经出现过这个词,用来描述一种由于失去了惯常的熟悉而引发的不安全感、无归属感、不在家的感觉。因此从内涵以及该词词根“heim(家)”的含义而译作“无家可归”。学界还有译作“莽森劲然”(王庆节)、“茫然失所”(陈嘉映)。的分析。这个在含义上与“人”相关的词与“隐藏(heimlich)”有着词根上的关联,这种关联显示的是“人之所是”是从“隐秘”中被筹划出来的。*Martin Heidegger, GA40, S.158-160.此处对“大地”的阐释则主要体现在“大地”与“大海”的关联中,作为“诸神中最高贵的”的“大地”,其特征是坚不可摧、不朽不倦、静谧孕育与馈赠。*Martin Heidegger, GA40, S.162-163.
(二)关于海德格尔自身思想的发展暗线

对于海德格尔在中期引入“大地”这一概念的理由,伽达默尔认为:在《是与时》的现象学分析中,海德格尔论述了作为现身情态的此是在“是者”中发现自身的这种极限体验,并且把“在-世界-中-是”的真实暴露归因于现身情态。而在现身情态中所发现的东西则显示出人之此是的自我理解的边界。“不可能从现身情态或情绪这样一种解释学的极限概念推出像‘大地’这样的概念。”*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第463页。之所以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会出现“大地”乃是因为诗意性的大地概念作为艺术品之所是的必要规定,是海德格尔突破传统形而上学和美学的关键之处。*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212页。
伽达默尔认为,传统美学在18世纪启蒙理性的光亮下获得了自己独立的美学尊严,但由于它是建基于心灵能力的主观性之上的,因此这门新兴学科面临着危险的主观化倾向。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的本源》所要克服的美学正是这个意义上的美学,即在主观化的审美道路上,仅仅作为客体展现的艺术。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作品是独立自持的,既不是审美的对象,也不是传统古典美学中仰赖于某天才的作品。为了从艺术作品本身的是态学结构出发,也为了避免重蹈美学覆辙,海德格尔引入了“大地”概念与“世界”概念成对,以此来说明艺术作品自身的显示与隐藏本质的内在统一。*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第463-464、466-467页。
伽达默尔还指出,海德格尔在这里的分析主要还是服务于其对“无蔽”之真的思考。因为无蔽之真,除了“无蔽”的维度之外,还有隐匿性的“大地”所强调的更为本源的“遮蔽”维度。也就是说,艺术作品所引发的“世界”与“大地”之争执,在本质上就是源初意义上“真之无蔽”与“真之遮蔽”的争执。单纯的“去蔽”、完全的“无蔽”在某种意义上取消“是者”的独立性,它们只能“作为”某物显现在一种耗费性的使用中。艺术作品的独立自持则恰好体现了“大地”所带来的“不可耗尽性”。
伽达默尔进一步认为,带有“大地”特性的艺术作品展示了海德格尔思想之路的前景:一方面,在其后期对技术本质的讨论中,计算性现代思想所造成的物性普遍迷失的境况,可以在艺术作品所保存的物性之中获得拯救的指引。因为隐匿性的“大地”庇护着的本性,使物之所是不只停留在《是与时》中的“有用性”那样体现,而是在“艺术作品”所敞开的“可靠性”中展示出了自持的不可耗尽性。另一方面,由于海德格尔将艺术的本质认作为“诗”,并认为艺术是一种投射,新的东西通过它而得以真实出现。同时“诗”之本质在于“语言”,因此,“大地”作为艺术作品中的隐匿维度,指向了海德格尔晚期对语言之本质的思考,*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第470-471、471页。即“遮蔽着解蔽”的大地暗合了“寂静之音”的道说。
海德格尔本人在《哲学论稿》中的说法也印证了伽达默尔的这一分析,他认为在思想的“另一开端”中,“抑制”乃是基本情调,因为它调谐着此-是之基础的建基,并且它还贯通且调谐着世界与大地之争执的亲密性,因此也调谐着本有之纷争。这种抑制创造了伟大的寂静,而这种寂静只起于本质性的沉默。*Martin Heidegger, GA65, S.34.
(三)“大地”隐匿着“反主体”或“反视觉”的倾向
基于海德格尔对艺术的独特理解,即艺术作品在建立一个世界、公开出“是者”之“是”的同时,还制造了大地,并将“是者”庇护入某种不可耗尽性中。因此,泥瓦匠对石料的使用与雕塑家使用石料的方式看起来似乎没有差别,但前者是对石料的消耗,如使某块石头成为垫脚石、铺路石、或垒起来成为某个石台时,石头本身却消失在这些有用性之中;而在后者那里,即在雕塑家的作品中,石料的厚重质感、绵密暗纹在尚未“作为”什么而成型的状态中,在艺术作品的庇护中自行显示了出来。艺术作品作为一物,并不置于某种关联之中,它独立自持,静谧于自身。这种独立自持性既不体现在“主体性视觉”的“打量”中,也不显示在对物的“使用”中。艺术作品恰好就突显了这种“非视觉”的独立自持,即在有所照亮的敞现同时,却还保持着某种隐秘的幽暗,这就是艺术作品中的“大地”因素。
《是与时》前后,海德格尔对物进行分析时,物之所是与“在-世界-中-是”意义上的世界紧密相连,这也就意味着与“此是”相关。无意蕴的“是者”在此意义上,只是意蕴缺乏者,而不是真的置于意蕴之外。这种分析“掩盖了世界的一个基本结构环节:让被隐藏,把对‘是者’单纯吸收到含义的关系中进行阻止的那种掩藏。”*奥托·珀格勒:《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第226页。而在独立自持的艺术作品中,作品把自身置回到大地之中,因而把自身展开到了无限的丰富性之中。在其以“语言”为主题的思想晚期,海德格尔不断强调着“倾听”,因为真之本质作为语言而发生。这并不是对“视觉”的反对,也不是一种“补充”,而是体现了对“非视觉”本质因素的承认与接纳。
“视觉至上”的传统并不是最原初的,学者弗雷德尔就认为最初的希腊社会乃是以听觉为主导的。经由他的考证,“听觉至上”从公元5世纪起开始失势,此后视觉便成为优先的。*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经过了柏拉图思想以“看”为词源的“理念”之光以及中世纪的上帝之光,“视觉”进一步夯实了自己的至上地位。柏拉图所引导的“视觉转向”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西方哲学的堕落。*韦尔施:《重构美学》,第180页。承载着这种“视觉至上”的柏拉图思想也被海德格尔认为是开启了传统形而上学“遗忘‘是’本身,而只看‘在场’之是”这一命运的肇始。因此,“大地”的特性在克服传统形而上学“视觉至上”的意义上,可以尝试进行一种“听觉”的解读。*韦尔施就认为,海德格尔针对“视觉居先”的情况,申求转向听觉。韦尔施:《重构美学》,第179-180页。
如果说“看”更强调“当下”与“静止”,“听”则显然更重视“过去”“当下”“将来”的连贯性,换句话说,“看”的东西通常在时间中“在场持存”,而听则相对更注意“消逝”现象或“不再在场”的现象。*很难想象一段音乐或一段话在进行时,出现的声响堆积而不消逝的情形。听觉就是在追逐这种消逝的经验中体现的。在此意义上还可以说,注重“发生过程”的“听”是更具“时间性”的。*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有过类似的分析,并将视觉划归为“是之是态学”,而听觉则属于生活的事件。因此前者更亲近认知和科学,而后者在信仰与宗教中更为适恰。韦尔施:《重构美学》,第183页。其次,“视觉”容易制造出“主人幻觉”,即“看”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主动性”,在这种感官的使用中,人们似乎更能自主地选择睁眼看或闭眼不看。与看相比,不能闭上耳朵的“听”似乎显得更“被动”或更具“接受”“承载”特性。可以说在“听觉”中,我们是无所庇护的,对待这种感官的态度应是“泰然让之”,期备着种种可能性的发生。这也正是海德格尔思想后期强调的对待源初本质遮蔽维度的态度。但亦如尼采的“大耳朵怪人”*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58页。的比喻,对“听觉”的强调倾向但凡过度,本质上也和“视觉中心主义”殊途同归了。
“大地”这个概念还暗含了由个体性的“此是”向群体性“民族”转变的倾向。当“Dasein”被拆开表达为“Da-sein”时,“此是”的非主体性色彩已经在有意识地被淡化,“此-是”与“人”的直接关联也被取消。海德格尔的思考不再从“是与是者”的差异,即是态学差异处生发,而是在转向中走到这种差异的源始根据处——“之间”。即各种“是者”如何在“遮蔽-无蔽”的运作之间能够在是之亮光中显示其所是。这种“之间”在艺术作品的主题中则表现为“Erde-Welt”结构,此是在“Da(此)”生存着而“sein(是)”其所是,民族则在“Erde”上“weltet(世界着)”而展开历史。当个体性的“此是”被“人”或“民族”取代,一个民族所生存的那片“大地”就是“Sein”得以成其所是的那个“Da”。
学者黑尔德(Held)则将其两者对应于“契机”和“伦理”进行理解,“世界(天空)”之契机关涉着接近的将来之切近,而“大地”之伦理则意味着进入到过去的遥远之中。因此,此两者的对峙作为一种“紧张的和谐,能使我们经验到非主体主义地被思考的时间的原始性。”*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32-134页。从主体性色彩浓重的“此是”之基础是态学转向“非人”的“艺术作品”,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海德格尔试图减少这种“主体性”诟病的倾向。
最后还要提到“大地”概念产生的一些其他影响。虽然《艺术作品的本源》演讲是以“克服美学”为意图的,但隐匿性的“大地”在某种程度上帮助美学提供了对部分艺术现象的解释。在现代艺术中可以看到一些很难说符合传统“美”之定义的表现方式,它们热衷展现奇异、惊愕、晦涩甚至丑陋。这被部分学者称为一种“美学任务”,即通过这类方式来中断和干预某种无边蔓延的审美化。通过这种“非传统审美”的表现方式来制造某种缓冲、冷静的地带,让人们从持续兴奋导致的审美疲劳中解放出来。*韦尔施:《重构美学》,第140页。从海德格尔的艺术看法出发,这些现象正是艺术本质“遮蔽”维度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与作用。
前文曾提到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谈到过“拒绝的遮蔽”与“伪装的遮蔽”两种遮蔽方式。拒绝在对象性的打量中袒露本质,与运用一种“中断”来冷却泛滥的审美热情,都可以视为“大地”遮蔽性的体现。艺术提供的冲击力从来不是对人快感的迎合,艺术之真也不是纯粹无所遮蔽地袒露。海德格尔用“Daß(如此)”*艺术作品作为特殊的物,对它的发问“这是什么”,无法给出类似某个处于牵连整体中的“用具”的答案。面对带有独特的自持性的艺术作品,我们大概只能回答“这是如此。”来表示艺术作品所带出的有所遮蔽的独特冲力,它所开启出的敞开性能够将人带入“无蔽-遮蔽”的争执之中,并使我们在这种对“无蔽”与“遮蔽”的把握中,改变了与世界和大地的关联、抑制着流俗的行为评价,而逗留于保持着两者争执的作品所带出的“真”之中。在此意义上看,隐匿性的大地是在隐匿中庇护着美的本质,通过展现其“遮蔽性”而显示出艺术独特的冲力,避免它在单向度“无蔽”的意义上沦为审美的消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