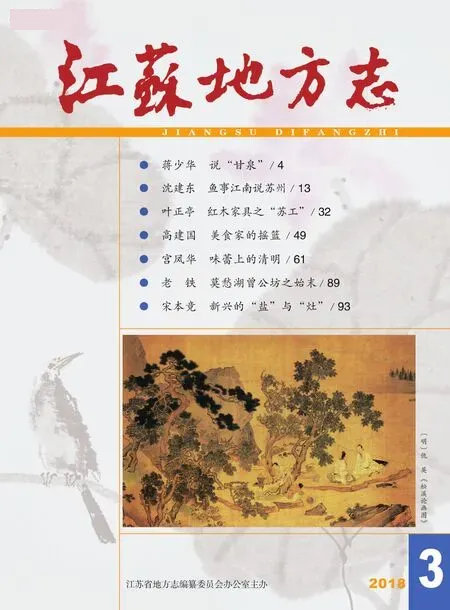《巢林笔谈》与白鱼叚
2018-08-01陈益
陈 益

生活在清康熙、乾隆年间的龚炜,自称“巢林散人”。他的曾祖父当过明朝官员,父亲是进士出身,也当过官,妻子王氏则为太仓望族后裔。到了他这一辈,家道已经中落。龚炜“喜经史,工诗文,善丝竹,兼习武艺”,文才特别出众。然而年过四十仍屡试不第,身体又常常有病。于是他放弃科第,甘于贫寒,以笔墨自娱。他一生写过《屑金集》《虫灾志》《湖山纪游》《阮途志历》等著作。最为人称道的是《巢林笔谈》,记载了大量清代社会的风土人情、逸闻趣事,成为研究明清苏浙地区社会、文化、历史、经济、人物乃至昆曲等方面的珍贵文献。
读《巢林笔谈·白鱼叚补志》等资料可以看出,他们家原来居住在昆山丽泽门,曾有丽泽书屋,后毁于兵燹。从先曾祖父西圃公开始,迁徙到县城西南白鱼叚,卜筑于此。这里原本瘠田茅舍,只是一个寥落的村墟。西圃公带领家人与村民修筑圩岸,疏浚支河,励以服田力穑,敦以孝友睦姻,倡导耕读传家,于是地沃俗淳,为周围各村人所称道。康乾年间社会环境安定,经济有所发展,数十年中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白鱼叚村气色日新。村上有龚炜曾祖父龚时升构筑的澞溪草堂和一座名曰长寿庵的寺庙,这是龚氏家族留下的文化印记。
白鱼叚,又名白澞、澞溪,今天称白渔潭,离城不过几里路。龚炜说,元代末年吴王张士诚曾在这里为爱妃构筑园林馆舍,歌舞宴饮,纵情欢乐。原有七十二楼,最著名的是鹳嘴、鹤颈、尧仁、齐可、荷花、花瓶等。溪水清冽,景色秀美。虽然家住在这里,平日里却没有尽情游玩。中秋节前夕,他“棹一野艇,随湾荡漾,秋清月朗,风淡波澄,渔唱灯微,犬嗥村静。”不由感慨——佳境也!
明嘉靖十八年(1539),时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昆山人顾鼎臣奏请朝廷批准,将原来的土城改用砖石砌造,以抵御倭寇入侵。为了支持昆山修筑城墙,他还带头捐出了皇帝的一笔赐金。昆山老百姓纷纷出钱出力,“入木于土,累石于足,封砖于表。”民间传说,白鱼潭是修筑城墙时的制砖取土之处。所以潭水深广,盛产白鱼。昔日经由大澞河与吴淞江、娄江沟通,久旱不涸,东流入海。
关于白鱼叚的名字,历来众说纷纭。龚炜认为,“白鱼”的含义很难详解。白鱼的模样很像鲤鱼,出自海中,莫非因为吴王张士诚曾驻跸于此,才以白鱼之祥瑞附会?古人有叚谷、叚溪的称呼,水乡称叚,也许有分段的含义?文人墨客的题咏,则称白澞或澞溪。这是因为它源于大澞浦吧。
《巢林笔谈》中,龚炜写到,“天久不雨,炎气酷蒸,且七日矣,今夜更甚,露坐溪上,水树无声,火尘翳面,虽云淡淡起,而风与雨杳不可即。”盛夏时节,很多天不见风雨的村落,酷热犹如蒸笼。他坐在澞溪岸边,仍感觉不到清凉。于是在夜半时分叩开朋友的门,一起跳入河水里。依然感到热,毕竟有些清气,比起在黑暗中喂饱飞蚊,挥汗如雨,好多了。
夏天日长,难以做事,他俯首温习经书。夜里热得无法入睡,就一边乘凉一边背诵史书。想起古人的经史之学,原本也是期望有所实用,他决定经以经、纬以史,撰写《裨政》一编。构思了一个多月,才开始握管动笔。不觉呼吸渐渐急迫,知道自己的老毛病又将复发,只得收辍而去。他不由感慨道:“乃知穷愁著书,亦终属有福人!”哪怕又穷又病,只要能够写书,总归是有福之人。《巢林笔谈》中的许多篇章,完全可能是龚炜在白鱼叚忍着病痛写成的。
曾有人问他,诗应该怎么作?他回答道:“我不知道。以鄙见论诗,只有三字:情也,理也,景也。”一言以蔽之,是“真写得”三字。龚炜认为:“真,是诗之根,非学无以殖之。须于吟诵时,得其真气味,然后下笔时可以发我真性情。何谓真气味?神在句外。何谓真性情?言出心坎。若意浅、神竭、韵粘、字呆,都不是真气味。热中人作高尚,富贵性谈场圃,伪君子讲节义,都不是真性情。”只有明白了什么是真,才可以谈论如何作诗。显然,他的这番话抓住了“诗言志,歌永言”的本质。
他记叙的一则关于归有光批注《史记》的故事说,有一位张先生,以自己收藏的一百多卷古书作担保,请求借款。先君同情他,根据这些古书的价值,给予款项。几年过去了,张先生流露出把古书要还的意思。先君答应把书归还。其中有归有光批注《史记》一部,是张先生先祖烈愍公珍藏的,龚炜也非常爱惜,心里始终没有忘记这部书。又过了几年,偶尔与张氏邻居陆惠三谈到归批《史记》,陆惠三知道张氏打算出售,打听什么价格,张氏故意把价格抬得很高,龚炜一时无法回应。回家后跟妻子商量,妻子卸下金簪一枝,交给龚炜。于是这部书就归龚炜所有。
归有光先生酷爱《史记》,阅读时下过很深的功夫,常用五色笔在上面圈点。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归震川氏取《史记》之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资其领会……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据为传授之秘,则是郢人宝燕石矣。”
龚炜当然懂得归批《史记》的可贵,妻子也非常理解他,以金簪换来古书,了却心愿。
龚炜生活的清代康、乾年间,昆曲创作和演出仍处于繁盛期,他的《巢林笔谈》有《戏题傀儡》《相公》《老郎菩萨》等多则记叙昆曲掌故。虽然他只是一个不仕文人,手头拮据,但仍然站在士大夫的立场表达自己对演艺界的看法。
当时有不少人认为,《牡丹亭》杜丽娘的原型是太仓人、明朝阁老王锡爵的二女儿王焘贞。汤显祖师从王锡爵,比他小十岁的王焘贞可算是小师妹。在昆山片玉坊将《牡丹亭》完稿后,曾交给王锡爵的家班上演。然而,王焘贞是个另类才女,未婚嫁而夫病死,于是修筑一个土室修炼,并且收了王世贞、屠隆等大名士为徒。不过汤显祖没有跪拜。龚炜在《牡丹亭非昙阳子事》中表明:“昙阳子(即王焘贞在入道后的法号)仙去,凤洲先生(明代大文学家,其族伯王世贞)传其事,而世或以《牡丹亭》诬之,误矣。”
王焘贞羽化之事,曾经轰动江南,招致朝野批驳,王世贞和王锡爵也因此受到了责罚。龚炜说,对于《牡丹亭》的误解,是将杜丽娘的“还魂”与昙阳子的“复活”混为一谈了。品行卓卓的汤显祖先生是决计不会这样做的。但是已经含冤二百年,没有得到申雪,所以我必须“表而出之”,澄清这个事实。
老郎庙里供奉的老郎神,是昆曲界的崇拜偶像、行业保护神。清代,不仅在老郎庙,一些戏园的后台也设有老郎神像或牌位。演员进后台,先要向神位拱手,称为“参驾”;临出场时再拱手,称为“辞驾”;下场进后台时又拱手“谢驾”。昆曲界一般认为老郎神是唐明皇。唐明皇多才多艺,不愧梨园鼻祖。但龚炜在《巢林笔谈》中说,“梨园所称老郎菩萨者,一粉孩儿也,平时宗之,临场子之,颠倒殊不可解。或云即唐明王。吾则有说以处之:开元精励,尽人可称为宗;天宝昏庸,优人得亵为子,恰合两截人。”他的分析很透彻,梨园供奉的老郎菩萨的形象是颠倒的,恰如唐明皇的精励与昏庸,构成了两截不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