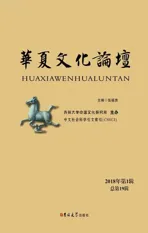词史时空向度的双重书写
——唐圭璋先生的词史研究论略
2018-07-24孙启洲
孙启洲 马 睿
词史通常都是一种历时性的研究,主要是展现词体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在这过程中,要清理一个断代或特定的历史时期个体词人的特点、贡献,以及词人群体和流派的形成发展,探究他们对于词发展过程的影响和意义。唐圭璋的研究不拘于此,他在搜集词史资料的同时,还注意词的创作与地域、家族的关系,考虑到词史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地理因素,与当下兴起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不谋而合,为词史研究开拓新的视野。唐圭璋虽然没有词史专著,但在其词学论文集《词学论丛》和与潘君昭合著的《唐宋词学论集》中,全面展现了他的词史观,贯穿着词学文献学家考证的本色。王兆鹏在《唐圭璋词学研究的体系、方法与贡献》中,有论及唐氏的词史研究,但并未进一步的展开论述,因此需要更深入的阐发,以彰其词史研究之功。
一、驳众家之论,立一己之言:“词起源于隋”之说
唐圭璋认为“词的起源问题,为研究词史的第一个问题”,因此梳理唐氏词史研究的成果,首当关注其对于词的起源问题的探讨。首先要明确一点的是,词的起源和词体最终成型的时间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词的起源,是指词体最初具备其本质特征的发生阶段或萌芽状态,而词体的最终成型,则是指词这一文体的创作方法的成熟,创作模式固定,并有专业的创作者。从词的最初起源到其最终成型,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时间。
词的起源是词学研究中最为基本的问题,涉及对词体本身及其发展的认知,为历代词学研究者所重视,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定论。传统的对于词的起源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从长短句的形式特征着眼,将词溯源至《诗经》和汉乐府。如汪森《词综序》曰:“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萧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这也是浙西词派为推尊词体而言的。第二种,词源于唐五、七言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第三种,泛声说。认为词起初依曲调填词多以齐言近体诗入乐,但齐言诗不合音律曲拍的节奏的急缓、短长,故在近体诗的基础上填了“衬字”“和声”“泛声”“散声”,后来将这些“陪衬”以实字填之,便也就成了长短句的词。持此观点的有宋人朱熹、沈括,清人吴衡照、方成培等。以上关于词的起源的说法,都只看到了词体的某一方面所受前代文体之影响,但尚不能说是词的起源。也就是说,词体的长短句形式或者音乐性固然受上至《诗经》下至齐梁乐府创作形式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词就起源于此,判定词的起源即词体的产生,需要多个限制条件加以界定。
唐圭璋认为,探究词的起源有两个不可忽略的主要条件:首先论述了词与燕乐的关系。词是合乐而兴的一种文体,且其所合之乐为隋唐时流行的燕乐。在古音乐的分类中,秦以前为雅乐,汉魏六朝乐府使用的音乐为清乐,而燕乐则是隋唐时新兴的曲调。在他看来,有了乐谱即有歌辞,“配合‘燕乐’乐曲的‘歌辞’就是‘词’”,故前人所言词源于《诗经》、乐府皆可证伪。第二个必要条件:词是起源于民间的,这是很多学者容易忽略的地方。一方面,词所合的燕乐中的曲调就有民间音乐的成分,比如我们认为燕乐是“胡夷里巷之曲”,而“里巷之曲”就是指中原地区民间流行的曲调,和清乐系统中流传较久远又经过翻新的南方吴音以及北方地区的民歌等等。另一方面,从发掘出的敦煌曲和《教坊记》中的曲名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多为表现劳动生活和下层民众的情感,如渔歌、婚恋歌曲和娱乐游戏等。因此,将民间词与文人词分开讨论,更符合客观实际,才能厘清词之起源。
唐圭璋正是以上述两项条件作为论词的起源的主要依据,将词的起源的问题一分为二地论述,区分词的起源和文人词的起源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论词的起源过程中,他从唐人崔令钦的《教坊记》中寻找依据。《教坊记》主要记录了当时皇帝所设的音乐机构教坊中的300多首曲调名,但由于唐朝尚未有采诗制度,故无法了解其声与辞。唐圭璋还依据《隋书·音乐志》《词品》《碧鸡漫志》等史料考证出“隋曲者有三,即《泛龙舟》《穆护子》和《安公子》”,并对三者作一一阐发。据此他认为,词起源于隋。除此之外,他又引敦煌曲来证词的起源,唐氏早在1943年就发表了《〈云谣集〉杂曲子校释》。敦煌曲是唐代民间作品,迄今可见其存调名共六十九种,与《教坊记》相重者四十五种,唐氏认为其中有四种为隋曲,分别为《泛龙舟》《斗百草》《水调》和《杨柳枝》,其中前三首虽有史料记载为隋炀帝及其乐工所作,但在唐氏看来皆是隋代民间曲子,更证明了词起于民间而非帝王。
唐氏还通过《碧鸡漫志》,考证出《河传》亦为隋代曲子,至此可知,唐氏通过前人词话及各种史料记载考证出总共有七种属于隋代的曲子。正与王灼“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之言相印证。而且他认为有乐曲就会有歌辞,因此这些词调均可作为词起源于隋的直接证据。此外,唐氏还从敦煌曲中发现,其中不仅有《南歌子》和《望江南》一类的小令,还有像《内家娇》和《倾杯乐》那样的慢词,这些词多作于盛唐。他因此认为这些在盛唐时就已经臻于完备的民间词,也可作为词源于隋的一个旁证。进而,其在敦煌曲的校订中还发现《天仙子》《破阵子》等五调,与后世词调几乎相同,这就证明并非因诗加泛声之后才有词,破词为诗余之说,正如汪森所言:“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驰,非有先后。”后来学者叶嘉莹在其《论词的起源》一文中亦同唐氏的观点一致,她说:“至于长短句词,则是隋唐以来,为配合当时流行乐曲而写之歌词。二者在唐代固曾并行一时,而并非先有声诗之吟唱而后演化为词的情形。”
对于词的起源,现代词学家也多有论述,但各家具体观点不尽相同。在吴梅看来,梁武帝的《江南弄》、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和沈约的《六忆诗》,是词的滥觞,因为齐梁以来,乐府音节已亡,一时君臣尤喜制新调。唐圭璋在其《论词的起源》首先予以澄清,认为《江南弄》等所配之音皆为“吴声西曲”,清商曲的一种而非燕乐。其次,以帝王之作论词的起源,本身就不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为唐氏所反对。王国维曾与胡适讨论过词的起源问题。王国维最早在其《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从书中三首词的句法推断其词调为《望江南》和《菩萨蛮》,且引《教坊记》为证,但对于词的具体创作时间依然存疑,当时他并未见到《云谣集杂曲子》。1925年,胡适就其《词的起源》询问王国维的意见,他认为词起源于中唐。而此时,王氏已经看到《云谣集》,并作了《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提醒胡适关注盛唐时已有的《教坊记》,但胡适本人怀疑《教坊记》的可靠性,而不以其为据。唐圭璋认为《云谣集杂曲子》一方面是对王国维之说的证实,一方面是对胡适之说的证伪,他在王国维的基础上将词的起源继续前推。
龙榆生虽然也将词的起源追溯至隋,但他与唐圭璋在具体问题上持论不一。龙榆生在论词乐时,根据《教坊记》所载,认定《安公子》为隋大业末的“内里新翻曲子”,这与唐圭璋的观点一致。但是他又依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言,将词之起源上溯至隋炀帝的《纪辽东》一调,他认为:“综观一调(即《纪辽东》)四词,虽平仄尚未尽恰,而每首八句六叶韵,前后段各四句换韵、句法则七言与五言相间用之,四句无或乖舛者,欲不谓为制词之祖可乎?”唐圭璋对此观点也表示怀疑,他指出,由于《教坊记》和敦煌曲中均未有记载,故《纪辽东》是否为词调尚未有证明。其次,他从《纪辽东》的题目和内容出发,认定此调是隋代统治者穷兵黩武,宣扬武功的庙堂乐章,其所配音乐应属于庙堂音乐范围的“雅乐”,而非燕乐。而且,龙氏将帝王之作认定为词之起源,忽视了词起源于民间的事实。唐圭璋在给秦惠民的信札中曾言:“词源于隋,尚指民间,炀帝过早,《纪辽东》龙沐勋主张,仍从龙说,我以为仍是古体诗。今日争鸣可以各抒己见,我也不能说了算。”可见唐氏自始至终坚持词起于隋且兴于民间的观点。
詹安泰也反对龙氏的《纪辽东》说,但最终关于词起源的时间点则与唐圭璋相异。在詹安泰看来,把一种文体的产生,归结为一个帝王或臣子的创制而忽略民间创作,是不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且因为在目前所能考查的曲调集中并无《纪辽东》一曲,故詹安泰认为将其作为词的起源并不符合事实。詹安泰从音乐和文辞两个方面来举证,得出“把词的起源摆在初唐更恰当些”的结论。从音乐方面论,他也认为合于词的燕乐起于周隋之际,同时他还论证敦煌曲中可以看出远在盛唐以前的民间词作。他和唐圭璋观点相左之处在于“我们不能仅凭调名的来源就判定作品的产生时代,创调年代和作词年代是有区别的,它们可能同时产生;也可能先有调然后才依声填词。”詹安泰又根据敦煌曲中作品多是描写初唐时期的战乱的社会现实,因此,他联系燕乐的产生和民间词的首创性两个因素,将词的起源定在初唐。唐圭璋则认为有曲调就会有歌词的产生。
在文人词方面,唐圭璋指出民间词向文人词转变发生在初唐时期,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的文人词有唐玄宗《好时光》、李白《菩萨蛮》和《忆秦娥》、张志和《渔父》等。其师吴梅亦持此观点,“至玄肃之间,词体初定。李白《忆秦娥》、张志和《渔歌子》,其最著也。或谓词破五、七言绝句为之,如《菩萨蛮》是。”但胡适却认为,现存可见的初、盛唐的乐府歌词,都是整齐的五、七言,或六言的绝句,尚未有诗与词的区别。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李白的《忆秦娥》《菩萨蛮》《清平乐》皆是后人伪作。龙榆生亦曾言:“白目律诗以俳优,不愿受其束缚。长短句系依曲拍而制,其声调上之束缚,视律诗如何啻倍蓗。开元、天宝间,其他诗人尚不肯为,而谓天才纵逸如太白,而肯俯就南蛮歌曲之节奏,为之制词乎?此二词尚难信为白作……长短句词体,在开元、天宝间,尚未为文人采用,较然可知矣。”
唐圭璋不同意胡、龙二人的观点,他明确指出《教坊记》和敦煌曲中均有调名《菩萨蛮》,且北宋文莹的《湘山野录》也言此调为李白所作,因此李白在开元、天宝时有依调作词的可能。另外,其《忆秦娥》已有北宋李之仪“用太白韵”的和词,说明此词调在北宋已广为流传,并将其作者认定为李白,因此亦可否定其为伪作之说。再有,唐圭璋还专门论述齐言绝句诗入乐传唱的情况。他承认在文人词发展之初,以齐言诗入乐比长短句新词的创作要早。当燕乐流行时,一方面依曲拍为长短句之词,更多的则是由于对歌词的大量需求和追求优美动听的词句而取现成的名作以配乐,受听众欢迎,诗人也以此为荣。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这类作品不是词,因此唐氏正面否定胡适的观点,他认为胡适将《忆江南》当作“依调填词第一次”,是不符合事实的,将民间词与文人词混淆,作出词起源于中唐的说法亦是错误的。
不破不立,唐圭璋一方面破除各方不妥当,有违事实的证据和观点,一方面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各种资料来立一己之论,对各条证据逐一核实,论证详细,考论结合,剖析厘定关键概念和思路,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当然词的起源本身并非一个确切的时间点,而是一个时间段的考量且源于民间,加之史料记载不足,因此要明确断定起源时间尚有困难,有待后世新资料的发掘。目前,学界大致将词的起源定于隋唐之际,这样一个较宽泛,模糊的范围内。
二、观一代词史:词史的时间书写
唐圭璋没有专门的词史专著,其有关词史的研究主要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呈现。既有考证之文,亦有论述之章,《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后收入《宋词四考》中)是其中最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之一。词史本来就多指,通过对词人、流派及其作品进行历时性的书写,结合时代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对词的发展流变作规律性的总结。因此,考证词人时代先后,包括其生卒年及其他方面的原始资料和基本信息,就成了词学家研究词史最为基础性的工作。唐圭璋是在陈伯弢《两宋词人时代先后小录》之后,重新进行的考证,陈氏之录是根据词人登第先后,顺次排比,共有165人,但仍漏略不少重要词人。除此之外,唐圭璋认为科举登第自有先后,仅以此为据,或未能尽当。因此,唐氏广搜稗史、地方志、族谱、年谱、选举表和登科录诸史料,继陈氏之后重考词人时代先后,以观一代词史之源流变迁,正如其所言:“宋词人时代先后,有关词学发展过程,述先后考,为学者知人论世之资。”
唐圭璋《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一文,考证了从北宋王禹偁到南宋徐君宝共计693位词人。他首先是按照词人生卒年排序,生卒年不可考的词人将考其登第时间,登第时间不可考则考其仕官踪迹及所与交往之人等相关信息,简要考察个人的身份履历,如均无可考则阙如。唐圭璋撰述此文的体例:首先,是词人的姓名字号,因为古人常有同名异字或异名同字者,如果混同则遗误词史。其次,考明词人籍贯。再有,此文的关键,即考证词人的生年、登第时间、卒年、享年几何,并点明具体生活时间范围,全文以词人生年排序。如王禹偁,生于周世宗显德元年,太平天国八年进士。卒于咸平四年,年四十八(954—1001)。中间或加注其具体担任官职,如潘阆,“真宗时为滁州参军”,但如果以上均不可考,则考其踪迹及与其亲近之人,如“徐君宝妻,有词见《辍耕录》。君宝,宋末岳州人。其妻被掠杭州,弗从敌,投水死。”然后,还要点明《宋史》是否有其传。最后,考词人有无词集以及词集名称。如果没有词集,则考其词之出处,以备学者或读者核实。由上可知,其所考词人之简略史料较陈伯弢更为合理、详尽,且词人数量众多,对于后世的词史研究者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史料来源。
词人的生卒年的确定,一方面,关系到对词人词作或其生平经历的考察;另一方面,词人时代先后的排序,对于词史的书写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以张元干为例,唐圭璋在1934—1935年发表此文时,已考其生年为元祐六年(1091)。之后,曹济平再次以充足的证据考其生年为1091年,确凿无疑。但《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和《知识丛书·宋词》皆误认为张元干生于1067年,卒于1143年。而事实是,张元干也并非卒于1143年。由于生年错误带来的问题就是张元干寄李纲及胡铨的《贺新郎》一词的时间,也随之俱误。小则影响对词人词作的解读,大则可能将使词人生平经历、交游出仕等重要信息出现误差,如误认为张元干生年为1067年,比真实生年早了整整24年,那么在1067—1091年间发生的事可能会误加到词人经历中,而导致1091年后的事,如张元干与李纲、胡铨的交往,这样关键的事件被误读,甚至某些事件因时间的冲突而被质疑,进而影响与其相关的其他词人事迹的考证,导致词史上某个时间段的混乱。
再次,以柳永为例。在唐圭璋此文的柳永条目中,考证其约生于雍熙四年(约987年),约卒于皇祐五年(约1053年),比张先大三岁,比晏殊大四岁。唐圭璋在1957年在此发表《柳永事迹新证》一文,对柳永的生卒年及其身世做了详细的考证,他根据《能改斋漫录》、地方志等史料,与柳氏词作相结合加以印证,以文史结合的方式再次补充说明自己此前的结论。詹安泰在对宋词作家按照时间排序时,柳永排在范仲淹、张先和晏殊等人的之前,除此之外,詹氏在其《谈柳永的〈雨霖铃〉》一文中,认定柳永于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中进士,与唐圭璋所考证的时间亦相吻合,唐氏的考证得到了当时学者的认可。倘若如此,那么意味着传统的宋词分期,尤其是考察宋词初期的创作分期则要有新的转变,词史的书写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王兆鹏在《词学研究方法十讲》中,就以柳永为例说明词人年代的考证对于词史研究的影响,他说:“一个词人生活年代的确定,可以丰富”甚至改变我们对于词史进程的认识。过去的文学史和词史,都认为柳永比晏殊、欧阳修们要小,所以给宋词分期的时候,是把晏欧划在第一个时期,而把柳永划在后面的第二个时期。我老师唐圭璋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考明,柳永实际上比晏、欧还要年长,他的创作早于晏、欧,这样就把颠倒了的词史纠正过来了。一个词人生卒年的确定,竟然改写了我们对词史进程的认识!所以,考订词人的生平事迹,不光对研究个体词人有价值,对研究整个词史的演进历程也有重要意义。如在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中,就认为初期的北宋词继续着晚唐五代词的作风,是小词发达的时期,晏、欧同属北宋词的第一期,张先跨北宋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他将柳永放在北宋词的第二时期,认为北宋第二时期词的转变是慢词起兴,且把柳永当作慢词的创造者。除此之外,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薛砺若《宋词通论》、龙榆生《中国韵文史》,均将范仲淹、晏殊和欧阳修放在宋初词的第一期,而将柳永放在第二期,这也正坚持了传统词学所认为的,宋初主要是继承唐五代小词的观点,想当然地认为小词在宋流行早于慢词。而唐圭璋考证出柳永出生年代早于晏、欧之后,则可还原词史原貌,即北宋初期慢词已经开始流行,而非晚于小令。在他看来“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业词人,是宋词昌盛的奠基人。……柳词是始出,张词是继出;柳词在先,张在后;柳是主,张是辅”,从而进一步否定了前人对于宋初词发展状况的错误认识。当下高校中通用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中,也采纳了唐氏的考证结果,将其放在北宋词坛的初期中去讨论,再现词史的本来面目。
由以上两例可知,词人生卒年及其生活时代的考证,对于词史的书写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唐圭璋通过对近七百位词人时代先后的考证,为词史研究者们提供编年词史可靠的参考资料,对于坚持词史撰写的客观性,梳理词史的发展源流功不可没。
三、述一地词风:词史的空间地理书写
产生于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自然会打上其时代的烙印,是其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体现,各自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内容,正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同一时代不同区域也会有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呈现。关于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不言而喻,除了鲜明的时代性外,文学作品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因此,在我们对于文学史的梳理和研究中,如果只探讨其时代性特征,而忽略其地域性特征,只进行历时性的编年,而忽略共时性的地域文学研究,那么这就很难写出全面、客观或接近于历史原貌的文学史,所以我们应将文学的时代性与地域性相结合,以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交互配合的方式书写文学史,这样方能真正反映文学史的全貌。
唐圭璋以《两宋词人占籍考》《唐宋两代蜀词》《宋人父子能词》和《宋人兄弟能词》等为主的四篇文章,正是体现了在词史研究中对于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的关注。通过对词人具体地域分布的梳理和其家族创作的介绍,为词史的空间书写准备了翔实的资料,便于词史研究者,一方面探索词史发展中所受的地域环境的影响,正如唐氏所言:“兹考两宋词人之籍历,按省分列,借以觇一代词风之盛,及一地词风之盛。”同时也启发了后世学人,探索家族文化与词人创作的承继关系,包括词人品行、学养、词风的形成、表现手法、情感内容等多方面的影响,从多元的视角和方法,还原词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对词的演进变化有更为深入、立体而全面的认识。通过以时间和空间相结合的书写方式,来实现文学史的勾画中动态与静态的交互,最终达到尽可能还原文学在历史中原本存在的状态,展现文学在某一时代的空间差异和某一空间的时代变迁。
这就与当下文学地理学研究不谋而合。杨义曾较早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构想,更是直接阐发了文学史空间维度书写的想法:“‘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一个旨在以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通解文学之根本的前沿命题……地图概念的引入,使我们有必要对文学和文学史的领土,进行重现丈量、发现、定位和描绘,从而极大地丰富可开发的文学文化知识资源的总储量。”其后,曾大兴对 “文学地理学”作了具体概念的界定,通过对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对文学家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等构成的影响;还要考察文学家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形成的文学传统、营造的文学风气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构成的影响。此段表述一再强调的就是文学与地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文学的地域性。
(一)词人的地域分布
在《两宋词人占籍考》中,唐圭璋共列出两宋词人871家的籍贯分布,不仅仅标注词人所属何省,更进一步点明其所属具体地名,如张炎,除了标明其籍贯所属浙江省外,同时亦确定其为枢子人。这不仅让我们在宏观层面上看到词人的南北分布,又可看到南北区域中的省际分布,再进一步划分省内区域词人,研究不同区域文化对词人创作的影响。简列下表:

表1 两宋词人地域分布表
从上表即可看出,两宋籍贯可考的词人中,南方词人的数量是北方词人数量的四倍还多,浙江或江西一省词人之数是北方五省词人之数的总和。虽然尚有籍贯不明者未予统计,但这也足以说明宋词所属之地域分布的概况。浙江词人数量最多,和江西词人相加已过半数。一方面,在两宋时期,尤其北宋后期至南宋,北方地区频遭少数民族入侵,地区形势不稳定,战争带来了经济、文化方面的破坏和人口的减少,温饱尚成难题又有何闲情雅致去填词赋诗;另一方面,江、浙地区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地区则相对稳定,人口南迁,带去了高效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南方经济发展,同时北方的文化也逐渐与南方文化融合。
至南宋时期,定都杭州,帝王们“直把杭州作汴州”,当时南宋小朝廷的苟安让文人有了暂缓奔波的休憩,故词作会有增加,且明显南方词人多于北方。这些词人中一部分是沉溺于醉生梦死的歌舞升平的假象中,作淫狎妖艳之词,另有一部分人则因战争带来的流离之苦和家国之恨,而心有郁愤喷薄而出,多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普通受难民众的同情。直到清词中兴时,浙西词派仍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词学流派之一,这种词史上的地域渊源和潜在的文化影响都值得我们思考。除此之外,如江苏词人的创作以致其所形成的地域文化对于其形成常州词派词论思想的影响;两宋时期四川词人创作与五代西蜀词之间的承继关系,以及四川特有的巴蜀文化对词人创作的影响,词人风格与其他南方地区的词风有何不同;广西仅有的可考籍贯的两位词人均为临桂人,而清季四大词人中临桂词人就占了半壁江山(王鹏运与况周颐),乡学渊源素来有自,其所处之地,较中原地区而言,甚为偏远,且经济落后,但临桂却在词史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系列的词史现象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王兆鹏《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一书,在唐圭璋此文的基础上,依据词人生平事迹新的发现和现行行政区域的变更,对宋词作者的地域分布作了重新统计,他将词人按地域不同,划分南北方,依各省统计,同时按时代不同分北宋和南宋,并统计每个时代每个省份词人及其作品的数量,以及所占总量的百分比,还对各省进士人数进行列表汇总。将时代、地域、作者人数、作者数量,四者结合进行分析,更有利于在研究词史过程中,发现不同地域文化,在不同时代中,词人创作的分布情况,进而对词人词作集中的区域作重点研究,探索地域文化和时代变迁与词创作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说词的地域特色。
唐圭璋《唐宋两代蜀词》,可以看作是对《两宋词人占籍考》的继续和深化。《两宋词人占籍考》虽已有注明词人具体的府县名称,但并未进行归类,亦未对词人做进一步的评述。而在《唐宋两代蜀词》中,唐圭璋对从唐代李白起的蜀地词人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内容主要涉及唐宋蜀地词人可考姓名者60人(包括蜀妓),作者对其中除蜀妓之外的55位蜀地词人进行简述。唐氏首先介绍词人姓名、字号,另有词人登第及仕宦情况,然后言及词人词作的保存状况,收录于何集,总概括其词风,并引前人序跋或词话中对词人的评论,最后举词人名作一首,作简要地赏析。因唐代蜀地词人相对分散,而宋代则相对集中,故唐氏对宋代蜀地词人进行了归类并置,列简表如下:

表2 宋代蜀地词人地域分布
从表中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宋代蜀地词人中,以眉州词人最多,其主要作者有苏轼、苏辙、苏过、程垓、杨恢、李从周、家铉翁八家,其中苏轼、苏辙兄弟文名远播,为宋代第一流的学者。想必这也并非偶然,造成词史发展地域性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是通过其对于词人生活方式、品行的滋养,以及初期教育等方式发生着作用。正如刘扬忠所言,五代时,西蜀“花间”词有着鲜明的西蜀地域文化的印记,而这样的词风传统受着四川地域文化的熏染,也影响着一代代的蜀词风格。在他看来:“至今我们还缺乏将词的地域性作为贯穿一部词史的一种地理文化现象来对待的全面系统的研究。”
(二)词人与家族文化
法国文艺评论家丹纳曾经指出:“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也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一个地域的文学家族,也是其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考察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来进一步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最终探索其文学作品的地域特色,成为当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陈寅恪在其文中也指明此中关系:“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系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所以曾大兴在其建构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时,也一再强调文学家族所具有的地域与血缘的双重属性,将文学家族作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就此而言,词人与其家族文化亦成为词史空间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圭璋曾撰有《宋人父子能词》和《宋人兄弟能词》两篇文章,他曾自言道:“予考宋人父子之能词者,复考宋人兄弟之能词者,以资研究词史者之探讨”。其粗略地考证宋代父子、兄弟皆可作词者,这就为我们研究词人创作与其家族文化之间关系提供了线索。
宋人父子能词者有22家:1.赵项—其子赵佶—赵佶子赵桓、赵构—赵构所立太子赵眘—赵眘孙赵扩。2.晏殊—其子晏几道。3.王益—其子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王安石子王雱。4.范仲淹—其子范纯仁。5.韩琦—其子嘉彦。6.曾布—其子曾纡—曾纡子曾淳。7.秦观—其子秦湛。8.晁冲之—其子晁公武。9.米芾—其子米友人。10.葛胜仲—其子葛立方—葛立方之子葛郯。11.胡舜陟—其子胡仔。12.朱松—其子朱熹。13.曹组—其子曹勋。14.韩世忠—其子韩彦古。15.洪皓—其子洪适、洪迈。16.韩元吉—其子韩琥。17.周文璞—其子周弼。18.牟子才—其子牟巘。19.周晋—其子周密。20.冯取洽—其子冯伟寿。21.刘辰翁—其子刘将孙。22.张枢—其子张炎。
宋人兄弟能词者共计21家:1.王琪—其弟王珪。2.苏轼—其弟苏辙。3.曾巩—其弟曾肇。4.孔武仲—其弟孔平仲。5.谢绛—其弟谢维。6.黄大临—其弟黄庭坚。7.秦观—其弟秦觏。8.晁补之—其弟晁冲之。9.苏庠有—其弟苏祖可。10.谢逸—其弟谢薖。11.朱敦复—其弟朱敦儒。12.黄公度—其弟黄童。13.楼锷—其弟楼鑰。14.楼扶—其弟楼槃。15.李洪—其弟李漳、李泳、李淦、李淛。16.陆淞—其弟陆游。17.吴渊—其弟吴潜。18.萧崱—其弟萧泰来。19.严羽—其弟严仁、严参。20.翁元龙—其弟吴文英。21.李彭老—其弟李莱老。
唐圭璋还注明了每一位词人的词集或其词的收录情况,以备研究者复核。沿着唐氏所列词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考察词人父子或兄弟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其家族文化中对词人成长、品性和学养,进而对其词的创作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家族文化的特征也是地域文化的特色,而地域文化的特色也需要家族文化来表达和呈现。
上文中根据唐圭璋的考证,王益及其子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王安石之子王雱均有词作流传。王安石之父王益,22岁中进士,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能改斋漫录》存有其词,多抒发相思之情,温婉缠绵,未脱晚唐之风。王安石之弟王安国,以文章而著称于世,其词存于《花庵词选》。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中收录其《清平乐》(留春不住)一词,唐圭璋以“颇为名隽”赞赏此词。王安石弟王安礼,官拜尚书左丞,亦有文名,其词存于《王魏公文集》。王安石子王雱,诗文词兼善,其与王安礼、王安国合成“临川三王”,是临川文学的杰出代表,其词见于《扪虱新话》。薛砺若在《宋词通论》中评价三人之词时言:“他们叔侄词虽不多见,然较介甫蕴藉婉媚多矣,足见当年临川王氏家学一斑。”薛氏在论词时也注意到家族文学对其词创作的影响。
当然王氏家族中,最负盛名者当属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文均堪称一流之作,自不必多言。另有词集《临川道人歌曲》,与其诗文相比,留存之词较少,但以《桂枝香·金陵怀古》最为著名,唐圭璋称赞此词“笔力劲峭”。更详尽的探讨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比较研究,比如家族成员之间,创作手法、作品内容和风格之间的具体异同,发现其创作中所具有的家族基因和区域特色。这为词史的书写,提供了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元的研究视角,举一反三,亦可以以此为突破点,扩大词史的研究范围。当下已有学者尝试将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相结合来撰述词学史或文学史,使文学史研究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唐圭璋虽未有专门的词史著作,但其对于词史的相关研究对于当下词史的书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唐圭璋对于词的起源的认识,既受当时敦煌文献研究的影响,也受当时文学研究关注民间文学的学术思潮的牵引,其观点也与诸词学家观点不尽相同,他坚持己见,但并不定于一尊。他的《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凭借其《全宋词》的考辩之功,澄清词史中存在争议的时间节点问题。这些研究工作均是对于词史的时间限度上的把握。与此同时,唐圭璋对于词史空间向度的书写,则更对文学地理学,或词学地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