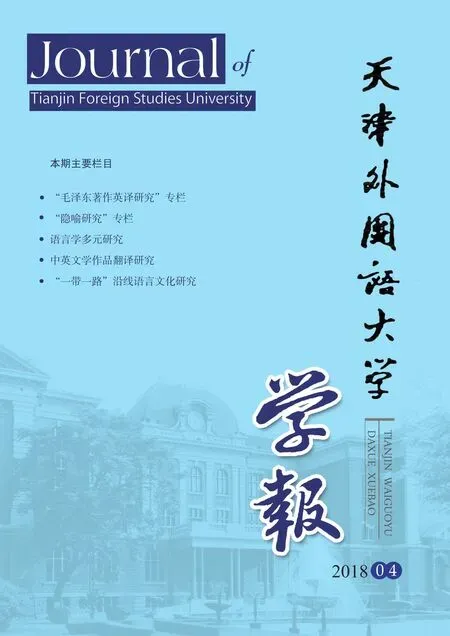毛泽东诗词英译与意识形态
2018-07-20李琳,陈琳
李 琳,陈 琳
毛泽东诗词英译与意识形态
李 琳1, 2,陈 琳1
(1.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2. 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从组织方式、出版背景、翻译形式等译本外部因素以及文本语言特征对国内文革时期的官方定本与同时期西方出版的各代表译作进行考察,进而厘清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的表现方式。作为集体翻译成果的官方定本在内容上忠实原文,政治意识形态操纵痕迹较重,而西方的译作数量大,翻译形式丰富,译者的自主性强。同时也分析了指导译者行为的形式、习俗与信念等因素,这些因素和意识形态的政治表现方式合力造成了毛泽东诗词译文的多样性。
意识形态;毛泽东诗词;翻译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重点从文本内部逐渐转移到了文本外部,在秉承并发展这一研究路径的文化学派学者看来,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单纯语言转换,他们关注翻译活动所处的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等语境,并认为翻译带有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引入改写的概念,用以包含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过程,并指出翻译是最为明显,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改写形式,产出的译文可以脱离源语文化环境在异域落脚,进而在目的语文化中塑造原语作者和作品的形象。
改写理论聚焦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研究,提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种意图的改写“都是对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反映,并通过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学进行操控,使其在特定的社会中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Bassnett & Lefevere,1990:47)。文学翻译作为改写的一种形式产出的翻译文学是文学系统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在勒弗维尔所讲的意识形态、赞助者和诗学三者中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翻译过程的各个层面,当对语言的考量与意识形态有冲突时,后者总是胜出(Lefevere,2011:39)。虽然三因素论中的诗学因素也是文学翻译的主要操纵力量,但是在意识形态处于文化系统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诗学因素也受制于意识形态,并成为其附庸。
文学外译作为文学翻译的组成部分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意识形态在政治高压时期对翻译的影响程度、方式和结果需要从文本出发,重视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取向以及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本文以外文社出版、俗称官方定本的《毛泽东诗词》()和西方出版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为例,横向比较和分析中西社会文化背景下毛泽东诗词英译的意识形态。本文的目的并非为了验证勒氏理论的正确性,而是客观还原不同译本生成的时代背景,分析其意识形态印记和社会与文化影响,折射其在各自文化语境中的功能性。
二、中西毛泽东诗词英译概况
国内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8年的英文版《中国文学》上刊载了19首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文,并于同年由外文出版社结集出版,定名为《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是我国首个毛诗词英译单行本。迄今为止,如不计入再版数目,我国共出版毛泽东诗词英译单行本14部,其中五部在香港出版。相较之下,西方国家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实践要早于国内。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其中收录了作者对《七律·长征》的英译文,这是国外出版的首篇毛泽东诗词英译文。据笔者掌握,西方国家共出版毛泽东诗词英译单行本五部以及包含毛泽东诗词英译文的专著八部,其中毛泽东文选一部、毛泽东研究专著七部。毛泽东诗词译文被纳入了三部中国诗歌集和一部中国文学选集,并在包括《中国季刊》、《亚洲研究》在内的六种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通过国内外多名译者的长期努力,毛泽东诗词英译呈现出选目完整、名篇集中的特点。
文革十年中国大陆的对外文学翻译几乎停滞,这一时期被称为翻译出版的空白期或真空期。而毛泽东诗词作为毛泽东作品外译的生力军之一在文化断层的文革期间经过大规模的修订和重译成为国内翻译出版萧条大环境中的特例,产生了带有浓重时代烙印的集体翻译成果《毛泽东诗词》。该译本的翻译由肩负国家对外宣传任务的宣传部发起,同时指定成员组成毛泽东诗词英译文定稿小组,最后以单行本的形式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该译本被外界称为官方定本。它的出版和对外传播肩负我国文学输出和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双重使命(马士奎,2006:17),是谨慎的政治任务,并为毛泽东诗词法、德、日、西等几种语言的翻译提供了参考(李崇月,2011:106)。与国内文革时期严格的出版环境相比,同时期在西方国家出版或发表的毛泽东诗词英译作品较丰富(见表1①)。

表1 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统计
续表

序号译/作者书/篇名出版社/刊物出版地出版时间篇数 11王慧明(Hui-ming Wang)《毛泽东:诗词三首及书法手迹》(Mao Tse Tung: Three Poems and Calligraphy)American Poetry Review美国19743 12王慧明(Hui-ming Wang)《毛主席诗词手稿十首》(Ten Poems and Lyrics by Mao Tze-tung)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Jonathan Cape美国英国1975197610 13柳无忌、罗郁正(Wu-chi Liu & Irving Yucheng Lo)《葵晔集:中国三千年诗词选》(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美国19768 14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组《毛泽东诗词》(Mao Tse-tung Poems)Foreign Language Press北京197639 15中国民航内部印行《毛主席诗词十首》未正式出版中国不详10 16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内部印行《毛主席诗词(汉英对照)》未正式出版中国不详 17黑龙江大学内部印行《毛主席诗词(汉英对照)》未正式出版中国不详
综观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情况,译作的出版或发表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的译作集中于英美两国,达到13部/篇,大大超过了国内的译作数量。国际力量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分化和改组,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毛泽东作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大国领袖站在了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面。文革为当时的国际关注焦点之一,其发起人自然也获得了相同的国际关注。西方关于毛泽东其人其文的英文著述增多,也刺激了汉学家、作家、诗人等群体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欲望。而同时期出版的官方定本作为对外宣传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的一种形式也被赋予诗学价值之外的政治文本意义,成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并代表着整个文革期间对外文学翻译的最高成就。
三、意识形态对官方定本的影响
勒菲弗尔意识形态三因素论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界限并不明确,就建国后我国的翻译工作而言,诗学服从于意识形态。翻译并出版官方定本主要不是出于诗学目的,而是以毛泽东诗词的诗学特征为载体的外译行为,“以服务本社会的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为目的”(李晶,2007:18)。政治工具性渗透于翻译的全过程,意在塑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积极正面的新中国领导人形象和国家形象,成为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手段,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机构服务。
1 意识形态对翻译选目的影响
国内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新政权,主流意识形态加强了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本时期国内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政治凸显,文学的现实意义即为意识形态性。官方定本的内容为毛泽东亲自校订、审定并于去世前公开发表的诗词39首,从创作于1925年的《沁园春·长沙》到1965年的《念奴娇·鸟儿问答》,时间跨度40年,其中包括反映建国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3篇,如创作于大革命时期的《沁园春·长沙》、土地革命时期的《清平乐·蒋桂战争》和《长征》、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等名篇;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诗词16篇,如创作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游泳》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送瘟神》和《卜算子·咏梅》。这些诗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诗化表达,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史诗”(李左人、夏春秋,1993:27),也是被普遍认为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反映诗人个性特点的诗词合集。官方定本收入了毛泽东和柳亚子、郭沫若等人的唱和诗五首,其中和郭沫若的两首唱和诗被认为“不仅是有才华的作家和国家领袖之间友谊的文学性表述方式,更是历史背景下抒情诗浪漫化的佳证,为研究浪漫主义和革命主义、政治和诗学、意识形态和文学形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个案”(Yang,2008:132)。官方定本翻译的36首译文以诗学价值为依托,将毛泽东的诗才和诗名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
2 意识形态对翻译方式的影响
1957年1月,毛泽东诗词在《诗刊》创刊号上首次公开发表,并于1958年10月、1962年5月、1963年12月和1976年元旦陆续由《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发表或出版,在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诗词的热潮。面对这股出版热潮,毛主席诗词的英译紧跟其后,1958年,《中国文学》英文版上刊登了《诗刊》创刊号上的全部18首毛泽东诗词英译文,并于同年由外文出版社结集出版。后来陆续发表的诗词译文也分别发表于《中国文学》英文版1960年第1期、1963年第1期和1966年第5期上。
官方定本的组织发起代表国家和政府意志。1961年1月,外文出版社呈报对外文委、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文定稿小组,决定由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任小组负责人,成员有袁水拍、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和外籍专家苏尔·艾德勒,还包括外文出版社英文组的于宝榘、汤博文以及后来新增的赵朴初。袁水拍和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共同保证译文的政治导向,并确保对原作的阐释正确,凸显了文革时期毛泽东及其作品的特殊历史地位。翻译目的或动机最为主要的只有一个,即忠实地对外译介和宣传毛泽东诗词(张智中,2005:167)。官方定本还负有匡正其他译本谬误的责任,如小组成员叶君健曾指出:“(国外译本)由于译者随意简化,并且认为他们自己的解释,在正确性方面超过了外文出版社的译本,译文也出现了不少的误解。”(叶君健、吴瘦松,2003:26)官方定本采取集体翻译的方式,符合并维护了文革时期意识形态的需要,树立并宣传了诗人的正面形象。译本定稿时采用了小组成员、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建议,除了毛泽东自己的注释,其他人所作的注解一律撤销,连《蝶恋花·答李淑一》原有的编者注也没有采用。译本后附有《原作诗体简释》,以达到最大限度地凸显原作者和作品本身,实现意识形态输出的目的(马士奎,2006)。
3 译本中的意识形态
官方定本的译文标题统一用代表革命的红色,包括组诗在内的各诗词首行第一个字母的字号大小与标题一致,即为普通字号的两倍,契合毛泽东诗词气势恢宏的特点。我们以《忆秦娥·娄山关》第一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的译文为例,官方定本的译文为Fierce the west wind, /Wild geese cry under the frosty morning moon.正文首词fierce首字母的大写从词形和词义以及句式倒装等方面凸显了“烈”字的力度和凛冽之意。译文在内容上忠实传意,把原词的思想内容完整、准确地进行传达,最大限度地向原文的意义靠拢。创作于长征路上的《忆秦娥·娄山关》是遵义会议后红军在鏖战中重新占领娄山关后创作的。从艺术手法来看,本词采取高度浓缩的写法,表达了特定时刻的情感意绪,自然景物是实写,红军战斗是虚写,以实写反衬虚写。下阙中“真如铁”和“从头越”共同表现出红军坚强的信心,既严肃且从容。官方定本分别译为a wall of iron和cross its summit,忠实表达了原意。中国文化中表达城池易守难攻会用“铜墙铁壁”来形容,官方定本的a wall of iron表达的意象即是如此,直观地描述了娄山关的险要和坚固,符合中国文化的认知。
作为我国文革时期文学外译的代表作,官方定本坚持集体翻译,并由定稿小组负责人袁水拍和乔冠华共同把关,避免用词模糊,保持译文政治导向正确,最大限度地向原文意义靠拢。它使用的语言,尤其是与革命事件直接相关的用词在语义上呈现出立场清晰、表达明确的特征。如创作于土地革命时期的《清平乐·蒋桂战争》描述了闽西地区新旧军阀的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而最后一句“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呈现出红军抓住时机开辟新革命根据地的情形,“解放了祖国山河的一部分,还到人民手中”(张仲举,2009:19)。官方定本将其译为We have reclaimed part of the golden bowl/ And land is being shared out with a will.原文中的“收拾”和岳飞的《满江红》中“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的用法相同,reclaim意义恰为收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即收复(疆土),凸显金瓯寓意的国土重回人民手里。使用了现在完成时态的reclaim与后文的bowl形成动宾结构,但是由于宾语前的限定成分part of,译文也明确了将破碎金瓯的其他部分陆续收回的联想意义。句中“金瓯”的原意是金属杯盆或盂等器具,后用于喻指国家疆土完固。官方定本译为bowl,碗让人自然联想到米,进而和出产稻米的土地相连,和后文庄稼生长的land形成了语义连贯。作者是伟大的革命主义诗人,不会使用统治阶级使用的装饰物件来象征战火摧残、饿殍千里的中国。与同时期出版的译本用的vase相比较,bowl的联想意义和金瓯的比喻意义较为契合。因为vase为家居器具中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同时带有封建享乐的含义,用来翻译“金瓯”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分田分地”中的“分”在官方定本中被译为share,比divide和redistribute更为准确。因为当时苏维埃政权分田分地的实质并不是指土地归农民个体所有的,而是分享,土地的所有权在当时并不是最重要的。
四、意识形态对西方国家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影响
相对于中国文革时期严格的政治环境,西方国家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具有译作丰富、出版背景宽松、译介目的多样、译者主体性更强等特点。这些译作的译者多为个人独译或中西合译,翻译策略也展现了较大的差异性。翻译策略和方法的拟定及实施等也受到不同的影响。
1 意识形态对翻译选目的影响
作为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代表,英美两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领导人的关注在中国文革期间达到新的高峰,出版了大量毛泽东传记和政论文的翻译。毛泽东诗词英译共出版八部著作,其中单行本四部,包含毛泽东诗词译文的中国诗歌集两部、毛泽东研究专著两部,还有五篇包含诗词译文的期刊论文。表1中译本2,7和9为当时毛泽东审定并发表的诗词全译本,译本6对10首毛泽东诗词进行了英译或引用,其中八首为毛泽东创作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词,其他两首为建国后的唱和诗;译本8英译了16篇毛泽东诗词,依据的原文是何如的法译本;译本12翻译了10篇,选目来自1969年上海东方红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首》。
2 意识形态对翻译方式的影响
在英美出版的八部毛泽东诗词英译单行本中有一部为个人独译本,其他三部为中西译者的合译本②。本时期英美文化语境中的毛泽东诗词翻译通常与对毛泽东的个性和中国革命的叙述结合起来,同时兼顾对中国诗歌传统的介绍。较之官方定本中对译者痕迹的淡化,英美各译本将较大篇幅用于前言、结语、注释、画像及照片、诗词手稿等副文本信息上,侧重于以诗词为媒介全面介绍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满足读者群了解毛泽东和东方世界的需求。译本12的译者王慧明是一位热爱中国诗歌的木刻家、画家、书法家,他在译本的介绍部分交代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并把诗歌翻译和教授中文诗歌结合起来。他重视诗歌中汉字的象形意义,将其看作诗境的画意表达,并认为在译文中再现中国诗画一体的传统是有益的。因此,他的译本里包含了大量毛泽东的诗词手迹以及译者本人根据诗词主题创作的木刻作品。译者使用威氏拼音展现毛泽东诗词的音韵特点,还利用毛泽东诗词书法手迹多角度展现诗人的文才。
3 译本中的意识形态
受制于所处在政治高压环境,官方定本的文本形式与原文保持高度一致,在用词上注重准确度,并经过严格的政治把关。而英美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文对原文不再亦步亦趋,根据不同的翻译倾向和目的,译文在文本形式和用词等方面体现了诸多西方意识形态特点,用词的整体特点为向英语文化词汇和表达靠拢,同时对负载政治敏感性的词汇处理存在任意性。首先,英美译本对文本形式的处理较为灵活。译本9对每首译文都给出详细解释,包括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以及诗词创作背景等的介绍。译本12的每篇译文分前后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把各诗行从上至下分成四个子部分:(1)诗词原文汉字的威氏拼音;(2)诗词原文;(3)字对字翻译;(4)诗行直译,随后列出经过句法调整的该篇译文和注释。译者实现了自己在前言中交代的通过诗歌翻译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学习中文诗歌。在对第三个子部分字对字翻译时采用英文中最常见的词,以便简单明了地交代原文中各汉字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原诗的风貌。其次,英美文本具有多用英语文化词的特点。《清平乐·蒋桂战争》中“分田分地”在译本7中的译文为meadow,为英语中常用的土地概念,但意义为草地、牧场,和中国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田地概念相异。《忆秦娥·娄山关》中的“真如铁”在译本12中被译为ironclad,为西方战斗中人们熟知的装甲,符合西方对战斗的认知。
英美译本在翻译政治敏感词时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译本2和7把“分田分地”中“分”译为redistrubute和give away。作为英美四部毛泽东诗词单行本中唯一的独译本,译本12的译者王慧明使用了share。他引用太平天国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和1906年黄兴在湖南领导的暴动等示例解释了redistribution等词不成立的原因。分田分地即为革命旗帜,分不是划分或重新分配,而是分享集体农业劳动带来丰收的希望,田地的所有权在谁手里显得不那么重要。重新分配也许更科学、现实、合法,而分享更道德和符合人性,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意义所在。
五、结语
翻译在目标语系统中有现实存在性和重要功能性。我国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成为我国塑造积极、正面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的重要手段。我们从本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组织开展带有明显官方背景的毛泽东诗词小组英译活动,并对翻译过程和结果进行政治上的把关,被赋予强烈的政治依附性。而英美的毛泽东诗词翻译均为个人行为,译者的翻译倾向和目的是多元的,出版环境相对自由的英美国家给译者带来更大的自主性,可以最大限度地去迎合西方读者,而不用担心译文的处理会犯政治错误。
注释:
①本表按出版或发表时间统计了国内和西方国家出版或发表毛泽东诗词英译单行本以及包含毛泽东诗词英译文的著作和期刊论文的情况,内部印行本因时间不可考而置后。其中译本2为重印本,首译本于1965年在英国出版;译本15由中国民航内部印行,译文和官方定本基本一致,仅有极少数的句法调整。
②译本7注明由Willis Barnstone和郭清波合作完成,但在2010年再版时去掉了原版中的合作者郭清波,并在封面内页和版权页上注明该译本的翻译、介绍以及注解均为Willis Barnstone完成。鉴于本文分析的为原版译本,在这里仍把该译本视为合译本。
[1] Bassnett, S. & A. Lefevere. 1990.[M]. London: Printer Publishers.
[2] Lefevere, A. 2011.[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3] Yang Haosheng. 2008. A Modernity in Pre-modern Tune: Classical-style Poetry of Yu Dafu, Guo Moruo and Zhou Zuoren[D]. Harvard University.
[4] 李崇月. 2011. 毛泽东诗词翻译研究述评[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106-109.
[5] 李晶. 2007.“文革”时期的中国翻译——“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D]. 南开大学.
[6] 李左人, 夏春秋. 1993. 毛泽东诗词与中国传统文化[J]. 社会科学研究, (6): 27-33.
[7] 马士奎. 2006. 文学输出与意识形态输出——“文革”时期毛泽东诗词的对外翻译[J]. 中国翻译, (6): 17-23.
[8] 叶君健, 吴瘦松. 2003. 毛主席诗词在欧美文字的十种译本[J]. 出版史料, (4): 18-29.
[9] 张智中. 2005. 毛泽东诗词英译比较研究[D]. 南开大学.
[10] 张仲举. 2009. 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of Mao Tse-tung’s Poem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 Lin & CHEN Li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official English version of Mao Tse-tung’s poem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ith the western versions from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ways of organization, publishing backgrounds and translating methods, as well as internal aspects like language features, so as to explore the power of ideological factors over translation. The official version abides a prudent pursue of faithfulness, whereas the western translations are diversified in free style. The paper also analyses the forms, customs and faiths which govern translators’ action, together with the political ideological control, to bring diversified translations of Mao Tse-tung’s poems.
ideology; Mao Tse-tung’s poems; translation
H315.9
A
1008-665X(2018)4-0010-09
2018-01-15;
2018-02-14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毛泽东诗词英译与译者主体性发挥”(15YBA356);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专项“意识形态对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影响研究”(14MY32)
李琳,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学、毛泽东诗词翻译 陈琳,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