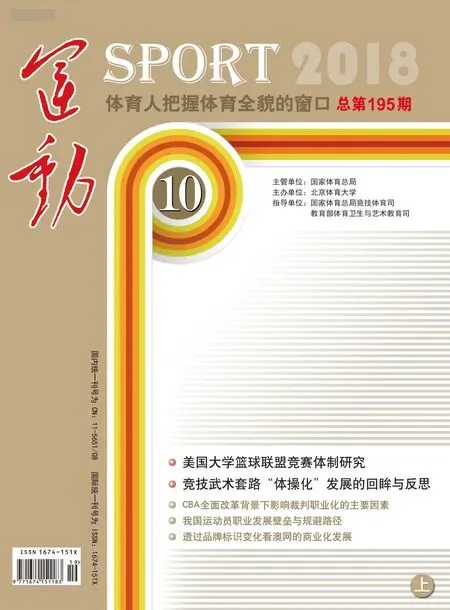武陵山片区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景观研究
2018-07-14周丽华
周丽华,唐 强
(1.湘潭大学体育教学部,湖南 湘潭 411105;2.长沙市明德天心中学,湖南 长沙 410007)
1925年,伯克利学派学者索尔发表《景观形态学》,成为以文化景观研究为起始的文化地理学开端。民族传统体育经历数千年的积累沉淀,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其所呈现的文化景观既简单又内涵丰富,电视节目、舞台艺术、节日庆典、田间娱乐形成了可感知、可欣赏的体育文化景观形式。武陵山片区作为湖南、湖北、贵州、重庆三省一市交界之地,境内聚居着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等众多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丰富。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景观体现了武陵山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传承积累而自然凝聚的民族所共有的人文精神与物质体现的总和。
1 民族传统体育景观类别
根据武陵山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开展形式、表达内涵等方面,可以将传统体育文化景观分为以下几大类别。传统(伯克利学派)分类方法可以将传统体育文化景观分为物质文化景观与非物质文化景观;传统体育的物质文化景观包括开展体育活动的场地、器材、服装、道具等;民族传统体育的非物质文化景观主要表现为民族精神、民间信仰和参与者的情感体验等方面的因素。
根据体育文化景观特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物质文化景观与非物质文化景观难以有明显的界线。非物质文化景观常常需要物质文化景观形式体现,而物质体育文化景观中蕴含着非物质体育文化景观的文化内涵。因此,传统的文化景观分类方法不是全面体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性的认知方式,不具有基于文化地理学研究体育文化现象的意义。为了更好地归纳武陵山片区各民族体育文化景观的类别,根据民族传统体育不同的表现形式分为以下几类。
1.1 节日体育文化景观
传统节日活动是民族传统体育的载体。民族体育活动构成了民族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种多样的传统体育活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节日文化生活,而且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成为区域性的文化景观形态,能够成为人们关注的活动形式、吸引关注者的原动力。例如,苗族赶秋节是湖南湘西花垣、凤凰、泸溪等地的大型民间活动,2017年8月7日在调研花垣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赶秋”活动中获悉,“上刀梯”、鼓舞、舞龙、舞狮、接龙舞、八人秋、椎牛、绺巾舞等传统体育活动是赶秋节中重要的活动组成部分,是各村各寨民族文化展示的大舞台。除苗族赶秋节外,苗年、龙船节、六月六、四月八,土家族舍巴日、过赶年、六月六、牛王节,仡佬族毛龙节、敬雀节等传统节日活动中的体育文化元素构成了节日活动的主体,成为节日活动中的文化景观形态。
1.2 村寨体育文化景观
村寨是民族体育文化活动的基本单元,是体育文化产生的重要场所。在武陵山片区,因地理的封闭性和政治的边缘性,少数民族村寨成为各民族文化活动的基本场所,现阶段大部分少数民族村寨都很好地保存了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村寨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例如,具有浓厚苗鼓文化特色的鼓戎湖村,2014年8月被花垣县人民政府命名“董马库乡夯寨村苗族鼓舞传习所”。2016年8月调研中发现,该村男女老少都能参与鼓舞表演。在2016年8月5日花垣赶秋活动中该村鼓手占据70%,苗鼓200多面。在村寨文化建设中,民族传统体育成为各村寨的文化亮点,不仅满足自身文化活动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吸引外界各种资源的文化景观。
1.3 体育旅游文化景观
武陵山片区是多民族聚居区,保存着丰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资源。《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指出,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实施特色民族村镇和古村镇保护与发展工程,形成一批文化内涵丰富的特色旅游村镇,文化旅游已经成为政策规划的操作模式。作为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民族传统体育逐渐成为发展旅游产业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有效战略。体育旅游作为武陵山片区的特色文化资源,对推动民族文化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实效性。例如,酉阳县10万人同跳摆手舞,德夯苗寨的“百狮会”、鼓文化艺术节,花垣县“赶秋节”等传统民俗活动的表现意义中,体育旅游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点,其民族性、竞技性、观赏性等因素更赋予了体育旅游文化景观的特性。
1.4 小 结
综上所述,无论是节日体育文化景观、村寨体育文化景观还是体育旅游文化景观,其根本是民族传统体育在不同场合表现出的不同文化意义。因为作为主体的人对传统体育活动的理解不同、视角不同才有景观分类的意义。但寻其根源,节日体育文化景观、村寨体育文化景观、体育旅游文化景观具有同一性和类属性特征,没有明显的区别,体育活动的内容也可以相互转换。
2 民族传统体育景观符号
民族传统体育的符号化,如同摔跤与蒙古族勇士~龙舟与端午节~八人秋与苗族体育活动一样,成为具有民族特性的文化符号。民族传统体育所表现出的动态景观符号特征,不仅秉承着厚重、神秘的民族历史密码,更凝结着明朗而丰富的民族信息,从景观符号中可以领略浓厚的民族文化内涵。
2.1 器械类体育景观符号
器械的使用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在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人类逐渐探索出利用器械提升技能、娱乐生活、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手段。因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族产生了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体育活动器械,并且逐渐成为具有特色性、民族性的体育景观符号。例如,桑植白族仗鼓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艺术内涵,为研究白族人们的生产、生活习俗提供了重要依据,仗鼓也成为白族体育景观符号。
2.2 服装类体育景观符号
在少数民族区域,民族服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不同的场域不同的服饰特点体现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在民族体育活动过程中,各民族着本民族特有的服装参与传统的文化活动,既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也是信仰民族传统体现。例如,毛古斯的服饰极具特色,充满着浓厚的原始风情,通常是用茅草或稻草编制而成。这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服装,成为毛古斯活动中的重要元素,原始性的服装表现使其具有土家族传统体育景观符号特征。
2.3 动作表现类体育景观符号
武陵山片区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景观符号通过主客体——人的动态肢体语言展现出本民族鲜活、健康、常态、具体的文化内容。“动作”是体育活动的基本单元,不同民族体育活动因“动作”组成形式的差异性才具有民族特色,才能融入民族文化的精髓。例如,土家族摆手舞的身体动作主要取材于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和战斗场景,有单摆、双摆、回旋摆等。随着各地的发展变化,其表现形式在各地不完全相同,但其基本特点却是一致的,即顺拐、屈膝、颤动、下沉。正是因为摆手舞“顺拐”的舞蹈形式,其体育景观符号特征才具有民族性特征。
3 民族传统体育景观阅读
密歇根大学的 Nassauer 提出的4个主要文化原理中,强调人类对景观的感知、认识和评价直接作用于景观,文化建造景观。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景观的认识,由物质的具体属性转向表征、传统的索尔式的经验描述与理性认知。体育文化景观的表征不仅体现在静态的器物、场地或图像中,即便是动态的过程仍然在它的势力范围内。通过人特有的视角加以诠释,深入认识揭露体育文化的本质,这种景观的“观看方式”我们称为体育景观阅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景观作为民族文化认知的表征形式,以视觉作为认知民族体育内涵的方法和手段,通过建立人的主观性观察与体育项目所体现的意义之间的联系,对民族传统体育做出合理的解读。这种解读形式主要有干预层、知识层、感知层和诠释层4个层面。
3.1 体育景观阅读的干预层
干预层体现了各民族主体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实现体育健身、娱乐的目的战胜自然,改造自然是人类获得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例如,在浦市传统龙舟文化体系中,战胜自然是其龙舟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具有“小南京”之称的历史文化名镇,发达的沅水航运带来富裕的经济发展同时也面临洪水的困扰,想要享受富裕的生活要挑战自然,获得生存的技能。据湖南师范大学谭必友教授介绍,洪水是浦市传统龙舟的代表性特征,为避免洪水干扰,能够更好观看扒龙船、参与扒龙船,其先祖族“私开黄河”,将龙舟运动从沅水改至人工开凿的水域。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实现参与体育活动的目的。
3.2 体育景观阅读的知识层
知识层通过对体育文化的阅读获取信息,达到充分认识体育文化价值的目的。体育文化景观需要文化主体的认同与理解才具有其价值意义,在欣赏或观看体育表演时首先获得的是该体育活动的表面信息,在具备一定认知和知识的背景下,体育活动所展现出的内涵就会被文化主体“阅读”。作为外来文化者,苗族上刀梯是具有神秘性、惊险性,作为文化主体或具备一定知识体系的学者会认识到,上刀梯是古代巫傩法师进行度职传法或酬神还愿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程序。通过徒手赤脚攀爬锋利刀刃制成的刀梯,以表达巫师具备与众不同的特殊能力,可以开展替代凡人与天神沟通,为人消灾求福的法事活动。
3.3 体育景观阅读的感知层
感知层以民族成分、运动器械、活动场所、运动形式等因素带来的主观印象而不加思索形成的对体育文化的认知。这是最直接的阅读形式,但也必须建议在充分的认知基础上。体育景观阅读感知层的实现,是以知识加经验的组织模式结合体育活动展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特征做出的综合评价。
3.4 体育景观阅读的诠释层
诠释层从阅读者的主观体验出发,能够更主观、更纯粹的理解各民族体育文化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这是最高层次的体育景观阅读能力,主观阅读者能够透过体育文化的表征看清其本质特征,进行分析、归纳、整理,深入理解体育文化的背景、形成因素、基本特征、文化价值等深层次的知识体系。
3.5 小 结
综上所述,体育景观的阅读从干预层、知识层、感知层到诠释层,具有层次的递进关系。这是由浅入深的体育景观的认知形式,是符合人的正常需求模式。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深入放大,对体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感也会逐步加深。
4 结 语
武陵山片区因地理环境的特色性、民族构成的多样性、历史发展的边缘性使区域内蕴含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以人为主体的民族体育活动,在民族文化系统中形成了别致的文化景观,通过节日活动、村寨体育、体育旅游为载体展现出以器械、服饰、动作为符号的景观形态。从发展的视角出发,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景观塑造必须满足以人为主体的理论构建,具体表现为:(1)民族身份认同的需要。在民族传统体育的类属性质中,民族身份的认同常常会涉及项目形式、场地器材、人文环境、服饰道具、文化背景等因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景观的存在被塑造为象征性的形象特征,民族身份就建立在体育文化景观的特征之中。(2)文化主体传承的需要。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使具有丰富体育文化景观资源的武陵山片区在“变”与“不变”思路中完成区域内的自我转型。其一是在“变”的思路中主动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完成体育旅游、体育表演、体育文化传承的景观创造。其二是在“不变”的思路中被动接受文化保护,如以体育文化保护为主导思想的政治制度与保护措施的建立,通过传承原始的、珍贵的、特殊的传统体育项目以景观创造的形式延续发展。(3)体育文化实践的需要。文化景观在民族体育文化领域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智力过程。其内涵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传说、活动形式、器材特点、自然环境深入关联。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文化主体参与了民族社会构成、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政治干预等实践活动,我们在阅读体育文化景观的过程中需要思考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景观形态是如何产生,作为文化实践是如何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