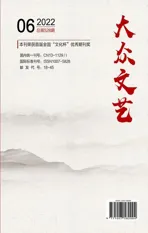查良铮诗歌翻译与创作
2018-07-12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教育系551300
(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教育系 551300)
一、查良铮诗歌翻译
穆旦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是如此深刻地交织在一起,把二者联系起来考察,借助它们之间的“互文”性来探讨问题,我们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译诗特点:意译、注重形式、语言优美
穆旦翻译诗歌的时候,一是直译与意译两者相结合,偏向于意译。他不赞同逐字翻译和硬译,认为应该依据原文风格进行翻译。穆旦翻译时,以“忠实”为准绳,这里的“忠实”不是仅仅字与字、句与句的对仗。这是他在《谈译诗问题》中对自己翻译原则的阐述。翻译过程中不能简单的照搬“信”的翻译原则,因为“信”不是逐字逐句地翻译,不是对其结构和词语的简单忠实。穆旦认为翻译诗歌时,对其风格和韵律的“信”才是关键的,这样才能向读者传达原作的实质精神。穆旦主张意译,但他强调意译是建立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基础上的。穆旦在翻译《致恰达耶夫》八行时,前两行被翻译成三行,而且没有翻译原诗中的“心灵”一词;翻译后四行时,不但没有翻译“神圣的”,而且还对原文的结构进行了一些变动。如果“信”仅仅是指忠实于原文的字句和结构,那么穆旦的译诗显然没有遵循这一原则。但是穆旦的这些变动却忠实于原作的意义,让译作的读者能更加准确的理解原作的主旨和韵味,这才是诗歌翻译的目的所在。直译的话,虽然做到了字句的忠实,但是翻译后的诗歌失去了原诗的韵味,从而失去了读者。穆旦翻译诗歌时,在原诗的基础上,再现诗歌的实质,打破了词语和结构的限制,这为再现诗歌作者的精神主旨是是非必要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穆旦是非常推崇意译的,意译有助于保存原作的生命力。
二是注意保留原文形式。穆旦在强调译诗时不但要考虑原诗的形象,同时要尽量保留原作的形式结构。但是,他认为“诗是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即使原诗用散文优美的翻译出来,但是却失去了原有的特定形式,这其实还是没有忠实地传达原诗的内容”。1穆旦认为形式是诗歌的基础,“诗从来就是有形式的,没有了形式,也就失去了诗”。2“诗歌翻译中,对那些不太重要的字、词或者结构,他会省略不翻译,或者进行转换;为了实现整体的和谐,穆旦在明知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翻译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不是妥帖的方式进行翻译。”3诗歌形式的美就如“三美”中的建筑美一样,可以增加其整体的美感,给读者带来视觉冲击。
三是行文通畅,易于译入语国读者接受。在翻译诗歌的过程中,穆旦力求使用本国语言的优点,尽量避免直译的欧化句子出现。穆旦的这种“为读者着想”的翻译原则,使读者读过译作后不会觉得是翻译作品,而且“翻译是既谨严又流畅,诗意盎然”。4有学者就提出“查译文之所以流畅、洒脱,是因为其翻译不是建立在字面意思的对应,而是依据诗歌的上下文和具体语境活译,然后遵循汉语表达习惯,忠实、准确地加以表达”。5这一点在译诗《给普希钦》中得到了恰当的反映,“可记得你的马车的铃声/彻响了我幽居的院落,/在我那积雪的凄凉的院中/你的来临使我多么欢乐”!6穆旦的这几行诗句可谓是对欧化的啰嗦的翻译的鞭挞,这几句诗歌的翻译是欧洲人表达的习惯,与我国读者的表达习惯不符,显然这样直接翻译原诗的语法结构是行不通的。于是穆旦对其进行修改,按照国人的表达习惯进行翻译,“当你的马车的铃声/ 彻响了我幽居的院落时候”,与“可记得你的马车的铃声/彻响了我幽居的院落”,这一改变增加了诗歌的美感,却没有改变原文的意思表达。
(二)译诗原因:服务于个人兴趣和时代要求
穆旦从事翻译不仅仅是因为个人兴趣,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当时的国人需要更多的优秀外来文化。穆旦翻译了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和大学教材,在1958年被剥夺著作和出版权利之前,他都是使用自己的原名查良铮和笔名梁真。但之后,翻译家的著作和出版权利被剥夺,国内的政治环境日益恶劣,穆旦的处境也越来越糟,而穆旦又是为何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坚持进行翻译呢?穆旦在其写给郭保卫的信中自嘲是“用普希金解闷”;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为中国文学注入新鲜血液的目标“这是我所喜欢的工作。我觉得中国需要这些诗”;7学者易彬更是认为,“穆旦译诗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首先,那些优美的文字足以缓解残酷现实的压力;其次,更因为那些优美的文字被赋予了复兴中国文艺的使命;再次,或许更是个人的原因:写现实如何的作品将有政治风险性;而迎合当时流行的‘小小靳庄式’的写法或图解政治,又想为历史所唾弃。但译诗可以避开这一点,译诗实际上成了写作的替代品”;8当然,回国后朋友的帮助和支持,给穆旦的翻译事业带来了强大的动力,特别是萧珊和巴金夫妇的帮助,“穆旦夫妇回国以后,当萧珊得知穆旦准备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将它介绍给中国读者时,十分高兴,鼓励他多搞翻译,快点拿出作品来。她愿意尽力想法帮助他出版。到50年代中期,穆旦一人出版的译作竟有十几本之多了。穆旦这些译作的出版,是和巴金、萧珊夫妇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分不开的”。9
(三)译诗优势:诗人译诗诗味更浓
不同于翻译散文、小说和戏剧,诗歌翻译在语言的韵味、形式和意象等方面要求很高。因此翻译诗歌的难度相对更大,所遇到的问题更复杂、需要运用的处理技巧更加精妙。穆旦是一位诗人,又有着深厚的外文功底,因此,在翻译外国诗歌的时候更能把握和传达原诗的美学内质。王小波对穆旦的诗歌与翻译极力推崇。他称赞他《青铜骑士》的译文为“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10穆旦对该诗作了这样的理解:爱情的关系,生于两个性格的交锋,死于“太亲热,太含糊”的附顺。这是一种辨证关系,太近则疏远了,该在两个性格的相同和不同之间找到不断的平衡,这才能维持有活力的爱情。单就诗歌的翻译来说,奥登鲜明的现代派诗风跃然在上,显然难以想象这是一篇译文!
再如穆旦翻译的C.D.路易斯的《两个人的结婚》,探讨婚姻的意义,讲述了获悉结婚到为何结婚、结婚的过程和婚姻的结束,全诗共五节,每节五行。第一节中,作者使用“那么”一次,讽刺那些认为踏入婚姻就能过上幸福生活的人们;第二节讲述了两人为何结婚,两人的婚姻誓言源于一天夜里靠窗而萌生情愫,不是传统的教堂里定情的方式;在第三节则是结婚的过程,自结婚起,两人彼此成为对方的私人财产;第四节讲述的是婚姻的破裂。然而,即使婚姻破裂后,两人彼此间的怨恨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诗人将彼此间的怨恨比作战争,而婚姻中的双方则是这场战争中的战士,即使战争结束,双方仍然不能和谐相处,忘记彼此的怨恨。最后一节则是探讨婚姻的意义,婚姻中充满甜蜜,同样也不排次冲突,有事婚姻只不过是人们想象中的空中楼阁而已,并不是那么的美好。在这篇译诗中,穆旦不但保留了原作的风格韵味,与原作一脉相承,同时又以流畅的汉语向读者展现现实的婚姻,婚姻是沙漠,是玫瑰,更是海市蜃楼。
二、穆旦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于缺乏外语人才,没能形成专业化的外国文学研究、翻译队伍,因此,大凡通某种外语的作家基本上都会兼事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在那些作家兼翻译家的创作和翻译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当时中国的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并没有明显的分野,而是个一而二、二而一的文学整体”。11穆旦在当时作为青年诗人已经崭露头角,出版了《穆旦诗集》(1939-1945)、《旗》和《探险队》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应该是穆旦诗歌创作的勃发期,他这时期的诗充满了现代主义色彩;五十年代,穆旦主要精力放在了翻译事业上。然而,五十年代末期,穆旦被打成右派,其诗歌创作的权利被无情的剥夺了,此时的诗歌翻译只能偷偷的进行,虽然环境恶劣,遭到迫害,但是这一时期穆旦却翻译出了很多杰出的译作。正如学者龙泉明说的那样“诗歌翻译过程也是译者与作者心灵会晤、精神契合的过程。穆旦翻译的大多为浪漫主义诗人作品,如布莱克、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等”12。其实,早在初登诗坛时,作为年轻诗人的穆旦就已经“钟情于那些浪漫派诗人,与他们产生过精神的共鸣,其诗歌创作资源直接与他们相关。其中布莱克以张扬原始生命力的‘野兽’意象触动了穆旦;惠特曼则以奔放自由的长诗体感染着穆旦;雪莱抒情诗的忧郁气质和拜伦叙事诗的优雅风格更使穆旦着迷。尽管由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独特的个性气质,穆旦很快走上现代主义创作道路,但浪漫主义诗人的启迪诱导作用不容忽视。在翻译中,穆旦同那些诗人再次邂逅,与其发生更加深刻的精神联系……”13。
作为诗歌翻译家的同时,穆旦又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这无疑对其诗歌翻译有很大的帮助。身兼翻译家和诗人,穆旦在创作和翻译诗歌时,可谓是信手拈来,相互融通。在读穆旦的诗时,我们可以读到济慈、布莱克和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人的风味,而在其译作中则似乎他以往诗歌的味道。如穆旦写的《妖女的歌》和济慈的《无情的妖女》,这两首诗歌主题和诗风都十分相似。穆旦歌颂童年的诗歌,不仅有惠特曼诗歌的“碎影”,还有着布莱克诗歌的影子。如布莱克有一首歌颂婴儿的《摇篮曲》“睡吧,睡吧,幸福的孩子,/天地万物已微笑着安息;/睡吧,睡吧,幸福地睡吧,/俯望着你,妈妈在哭泣。……向你微笑,向我,向全体,/他变成过一个小小的幼婴/童稚的微笑是他的真容,/将天国和尘世哄慰入静。”我们再来看看与这首诗歌相似的穆旦写的《摇篮曲》:“流呵,流呵,/馨香的体温,/安静,安静,/流进宝宝小小的生命,/你的开始在我的心里,/当我和你的父亲/洋溢着爱情。”在这两首诗歌中,主题都是歌颂婴儿,两位诗人对儿童的认同感是一致的,布莱克的诗对儿童的称赞带有西方基督教的味道,穆旦的诗则是用婴儿“柔和的声音”、“微笑的眼睛”和成人“造作的声音”、“恶意的命运”做对比,用成人的丑陋反衬出童年的美好。穆旦早年读过不少浪漫派的诗歌,或许是因为有着同样的感怀而越发记忆深刻,更或许是他在潜移默化中把那些诗歌内化为了自己的东西。这样的互动关系贯穿于穆旦诗歌创作及其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阶段:首先,査良铮早年在课堂上学习了浪漫派诗歌,并在课余时间深入阅读这些诗歌,这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翻译选材、翻译手法还是语言组织上,査良铮都深受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其次,“文革”前到“文革”中,査良铮被迫停止了诗歌创作,但是在翻译事业上依然笔耕不缀,为诗歌创作进一步积累了诗歌创作准备;再次,“文革”末期到逝世之前,査氏又投入到了诗歌创作中去,创作出了一批手法更为成熟、完善的浪漫——现代派诗歌。
注释:
1.查良铮.《谈译诗问题——并答丁一英先生》.《穆旦诗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2.孙潇.《诗人译诗,更见文采—试析查良铮的诗歌翻译》.《文化教育》,2006年第1期.
3.同上.
4.周钰.《穆旦的诗和译诗》.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5.孙剑平.《查良铮译:〈欧根·奥涅金〉的艺术成就》,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6.査良铮.《普希金抒情诗选》,《穆旦译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7.穆旦.《致郭保卫的信》,曹元勇编:《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
8.易彬.《穆旦”与“查良铮”——写在<穆旦译文集>出版之际》,《读书》,2006年第3期.
9.陈伯良.《穆旦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10.王小波.《我的师承》,《青铜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
11.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80页.
12.龙泉明,汪云霞.《论穆旦诗歌翻译对其后期创作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13.魏桥主编.《浙江省人物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