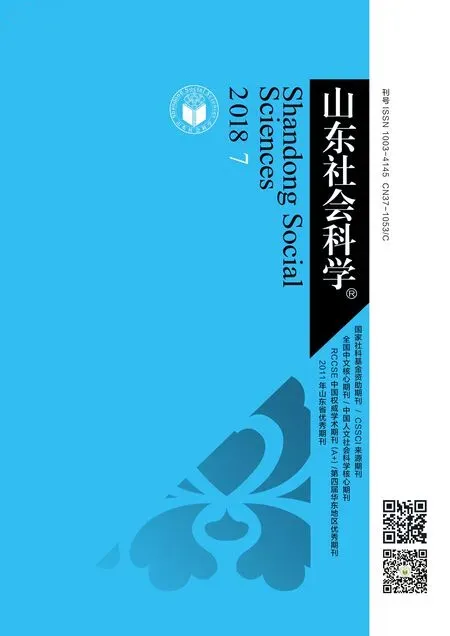移植真的成功了吗?
——器官移植受者的后移植困境及其应对策略
2018-07-10李怀瑞葛道顺
李怀瑞 葛道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600)
一、引言
人体器官移植*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对器官移植的定义是: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一直是令人们心动不已、充满想象的话题。早在公元前300年,《列子》中就有扁鹊为两人互换心脏治病的记载*注:《列子·汤问》中记载,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谓公扈曰:“汝志疆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志弱而气疆,故少于虚而伤于专。故换汝之心,则均善矣。”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于是公扈反齐婴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识。齐婴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识。二室因相与讼,求辨于扁鹊。扁鹊辨其所由,讼乃已。,扁鹊也因此被国际器官移植学会公认为器官移植的鼻祖*欧阳洁:《肾脏移植后身体体验与文化适应性探讨》,《医学与社会》2012年第11期。。古代西方也曾有类似的描述,如15世纪意大利诗人Calenzio有奴隶将自己的鼻子割下来给主人安上的描述;文艺复兴时期也有移植肢体的绘画*徐一峰、严非:《文化与健康:医学人类学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但这些大多是对器官移植的幻想,并未真正付诸实践。现代意义上首次人体器官移植实践发生于1936年,前苏联医生沃罗诺伊(Voronoy)将一个尸体的肾脏移植到一位汞中毒的病人体内,却未获成功。1954年,美国波士顿的莫雷(Joseph E. Murray)医生和他的医疗团队在一对同卵双胞胎之间成功进行了肾移植,将人类的幻想成功变成了现实,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夏穗生、于立新、夏求明:《器官移植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而随着血管吻合技术、移植物保存技术和免疫抑制药物的发明及运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体器官移植才得以真正发展起来*余成普:《器官移植病人的后移植生活:一项身体研究》,《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半个多世纪以来,器官移植技术水平日渐成熟和完善,时至今日已经在医学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然而器官移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吗?器官移植真的成功了吗?实际上,器官移植早已逐渐从医学领域走出来,由一个医学课题扩展成为一个或多个社会问题,涉及法律、伦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方面。诚如莫斯所谓的“总体性社会事实”,科学的、社会的、经济的、伦理的以及文化的问题都包含于器官移植实践中的各个环节。如果仅从医学的角度看,在器官移植受者的后移植生活(post-transplant life)中,他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需要长期服用抗排异药物,以防止移入器官的生理排异。但如果超越医学的视角,进而从社会学视角来审视器官移植受者的后移植生活,分析其中文化的、社会的因素,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扁鹊的解剖刀下互换心脏的两个人,在移植之后的生活中的境遇如何,这在典籍中没有过多描述,但却留给我们更多的想象空间——除了生理排异,是否还存在对器官移植受者的文化排异和社会排异等?因此,定义器官移植是否成功的临界点在哪里?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器官移植真的成功了吗”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发现医学层面以外的潜在问题,促进器官移植的健康发展。
笔者在对全国范围内的32名器官移植受者、6名器官捐献者家属、3名移植医生、5名红十字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之后,经历了一次比较强烈的文化震撼。在受访的器官移植受者当中,绝大多数的器官来源是公民逝世后自愿无偿捐献的器官,但也有少部分来自于2015年之前的司法渠道*注:我国自2015年起全面取消了司法来源器官(即死囚捐献),全面实施公民逝世后自愿无偿捐献器官,翻开了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的崭新一页。,另外还有个别属于亲属之间的活体移植*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他们都属于移植受者群体。对这一群体来说,生理排异尚有科学有效的应对之策,然而文化的排异、社会的排异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以至于将器官移植受者置于已经不能更糟糕的境地。这一群体都是在历经劫波之后,幸运地得到陌生人所赠予的“生命的礼物”(gift of life)而获得重生,这一特殊患病经历通常都会对其心态和理念产生诸多影响,并时常怀有感恩和回报之心。然而事情远没有他们预想的那么简单,他们在术后面临的是一次次的社会排斥、歧视和心理压力,重返社会的脚步迈得如此艰难。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想尽一切策略,积极走上了社会融入的坎坷之路。可以说,器官移植受者只有真正融入了社会,才可以说移植真正成功了。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如若没有现代医学的发展,器官移植不可能从人类的幻想变成现实。但如若没有一定的哲学思想基础,作为现代医学巅峰的器官移植同样也不会产生。器官移植源起于西方,然而在西方中世纪时期,外科手术却是一种地位低下、被限制的工作,因为在宗教神学的主导下,对身体的破坏被认为是对上帝的冒犯*余成普:《器官移植病人的后移植生活:一项身体研究》,《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文艺复兴以来彰显了人文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个人主义随之产生,带来的一个结果便是身体被发现。不同于集体主义社会中“个人消散在集体中”*[法]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西方社会将人作为个体对待,即作为掌握自我选择与价值、意义的主人。个人主义的上升进一步逐渐发展为区分人及其身体的二元论。在这一背景下,人体解剖学发展起来。最早的解剖学论著,也就是维萨留斯1543年发表的《人体构造》一书宣告了身体机械观的开始,并成为身心二元论的理论源头*[法]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这本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同年出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著,使得身体观念从此植入西方思想之中,在维萨留斯那里,身体的意义变得与其他任何事物都毫无关联,身体是且只是身体,人类从此学会放弃宇宙和集体,并进入了“我思”的体系。17世纪的笛卡尔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用他的身心二元论和身体机械观彻底地使身体与心灵分离开来。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从可以怀疑其他一些事物的真实性推断出“我”是存在的;反过来,如果一旦停止思考,纵然所想象的其他事物都是真实存在的,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是存在的。因此,“我”的全部本质只是思想,不需要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我”便成为与身体完全不同的心灵,即使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不失其为心灵*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69页。。很明显,笛卡尔更为注重的是心灵,而把身体当做一种物质性的东西来看待和观察。这种观点一方面给灵魂解去了束缚,另一方面放开了医学家的手脚,促进了实验生物学的发展*陈立胜:《身体:作为一种思维的范式》,《东方论坛》2002年第2期。。笛卡尔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身体机械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里讲到:“笛卡尔在其物理学中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力,并把机械运动看做是物质生命的表现。”笛卡尔认为在一切形体,包括天地、地球和生命的躯体,都是作机械运动的物质*[法]笛卡尔:《谈谈方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页。。他还举血液循环论为例,认为血液在人体内的机械运动就如同水泵压水一样,完全合乎机械原理。人的身体在笛卡尔的描述下变成了一台机器,身体成为可以解剖和分解的对象,也可以在某些零部件出现问题时进行维修或更换,以保证身体的良性运行。
身体的发现以及身心二元论和身体机械观的提出,成为器官移植得以产生的哲学基础。但器官移植作为现代生物医学,并非完全是“不受文化限制(culture-free)的科学系统”,在很多非西方国家,器官移植这一套理念与当地本土知识和传统相背离,并时常在这些地方遭遇尴尬*余成普:《器官移植病人的后移植生活:一项身体研究》,《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因此产生出诸多社会问题。即使是在器官移植源起的西方,身体也自始至终都受着文化的影响,文化赋予身体每一分血肉以意义和价值。身体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架构,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已知条件,而是社会与文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身体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本源,是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因此,从笛卡尔的哲学观点去认识器官移植是武断的,走出笛卡尔二元论的绝境是以后的哲学家们的共同要求。而器官移植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吸引了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关注的目光,不同的学科关注的重点也各异,例如社会医学关注器官捐赠的数量不能满足移植的需要*魏运歆:《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刘勇、董园园:《影响器官捐献的社会观念解析》,《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5期。;法学关注器官的法律定位和属性等问题*杨立新、曹艳春:《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法律属性及其支配规则》,《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伦理学侧重人的尊严以及身体健康问题*唐媛、吴易雄、李建华:《中国器官移植的现状、成因及伦理研究》,《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08年第8期;缪佳:《器官移植来源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思考》,《科学与社会》2012年第2期。;经济学上的难题在于理性主义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还是社会整体主义福利的增进*Joralemon, “Organ Wars: The Battle for Body Parts”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995, 9(3).;而社会学人类学的重点则在于研究影响器官捐赠行为的社会机制,器官捐赠中的市场逻辑、文化逻辑以及制度逻辑,器官移植受者的身体体验、身份自觉和自我认知等方面*Sharp, “Organ Transplantation as a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Anthropological Insights into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elf”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995, 9(3);Ikels, “The Anthropology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3, 42(42);余成普:《器官移植病人的后移植生活:一项身体研究》,《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受到文化差异、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器官捐赠与移植一直以来都具有高度的文化敏感性,并因此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理想田野。关于器官捐赠的国内外研究的取向主要集中在捐赠的家庭取向、身体与死亡的跨文化比较、礼物视角下的器官捐赠等方面,尤其以“生命的礼物”作为主题的器官捐赠研究最为常见。而对于完成器官移植手术以后的移植受者群体的研究,大致的研究取向包括身体视角下的身心关系、经验视角下的自我重建和心理适应、文化视角下的文化排斥*Joralemon, “Organ Wars: The Battle for Body Parts”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995, 9(3).等。本文暂不去探讨器官捐赠方面的议题,而是重点关注器官移植受者在术后生活中的经历和感受,希望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器官移植受者面临的种种困境进行解释和分析,以期提出该群体社会融入的合理路径。以器官移植受者的经历、感受和策略选择出发,我们会发现,除了普遍面临的针对移入器官的生理排异问题,该群体还面临着文化排异和社会排异,它们共同构成了器官移植受者的多重排异模型。在器官捐献者的大爱奉献行为影响下,器官移植受者群体普遍在心态和理念上较手术前有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加深了对生命的反思,强化了感恩之心,然而术后在生理、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多重排异却将他们再一次推入举步维艰的困境,直接造成移植受者群体在经济和精神上的双向压力,阻碍了他们回归社会的脚步,影响着今后在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方面的策略选择。正如勒布雷东所提醒的:“尽管通过移植手术,病人能够重新恢复健康和自理,但这很可能是最令人不安,也最难以承受的人类体验了。”*[法]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页
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是器官移植受者回归社会时必须面对的问题。考察相关文献可以看到,该方面的研究基本集中于对种族和移民*徐丽敏:《“社会融入”概念辨析》,《学术界》2014年第7期。、农民工*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2012年第5期。、流动人口*崔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石长慧:《文化适应与社会排斥——流动少年的城市融入研究》,《青年研究》2012年第4期。、贫困人口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周林刚:《社会排斥理论与残疾人问题研究》,《青年研究》2003年第5期。等取向。由于目前国内对器官移植受者群体的社会学研究本身就寥寥无几,因此几乎找不到从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的视角关注器官移植受者群体的文献。但从器官移植受者的弱势群体从属性质以及该群体面临的现实问题来看,可以用类似的分析视角来审视这一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融入概念起源于对社会排斥的研究,其概念通常是根据社会排斥所定义*徐丽敏:《“社会融入”概念辨析》,《学术界》2014年第7期。。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在劳动力市场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社会排斥造成被排斥者巨大的社会焦虑,他们不仅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更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一旦被排斥群体不能适应来自生活和心理的双向压力,并找到合适的社会融入策略,他们就很容易成为“边缘人”(marginal man)或者“陌生人”,加深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距离”。
结合文献和分析资料,笔者初拟了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器官移植受者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策略
三、器官移植受者的后移植困境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器官移植作为医学技术巅峰的典型代表,其成功率也在大大提高。然而,医学意义上的“成功”仅仅是器官移植受者回归社会的起点,社会学意义上的“成功”才刚刚迈出了第一步,而他们在后移植生活中的每一步都将面临常人想象不到的种种坎坷和磨难。
(一)生理排异
在上文曾提及的人类历史上首次现代意义上的器官移植实践,也就是1936年前苏联医生沃罗诺伊(Voronoy)进行的肾移植手术之所以未获成功,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医学界上没有应对生理排异的有效方法。生理排异,即移植排斥反应(transplant rejection),是指移植受者进行器官移植后,外来器官或移植物作为一种“异己成分”被受者免疫系统识别,后者发起针对移植物的攻击、破坏和清除的免疫学反应。这种复杂的免疫学反应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对人体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保护机制,但却是影响移植物存活的主要因素之一。
对移入器官的生理排异一直是移植手术的最终制约因素,但是随着环孢素*注:环孢菌素(Cyclosporine)也称为“环孢素”或“环孢霉素”,是一种被广泛用于预防器官移植排斥的免疫抑制剂。它借由抑制T细胞的活性跟生长而达到抑制免疫系统的活性。的出现,这一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环孢素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经发现,就成为器官移植的首选免疫抑制剂,它使得医生有能力延迟患者身体对移入器官的自然排异,同时不会危及生命。移植受者的生存时间因此得到延长,进一步导致移植数量的增加。例如,在1982年,也就是美国联邦药物管理局批准环孢素使用的前一年,美国共计进行了103例心脏移植手术;而1984年随着环孢素的使用,这一数字上升至346例;到了1988年,心脏移植数量进一步上升到1647例。
对于绝大多数器官移植受者来说,终身服药是他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免疫抑制剂在预防移植排斥反应的同时,也降低了身体的抵抗力,因此移植受者的免疫力一般比较低,需要特别对身体加以关注。
小G是一所知名医院肿瘤科的医学研究生,2014年5月初,她开始出现咳嗽、下肢水肿、严重心衰的症状,在做了心肌活检和基因检测后,得知自己发生了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竟成为全球首例家族性缺陷性基因突变型限制性心肌病,并肥厚表型。在没有其他治疗办法的情况下,小G于2014年10月13日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以后的恢复过程非常不顺利。小G这样述说自己的抗排异过程:
术后5天,出ICU,当天晚上就心包填塞,考虑急性排异,又拖到ICU抢救了。晚上12点多,抢救到凌晨5点钟左右,然后在ICU又待了三天,我就吵着要回隔离病房,ICU太贵了。哪知道,这排异还只是开始。第二次出了ICU以后,没过多久,又心包积液(心包填塞是大量心包积液,压迫心脏,心脏无法跳动,严重可致心脏停搏),做了心包穿刺,又积液,又穿刺……一直这样,从2014年10月,住院住到了2015年3月。2015年3月份,为了确定是不是继续排异,排异程度怎样,我第二次做了心肌活检,结果显示轻中度排异。为了控制排异,医生前前后后给我用了很多办法,包括激素冲击、加大抗排药物剂量。最后换了一种抗排药物才好。于是,我于2015年6月底出院了。(20170505)
出院之后的小G虽然基本上与移入器官和平相处了,没有再出现器官排异,但她却继续延续着与身体的抗争之路。由于药物的副作用,2016年4月,小G出现了药物性低血糖,昏迷抢救了一次,之后又在2017年2月因药物引起功能性子宫大出血,因此又做了子宫内膜消融术。然而目前她所经历的波折依然还在继续,现在她的股骨头又因为长期服用激素性药物引起坏死,正在和医生商量调减激素用量。
小G的案例属于发生率很低的急性排异的情形,器官移植受者群体中出现的排异情形更多地属于慢性排异。慢性排异虽然不像急性排异来得猛烈,但它也是不可逆性的危害极大的排异现象,需要在移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谨慎预防。对于慢性排异,在移植受者群体中有这样一种说法:“熬过了一年熬三年,熬过了三年熬五年,五年之后就比较安全了。”不论哪种形式的排异,生理排异都是危及移植受者生命的主要因素。
(二)文化排异
在对器官移植受者群体进行研究时,Joralemon提出了与生理排异相对应的“文化排异”*Joralemon, “Organ Wars: The Battle for Body Parts”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995, 9(3).的概念,将其运用在移植受者的后移植生活的解释上。他认为环孢素作为生物免疫抑制剂虽然能够起到抵抗移入器官的生理排异的作用,但却无法避免文化上的不适应,由此提出了“文化的抑制免疫”(Cultural Immunosuppression)的概念,提出了如何使移植者在心理文化上进行适应的问题。同必须利用环孢素等抗排异药物来抑制生理排异的做法一样,为了使器官移植在文化和社会意义上同样获得成功,需要一种在文化意义上类似于环孢素的“等同物”(ideological equivalents),以抑制移植手术后的文化排异。但Joralemon在论述中所表达的文化排斥更多地是针对器官捐赠主题而提出的,他提出的“文化的抑制免疫”是礼物赠予和财产权利的观念,并对这两种观念进行了详细解释。虽然这两种观念不适用于本文想要解释的针对器官移植受者在术后的文化排异,但他的研究给出了宝贵的启示。
相对于身体对移入器官的生理排异而言,本文中所论述的文化排异指的是移植受者及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对器官移植表现出的不适应和不接受。器官移植受者在移植手术完成之后,首先面临的是他者感(Otherness)的冲击。在身体社会学看来,身体具有整体性,人并不是器官的总和,身体是身份的物质基础。移入器官对于受者来说并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器官移植手术带来的是移入器官和移入身份的双重过程,这一经历将令他们或长或短地遭遇一定程度上的身份困扰和紊乱。即使受者不知道捐赠者的身份,也会通过想象来赋予其身份和特征,从而与自身紧密联系起来。因此,陌生的器官不仅在身体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同时也打破了自我的边界,让“我”与“他者”的身份模糊起来,在深层次触及了病人的价值观及其存在的理由。从此,相异性便驻进了自我,使得受者时常感觉到“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觉得身体里住着另一个人”。
“他者感”带来的身份紊乱时常体现在器官移植受者的潜意识中,尤其是在梦境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位接受过心脏移植的受者小H这样描述和解释她曾经做过的梦:
刚做完手术那会经常觉得,这个心脏不是自己的,经常做梦,梦见自己灵魂出窍。尤其排异的时候做梦更多,我觉得心脏是不想待在我体内。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是梦到灵魂出窍,自己的灵魂飘荡在自己老家的家门口,看到家里人围着我的躯体在哭,其中哭得最伤心的就是我妈妈,我想喊她,却喊不出来。还有一次,是梦见一个年轻女孩,发生车祸,隐隐约约中,也许是我自己暗示自己,我感觉那就是心脏的主人……我好几次在梦中梦到的小女孩儿,或许就是那个心脏的主人,因为我从医生那里听说,我的器官来源是一名年龄在22—24岁左右的女性。(20170601)
器官移植给受者带来了移入器官和移入身份的一种特殊的双重体验,即便受者并不了解器官捐赠者的经历和性格,也会通过想象来赋予移入器官以身份和特征。“我”与移入器官的相异性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体现在移植受者的观念中。这种相异性或许是令人痛苦的,也可能是令人欣慰的一种相对温和的文化排异,因为有些人能够很好地接受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处境。然而不管痛苦或温和与否,相异性以及“他者感”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
器官移植受者对移入器官的“他者感”是文化排异在“我”身上的体现。除此之外,随着后移植生活中在身体管理上发生的客观化和科学化的转向,他们在文化意义上的康复便再也难以实现,器官移植的经历不断成为隐喻和象征的来源,病态的身体和病人的身份被持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器官移植在带来身份认知的失调、破坏身体的感性体验的同时,也造成了接下来的一个结果——身体的客观化和科学化管理。在进行过器官移植手术之后,受者群体普遍会在后移植生活中对身体健康状况给予更多的关注,身体以及身体的科学管理成为该群体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由于在后移植生活中需要终身服用抗排异药物,而抗排异药物又降低了受者身体的免疫力,使得他们的身体相对于常人更为脆弱,因此,永久性的治疗过程迫使他们必须在动态中掌握移入器官的功能状况和身体的健康情况,防止排异的发生和疾病的入侵。永久性的药物服用以及对健康状况的担忧使得身体成为需要管理的客观对象,而管理的手段则变得科学化,如每天定时服用精准剂量的药物、学习中医养生知识等。表1是一位肾移植受者每天的抗排异用药安排:

表1 一位肾移植受者的用药安排
(笔者根据访谈资料整理绘制)
在冗杂的符号名称和冰冷的剂量数字以及对身体种种的限制性规定面前,身体开启了它的“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过程,并从此不再具有康复的可能,器官移植的隐喻在受者的身上不断被体现,从而使器官移植受者病态的身体属性一次次得到强化,病人身份也持续着再生产过程,这成为接下来面临的社会排异的文化基础。
(三)社会排异
上文提到,文化排异是作为与生理排异相对应的概念而提出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不妨也把社会排异的概念与之类比,由此提出社会排异的新概念:即社会成员对移植受者出于消极或积极的心态而采取的特殊对待方式,包括排挤、歧视、区别对待和“照顾”等,使移植受者群体面临社会区隔以及被边缘化的危险。由于移植受者在手术后的生命状态和生命历程遭遇改变,加上器官移植的隐喻被持续强加在受者的身上,社会成员在面对该群体时采取了特殊对待的方式,造成了移植受者群体社会空间的压缩、社会距离的拉长和社会孤独感的增加,从而令其感到自我价值缩小,与实现自我价值的迫切感相冲突。社会排异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就业、社交、婚姻等,造成移植受者巨大的社会焦虑和心理压力。
就业压力是移植受者群体普遍面临的一种社会排异的困境。肺移植患者小W在访谈中讲述了她在找工作时的一段经历:
我在患病以后就放弃了原有的工作,现在恢复过程中,也尝试过回归工作。我们一些病友为了重回原单位,隐瞒了移植的病史。我之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每个月至少5天耗在医院,哪个公司能接受得了频繁请假?所以我们这些病程长恢复不太好的,要么就不能工作,要么只能做微商开淘宝。像我这种既想坦白病史,又想能正常工作的,还是少数,也挺矛盾的。找不到工作,干脆放弃这条路,转而去复习准备研究生考试了,因为学习是我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不和社会脱节的方法。(20170425)
接受了亲体肾移植(肾源来自于受者的母亲)的小C同样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遭遇了尴尬的困境,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创业,却仍然受到种种限制:
我在2012年7月份移植了我母亲的一个肾脏。移植之后恢复得差不多了,我开始四处找工作,可是我前前后后找工作找了25次,全部被拒绝了。最后没办法,我隐瞒了做过肾移植这件事,终于进入了一家公司工作。因为是隐瞒病史,所以平时吃药我只能偷偷去厕所吃,怕被别人看见。但有一次我在厕所偷偷吃药的时候,恰巧老板进来了,老板问我吃的什么药,我无奈之下说出了我的移植经历和病情,不出意外地被辞退了。后来我心想,没有单位要我,我自己创业总行了吧,所以我现在就在农村老家搞土鸡养殖、种植药材,没想到自己创业还是受到各种限制。贷款银行不贷,去政府相关部门申请汇报创业项目,都以各种理由拒绝。我在家里搞养殖、种植药材,做得很好,没有几人有我弄得好,可是人家不相信你要做事,他们觉得我们能活多久,还跟他们讲创业,有种歧视在里面。所以移植人创业比正常人创业难百倍。(20170614)
即使没有失去原有工作岗位,一些器官移植受者在重返工作岗位之后,也会遭遇与之前不同的对待,比如国企或事业单位等一些在人们眼中看起来比较稳定的工作。L先生在2014年做了心脏移植手术,器官来自于当时还没有彻底废止的司法渠道。移植之前他就职于北京的一家国企,手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在家中休养。L先生说:
我出院以后,领导说就让我在家好好养着,拖着不让我去上班,他们担心得太多,总觉得心脏移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回到工作岗位风险太大。我就这样在家养了两年,实在是憋坏了,跟领导申请了好几次,年初终于让我回办公室上班了。可是回去之后呢,就只让我做一些文字工作,特别照顾我嘛……唉……领导对我的照顾太多了,时刻把我当成一个病人来安排。以前安排的工作现在尽量少安排给我,或者是不安排给我。(20170511)
L先生口中单位领导对他的“照顾”多少显得有些无奈。而在这种“照顾”中所体现出的社会排异在器官移植受者的日常社交中表现更为明显。L先生继续说到:
生活中,同事和朋友对自己的照顾,这种状态也好也不好,比较复杂。一是觉得感谢大家的照顾,二是觉得大家永远觉得我是个病人,永远带着病人的身份。有一次,朋友以为要关照我,却当着别人的面在公众场合说出我的病情。其实我知道他本意是希望别人也一样关照我,但是这种方式实在让我感到尴尬难堪,因为我并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病情。(20170511)
此外,在对一些女性器官移植受者的访谈中,笔者经历了一次更为强烈的震撼。由于之前的患病遭遇和器官移植的特殊经历,女性已婚患者在移植之后被迫离婚的案例在笔者的访谈中出现了很多次。配偶在移植手术之后绝情地离去,使得这部分女性受者群体的人生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肺移植患者小W和心脏移植患者小Q的两个案例是她们在婚姻和家庭方面遭遇社会排异的典型代表:
小W:我的2013年简直太戏剧化了。在发现得病的时候我已经怀孕20周了,当时非常痛苦地把孩子引产了。那段时间我完全沉浸在失去孩子的痛苦里。等到了合适的肺源,终于进行了肺移植手术。但是出了ICU出了个岔子,对方家从医生口中得知我不能再怀孕了以后,就提出了离婚。我5.18住院,6.3引产,7月中旬评估,8.31移植,9.6出ICU,9.13接到离婚申请,是不是很戏剧化?一个女人最怕遇到的事情,我半年内全部经历了。我们病友基本上有两个极端,要么就是像我这种离婚分开的,要么就是到最后一刻都不离不弃的。(20160425)
小Q:因为移植我也离婚了,前夫一家没有一个同意我们继续在一起的。当时还在住院就提离婚,出院以后天天打电话逼离婚。当时他提离婚的时候我特别想自杀。那会排异还没有控制,之后要出院也需要找他签字,但是他不肯见我,不肯告诉我在哪上班,我那个伤心……出院后一共找了他三次,最后心凉了,同意离婚了。(20170523)
就业、社交和婚姻方面所表现出的社会排异对于器官移植受者来说仅仅是其遭遇的后移植困境中的一部分,然而已经足以让我们感受到社会对该群体所表现出的不包容。社会的排挤、歧视抑或是出于善意的“照顾”,已经有意或无意地压缩了器官移植受者群体的社会生存空间,增加了他们与主流群体的社会距离,从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考虑到器官移植经历给受者的生命历程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生命长度的改写,该群体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就变得更加迫切,然而社会排异所带来的社会焦虑和心理压力显然与这种迫切的追求背道而驰。
(四)小结
经济上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服药和检查以及前期的手术花费*注:器官捐献是志愿无偿的,而器官移植则需要受者付出一定的费用,这是因为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在获取、分配、运输和移植等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成本,器官移植受者所支付的费用是这些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费。上。以肾移植为例,一名肾移植病人每月用在抗排异药物上的费用大概在6000元左右。目前肾移植患者的抗排异用药已进入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但是除去报销的金额,大致还需要继续担负3000—4000元的花费。另外移植受者在术后一年之后一般每个月需要到医院检查一次,每次的检查费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一些人还要为此付出交通费和住宿费。如果再加上每月的生活开销,有的还因为移植手术而背负巨额外债,器官移植受者的经济压力足以让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陷入困难的境地。
精神上的压力有来自生理层面的,也有来自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一方面,为了控制生理上的排异,在生活中处处受到限制,导致移植受者群体较容易产生自卑感。并且长期带有对健康的深层忧虑,一旦发生急性排异就会有极大的生命危险,甚至意味着生命的倒计时,这种持续的忧虑给移植受者带来精神上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由文化排异和社会排异带来的失调和种种不适应,导致移植受者永远不可能回归到“正常人”的状态,将永远带着病人的身份,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排斥或“照顾”,日渐孤独和无助,不断积累心理上的焦虑和压力。
综合上文的论述,可以用表2对生理排异、文化排异和社会排异的异同作一个全面比较,随后提出器官移植受者的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问题。

表2 生理排异、文化排异和社会排异的对比
四、器官移植受者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策略
器官移植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医疗技术。针对器官移植受者的生理排异,目前的医疗水平已经可以有效地解决此类问题,而对于文化排异和社会排异,却并没有成熟的应对方案。但在与该群体的访谈中发现,移植受者会自然地采取多种策略进行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以他们特殊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难题,解答人生的疑惑,以期更好地“活着”以及被社会所接纳。
(一)文化适应
人体免疫系统对移入器官的生理排异随时间的增长总体上呈缓和的趋势,人体会逐渐适应外来器官在体内的运行。时间同样是冲淡器官移植所带来的文化排异的良药,移植受者在观念中也会逐渐适应这个“不速之客”并与之和谐相处。也就是说,该群体成员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对自我认同的重塑*Sharp, “Organ Transplantation as a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Anthropological Insights into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elf”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995, 9(3).,将原有身份与移入身份建立联系,实现体内两种身份的和解。
小W在二十多岁的花样年纪被查出患有晚期肺淋巴管平滑肌瘤病(LAM,一种罕见病)。遭遇这样的变故,她在医生的建议下于2013年进行了肺移植手术。然而对于器官捐赠者的信息,她并不知晓多少,只知道那是一个比她年轻的小伙子,在山里放牛时摔下来脑死亡后捐献的。小W亲切地称呼他为“放牛小弟”,每年,她都会给这位“放牛小弟”写一封信,她在信中写到:
无法见面的放牛小弟,我们从未谋面,但从院长的口中我知道,你比我小,所以就是我的弟弟吧。我时常想象你的模样,黝黑的皮肤,壮实小小的身材,笑起来会露出白白的牙齿,淳朴而懂事。经历过太多痛苦,有时,会觉得你曾经这么好的身体状况,给了我不小的压力。于是,有意无意地和你说说话。慢慢的,压力也转化成动力了。放牛小弟,我们约定吧:每一年的今天,我都给你写一封信,说说我们共同经历的时光。(20140831)
移入器官带来的文化排异在小W的身上体现得较为温和,因为她通过想象赋予了捐赠者以身份和特征,将“我”与“他者”的身份很好地结合起来,并在后移植生活中能够与其和谐共处。
在48孔板中接种细胞,待细胞生长至70%左右时,分别加入终浓度为0.6 mmol/L的VPA、终浓度为5µg/mL的放线菌素D(转录抑制剂)或两者联合加入,每组3个复孔。分别在加药前(0 h)、加药后2、4、6、8 h收集细胞,提取RNA,行逆转录后按照前述方法通过定量PCR分析细胞中mRNA水平变化。
此外,移植受者将移入的器官视为捐赠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奉献出的“生命的礼物”(gift of life),并把它解释为捐赠者生命在自己身上的延续,以期能够安心地接受这一“馈赠”,而不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生命的礼物”的说法是由蒂特马斯在研究献血问题时,在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注:莫斯提出赠予物带有赠予者的一部分,礼物带有赠予者的“灵性”,这种“礼物之灵”在赠予者和接受者之间产生纽带。他假设这种“礼物之灵”在礼物交换过程中代表了一种内在的、有生命的力量,具有给予者的个性。的基础上提出的,自提出以来便成为器官捐献和移植议题最为青睐的解释观点。然而莫斯曾经提到,在古日耳曼语中,“gift”一词同时具有“礼物”和“毒药”两种含义,古希腊语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歧义。因此,接受别人捐赠的器官却不准备知恩图报的人的名誉将会受损,这“迫使”受者不得不承担起某种义务,使得接受这一“生命的礼物”变得十分棘手,甚至可能出现“礼物的暴政”,因为它让人们象征性地欠下了人情债,而这种“债”是无法偿还的,让受者内心永远背负着负债感。对很多器官移植受者来说,如何“还礼”以便减轻这种负债感变得十分重要。对器官捐献推广活动的积极参与和承诺、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对其他移植受者的精神支持、树立饱含正能量的人生观,成为很多移植受者在后移植生活中进行积极的文化适应的策略选择。
面对生命历程的中断和缩短,心脏移植受者小Y在不能改变生命长度的情况下选择去增加生命的宽度和厚度:
以前不会考虑生命的长度这个问题,现在因为这个成了最主要的问题,反而有点紧迫感,会去发现生命的宽度和深度,会去追求生命的价值。其实我生病前就知道器官捐献,也很愿意死后把一切都捐出去,没想到这个心愿没实现之前,先成了受益者,现在能做的就是去宣传吧,我也登记成为了器官捐献志愿者,希望更多人了解、接受。我只能做一些小的公益,比如一些筹款活动,一些山区捐赠衣物等活动,当然金额不多,只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了。(20170504)
(二)社会融入
人是社会性动物,正常的人际关系是无可替代的。然而受到社会排异的影响,大多数器官移植受者在经历过这一特殊过程之后,以往人际关系中的朋友渐渐疏离,即原有的交际圈逐渐缩小甚至消失,而为了使自己不会成为孤立无援的孤独群体成员,一种基于“同病相怜”情感的新的交际圈却又正在形成。肾移植受者小C描述了他现在的交际状况:
我现在的朋友都是移植人,都是在医院认识的,大家留我号码一起交流,觉得很开心。我们还会组织见面或者其他活动,比如肾友会,还会一起约去检查。没病以前朋友很多,病后联系就没有了,很多人不联系我。现在主要就是病友。遇到一群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互相鼓励的人,使我们不再寂寞,不再孤独。(20170801)
可见病友在器官移植受者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病友之间的人际沟通成为该群体社会融入的重要一环,这对于移植受者疏解压力、释放孤独感、感受生命价值起到重要作用。器官移植受者之间的“同病相怜”,让移植受者群体的生物社会性得到很好的体现。另外,从各大医院的病友会以及组织的多样性的交际活动可以看出,病友群体也日益呈现组织化的趋势。因此,病友之间的持续互动成为该群体社会融入的主要策略。
五、总结与讨论
器官移植从人类的幻想变成现实,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医学奇迹”和“医学巅峰”,如今它已经成为挽救无数人生命的一种有效而成熟的医学手段。器官移植是一项集医学、法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问题于一身的“总体性社会事实”,从社会学的整体性视角去思考器官移植实践将有助于该项事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生物医学模式意义上的器官移植已经成熟,而社会学意义上的器官移植却并没有得到人们太多的关注,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不断改善这一“缺场”状态。
回到开篇的问题:器官移植真的成功了吗?本文的研究证明,器官移植受者所接受的移植手术在挽救生命的同时,并没有帮助他们彻底回归社会,而是陷入了生理排异、文化排异和社会排异的多重排异困境。生理排异是外来器官或移植物作为一种“异己成分”被受者免疫系统识别,后者发起针对移植物的攻击、破坏和清除的免疫学反应;文化排异是移植受者及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对器官移植表现出的不适应和不接受,表现为“他者感”带来的相异性所造成的身份紊乱(有的则通过自我重塑实现了身份和解)、“去人性化”和器官移植的隐喻带来的永久病态;社会排异是社会成员对移植受者出于消极或积极的心态而采取的特殊对待方式,包括排挤、歧视、区别对待和“照顾”等,使移植受者群体面临社会区隔以及被边缘化的危险,给移植受者带来巨大的社会焦虑和心理压力。生理、文化和社会的多重排异困境使器官移植受者进一步遭遇经济和精神上的双向压力,移植受者会自然地采取多种策略进行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对器官捐献推广活动的积极参与和承诺、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对其他移植受者的精神支持、树立饱含正能量的人生观,成为移植受者文化适应的策略选择;在原有交际圈缩小甚至消失的情况下,建立基于“同病相怜”情感的新的交际圈则成为器官移植受者社会融入的主要策略。
因此,器官移植尚未成功,只有当移植受者真正回归和融入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移植成功才能实现。需要指出的是,深入剖析器官移植受者的后移植困境,作出器官移植尚未获得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成功的结论,并不是否定器官移植作为一项伟大的人道主义事业的巨大价值,而是在发现和剖析特定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促进这一人道事业的健康发展。虽然生理排异可以通过医学手段得到解决,但器官移植给受者带来的文化排异和社会排异则需要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去慢慢改善,给他们应有的社会支持。
最后,本文还想就下一步研究的可能性做一点讨论。关于器官捐献与移植,可以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不同的问题:对于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而言,捐献的内在动因是什么?捐献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对于社会而言,文化对器官捐献的影响是什么?器官捐献又给社会带来了何种影响?如何动员和宣传器官捐献?对于公众而言,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水平如何?本文则仅仅从移植受者的角度,分析了与器官移植有关的问题。实际上,与器官移植课题密不可分的另一项内容就是关于器官捐献的研究。器官捐献涉及宣传、获取、分配、使用等多个环节,每一环节也同样嵌入性地隐含着文化与社会意涵。捐献者及其家庭的经历、捐献率的种族和地区差异问题、脑死亡理念的文化障碍、公众对捐献后经济补偿的接受程度等议题,都是社会学家在器官捐献研究领域感兴趣的选题。对接下来关于器官捐献的研究,可以有以下几种研究思路:首先是将器官捐献的文化意涵作为一项基础性研究,对器官捐献的文化结构进行全面描绘和分类,探讨文化对器官捐献的解构与建构之间的张力,并在调研公众、捐献者家属、移植受者等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找到并塑造一种公众普遍接受的、适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文化理念;其次,将社会学人类学视角下的“生命的礼物”作为一项解释性研究,从礼物赠予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器官捐献行为中的互惠关系——赠予和回报,这种互惠是一种匿名的、发生于陌生人之间的礼物关系,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礼物的循环;最后,将推动器官捐献的针对性措施和政策建议作为一项政策研究的内容,例如推动在领取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推动各地设立器官捐献者缅怀纪念场所、发挥社会组织在推动器官捐献中的作用等等。无论从何种角度推进器官捐献领域的研究,社会学的想象力都将使我们在这一主题的研究中有所斩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