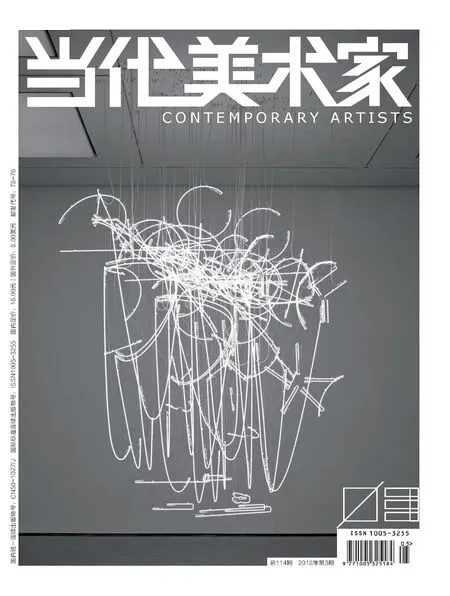立新、身份与反思:王大同艺术系谱中的几个关键词
2018-07-03尹丹YinDan
尹丹 Yin Dan

王大同风景三 左手系列80cm×100cm 2016
王大同油画展
展览时间:3月21—4月12日
展览地点:重庆国泰艺术中心1号厅
作为晚辈,我和王大同先生生前并无接触,却有幸通过川美各位师长了解到他与人交往、为人处世中的点点滴滴,也通过其他媒介了解到他的创作历程及主要作品面貌。前几天,非常荣幸地受到王大同夫人朱盛玉女士的邀请,得以较为全面地拜读先生留下来的色彩习作及主题创作作品。毫无疑问,王大同先生是四川美术学院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艺术家,也是本校油画人才培养历程中非常关键性的一位教师。
一篇小文难以全面地概括王大同先生的艺术、教学成就,我试着从观念立新、身份表征及文化反思几个角度来进行阐述。其中“立新”体现于教学和创作两个层面,在老一代艺术家中,这样的诉求显得尤为突出;布依族的“身份”认同或许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在艺术创作中的主题选择及文化趣味;他热衷阅读,善于思考,不断地吸取新知,自我反思。
“鼓励创新,他是让人印象最深的教师”
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的发展历程来看,王大同算得上是第二代油画教师的中坚人物。王大同1954年进入四川美院(当时名为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5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都未离开教学第一线。一般认为,奠定川美油画专业的第一代教师中,核心人物为刘艺斯、刘国枢、叶正昌三人。而第二代教师中比较突出的有夏培耀、魏传义、杜泳樵、王大同、张方震等人,他们都是奋斗在教学第一线的艺术家们。后来非常有影响力的77级、78级以及稍后81级、82级油画专业学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都离不开这两代艺术家们的教学及个人影响力。正如学生时代以《为什么》一画名噪一时的高小华所说的那样:“像魏传义、王大同、蔡振辉等几位恩师……正是这些园丁的辛勤劳作和理解,才使得我们这批稚嫩的幼苗得以茁壮成长。”1
川美恢复高考招生之时,王大同先生正当壮年,正是他在川美油画教学中担当起骨干作用的时候。这之后的川美油画能够产生全国影响力,自然离不开教师们的引导。“文化大革命”后,王大同便为77级油画系学生担任了写生课及创作课教师。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还回忆起自己为学生们所介绍的艺术构思“四类型”:形象型、象征型、对比型、叙述型。在几十年的教学历程中,王大同对学生们所产生的影响力受到了普遍的承认。如川美院长庞茂琨在文章中所谈到的那样:“王大同老师是我最尊敬的先生之一……记得刚进油画系的第一节油画静物写生课就是王老师上的,印象非常深刻。那使我第一次明白了油画笔触与肌理的关系,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艺术的格调。”
甚至到1997年时,他还在担任油画系毕业班的毕业创作导师,并积极尝试着让学生们以新的群体方式来完成毕业创作。从20世纪90年代就读于川美油画系的学生回忆来看,他们大多对王大同鼓励学生创新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样的判断在89级学生庹光焰及93级学生赵晓东那里都得到了印证。后者回忆道,当时川美的教学非常自由,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画”,教师大多都不会用学院教学的“条条框框”来束缚学生,其中王大同则是明确地鼓励学生多思考多创新的教师。而庹光焰甚至称他为当时教师中对学生创新“最”为鼓励、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位。对于这个问题,王大同自己也有非常自觉的认识,他在自述中谈到自己愿意“尊重学生的个人想法”,不会以教师的观念来束缚学生。赵晓东回忆起王大同先生在教学中的点点滴滴,还甚为感激。当年王老师还曾推荐亲友购买、收藏了他的作品,对于学生时代的赵晓东来说,这笔购画款项毫无疑问激励了他绘画的热情,增强了创作的信心。川美的创作在90年代晚期开始再次获得艺术界的普遍关注,这绝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因为川美一直以来就有着相对宽松与自由的创作氛围。这种氛围当然离不开教师们开明的态度,它一方面体现在鼓励学生对多种艺术观念的自觉接受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教师们对创新的推崇上。在老一辈教师里,王大同无疑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挣脱:从绘画语言到语义
这种“不僵化,善立新”的态度不仅仅体现于教学之中,也体现在王大同自己的创作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之中。作为20世纪50年代进入四川美院学习的老一辈艺术家,虽然也受到了刘国枢、刘艺斯、叶正昌、谢梓文等多元化的影响,但其早年主要的艺术语言仍然是苏派的,毕竟50年代正是苏联绘画在国内一统天下的时代。他未能像魏传义那样“有幸”到北京去参加马克西莫夫培训班的学习,但苏派绘画语言中那种大笔触摆结构的方式,那种银灰色的视觉趣味仍然深深地烙印在了他早年的绘画习惯中。如今家人所找到的一批80年代以前完成的纸本习作,基本上体现了这种风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流行于50年代到70年代的技法,多为我们同代人所采用,称为直接画法。画短期作业很显长处,俄罗斯的克洛文是此种技法的极致者。鄙人当年曾五体投地地崇拜过。”2如今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川美创作的革新,自然会首先想起更为年轻的一代,如以高小华、程丛林等人为代表的伤痕美术,以罗中立、何多苓、王亥等人为代表的乡土美术。但王大同在1977年酝酿完成的《雨过天晴》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此画在1979年获得了当时全国美展的银奖(当年未设金奖),迄今为止都是川美在全国美展创作类领域获得的最高奖项。这件作品在当时颇为大胆地借鉴了新印象派中的点彩画法,十分“透气”地再现出雨后玻璃窗的迷蒙效果。众所周知的是,“雨过天晴”这个名字还有一种象征性。上述原因也使得《雨过天晴》成为“文化大革命”后较早引起全国影响力的一件带有新时代隐喻的油画作品。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印象派”实际上是一个颇为敏感的名词,因为长期以来它几乎成为绘画领域中形式主义的代名词。一般意义上,我们将点彩画法看作是新印象派的代表性技法,但毫无疑问印象派与新印象派之间具备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所谓的“新印象派”与“印象派”两个名词在当时的话语体系中也并无本质性区别。对这些技法的使用在当时仍然是颇为大胆的尝试。可以说,王大同的这件作品拉开了川美创作在新时期“井喷”的序幕。用已经逝世的前川美院长叶毓山的话来说:“从《雨过天晴》问世之后,我院作品就像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呈现了朝气勃勃的局面。”

王大同寄往天外的邮包之一130cm×110cm 2007
《雨过天晴》为王大同赢得了非常高的荣誉和声望,其同名作又在1980年福冈举办的第二届亚洲艺术节上大受欢迎,后来被东京藏家以千万日元的天价收藏。在1987年纽约举办的“中国当代油画展”上,他的《母亲的怀抱》一画又被藏家以3.5万美元的价格收藏。在国内物价低廉、艺术市场尚未起步的时代来看,这个数字的确是让人瞠目结舌的。尽管如此,王大同并未停止不断改变自己的可能性。这种改变在1987年访问加拿大之后变得更为自觉,他愈发感受到停留在既有状态下的乏味与痛苦,用他的话来说便是“自由和创造是生命最宝贵的目标”。他选择的道路是,在保留写实方式的基础上融入新的绘画语言及观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凝固幻想”及“寄往天外的邮包”系列。在前一个系列的画面中,一位女子总是被凝固于冰块之中,但观者似乎感受不到任何痛苦感,女子往往处于沉睡或沉思状态。而后的“寄往天外的邮包”系列,王大同突然沉浸到看似枯燥、单调的画面物象之中,他不厌其烦地描绘一个个粗麻质感的邮包,一笔一笔地刻画邮包的纤维质感。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后来栗宪庭用“念珠”、高名潞用“参禅”来描述中国式抽象的表述。王大同这种用“笨办法”刻画纤维的方式,虽然乏味,倒似乎是可以使得内心沉静。从这个意义上说,手工艺术中的重复性的确与“禅”有着精神诉求上的同一性。邮包上写着“to out space”几个字,我们无法看清邮单上的具体文字,却隐约可以看到麻袋中的人形。这批作品可以看作是“凝固幻想”系列的延续。两个系列,人物均被束缚,却并不给人绝望之感,前者似乎在等待着冰块的融化,后者则将希望交给了现实世界之外的未来及外太空。我注意到,早在1990年,王大同便完成了一件名为《解脱》的作品:一位女性人体为白布所束缚,正在竭尽全力挣脱。这件作品同样再现了被束缚、包裹的身体,似乎可以理解为上两个系列作品的早期尝试。有意思的是,在80年代中期,丁乙、张国梁、秦一峰几人的行为艺术中,也喜欢用白布将自己的身体进行包裹。油画与行为艺术、媒介不同,却似乎可以体现出一个时代艺术家们共同的表达方式。不知王大同先生的上述作品,是否是对特定时代个体生存境遇的一种隐喻,是否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象征一种自我挣脱及对未来的展望。
身份的表征与认同
熟悉王大同的人都知道,他出生在贵州安龙,儿时有不少时光在离县约80华里的布依族山寨中度过。按照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学划分方式,他应属于布依族人。在他的那一批“乡土”作品中,其中不少的主题与少数民族相关。这批作品在王大同的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但仍然呈现出较为多元的倾向。大致可划分为三种:1.再现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带有平民现实主义特点的;2.强调形式美的,在构图、色彩层面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3.具有神秘感和超现实主义倾向的。当然,这三类作品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例如他那批再现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作品,在题材选择上具有现实主义倾向,在形式处理上却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点彩”的使用使得画面在视觉上呈现出明亮的跳跃感,着力打磨的构图关系、物象轮廓线透露出强烈的形式感……当然,在这批作品中,他不仅画了布依族的题材,同时也涉足藏族、彝族、蒙古族及维吾尔族人民日常生活的题材。我们也没必要过分地夸大王大同先生在此所表达出来的身份意识,它们或许更多地呈现出那个时代四川美院较为普遍的艺术倾向。毕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盛的乡土绘画在川美和全国产生了太大的影响力。川美的乡土绘画从最初的农村、知青题材逐渐转向少数民族题材,深入四川凉山地区进行写生也成为本校坚持了很多年的常规课程。
能够更为明确地体现出王大同对民族身份认同的是完成于世纪之交的《蛮荒古俗》系列作品,在此他同样强调了画面的形式感,但少数民族题材中的唯美主义倾向却被凌厉、崇高、可怖与神秘所取代。除了使用那些“古远”的造型符号外,也强调了颇具“滞留”感的外轮廓线。有意思的是,王大同用颜料覆盖亚麻线的方式“堆积”出物象的外轮廓线,这位总是愿意不断尝试的艺术家似乎是受到当时“综合材料”观念的影响,有意地进行新的实验。观者可以想象自己用手指沿着线的走向来触摸其轨迹,感受那种明显的凹凸起伏感。这倒可以理解为瑞士艺术史家沃尔夫林所说的“触觉性”艺术,他认为触觉性风格是人类艺术史早期阶段中最常见的艺术风格。如此看来,这样的表达方式倒非常适合用来表述这类远古蛮荒时代的题材。此外,王大同也有意地用干笔皴擦画布,产生厚重的稚拙感与粗野感。由于多次在家乡贵州的博物馆感受到原始面具、脸谱所带来的震撼力,激发了他创作此类作品的冲动。该系列作品从家乡贵州的博物馆获得灵感,体现出他潜藏于内心中的文化认同感。此外,他也颇为直白地表达那些野性十足的“生死爱欲”,这让人想起高更式的原始主义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90年代末,他又令人吃惊地创作了一幅直接体现布依族历史的大画幅作品《王囊仙——布依族农民起义女英雄》。王囊仙是清代布依族农民起义的领袖,失败后被清廷凌迟处死,王大同创作此件作品毫无疑问体现出他自己对本民族历史的兴趣,体现出他愈发浓厚的文化认同感。这件作品画幅高2.78米、宽7.8米,以鸿篇巨制的方式再现出女英雄就义时的场景,让人不由得想起巡回展览画派苏里科夫那件著名的《女贵族莫洛卓娃》。随后几年,他又创作了同样尺幅巨大的历史题材作品《灾难与屈辱:日寇侵华暴行》,以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的责任感追问这段屈辱的历史。实际上,在2000年前的四川美术学院,这种大尺幅的历史题材作品看起来略有些“另类”。而正是1998年贵州家乡王囊仙雕塑的落成激发了他创作大尺幅历史绘画的激情。
今天,身份问题毫无疑问是人文学科中颇受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同时也是争议非常大的一个命题。当代似乎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身份观念:一种在于通过强调少数族裔的文化身份感来支撑多元主义的文化诉求;另一种则将民族身份看作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其中渗透着非常明显的权力关系,美国学者安德森更将民族看作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他们当然不必非得像理论家那样太多地去思考身份背后的文化、政治渊源。同样的,对于王大同来说,民族身份更多的是一种有关家乡的回忆,一种浓浓的温情,这两者都是直观而真挚的。
反思:作为一种文化立场
因为这一代艺术家的经历,客观上他们容易形成保守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体现于文化认同上的非黑即白,但王大同却通过不断地反思来避免这种可能性,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兼容意识。他的《蛮荒古俗》及那一批民俗作品流露出浓厚的传统趣味和文化本位立场,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练习传统书法,同时也愿意去接受新鲜事物,愿意主动地理解、学习外来文化。
1987年,当他从加拿大归来,在感受到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开始反思我们固有文化中的优势和劣势:“中西的差别,主要不在技术层面,而在文化根基和精神状态。我们严谨有余而轻松不足,是精神结构使然。不是从表面放松大笔挥挥就能消弭差异的,下意识看到生存坐标,曾对自己说,‘在内心深处扬起自性,在心的深处摆脱惯性’。”2他说得很清楚,需要摆脱惯性,而这摆脱便来自理性反思。这种反思精神不仅仅理性地告诫自己要摆脱习俗、习惯上的惯性,同时也促使他确立了一种宽容看待新事物,不断立新的文化立场。于此角度,便足以理解为何王大同先生会在教学中全力鼓励学生尝试创新,也足以理解他为何在创作中不断思考、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性。他说得很好:“若要保持活力,就要不断吐故纳新,吸纳的质量和艺术概括越高,释放的能量也就越大。”2
注释:
1.宁佳:《川流不息》,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35页。
2.王大同:《画室独白:沉默语言伴我行程》,载于《王大同油画》,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