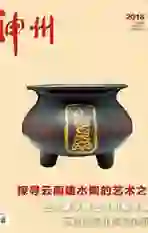浅析唐朝汉文化与胡文化交融
2018-06-28赵子俊
赵子俊
摘要:胡文化是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在唐朝,胡汉文化的交融达到顶峰,表现在民众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本文主要从具体的五方面对其进行介绍,分别为服饰妆容、饮食、商贸、建筑、诗歌。胡汉文化的交融的产物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华文化也体现着其极大包容性。通过研究胡汉文化交融,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同中亚友好的往来的认知,积极响应“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的福祉。
关键词:唐朝;汉文化与胡文化;文化交融;一带一路
唐朝无疑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无论是经济成就还是政治繁荣,在此之后任何朝代都无法超越。经过秦汉时期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的探索和创新,以及社会矛盾的逐步演化和发展,唐朝最终形成了一种社会各方面都相对稳定的局面。地主和农民、中央和地方、皇权与相权、正统儒学与佛道之间的关系呈现相对稳态,两者相互制衡、相互促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朝太平盛世的形成。于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更加开明的对外政策,民众思想的开放,少数民族的大量贸易往来,人口迁徙等极大的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与之后明清的外交政策相比,高下立判。通过研究和分析唐胡文华的交融,有利于深入了解我国相关地区的文化和历史内涵,为经济,政治的发展提供依据,促进地区稳定。如今,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通过了解文化交融也能够促进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地友好交流,促成这一战略的实现。
1、唐朝时期的服饰妆容
得益于唐朝的外交政策,唐朝的服饰融合了西部的西域、吐蕃地区,北方的匈奴、契丹、回鹘等民族的服饰特点,形成了唐朝兼收并蓄的服饰文化。少数民族的服饰尤其是胡服,具有简洁、方便、实用的特点,突显了女性身材的曲线美和男子狩猎放牧时潇洒豪迈的特点,由于中华文化极大的包容性,这些服饰元素很快就被唐文化吸收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以“大袖为主,上衣短小裙长曳地”的基本服装形态,体现了极强的异域风尚。就色彩来看,唐朝服饰颜色极其艳丽夺目,油墨重彩,且多以单一色调为主;从图案上来说,唐装继承了唐朝绘画雍容华贵、娴雅明丽的特点,内容多为山水草木、花鸟鱼虫等自然景观,如《新唐书·车服志》所记载的文官官服花式:“三品以上服绫,以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双孔雀;四品、五品服绫,以地黄交枝;六品以下服绫,小窠无文及隔织、独织。”[1]
唐朝妆容的多元化也丝毫不逊色于唐代服饰。在唐代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化妆步骤,一敷铅粉,二抹胭脂,三画黛眉,四贴花钿,五点面靥,六描斜红,七涂唇脂,八戴发式。其中唐朝妇女的发式也大多融合了胡人的特色,如回鹘髻、百合髻、云堆髻等二十多种发髻。在大唐元和年间,长安贵族妇女流行一套异域妆面,白居易就写有《时事妆》表达其对唐朝女子异域妆容审美的看法,文中说道“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这款乌啼妆以乌唇、八字眉等与唐朝主流妆容格格不入的元素为潮流,深刻反映了胡文化对唐妆极大的影响力,以至形成了在白居易等大家以及我们现代人眼中的一种变态美。
2、唐朝饮食中的胡文化
中国古代汉族的饮食文化与来自游牧胡族的饮食文化风格迥异,各具特色,两者的相互交融丰富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内涵,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独树一帜,屹立不倒。
胡饼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我们现代人也叫作“馕”,是新疆的特色美食。西域的制饼材料如芝麻、胡桃等被中原人引进,由此形成了以胡桃仁为馅料的圆饼。在《续汉书》中记载:“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后董卓拥胡兵破京师之应。”[2]可见皇帝对胡饼的喜欢使得民间形成了一股追捧胡食的风潮,也成了其亡国的重要缘由。胡饼在唐朝达到了鼎盛。《资治通鉴》玄宗纪中说:“日向中,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3]也就是在安史之乱时,玄宗西幸,走到咸阳集贤宫,没有东西吃,只好用“胡饼”充饥。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州》“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用胡麻所做学的却是京都的样子,这是饮食上的交融。
饆饠,亦作“毕罗”,是一种始于唐朝的,由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特色美食。饆饠丰富的馅料为其一大特色,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既有鸡鸭鱼肉也有瓜果蔬菜,大到猪肝羊肾,小到蟹黄樱桃都可被当做馅料,可见饆饠在唐朝社会被极度多元化。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下:“赤母蟹,壳内黄赤膏如鸡鸭子共同,肉白如豕膏,实其壳中。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黄饆饠,珍美可尚。”[4]又有野史记载,晚唐有位会做樱桃饆饠的士大夫名叫韩约,他所做的饆饠面皮酥嫩柔软,馅料鲜红诱人,不禁令人垂涎三尺,人人竞相购买品尝,风靡一时。
又如王翰《凉州词二首》“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中用“葡萄美酒”表现出这美酒佳肴盛宴不凡的诱人魅力,以及将士们豪爽开朗的性格,可见葡萄酒在唐朝被视作珍馐甘露。在唐初,尚未掌握酿制葡萄酒的工艺,所以葡萄酒便显得格外珍贵,直到唐太宗平定高昌,葡萄酒的酿制技术才得以流传。《太平御览》曰:“蒲萄酒,西域有之,前跟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高昌,收马乳蒲萄实,於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为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5]集中体现了葡萄酒从西域传入中原,并受到汉民族喜爱的历史事实。同时,用于饮酒的夜光杯也颇具西域特色。夜光杯是甘肃酒泉特产的玉制餐饮器皿。《海内十洲记》的《凤麟洲》记载:“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长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6]可见在先秦时期,夜光杯就是胡人进献给皇室贵胄的贡品。到了唐朝,夜光杯更是闻名遐迩,与葡萄美酒相得益彰,也因此颇具盛名。
3、唐朝时期建筑胡化的倾向
胡文化在唐朝的帝王陵墓、寺庙等古建筑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汉、胡文化的交流总是要在特定的文化场所进行,或是市井的商品贸易,或是沙场上的戰争交锋,而在太平盛世的的唐朝时期,城市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成了胡汉文化交流的主要场所,城市文化中的胡风元素由此日趋丰富,城市建筑也自然包含其中,比如大名鼎鼎的佛光寺,就是其中的代表建筑。佛光寺,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被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誉为“中国第一国宝”,是我国典型的木结构建筑。佛光寺的大门东大殿,大殿架架的最上端用了三角形的人字架。这种梁架结构的使用时间,在全国现存的木结构建筑中可列第一。”此外,文殊殿的殿梁架使用了粗长的木材,两架之间用斜木相撑,构成类似今天的“人字柁架”,增加了跨度,减少了立柱,加大了殿内空间,足以见当时的妙手神功。从唐朝到如今,佛光宝寺经历千年的岁月沧桑,仍然历久弥新,屹立不倒,可见其建筑技法的高超。
文化总是经济政治的反映,而佛教的兴盛与其背后的政治因素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唐太宗执政期间,历经战火无数的唐太宗崇尚武功文治,认为僧侣只是他们为了获取权利而利用的对象之一,加之佛教在民众心中具有不可小觑分量,唐太宗对待佛教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基于此种观念的影响,唐太宗在贞观初年延请波颇于大兴善寺译经,既为佛教点缀,亦为朝廷政治目的。贞观十五年,玄奘从印度求法而归,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其所译经书给予当时的佛教以重大影响。武则天篡位之初,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将她的夺取政权说成是符合弥勒的授记,来论证自己政权的合理性,可见唐朝统治者愈发重视佛教的政治功能,佛教在唐朝极为繁盛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它成为了统治者统治国家稳固政权的有力工具。随后武择天又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
4、唐朝的商业贸易
唐朝时期,有大量胡商来华与唐人举行商业贸易,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极其优越的交通條件。唐朝时期的对外交通主要有三条,一是著名的丝绸之路,通往西亚与欧洲的阿拉伯帝国,加洛林帝国和查理帝国等。第二是唐朝与日韩的交流。第三是海上丝绸之路,通往印度。由此为唐朝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胡商因此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唐朝寥廓的疆土上。据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讲道:“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一个时期竟达 12 万人.”[7]唐人在和胡商交易的同时,彼此相互了解,相互学习,促进了胡文化的传播。其次,胡商交易活动活跃。市场上异域商品广泛交易,进口商品日渐丰富,如来自波斯的珍珠、玻璃,来自大食的香料、药品,来自西域的葡萄酒、玉器、汗血马等。甚至别国货币也在中国市场市场流通,如大食金币,波斯萨珊货币,东罗马金币等。再者,胡商的贸易精神也赢得了唐人的尊重。来着五湖四海的胡商千里迢迢,风餐露宿地来华经商,他们辛勤勇敢,聪明能干,和当地商人和平相处,患难与共,深刻影响着当地的商人。最后唐朝的政策也偏向胡商,一反传统的本末思想。统治者设立邸店和住坊,专门接待胡商,沿海城市设市舶司对贸易进行管理。
5、唐代诗歌中的胡元素
唐王朝建立之后,大漠首先被李世民征服,之后天山南北的龟兹和高昌也一一被攻取,为了便于管辖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太宗便在此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唐朝一统西域后,又颁布了一系列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政策,大大推动了胡汉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由此可见唐朝与外国所进行的和平友好的交流,更加显示出万国来朝的辉煌景象。同时,唐朝与胡连年战争,士大夫之族弃笔从戎之风十分繁盛,客观上亦促进了文化交流。王昌龄《出塞》“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骆宾王《从军行》“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李白《胡无人》“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诗人渴望战胜祖国边境的胡人,报国杀敌,使百姓免于胡人侵扰,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同时表达了自己壮志雄心。王维的《过崔驸马山池》:“画楼吹笛妓,金碗酒家胡。锦石称贞女,青松学大夫。脱貂贳桂醑,射雁与山厨。闻道高阳会,愚公谷正愚。”其中的酒家胡是侍酒胡姬的另一种称谓。唐朝顾客喝酒时,酒馆内的胡姬便会为消费的客人提供歌舞音乐以助兴。岑参在《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鋋歌》说“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和刘禹锡的《观柘枝舞》“胡服何葳蕤,仙仙登绮墀”可见胡曲,胡乐,胡舞的兴盛。
如今,我们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提议,通过研究中国唐朝胡汉文化交融的史实建立起沟通中国同中亚诸国的友好交流的文化桥梁是当今的重要课题。了解唐朝胡汉文化的交融同时也为我们同中亚建立友好外交提供历史经验和理论支撑,促进中国同中亚更加密切的交往。
参考文献:
[1]宋祁,欧阳修,范镇等.新唐书:车服志.中华书局.1975
[2]司马彪.续汉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3]司马光.资治通鉴:玄宗纪.中华书局.1956
[4]刘恂.岭表录异.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5]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2017
[6]东方朔.海内十洲记:凤麟洲.文史哲学出版社.1993
[7]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