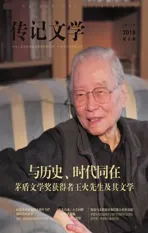一代电影大师沈浮(下)
2018-06-13丁亚平
丁亚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
三
1947年,沈浮在完成影片《追》的导演工作后, 被“中电”指定导演一部“反共”影片《铁》,以配合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戡乱”。面对当局以副厂长职务为诱饵的拉拢手段,沈浮毅然决然选择了拒绝,离开“中电”,举家回到上海,加入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
有评论者曾指出,沈浮于此后的电影作品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平民意识,“除了艺术内容上体现为高度的‘平民意识’之外,沈浮在运用电影形式手法时,也时刻不忘劳动大众是他作品的接受主体,渗透出明显的‘平民化’倾向”。
沈浮的电影作品,洞察人情,体察世故,说它体现这样的一种“平民意识”,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在笔者看来,沈浮的电影更体现出一种独立的尘世自我。这种不同于纯粹自我的价值态度和思想立场,为他的电影观念和艺术活动开辟了道路。沈浮的电影中所体现出的艺术观念和风格特点对时代和观众的影响,比任何关于它们的历史解释都要更直接。这是为什么呢?很显然,对观众和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不止是因为这些影片的故事好、内容好,而主要因为敢直面现实,故事说得好,拍摄技巧也高。在近六十年的电影旅程中,沈浮通过自己的踏实、坚韧与电影艺术告诉观众:电影是现实主义和电影家的展现,“开麦拉是一支笔”。
沈浮一直在思考: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连接一个故事,如何用生动真实的生活细节构成人物形象的“血肉”,以及开头用什么样的叙事形状或镜头等一些电影技巧层面的问题, 50年代他写过一篇文章《电影语言在电影创作中应用的一般规律》,文中道:“我看我们的毛病,不在于不懂文法,而是急切地求简练。其实应该先从明确入手,不怕遵守一般规律,不怕俗套。”在《“开麦拉是一支笔”》一文中,他说:“一般地讲,现在的国产影片观众,还倒是挺喜欢看情节的。因为故事性强,才有戏,有戏必有斗争,有斗争才会有好戏看;但问题是一个戏,如是太偏重了情节,专为故事而故事,那往往就会因为牵强附会、偶然巧合这些东西,显得戏不真实,而人物也会写走了样。我所说的人物,当然是指人物性格而言,我认为一个戏有什么样的内容,一定有它最合适的风格,什么样性格的人,也必然会演出什么样的戏。所以说从人物性格上来发展故事是最科学不过的。并且,人物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人过的又是政治生活,透过这人物,还可以写出这人物所生活的世界、国家和他的社会。”
沈浮对于电影技巧层面的思考与探索在他的作品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如《狼山喋血记》的剧本《冷月狼烟录》,在故事结构方面,即不同于所谓“戏剧性”丰富的作品,无论是内容与形式、故事与人物,还是作者与观众,以及电影性与戏剧性,都能看出沈浮在努力去保持适度的平衡,竭力避免过分注意其中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只可惜,这部电影在上映后反响平平,仅收回了拍摄成本。而在影片《万家灯火》中,则明显可见沈浮的导演技巧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部主要讲述婆媳之间、夫妇之间和家庭与社会之间矛盾故事的电影,“朴素无华,真切感人”,不仅故事、人物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典型性,而且导演手法和镜头的运用也很有特点,“使人感觉不到导演和镜头的存在,完全为剧中气氛和人物情结所吸引片中”,因此收获较多好评。
中国有许多片子是图式的罗列,情节的卖弄,玩噱头,耍技巧,每一个演员在矫揉造作,在“演戏”,许多动作是为了博得观众廉价的喝彩。……《万家灯火》超拔于这些庸俗的泥沼,写的是平凡的小事情,平凡的小人物,既不轰轰烈烈,也不曲折离奇,像是一溪清流,自然,明快,而又丰润。编导的企图,达到相当谐和完整的境地。这是难能可贵的。
绝大多数的演员都适合于角色的身份,如日常生活一般的在层层展开,奇峰迭出;这里自然有艺术上的加工,然而既不做作,也不过火,纯熟,贴切,恰如其分。这种亲切感,是来自丰富的生活内容和饱满的人情味。(周而复《评〈万家灯火〉》,香港《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12月第5辑)
沈浮认为,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都值得研究,都是一种知识,都可以作一种观察、表现和批判。《万家灯火》取得成功,就与生活所给予沈浮的启发有关。这部影片取材朴素、真实,生活意味盎然,现实感很强,有评论者称其中“有你的生活,有我的生活,也有他的生活;有你的感受,我的感受,也有他的感受”。而关于影片中胡智清这个人物,编剧阳翰笙评论道:“他只是一个中下级的职员,他有向上爬的天真的梦想,性格非常软弱。他只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物,根本没有想在这个人物身上放一点革命的气息进去,而且一家人全是一般的小市民而已,像这样的家庭因而也闹出了这样的悲剧。因此我们所表现的是把他当成小市民阶层的人物来写,而最后他自己又把他自己否定了的。”沈浮则说他对这个人物的处理更多地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考虑:“我们之所以写胡智清,简而言之,是因为目前社会上胡智清这样的人太多。我们之所以在《万家灯火》里来否定他,也只是想在他们走错了的路上,牵一牵他们的衣角,指给他们一个方向而已。因为我们觉得今天的胡智清群是值得同情的,而且他们也是种力量。”影片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虽缺少辛辣的讽刺味,却一定程度地触及了人和社会的本质。

《万家灯火》剧照
陆弘石在《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中认为,《万家灯火》和《小城之春》一样,是战后“灵魂的写实主义”创作系列中的重要的作品。“它们分别从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这两个互有差异的‘路向’,共同抵达对灵魂的深刻展示。”这种分析颇有道理。
沈浮 “过去的作品,在内容方面,只是为了表现一种空洞的政治概念,虽然也刻画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实际上是和真实的生活脱了节。而《万家灯火》却诚实地刻画了生活,同时在这样的生活面前,显示了一种热切的搏击的力量和意识”。夏衍对《万家灯火》也大力肯定:“一张影片很难得到两全,而《万家灯火》则不仅两全,而且三绝。剧本好,导演好,演技好。这样珠联璧合的艺术品,是在近年来所罕见的。”
在中国早期电影史上,沈浮是最擅长使用“灯”的物象来表情达意的电影艺术家。“灯”是电影摄影不可或缺的光之来源,更被当作“黑暗”里的“光明”之源。当“灯”的意象在影片中反复呈现的时候,“打破黑暗追求光明”的象征意蕴便昭然若揭。
电影《希望在人间》中对“灯”这一意象的取材和处理,就体现出追求光明、自由和民主的思想主题。主人公邓庚白受了三年的监狱生活,但还是视死如归,在影片结尾,他抽着烟斗,慨然出门,这种勇敢的牺牲精神正源于他深知自由的可贵,而沈浮则通过这部电影表达了自己对自由、民主的坚决拥护与捍卫。
四
1949年以后,沈浮意识到自身的转变以及“如何向人民学习”的重要性,尤其是参加完文联大会,关于这方面的心得感想就愈发深入了。沈浮认为向人民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让自己真正地“溶合在广大的劳动群众中间”,学习他们的吃苦精神,放下架子,与他们“共同生活,共同战斗”,这样才能从生活到思想情感上与他们保持一致。不然的话,“也是空空地去”,“空空地来”。
沈浮满怀热情地追随着时代的步履,积极主动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拍摄了《纺花曲》《斩断魔爪》《老兵新传》《万紫千红总是春》《北国江南》等一系列讴歌新时代、赞美劳动群众的影片。今天看来,这些电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无一例外地带有时代的印记,如《纺花曲》仅仅停留在活报剧的层面,属于附和主旋律的急就章;反特题材的影片《斩断魔爪》则围绕真假图纸,讲述公安干警将海外潜回大陆的国民党特务抓获的故事,电影语言和造型借鉴了恐怖片手法,视觉效果不错,但整体水平较弱;1959年编导的影片《万紫千红总是春》讲述的是发生在大跃进时期的故事,这部电影上映后还曾引来一场意外之事——因片中有里弄妇女组织生产组向组员借用缝纫机的描写,云南省委某负责人的夫人观看后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周总理对影片做了修改指示:缝纫机是个人私有财物,非属生产资料,在有关借用缝纫机的情节描写,必须按照政策明确地阐述清楚,不能稍有含混。于是,遵照总理的指示,这部影片后来又进行了修改。

《希望在人间》剧照
沈浮在经过不断的摸索尝试后,意识到要拍出劳动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必须遵从艺术规律,从实际出发,从艺术出发;好与不好,不应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来评价。因此,在进行《李时珍》的拍摄时,沈浮就尽量避免夸张、浮躁的剧情,就像片中人物说的:大家需要的东西才是学问,空谈是没有用的,“一生都在逆流里,可是还得往前进”。此片取得了较为不错的艺术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浮曾被选派赴苏联学习宽银幕电影摄制技巧与方法,去补上电影的现代技术这一课。他在总结学习宽银幕电影技术的经验时认为,那些小题材的、人物较少、场景简单、没有重大情节、单纯朴素的剧本,是不大适于拍宽银幕的,而特写镜头之用于宽银幕电影也不像普通银幕那样的随心所欲。电影《老兵新传》是沈浮拍摄的中国第一部立体声宽银幕故事片,让小人物演出英雄的传奇,是他在新时期的一次尝试。该片于1959年获第一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技术成就银奖。
1963年拍摄的《北国江南》,是沈浮和阳翰笙再度合作的一部电影,是关于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打井抗旱改造大自然的故事,不意 “影片刚刚上映不久,就遭来了急风暴雨般的摧残。把现实主义当成修正主义来批判;表现人的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文艺要通过塑造各种不同个性人物来表现生活,被说成歪曲现实;而表现人物的复杂内心矛盾和转弯,又说是写中间人物……”这一切正反映了当时文艺界的变幻无常、波谲云诡。

《李时珍》《追》《曙光》剧照
“文革”结束后,沈浮接受的一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即电影《曙光》(上、下)的拍摄,故事的背景发生在1930年代的洪湖革命,主要讲述贺龙和王明左倾路线拥趸者斗争的故事。曾在影片中担任副导演的宋崇后来回忆说:沈浮在此片拍摄过程中试图遵循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力求符合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对于影片中的服装、道具、后景的陈设,都要求十分严格。红军的服装、领章、帽徽,农民的衣物、斗笠等,沈浮坚持要破、旧和自然。服装工人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把新做的服装洗、晒,让风吹雨打使其变旧,而为了选择帽徽领章的颜色,找来近十种旧红布,沈浮仍不满意,后来他自己从建筑工地上找到一块带有深浅不同铁锈色的石头,让按照这样的颜色制作。他们还专门买了一百顶新斗笠到洪湖向当地农民换取一百顶破、旧的斗笠。拍摄贺龙抱着穷孩子演说一场戏的几件破旧儿童棉衣,也是沈浮亲自过目挑选的。
沈浮经常对我们说:电影是门综合艺术,只有充分发挥各个合作者的积极性,影片才能好上加好。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如果互相扯皮,综合艺术则成为综合并发症。甚至造成作品畸形或夭折。沈浮在合作上十分尊重创作友谊,从不因自己是总导演而以地位压人,注意充分发扬艺术民主,提倡各抒己见,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耻下问。摄制组任何人提出意见和问题,他都耐心地听完,并认真加以思考,吸取大家的合理意见。”他感觉,在拍摄现场不能依靠看剧本工作,“导演心中要有一部电影,几百个镜头全装在脑子里”。(宋崇:《在沈浮老师身边——〈曙光〉导演学习札记》,《电影艺术》1979年第3期)
这部电影显示出沈浮非凡而锐敏的艺术处理与表现能力。虽然影片的主人公是贺龙,但沈浮坚持“不要造神,而是塑造人”的创作宗旨,避免混乱的热情和太过革命与神圣化的修辞,将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冷静、理性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给予观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据宋崇回忆,沈浮曾反复强调,文学即人学,一个导演必须观察社会、观察一切人和事,要做有心人,注意各种人的性格、情感、生动的语言和生活细节,还要把观察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导演的头脑应该象一个中药店,把储存的东西隔成一个个小抽屉,里面放着当归、人参、地黄……到配药时,这里取二钱,那里取四钱,就能配出治疗百病的灵丹妙药。导演和作家一样,要想拍出真实感人的影片,头脑里的小仓库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只有在扎实的生活基础上,想象的翅膀才能飞翔。
沈浮比较擅长刻画两类人物,一类是转变型人物,如《万家灯火》中的胡智清、《狼山喋血记》中的赵二、《万紫千红总是春》中的职员。二是复杂型人物,如《乌鸦与麻雀》中的“麻雀”、《曙光》中的林寒、《追》中的方子久,而他们都可以说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物。沈浮的电影力求符合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在题材的处理上,无论故事讲述还是心理刻画都十分尊重本来的面貌,要求符合常情,反对牵强附会,生搬硬套, “对于影片中的服装、道具、后景的陈设,都要求十分严格。”而在指导表演上,沈浮的“说戏”很有特点。演员温锡莹曾专门写过文章,回忆沈浮的说戏:“我是演员,在与沈导演一起工作的全过程中,发现他总离不开说戏。说戏是他导演思维演绎的全过程。我常常从他绘声绘色的说戏中,理解了我的角色,掌握了角色的基调。说戏对于沈导演,就是头脑中的形象思维,也就是电影蒙太奇的产生、选择、使用。我们常常是在他的口述下被感染,而进入创作性的内心活动的。” 温锡莹是著名演员,他的回忆着墨不多,却不难看出他于字里行间对沈浮的尊重之情。
沈浮为人“宽宏、真诚而又无比善良”,李天济曾说他自1940年认识沈浮,几十年来,从未听到过和自己同辈的人称呼过沈浮为“先生”或“厂长”的,总是叫他“沈大哥”。“他从来是与人为善的,在艺术上尊重甚至鼓励别人反对他。找他谈剧本,他总是把你写的人物、情节海阔天空地大加发挥,说得眉飞色舞,好象是在谈他自己的作品。到最后又总用这么一句话收场:‘我随便讲讲,该怎么写,随你呗!’其实他何尝随便,他是从各个角度帮助我们打开思路,为我们插上创造和想象的翅膀。”
沈浮的电影作品,无论是《大皮包》《联华交响曲·三人行》《狼山喋血记》,还是《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李时珍》《老兵新传》等,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头,将对人的价值、尊严与自由的关注,置入日常化的现实生活的展现之中,从而具有较为丰富的意义和一种“希望的哲学”的历史意涵。回顾沈浮的一生,从中可以看出一代电影艺术家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而不懈努力的奋斗历程,而珍重他们的话语遗产和视觉艺术,在当下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