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柏尔,从此不再陌生
2018-06-12徐晓雁
徐晓雁
梁文道的节目里有一句口号(slogan):每一次阅读,都指向一场旅行。于我,反之亦然。每一场旅行,都指向一些新的阅读体验,甚至是与书本的有趣相遇。
此刻我在上海冬日苍白的阳光下,打开一本黑色封面的法文版小书:
这是我被关进牢房的第二天。阿米德掏出铅笔在墙壁上写下突尼斯诗人卡桑·夏比的两句诗:
人民如若渴望生活/命运必得给出回应/无论如何黑夜终将逝去/枷锁定会被砸烂

摩洛哥沙漠日出
“太棒了!”我說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但是太棒了,我能感觉到这很美。但是这些话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渴望生活,就是说受压迫受奴役的人或人民寻求解放,上帝会回应他们,就像没什么能阻挡黎明的到来。”
“你运气真好。” 我对阿米德说。
“为什么?”
“因为你认字,还会写字。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学会认字和写字。”
这里的“我”,是二十岁的穆罕默德·苏可里(Mohamed Choukri),他在丹吉尔被抓进监狱的时候还是个文盲,后来却成为有名的作家。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因为他来自柏柏尔族,一个神奇的撒哈拉游牧民族。

德吉玛广场
苏可里的书仿佛又把我带回到摩洛哥的阳光、沙漠、骆驼,当然那里还有难忘的柏柏尔人。
我们要从摩洛哥第三大城市马拉喀什出发,去东南部的梅尔祖卡沙漠骑骆驼和看星星。马拉喀什在柏柏尔语里就是“上帝的故乡”之意,这真是个令人喜欢的城市。我们住在老城一家法国人开的民宿,房子是典型的被称为利雅得(Riad)的摩洛哥传统建筑,里面的细节、服务、早餐又处处体现着法兰西风情。法国人对于摩洛哥的情怀当然是剪不断理还乱,当年大批法国文人骚客,在此留下不少美谈。我在马拉喀什博物馆的墙上,就看到过那个写了《冰岛渔夫》的作家皮埃尔·洛蒂对于摩洛哥的感受:“忘掉一切,只享受当下经历的那些不会骗人的事物—漂亮的女人、骏马、美丽的花园和鲜花的芬芳。”皮埃尔·洛蒂也是个大旅行家,据说他每到一个国家,便会娶一名当地女子为妻,并写一本与当地有关的小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娶过柏柏尔女子为妻。为摩洛哥留下感慨的还有大画家德洛克瓦:“在这些充满阳光的国度,生活被空气和光线带来的愉快超越。美丽在大街上奔跑,我们不大会去想那些扰乱心神的浮夸虚荣。荣耀在这里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词汇。”
此去撒哈拉,我们事先定了一辆车和一名司机,旅行社说好司机早晨会来德吉玛广场接我们。德吉玛广场是摩洛哥最大的露天集市。傍晚时分最是热闹,游人如织,摩肩擦踵,人声鼎沸。但现在它似乎还未醒来,静悄悄的,只有几辆卸货和等人的车。
迎接我们的是一辆簇新的黑色奔驰SUV。司机从车上下来,与我握手,我们用法语致意。他中等身材,肤色黝黑,黑色的卷发剪得很短,穿一条牛仔裤和T恤衫,眼角有微微的皱纹,一时不好判断年龄。他应该就是哈桑(Hssain),旅行社昨晚已经告知司机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有无数个哈桑,这名字就像我们的小明、小刚那样常见。
车开出马拉喀什,城外新修的柏油马路十分平整,道路两旁的橄榄树和崖柏郁郁葱葱。摩洛哥全然不是我想象的落后模样,而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哈桑说阿特拉斯山脉冬天的积雪在春天融化,提供了丰富的地下水,所以这一带的植物十分茂盛。
我问哈桑是不是柏柏尔人,他说是。
“那,你是图阿雷格人吗?”我想起看过的电影和翻译过的书。
“哦,不,图阿雷格人主要在马里和阿尔及利亚一带,我的族群是卡巴什(Khebbache)。可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中国人知道柏柏尔人和图阿雷格人的呢。” 哈桑有点惊讶地说道。

哈桑(Hssain)
确实,柏柏尔人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遥远、神秘的族群。我也是因为要从摩洛哥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去西班牙的塔里法,才读了张承志的《鲜花的废墟》一书,得知当年阿拉伯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先锋就是两位柏柏尔战士,陀格里和塔里甫。陀格里带领几百勇士,没费什么事就攻下了直布罗陀,随后一连串地略地拔城,很快攻下了半个西班牙,柏柏尔人的骁勇善战可见一斑。这两位勇士,一位留下地名直布罗陀(Gibraltar,原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思是陀格里之山),另一位留下的地名是西班牙最南端的小城塔里法。
我对柏柏尔人充满好奇。哈桑见我对此感兴趣,自然十分高兴,给我讲起柏柏尔人的历史。
他讲了许多,当然我没能全记住,但加上事后的阅读,我对北非的柏柏尔人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他们主要活跃于撒哈拉大沙漠,是个十分古老的民族,今天主要生活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一带,利比亚、突尼斯、埃及、马里、毛里塔尼亚等地亦有分布。按照哈桑的说法摩洛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是柏柏尔人,而我在一本中国人写的书中看到这个数字是百分之三十。也许两者都对,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指有柏柏尔血统的人,而百分之三十应该是指纯粹的柏柏尔人。实际上柏柏尔人并非单一民族,它是众多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方面相似的部落族人的统称。这些部落中最出名的要算图阿雷格人(Tuareg),但关于柏柏尔人的起源则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我问哈桑同样是柏柏尔人,为什么图阿雷格人这么出名,而其他族群,比如他所在的族群,知道的人就很少?他说因为图阿雷格人同法国人打过仗,法国人写过很多有关图阿雷格人的书。前几年马里还陷入动荡和内战,因此那里的图阿雷格人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施密特《火夜》法文版
“那我还有一个困惑:柏柏尔人在北非本来是大多数,为什么阿拉伯人来了就能统治这块大陆,他们人数远少于你们。”我继续抛出疑问。
“因为柏柏尔人淳朴善良,他们最看重的是自由。政治、权力游戏这类东西对他们而言比较陌生。”当然,这是他作为一名柏柏尔人的解释,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较确认的是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北非,柏柏尔人也曾经帮助阿拉伯人扩张至安达卢斯。这块大陆由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交替统治。在欧洲殖民时代,柏柏尔人同阿拉伯人并肩作战,最终赢得了国家独立。但独立后的北非国家却无一例外地成了“阿拉伯国家”,柏柏尔人的经济和文化权益受到削弱。
我们一问一答,甚是投缘。哈桑的法语十分流畅,极少口音,比我一路碰到的大部分摩洛哥人说得都好。哈桑今年二十八岁,还没有结婚。他说这对一名穆斯林来说确实比较少见,但他不愿意结婚一两年后,像很多男人那样,到外面去找别的女人,这太没意思了。他希望找一位能够灵魂相契的姑娘。“但这太难了,我的朋友们开玩笑说你要找的姑娘还没有出生。”他有些苦涩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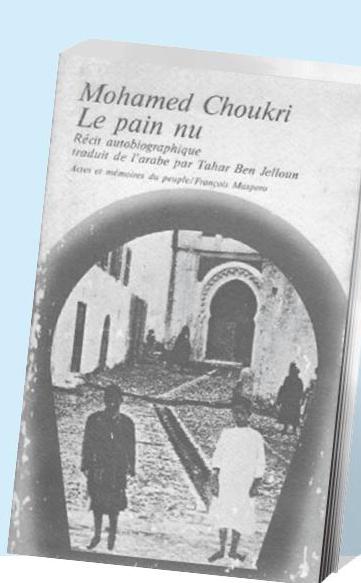
《赤裸的面包》法文版
他的语言能力,他对于柏柏尔历史的了解,对婚姻的态度,都超出我对于一名司机的期待。加上他一路上对于客人的尊重、细心和无懈可击的职业素养,让我感觉他很可能受过高等教育。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柏柏尔沙漠游司机?我对哈桑充满好奇。
“哈桑,你的法语和英语都说得这么好,是在学校学的吗?你还会说什么语言?你知识那么渊博,见解那么深刻,是不是上过大学?或者是哪个贵族的后裔?”我开玩笑道。
哈桑笑了:“哪里啊,我只上过四年学,爸爸妈妈都不识字。我十五岁出来打工,养活自己。英语和法语,还有西班牙语,都是跟客人学的。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不会说英语,可某一天我突然发现,我能说英语了,就是这么神奇。我还能听懂一点德语,但不怎么会说。”
我和同伴们张大嘴巴,惊讶得一直没合上。所以加上他的母语柏柏尔语和阿拉伯语,哈桑会说六种语言,甚至还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单词,而这一切完全靠自学。就如哈桑所说,社会是最好的学校,时间是最棒的老师。
我们问他,柏柏尔人都像你一样聪明吗?他谦虚地说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因为沙漠里生存条件艰苦,必须学会适应各种环境,细致观察一切。所以柏柏尔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特别强。确实,我们后来遇到的柏柏尔人通常都会说好几种语言。接待游客时,既是司机、导游,又是厨师、餐厅服务员,样样上手。
在到达沙漠之前,我们途经录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城瓦尔扎扎特,许多著名的影视剧如《阿拉伯的劳伦斯》《权力游戏》等都在此取景。我们入住古城外山顶上的一家小旅馆。晚餐后,星星和月亮都已升起。十月底临近撒哈拉的小城,暑热已退却,寒意还未降临。舍不得这如水的夜色,我决定爬到院子的露台上去看星星。
我穿过门廊时,哈桑正坐在休息处的沙发上抽烟。我来到庭院,沿台阶小心拾级而上。露台没有灯,很黑。未及我站定,哈桑就已来到我身边。我不得不再次感叹他的心细如发和职业素养,他一定是从窗户里看到我一个人爬上黑乎乎的露台,不放心,赶过来陪我。我得承认如此细致入微、体贴的服务,之前很少遇到。后来我才知道哈桑在做沙漠游司机之前,在酒店做了八年服务生,练就一身客人还未开口,他就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的本领。
仰望苍穹,星斗满天。我努力寻找着小时候经常看到的北斗七星,但我已经不认得了,身居闹市的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
我问哈桑认得这些星座吗?他说小时候认识很多,现在也有些淡忘了。
看着哈桑,看着星星,我忽然想起法国作家埃里克-埃马努埃尔·施米特笔下的柏柏尔向导阿贝格。施米特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我翻译过他的好几本书,最近刚刚完成他的自传体小说《火夜》,讲述他二十八岁那年在撒哈拉大沙漠遭遇的奇迹。
于是我给哈桑讲故事:“有位很出名的法国作家,年轻时来撒哈拉沙漠徒步,在霍加尔高原迷了路。于是他看星星,希望能借助星座找到露营地的方向。可他是个城里人,天文知识贫乏。太阳一落山,二月的霍加尔高原寒气逼人,他只穿着短袖短裤,只能紧贴着还带有阳光余温的石头。没有食物,水壶里只剩最后几滴水。几乎绝望的作家没有办法,只能在沙地上挖一个坑,把自己埋进去,盖上沙子取暖。他想:要么我熬过这一晚,要么这就是我的坟墓。”
哈桑听得十分专注。
“正当施米特在沙坑里等死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看到一团火,然后有一股力量将他托起到空中,他的身体无限膨胀。没有恐惧,没有痛苦,相反是一种极度的欣快感。随后这股力量又将他轻轻放到地上,他便沉沉睡去。而此时此刻,他的柏柏尔向导阿贝格正疯了似的在寻找他,用在沙地里艰难收集到的荆棘枯枝点燃一堆堆篝火,希望能讓他看到。第二天施米特奇迹般地醒来,沙坑没有成为他的坟墓。他发现自己搞错了方向,下到山脊的另一侧,于是返身再往山上爬去。就在他筋疲力尽之际,他看到了那个找了他整整一夜的蓝色身影,穿着柏柏尔蓝色长袍的阿贝格。他一下子倒在了阿贝格的怀里。”
“哦,太好了!”哈桑松了口气。
施米特在书里用很大篇幅写了他的柏柏尔向导阿贝格,书中有个有趣的场景:平时勤勉谦卑为游客服务的阿贝格,有一天走到一个山口时,却让大家停下,恳求众人给他几分钟时间。他换上节日才穿的镶边长袍,骑上骆驼,俨然一位骄傲的王子,全然不顾面面相觑的游客。转过山脚时大家才恍然大悟,那里一棵灌木下,坐着一位仙女般的牧羊女,周边围着一圈羊羔。少女低着头假装没看见他,他直视前方也假装没看见她。可是旁人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两个相互吸引的年轻人。可是骄傲的他们,谁都不愿意先跨出这一步。
施米特感慨道:对阿贝格来说,追一个姑娘,也许要花几个月才对她说出第一句话,也许一年后才敢尝试亲吻,也许要花两年时间才能照着规矩求婚。这就是慢的力量,柏柏尔人阿贝格深谙伟大的爱情之道。
哈桑听得十分入迷:“你的故事,太美好了!”
经过一天的跋涉,终于到达大漠边缘。傍晚时分我们在驿站换上骆驼进入沙漠露营地。沙漠帐篷出奇地奢侈,有抽水马桶,有热水澡可洗,在缺水的沙漠,倒让人心有不安。营地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上菜的小哥俩及刚才替我们牵骆驼的小伙子都是柏柏尔人,都有着轮廓分明的精致五官,颀长的身材和明亮的眼睛。说实话哈桑跟他们比起来并不算帅,却是最有魅力的一个,因为他有阅历。

菲斯书摊
吃过晚饭,篝火燃起,有人开始打鼓。我欣喜地发现火堆边打着鼓的正是哈桑,他的节奏感极好。鼓声越来越热烈,人们开始围着火塘拉起手跳起舞,我则在一旁含笑而立。哈桑放下手中的鼓,朝我走来说:“走,我们去沙脊上看星星!”
我们离开人群,朝露营地背后的沙脊爬去,那里一片漆黑,沙子在脚下打滑。哈桑伸出手,我很自然地就握住。他的手温暖而有力,有一点点粗糙,拉着我一步步登上了沙脊最高处。我们在沙堆上抱膝而坐。
黑色的苍穹无边无际,大漠万里,闪烁的群星如镶在黑丝绒上的颗颗宝石,又如伊甸园串串银色的苹果。语言在这个时候是多余的,我们默默看着星空。
一颗流星划过。他说:“看,流星!”
我说:“是的,流星!看,那里又有一颗!”
他忽然感慨道:“我们见面才两天,可我好像已认识你很久!”
我说:“是的,因为我已经在书里认识了你好久。你还记得昨天晚上我给你讲的法国作家的故事吗?书中作者对他的柏柏尔向导充满深情。他说那些牵着骆驼的柏柏尔人,有着一种骨子里的高贵。他的描述深深感染了我。今天遇到你,我从书中感受到的一切,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在我眼里,你就是阿贝格的化身。我会不断把你跟阿贝格重叠起来。所以,我们已经认识了好久。”
“认识你真好!”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中国女人会如此关切柏柏尔人。”
“你知道《赤裸的面包》这本书吗?”我突然问。
“知道,是穆罕默德·苏可里的书,他就是柏柏尔人,我喜欢这本书。”
实际上我是不久前才第一次听说这本书和这位作家。动身来沙漠之前我们在马拉喀什老城闲逛,街角的一扇小门引起我们的注意,门廊以混合了毕加索和达利风格的壁画作装饰,一位身穿花衬衫,花裤子,戴一顶窄边草帽,有着花白大胡子的画家,正侧对着小门,在画板上涂着颜料。
我们进去参观他的画室,二楼墙上挂着许多表现马拉喀什迷人风情的油画。画家告诉我们他当年就出生在这所房子里,他们家四代居于此。我感觉他是个很有文化素养的人,可能出于译书人的职业习惯,总想着要把有意思的书介绍给中国读者,便问他有没有好的摩洛哥作家和文学作品可推荐?他告诉我有一本叫《赤裸的面包》的书,作者是一位在摩洛哥很有影响力的作家穆罕默德·苏可里。
苏可里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摩洛哥北部一个贫穷的小村子,父亲十分暴力。为了逃避这一切,苏可里十一岁时离家出走,到大城市丹吉尔街头流浪。饥饿、贫穷、暴力、毒品,构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二十岁那年,他被当时统治丹吉尔的西班牙人抓进监狱。在狱中他认识了一位参与摩洛哥独立运动的难友,教会了他读书和认字。本文开头讲述的就是这一场景。
苏可里后来做了小学老师,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写作,并在阿拉伯语文学杂志上发表处女作《沙滩上的暴力》。他的世界性声誉则来自于自传体小说《赤裸的面包》,描写了他的童年时代,其中他对于现实的抗争和顽强的生命力,令人动容。小说写成后,美国作家保罗·鲍尔斯将其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大获成功,随后法国人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一九八二年小说的阿拉伯文版终于面世。二○○三年,苏可里因癌症去世。摩洛哥文化部长、文化界名流以及皇室的代表都出席了他的葬礼。
这样一本书,如果有出版社感兴趣,我确实有心译介到中国。本想择机托人到法国买一本法文版的,只是没等我回国,就在菲斯的一家旧书摊上找到了本书的法文版,店主硬要以高于标价一倍的价格卖与我。开始我没要,走了几步后又回头,想想还是应该在摩洛哥买下这本书,为这趟与书的相遇画上圆满句号。
哈桑喜欢这本书,我一点不觉得意外。苏可里从一个在饥饿、暴力、毒品中挣扎的街头流浪儿,二十岁之前还是文盲,成长为替底层人民发声的摩洛哥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这样的经历一定让从小家境贫寒,只读过四年书的哈桑有所触动。他十五岁开始在餐馆、酒店打工,养活自己;做旅游团司机后,又為父母、哥哥造了房子。同时他像海绵一样吸收来自各处的知识和智慧—从大自然、从朋友、从游客、从书本。从他的谈吐和聪明程度,我感觉他的志向绝不满足于做一名沙漠游司机。出过陀格里、塔里甫、苏可里这样人物的柏柏尔族,说不定哈桑某天也会成为一位杰出人物?
如果说施米特带给我的是书本上柏柏尔人的美好形象,那哈桑给了我一个有血有肉的柏柏尔人的美好形象。通过这次旅行,柏柏尔对我不再是个陌生的词汇。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Barbari(野蛮人),这是罗马人对他们的称呼,他们自己称自己是Imazighen,意即自由而高贵的人!是的,就如我眼前的柏柏尔小伙哈桑,就如《赤裸的面包》的作者苏可里。

摩洛哥最古老的图书馆
买到这本《赤裸的面包》我已十分开心,不过它还在旅途中继续发挥奇妙的作用。那是在古城菲斯的最后一天,我们去寻找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卡鲁因大学。它建立于公元八五九年,其历史比欧洲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还要早二百多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认可为最古老的学位颁授大学。它同时也是一所清真寺,最早的教學方式是学者向教徒们讲解《古兰经》。
找到大学后发现大门是紧闭的,非穆斯林不得入内。又走几步,发现旁边有一扇半掩的门,原来是卡鲁因图书馆,摩洛哥最古老的图书馆,始建于十四世纪,只对研究人员开放,游客不能进。我不死心,掏出刚买的那本《赤裸的面包》,与看门的老先生交涉:你看,我是一名中国的文学译者,我想翻译你们著名的作家穆罕默德·苏可里的作品。这里是世界上最古老大学的旧址,让我进去看一眼,拍几张照片吧。老先生大概被说动了,就让我和一个同伴进去。他带我们看了阅览室和藏书的地方。我拍了几张照片后,有些疑惑,吃不准这里是不是真是我以为的最古老大学遗留的建筑,它看上去似乎没那么古老。后来看介绍,得知文化部对这里进行过翻修,由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在几年前剪彩。所以,我应该算是很有幸?看来书的力量真是神奇。
迷迷糊糊转了一圈后老先生忽然不见了。回到出口,守门的保安说老头很友好,带你们参观了一圈,是不是要有所表示啊。一想也是,摩洛哥是一个小费国家,于是翻出仅剩的二十个DH(摩洛哥币,相当于14元人民币)。结果被保安严重鄙视:这点钱,你们以为是打发叫花子啊。刚才因书带来的庆幸、喜悦被摧残殆尽。原来并不是看在书的分上,是看在钱的分上?其实一路上我们一直给餐厅服务员、司机、酒店服务生等小费,唯独在图书馆,我忘了小费这事,因为是图书馆。看来我错了……
二○一七年十一月初稿
二○一八年二月九日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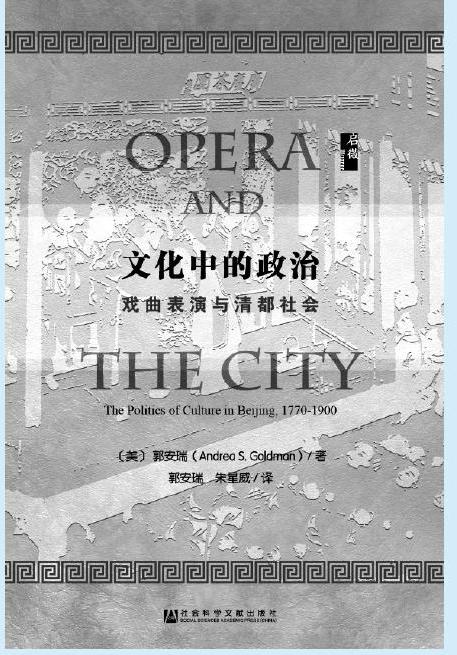
《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精装)
[美] 郭安瑞著 郭安瑞 朱星威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版
2014年美国“列文森图书奖”作品
晚清北京戏曲行业的社会文化史
清代的北京戏曲流派百花齐放,吸引了大量观众。它就像一种文化黏合剂,跨越社会阶层、性别和文化,成为清代北京城公共话语表达的重要场所。
作者通过“观众与演员”“场所与剧种”“剧本与表演”三个部分探讨戏曲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呈现了戏曲在清代北京的重要地位。从对戏曲表演的描绘中作者带给我们一部近代北京的社会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