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怯懦—《繁花》,仅谈话剧,不涉改编
2018-06-12南妮
南 妮
在复旦中文系受益最深的,是一二个名师;完备的图书馆;每年观剧的安排。萨特的《肮脏的手》、焦晃的《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梅丽尔斯特里普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等等,在上世纪80年代,于我们有艺术与思想的启蒙意义。记得有一年被通知看上海戏剧学院藏语班学生演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是藏语班演出,我竟然放弃观剧。看完戏回校的同学直呼“好看!”—是藏族学生用普通话演的。
因为一个愚蠢的念头,酿成了终生遗憾。
就是用藏语演出,那还是莎剧。
20岁看“罗朱”,与40岁看,那是不一样的。
也许因为这终生的遗憾,毕业以后,凡是“罗朱”剧的各种演出都看。话剧、芭蕾舞剧、音乐剧……剧情如此熟悉,但是每一次的舞台演绎都有不同味道,这一夜,激情荡漾,浮想联翩,便是必然。
关于悲剧,叔本华说:“我们在悲剧中看到的是难以言说的苦难、人类的悲哀、邪恶的胜利、机遇的恶作剧以及正直无辜者不可挽回的失败。”尼采说:“悲剧引导我们走向终极目标,即妥协。”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在其著作《现代悲剧》中指出:尼采与叔本华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真实的。尼采所改变的不是叔本华关于生命悲剧性本质的理解,而是随之而来的悲剧定义。对于尼采来说,我们必须做出的反应是积极的,是一种人类不可避免的苦难中获取的悲剧性快感。悲剧行动展现苦难是为了超越苦难。按照尼采的观点,悲剧戏剧性地表现冲突,然后在一种更高层次的和谐中使之得到解决。
以爱情剧的眼光来看沪语话剧《繁花》,它似更应该是一出风俗剧,而不是悲剧。虽然剧中的三对男女都有各自的悲剧故事。
也许拿《罗密欧与朱丽叶》来比照《繁花》终究是不公平的。
“真爱总是敌不过愚昧”“死亡是爱情的至高高潮”。—莎翁在剧中对于世俗的批判与对真爱的讴歌形成巨大的抒情张力。
朱丽叶假死,罗密欧真死,朱丽叶最后殉情—死亡将激情一次次递升。两大家族因为这一对年轻人的死亡而消除积怨。死亡净化了苦难,爱情的意义无限升华。
蓓蒂是阿宝的初恋暗恋。蓓蒂在话剧《繁花》中以不出场的方式出现。她是阿宝的童年记忆,但仅仅是记忆。她是阿宝避世的、自卫自恋的好看的武器。蓓蒂只是阿宝叙事的进入方式,构建性格的重要成分,打造性感的精心花式。也许是刻骨铭心,也许是曾经沧海,但我们在舞台上见到的,只是阿宝的“说”,他没有去找失踪的蓓蒂,他甚至没有问一下熟人们她的影踪。还是由别的人告诉他:“蓓蒂变成了一条鱼。”
一个没有行为力的情种。他甚至没能深究变成鱼的故事。他的冲突只发生在体内,或许是想要遗忘与遗忘不了的冲突。他与环境的冲突等于零。
在温柔乡里可以遗忘世事的小毛与银娣,一度也是可以抵抗现实的同盟者。第一波的风雨一来,即刻缴械投降。小毛转身而去,银娣乍然变脸。他们都选择了生存。虽然样子不好看,但生存的意志要紧。阿宝选择的,也是生存。生存比毁灭更本能的话,一切的“投诉”便只是“自我怜悯”—而“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姝华,《繁花》最重要的女主角。能够大段背诵叶芝诗歌的才女,青春期的光华昙花一现陡然心惊。远离,远嫁,失语,疯狂。爱她的沪生,你做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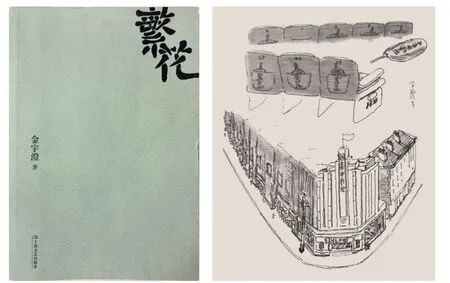
《繁花》封面及插图
舞台上最后一个场景:沪生坐在邮政车上,恶作剧,从麻袋里与工人一封封抽拿、拆开他人的家信。他忽然双眼刺痛泪水涌出,因为他想起了姝华在插队吉林半年后给他的信,也是唯一的一封。“人已经相隔千里,燕衔不去,雁飞不到,愁满天涯—人和人,无法相通,人间的佳恶情态,已经不值一笑,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我就写到这里,此信不必回了。”
连回一封信的可能也不给予你,对于你的绝望已经到达什么地步了。深知无力,不寄希望。若此绝望,才可能让人在一块陌生之地铁定地生存。
仍是生存。生存大过于一切。
若此不顾心愿的生存有意义吗?或许说意义也是一种奢侈。逃生,偷生,生然后有新的希望?“最有价值的东西与最无可挽回的事实于是被人置入一种不可避免的关系和冲突之中。”雷蒙威廉斯这样说,“将这一特殊矛盾抽象为关于人类存在的绝对事实意味着固定并且压制那种关系与冲突。这样,悲剧就不再是一次行动,而成为一个僵局。宣称这个僵局是悲剧的全部意义就等同于将一个受文化和时间制约的局部结构投射到普遍历史之中。”
有冲突吗?没有看到什么冲突。连冲突的些微挣扎也没有见到。只有悲剧女主角的自我放逐,自我解构,自我了结。若是一出女性主义的戏剧,倒是悲凉到家的悲剧了。
也许这样去想,便没有必要拿“罗朱”剧来比:沪生与姝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在姝华插队去吉林之前有过的肌肤相亲,匆匆,不承诺,可以让沪生选择逃避无需执着。两个人没有罗朱那样一见倾心的强烈震撼。但是对于传统的中国人,不习惯强烈震撼而习惯压抑的中国人,沪生与姝华的“离别之吻”是不是已经够厉害了呢?
除了蓓蒂的缺席,《繁花》中的女角比之男角,在感情生命上,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更负责的态度。至少,她们跟自个儿“冲突”了。剧中的男人们,逃得迅速,避得及时。小毛靠妈妈解决“后患”,阿宝被北方女吃定,沪生呢?索性面目模糊。与女朋友,与父母,与违和的环境,连冲突的发令枪都没有听到,就阉了。
也许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剧作者无法超越原作无法超越时代。蓓蒂若是活着,不见得有什么情场上的好下场。石俊先生建议《繁花》第二季可以在蓓蒂身上做文章。以为然!敢爱敢恨,或者恪守宿命,自可有一番演绎天地。
《梁山伯与祝英台》,可谓是中国式的罗朱剧。区别就是梁山伯是病死的。仿若是中国式情人的暗喻。
契诃夫说:戏开场之时,挂在墙上的一把枪,在戏结束时,要派上用场的。这是古典主义的严谨。
《繁花》有枪吗?
小店,小名,诗歌,信……
最大的枪,应该是它—沪语,上海话。
“我爱你!”—如此表述需要换作普通话的上海方言,究其实质,是无法演一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感情永远不是这个城市的命脉。浪漫,仅仅用于法国梧桐的被讴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