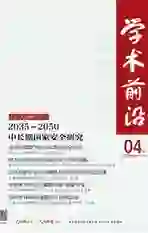海外利益保护与生态累卵性
2018-06-11周雷
【摘要】 如果“安全”的主体逐渐从传统的政治主体,转移为不断分化的个体和社会化集体,那么“安全观”首先应该是一种对社会新兴主体、个体、群体的深刻觉察。如果国家治理的工具逐渐和科技结合,当国家在使用科技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科技还可以不断消解原有的权力主体,并产生新的治理对象和权力中介形态,如此视角之下,国家安全不再是基于地理主权疆域,而是没有明显内外界域的新安全观念。灾害频仍的人类纪世代,人类正在目睹一次生物大灭绝和人工智能的崛起,它预示着一种全景化的危机型社会的来临,世界政治权力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全球政治的新游戏规则正在重新生成;同时由于人类不断干预自然和人文的界限,尤其是不断通过科技创造新的能动性赋予方式,国家总体安全于是直接体现为对不同真实程度的安全护卫:现实安全、超现实安全、模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安全。
【关键词】累卵性 积极安全 消极安全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05
导言:剧变的安全整体图景
微信、阿里巴巴、人工智能、百度无人驾驶、区块链技术、猴克隆技术,这些发生在国内的部分技术词汇罗列预示了一个基本的治理新场景:由于技术的渗透和干预,技术使得传统的亲属关系社会解体了,使得人类对于不同的物体和技术集合产生了情感,并通过它来传递情感,情感的亲密性和应用的舒适便捷性逐渐再衍生出新的“类人”亲属关系,也就是本文所称的kinship humanoid。同时因为技术重新组织了社会,创造了新的层级,在原有的差序格局社会上重新排列了新的顺序,这种技术导致的人类关系束(enclaves of relations)整合,使得所有传统型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集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发生了根本性革命变化。
安全仍然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提出的,而时下的技术革新和超人类技术形态生产已经在催生“新人类”和“介质化半人”(mediated humanoid),因此,我们讨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落实首先需要进行本体论导航设计(ontologica lnavigation)。
考虑到国际社会的技术形式发展、社会形态变化、权力斗争形态变化、权力主体变化,国家新的总体安全观,如果没有本体论意义上重新认识和再评估,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可能再也无法修筑物理的藩篱、堡垒来保护安全,无法找到保护的主体和入侵主体,无法理解侵入和占据的方式,无法预示风险的远期性。在“谁通过什么试图如何影响何种对象并产生何种安全/风险效果?”这个有关安全的基本问句中,几乎所有主体都在发生重构。
问题的提出:何为安全?险在何处?
要让安全总体化并可知化,最好先界定安全。而如果要回答什么是安全,最好的答案是重新定义风险和危险,现代社会有时候把所有不确定性都当成风险和危险,这个过度防御机制本身就是危险的来源。把所有社会现象和安全分析场景看成佛教式的“诸行无常”坐以待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试图穷尽所有手段来改造所有无常,或者让一切“照常”进行,也是不科学的。
现代社会对于风险(risk)和危险(danger)的讨论很多,有一个偏社会学层面的风险或不确定性概念讨论较少,那就是precarity (precariousness),笔者把这个概念翻译成“累卵性”——正如中文“倒悬之危,累卵之急”所达之意。累卵性有时候是表显的,有时候则存在隐蔽性,但是无论如何,社会的累卵性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破坏势能,同时还对应存在着结构化的倒悬,一旦该机制被激活,它多半不可逆,并产生重大的灾难影响——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
安全在造词表意上是“护生”的,它守护的核心是生命和可能性,因此笔者认为对安全观的首要检讨在于分析现代社会中“生命”本身的变化,也就是life itself被高度技术化、干预化、工程化了,现代科技的进步将所有要素都利用起来,用于将生死转化成一种永续的再生产,以此来换取财富、能动性、价值、资源,这是一种“泛生命化”的工程社會学和生物经济学(global biological economy);在这种广谱的泛生命化工程和全球经济动员过程中,技术将生命转化成一整套信息束,并把这个信息生产机制和最前沿的DNA分子干预和分子模拟结合起来。应该说,这才是我们讨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场景——当然前提是,我们仍然希望通过守望新风险来长时间守护传统型、固定疆域、固定治理对象、固定权力主体、攻守安全模式型的传统国家。
作为源头型的生产力和繁殖力,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女性经常被视为一种“二度自然”,母亲也因此和大地、自然、坤德联系起来,在讨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突然引述女性,原因在于接续上面的讨论:当生命本身发生变化,女性和母亲是否还是一个社会繁衍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源头?在讨论安全问题时,有必要提问国家的女性、母亲们、孕育生命的物理源头是否安全?正如前面已经简要描述,技术创造生命主体,而非简单成为工具;技术创造自然力,而不甘心被物化;技术改变社会组织方式和亲属关系,技术因此整体革新了作为现实的身体(reality body)和作为社会的安全治理情境(social governance scenario)。
只有厘清上述问题才不会形成前后矛盾和自我否定的安全守备观念和现实操演模式,我们能吸取的最直接的简单教训是:如果要维护传统国家形制和传统安全观,那就要对传统安全的主体和本体进行守护,尤其是对技术进行干预,对技术克制使用;如果想创设新的国家安全观和总体型超现代安全观,或者我们觉察到“敌人”不再是传统的某个具体国家和组织,而是某种现象和状态,我们需要寻找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安全获得模式。毕竟,保护生命、保护生命体、保护身体、保护类群是四种完全不同的安全保护模式,尽管某些层级存在交叉。
风险/危险的几种新类别
自然与人文,人类与人机对话,人类与物质交换,人类叙事与人类实践,这四种关系是传统型国家总体安全的核心要素。
自然和人文较好理解,那就是在完全不干预自然(原生态)、半干预(类生态)、纯粹人造的二度自然(次生态/人造生态)这几类关系中,我们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主体该设置哪些界限并创设何种生态治理模式,避免善始害终。
人类主体和人际对话则是权力和话语作用于身体的反应,身体和技术的互动最终对生命主体本身产生革命影响。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人的能动性是否需要让渡,并有条件让渡,同时设计出的能动性可以随时收回来。当然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人的核心创造、知识生产、本体生产是否需要通过人际互动的方式来辅助完成,而不是通过机器和智能模拟中介化?
人类与物质交换的问题,则由于发展不可逆,人类利用物质的有限性和条件性,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势必造成一部分人类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造物和模拟物质,甚至直接从概念到物,3D打印、仿生材料制造、生命模拟、基因干预(manipulation)等科学技术现象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进行更迅速的人类与物质交换和转化,其核心中文概念就是“变”,但是人类的“三十六变和七十二变”,已经成为七千二百变,这种概念源头意义上的“创造性弥散”正在产生严重的生态效果和治理后果,当然也会影响传统意义的国家总体安全。同时,在上述三种情形当中,都会伴随着观念、知识、伦理观念的生产和再生产,我们通常会在一个假设前提下进行上述的革命尝试和冒险。在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中,他人或异国的错误经常被理解为本国和本族的机会,如果不能消灭风险和危险本身,让它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分布,甚至将这种风险分布和导入变成一种全球化风险分层设计(globalizing stratification of risks)就成为国际博弈的常见玩法,而这种游戏的核心规则是“让对方自以为是”,让对方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在知识意义上,让对方“不知其所不知”更重要(unknow unknown)。把人类的生物学特质变成政治策略和战略决策的主体性工具,并通过具体的反应机制来实现,这就是福柯生物政治(biopolitics)的核心内涵。
这种生物政治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为了获得一种事先规划的发展预见和成果实现,要对所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力的要素进行驱除和割裂,也就是事实创造一种“无菌环境”——或者说避险机制。为了能获得孙悟空“火眼”判险、预险、除险的能力,生物政治必然导致人工智能的过度应用和超边界应用,最终将“物”主体化,物“能动性”增强,所以在没有完全获得“无菌式”安全之前,存在被认知主体代偿和主体弱化的风险。当我们寄希望于机器愈发理性,物体产生能动性时,我们同时开启了一个新的总体安全观黑洞,在这个依赖中介化、虚拟化、智能化、效能化存在的“生物政治”区域里,蕴藏着更大的安全风险,并同时触发了新的超现实、增强现实安全观。生物政治和生物治理(bio-governance)如果不克制,将可能出现“基因难民”——越呈现人类认知模式、人类情感模式、人类伦理模式、人类美学模式的基因将被淘汰。我们获得的是另一种“转基因式创造性”——或者说“创造性绝育”:由于长期的认知代偿、能动性让渡和物化再生产,某些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基因、人类类群、人类个体被整体驱逐成为基因难民。与此同时,由于排斥所有的不确定性,或者将所有不确定性视为风险,它使得一个社会的创造力整体削弱,创造的原始本意在于突破边界和开放性,甚至可以说创造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意外,而在这种生物政治概念下,只有某一种或某几种创造效果满足初始任务目标时,创造才能出现——创造因此变成是一种条件满足下的知识再生产。如此一来,创造不是灵光一闪(lightening of genius idea)而是“驯服效能的再生产”(domestication of innov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argeted creativity)。
最后上述三个方面都会作用到人类叙事和人类实践的关系讨论上,生物政治开始会再造自己在社会和人类中的意义和地位,并不断创造被下一代持续传承和记忆的表述和叙述。如果上述三个方面是“生物政治”在改造人类硬体的话,这些叙述和记忆就是在改造人类的软体——当然如果我们仍然相信传统的国家总体安全观在维护三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东西:人、生命、家园。
与传统攻城略地、占据资源、灭絕文化、创造文明范式的安全观念1.0不同,现代治理语境和生物政治思维泛滥的社会实际的治理情境是安全观念4.0,甚至是“抗原式”安全场景(anti-prototype),也就是不断攻击原式,它的危险之处在于让人类自愿身处危险和坐稳奴隶的时代,并甘之如饴。在这种情形下的最大外来风险以及瓦解敌人的手段是让对方自动将有益物质甚至遗传物质识别为异类和杂质,并自动产生排异清除反应。因此,描述安全图景,远没有重新描述和建构敌人更重要。
生态风险例证:应用场景分析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尤其是泛第三极区域,因其与河流源头、冰川、生物多样性、多元族群互动、宗教文化圣境等因素的密切关联,它成为举世瞩目的生态监控区域。然而,因为人类活动区域持续扩大、经济发展失衡、低科技发展水平重复开发、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泛第三极区域以及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在经历极为严重的生境退化和生物灭绝,如何避免中国在这一区域的投资和国际发展擘划与负面的生态环境退化联系起来?如何阻止部分国际社会利用大背景下的生态退化与同一时间的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巨量海外投资联系起来,以此来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通过科学研究、科学设计、科学施工、科学传播探索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越式发展的新思维和新工具?以上问题都迫切需要对“一带一路”重大工程和重点国别旗舰物种多样性进行数据基础研究、保护策略设计和科学传播实施。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国传统型总体安全的获得和表达需要对沿线科研、建设、文化互动的等多个环节进行设计。
自然与人文。如何恢复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何避免一些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精神运动打着原生文化的旗号死灰复燃?自然的退化必然导致一种文化纯化、自然圣境化的原教旨主义风潮,如何克服这种精神势力的抬头?
人类与人机对话。“一带一路”存在诸多工程类和基础设施类项目,甚至出现一些跨越式经济和科技合作项目,特别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全球智能物流系统,这些项目在经济上都是可行的,但是其存在宗教、政治、民族意义上的回火,谁来设计这些项目的自检模式?
人类与物质交换。在重大科研项目、民生项目、基础设施工程项目、能源项目设计和施工上,还要注意人类之外的生命权,避免项目成为纯粹效度表达的人类中心主义——甚至人种中心主义;我们一定要设计机制让善意、资源、能源重新回到自然系统和底层文化系统,否则这种过程不仅不可持续,还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
人类叙事与人类实践。在重物质轻文化,重工程轻思想的整体投资和跨文化互动中,我们容易忘记,真正让我们呈现人类创造性的源头就是文化和思想;基于叙事和文化记忆的民间知识生产是所有后发社会实践和精神生产的基础,我们因此要强化文化的深度学习,同时进行零物质损耗的概念生产、文化互动、意识流动,而非一切都以物质、利益为鹄。
要实现上述研究目标,亟需对下列任务进行排序、梳理:(1)全球气候变化事实、成因及多尺度作用对“一带一路”重大工程区域以及泛第三极区域的生态影响过程和机理;(2)“一带一路”区域海外国家重大研究和数据出版监控,第一时间了解西方发达国家和项目所在地国家的大型工程生态影响评估和可预报分析,针对重要全球变化敏感区基于旗舰物种变化/退化所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影响风险评估;(3)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人为气溶胶排放对泛第三极区域和“一带一路”重大工程区域的案例影响研究,基于旗舰物种研究的生物圈结构、冰冻圈、粮食安全、海洋环境、气候灾难、人类疾病控制影响评估、信息系统管理、综合风险防范评估;(4)基于学科交叉数据、综合观测、数据集成研究、高精度遥感原理研究、多源观测数据的“一带一路”重大工程旗舰物种景观风险预测和应对共享数据库研发。
在上述目标梳理基础上,我们才能实施如下研究和数据应用研发,以及后发的建设项目设计和施工:(1)“一带一路”旗舰物种综合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集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于生物多样性中心、城市发展、能源利用、污染控制、反社会运动、人工智能负面影响、发展伦理、社会阶层变动等跨学科、跨界域的数据集,形成可以支持决策和科学传播的国别风险预警和干预系统,为未来地球计划和气候变率及可预测性研究计划等国际计划提供“旗舰物种”和“旗舰问题”分析工具;(2)支持国家气候中心,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灾害风险管理等标志性工程,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针对气候灾害性(vulnerability)和本土适应提供旗舰物种多样性数据模型和数据同化技术服务,甚至开启“旗舰物种生态预报”“一带一路重大工程生态风险预报和预警”等特色知识服务;(3)旗舰物种监测、旗舰生态干预工程、旗舰生态设计系统设计工程,基于上述两项基础设计,为中国“一带一路”沿线重大工程的生态优化、减缓和适应全球变化、国际生态合规能力、中国外向型投资可持续转型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服务、知识融合解决方案设计。
最终形成中国基于旗舰物种研究的“一带一路”重大工程生态影响力优化数据集/库,自主品牌的旗舰物种生物多样性预测和评估系统模式开发,建立旗舰物种生态多样性的信息综合模拟、实验模拟、案例分析模拟、决策模拟的公共平台和“一带一路”重大工程大数据管理平台,实现数据、研究、设备、模型、软件、资料的高度共享,基于旗舰物种多样性研究、风险研究、总体安全设计研究培育一批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有关的“一带一路”国家科学研究群、科学传播群,特别是内嵌式、外向型、协作型跨国生态预警和问题应对机制。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生态治理,及时把握基于旗舰物种数据的国际气候谈判新策略、政经互动新策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经济可持續发展和生态友好型投资转型提供强有力科学支撑和传播支持。
科技与生态如何结合:减少中国海外安全的累卵性
2018年1月,笔者在巴西、阿根廷、智利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查,通过进入巴西大豆种植区、中国锂矿投资地、中国投资港口、中国经济投资活跃的旅游区域观察和采访获得现场知识,并进而思考中国与拉美互动的战略。与一般的调查不同,采取的人类学的“多音位”调查方式,特别邀请了巴西土著夏湾提人(Xavante)拉法约先生作为巴西本土声音的代表人,他的祖父是巴西政治历史上的第一名国会议员,他已经成为巴西马托格罗索区域土著文化保护与巴西利亚土著权益运动的协调人。
在与马托格罗索的企业家、政府代表、农民代表讨论的时候,我们提出另一种发展思路供商榷,也就是如何开发巴西的“本土叙事”这一“精神特产”:巴西有着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生态多元性和地貌多样性,这些多元地貌还有第二层多元性,那就是历史、文化和族群多样性,殖民历史、本土政治、土著文化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文化过渡区和生态岛。
在植物利用和生态知识整理方面,我们特别介绍中国和巴西可以在中国科学院框架下进行亚马逊植被的深度研究工作,例如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在环喜马拉雅地区的民族植物学、种质基因库、菌物学研究方面与巴西就存在诸多共同性,中巴在共建植物多样性与资源可持续利用联合实验室、分子生物多样性实验室以及植物分类与资源可持续利用实验室等方面存在重大科学、经济和文化价值。此外,中国和巴西还可以在西双版纳的纳板河流域热带雨林以及巴西亚马逊雨林进行生态多样性和文化传承比较研究。
通过谈判我们建立了一个高校、企业、自贸区、设计师、民间组织构成的雨林工作组:其中具体方法是我们获得与马托格罗索的大学合作的机会,在位于热带雨林核心区域之一的巴西马瑙斯自贸区和上海自贸区发起成立一种文化对接机制——雨林城市文创机制,将巴西和上海的文化、物产、生活方式、创意产品渠道打通,并通过中巴创造、巴中互动、“土洋结合”和手工科技集成方式创造独特的文化创意产品,孵化独特的第三产业集群,然后通过这个集群来合理分布开发区、农业区、景观区、文保区、生态敏感区的复合产业形态。
在阿根廷考察苏斯克斯(Susques)周边浩瀚的Salinas Grandes大盐矿和Adlante锂矿区之后,笔者采访了胡回省的矿业部主任,并和盐湖区的工人进行了整整一天的现场考察和访谈。我们加深了本地人有关资源“生态魔咒”感受——南美当地底层民众已经对“人类与物质交换”“投资破坏自然和人文平衡”问题存在负面评价。卤水锂矿的开采会逐渐透支盐湖水体和周边湿地的生态承载力,这还不包括提炼锂矿需要增加的各种具有强污染的化学物质。
锂与电动车、蓄电池、手机、智能装备密切相关,这个指向未来的能源开发,却经常和民风淳朴、民族众多、保守落后的区域连在一起,它形成了四重困境:自然人文困境、人机交互困境、人类物质交换困境、叙事与实践困境。具体来说,这些锂矿开采破坏的自然和人文平衡,在帮助其他国家智能化的同时,本土深陷后发展和后现代的贫困;电子产品、投资者、旅游者的涌入,不断破坏当地原生文化的生境和社会关系组织模式;本地输出锂这一贵金属,但是并没有输入重要的思想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相反,本地的传说、文化传统、风俗、仪式等基于传统叙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稀薄,社会开始贫富分化,形成了典型的矿业城市综合症。
另一方面,南美又是实现中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区域,也是和美国产生直接物理上遭遇的文化场域,在这个美国后院进行经济和文化互动,一定要超越美国思维和美国模式,寻找中国和南美的文化共同体,特别是科技与生态结合的发展模式。
首先是建立高地文明(highland)协作区,在前西班牙殖民时代,南美有过辉煌的印第安文明遗产,这些文化保护和生存经验非常值得在现代社会背景下进行再阐释和再挖掘,我們在阿根廷看到了许多区域博物馆都在进行高地文化的考古和公共展示,对此我们认为还可以比较不同区域的高地遗产,例如喜马拉雅文化圈中的尼泊尔、中国西藏、印度高地的高地文明协作模式。
其次是旱地耕作和天文型建筑模式比较文明试验区的概念,通过比较和转移来自以色列中东地带、中国新疆、北美荒漠、南美干旱区的旱作型文化、聚居、生产、物产模式,创造多种知识融合的机会和产业发展机会。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就是按照一个飞行器模型设计的前瞻型景观社会,尽管这些设计背后存在现实应用的缺陷,但是这些低密度建筑、丰沛植物、功能区划模式的确产生了一定景观和现实效果。对于南美的这些生态脆弱、资源丰厚、地貌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区域,应该研究设计出新型的天文型建筑城市和未来型城市,与巴西利亚的概念型城市不同,这些矿区要有“况味”就需要把城市的本体设计成一种未来观念,而非简单美学形态。
在我们调查阿根廷苏斯克斯盐湖区期间,当地土著正好在庆祝圣玛丽宗教节日,来自周边和部分偏远区域的土著都将自己的教堂圣像抬到当地,进行环绕村落的仪式,时间长达一天。这类文化在南美的许多矿场集中地很普遍——矿区往往就生活着土著,但是目前的矿产开发往往与土著较少合作,更多体现出一种对立和竞争关系。如果能够依托矿区设计前瞻型、未来型、理念型城市,通过标志性、功能性的建筑和生态布局,将土著文化与未来城市设计结合,可以产生另一种新型盈利形态和文化传承模式。
最后是未来型天文型城市的设计和知识研发,南美的地理趣味性在于他们的地理有一种超现实的永恒性,那些外星式地貌不仅是南美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也是现代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外太空人类学、灾害地理学、未来超级城市的理想试验地,如果地球的气候变化不可逆,人类整体的趋势是向更为精细化、精确化、科学化的仿生学和天文学聚居形态发展。而在这些奇特生境进行新型城市规划、新型建筑设计、新型大学知识形态设计、跨文明比较和知识协同,就可以产生极为独特的中国—拉美科技经济体和文明互动的机会。
理论小结:远离累卵性社会
累卵性社会是对国际学术界有关Precarity概念研究的深化(国际学界有人已经把“无产阶级”proletariat改为“累卵阶级”precariat,以勾勒出它作为一种现象和集体的重要性),它的核心是社会脆弱性和个体危机感受,它表现为若干社会规程在剧烈社会变化的消失,这些社会公序良俗和行为约束规程与本文讨论的四重困境密切相关。由于个体不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物理性、身体性、社会性个体存在,而是需要多重条件满足才能成为个体,它使得社会的风险性和累卵性大大增加。国家的总体安全观,如果脱离个体和集体来讨论,它虚泛而无意义,这里所说的安全有积极安全和消极安全,所谓的积极安全就是不断重新理解安全的理论原意、社会意义和实现路径,而消极安全是固守在完全确定性、固定理式、程序化范式影响下的矛盾式安全观——无论对方是否用矛,都以盾牌来抵挡,无论危险是否来自外部,都持盾向外的机械安全思维观。
如果累卵性社会是通过瓦解个体、瓦解边界、混淆伦理、混淆群我的方式来进行的,它就不再局限于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这些具体门类化、条块化的安全。我们更重要的是保护主体安全和文化本体安全。
累卵性社会的分析进路是基于权力结构、社会变迁、经济互动、组织嬗变等方面的剧烈变动而作出的,其核心是判断和守望那些未知型风险,所谓未知险为何物,安知安在何处?权力总是为给不同个体和群体以保护的权重,如果当权力将更多的权重给予不同的物和技术,甚至把这些物化的中介当作核心安全时,我们就变成了一种条件化生存的社会(conditional society),那就带来严重的社会累卵性。传统的安全观首先在于界定安全区、危险区、安全线、危险线、安全点、危险点这些与空间和时间有关的要素,让身体对空间和时间有深刻觉察是判断风险、预警的重要前提,如果将这种综合分析、判断、预警和应对的能力交给一个代偿的中介——哪怕是我们以为能控制的技术、物质、材料手中,那么都创造一种依赖性和条件性,这就是累卵性的根源。
由于对任何不确定性的不信任和排斥,消极安全观思维下,人们容易通过控制“预犯罪”“前犯罪”“潜犯罪”的方式,把各种不确定性扼杀在萌芽当中,这就造成了社会的“无菌化”——无菌化是实验室社会的根本特征,它的代价是社会活力的丧失,而活力、动态性,构成了生命的前提,它在这个意义上是违背安全理念的。我们需要的安全是积极安全、动态安全和活力安全,而不是“涅槃寂静”。
另一方面,对于能源、物质的过度需求,并把对能源和物质的操作当作社会的正常态、活力、强大来看,这造成了我们社会对某些技术、物质、中介的高度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会不断叠加,进而形成严重的条件型社会,它是累卵性社会的重要表征。一箪食一瓢饮,人不改其乐,才是具有人类创造力和主体属性的特征,通过激发内在的稳定感和平衡感来获得安全是积极安全的不二法门。
消极安全观存在对自由意志和未知个体的莫名恐惧和担心,于是它激发一种内控而非外防的安全保护机制,这和基因操控的思维是一致的:内在基因控制,比控制显性的表征要重要得多。因此,自我控制、一级控制成为最重要的消极安全获得手段。
以上的累卵性因素将造就低创造力、低繁殖性社会(infertile society),权力高度依赖具体的物理介质和中介技术团体来运行,如果国家不能完全控制这个中介技术团体,就有可能成为代理型和过渡型主体,安全从内向外突破,而非从外向内攻入,此时的总体安全就无从谈起。
参考文献
Judith Butler, 2008,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Sarah Franklin, 1997, Embodied progress: A cultural account of assisted conception.
Sarah Franklin, Celia Lury, and Jackie Stacey, 2000, Global nature, global culture.
Michel Foucault, 2009,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周雷,2015,《东方的消失和马航现象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