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认出《金瓶梅》中那些器物
2018-05-24徐梅
徐梅
扬之水将文史材料、雕塑绘画,及她在各地博物馆所看到的实物比照分解,读后令人,阮然大悟,原来“满冠、掩鬓、围发、分心”都是头饰的具体名称,依照插戴部位的不同而得名,至于“广寒宫”、“桃源境”、“荔枝丛”,以及“观音盘膝莲花座”,也都是当时时髦的纹样,并无半句夸张比喻
名物学家扬之水今春连发三本新书——《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李煦四季行乐图>丛考》,以及《物色:金瓶梅读“物”记》。这也是她十多年来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奔走于国内外博物馆、打通案头之诗与有形之物的一个学术成果“特展”。
文雅图精,两相对照,乃读者之幸。对她来说,却是案头工作一分不能减少的同时,又多了四处看展“物色”实物的线下工作。
“物色,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四处寻找,一边阅读图录,一边到博物馆向实物求证我的阅读判断,这样做下来非常有收获,体会到博物馆参观的种种好处。”
二十年来她和老伴儿从国内到境外,从东南亚到欧洲、北美,跑了许多博物馆,扩展见闻、搜集资料。她说自己从来不赶潮流,“但是这几年开始流行起来的逛博物馆,我的确是走在了潮流前面,稿费和退休金都砸里面了。”
“这是什么?叫什么名字?什么用途?”揚之水说名物研究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她从文物学家孙机先生那儿师承的工作方法,她希望读者也以此来检验她的研究,且能够更多认识、尊重名物学研究的知识含量和学术价值,“我经常觉得有些读者其实没明白我在做什么,他们的注意力放在我的文字或者我所挖掘的古人的风雅生活上了,但这不是我工作的真正价值。”
“诗和物本来就是水乳交融的依存状态,但这些知识在历史的长流中分散了”,“定名与相知”,是她为自己的研究制定的目标。
对历史文化遗存的认识,需要从命名开始,此谓“定名”。定名涉及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多个学科的信息和知识。“相知”则是在定名的基础上往前一步,明确某器某物当时的用途与功能,在“文”与“物”或“文”与“史”的碰合之下,让某个时代的“诗”与那个时代的“物”“重新聚拢”,“完全融合在一起,能够互相说明,甚至是不用说明,因为它们原本就是一体的。”
每一个聚拢的瞬间都是一束光,照亮已经消逝却又确定无疑的某个生活场景,“细节历历,伸手可及”,考证解惑,她以这种方式在诗与物之间游走,重温古典,“充满好奇,充满激情”。
“真好比是明代首饰的一个小型展销会”
《金瓶梅》里的金银首饰,是扬之水名物研究的入口,当年她写给孙机先生的第一封信,就是请教关于鬏髻的问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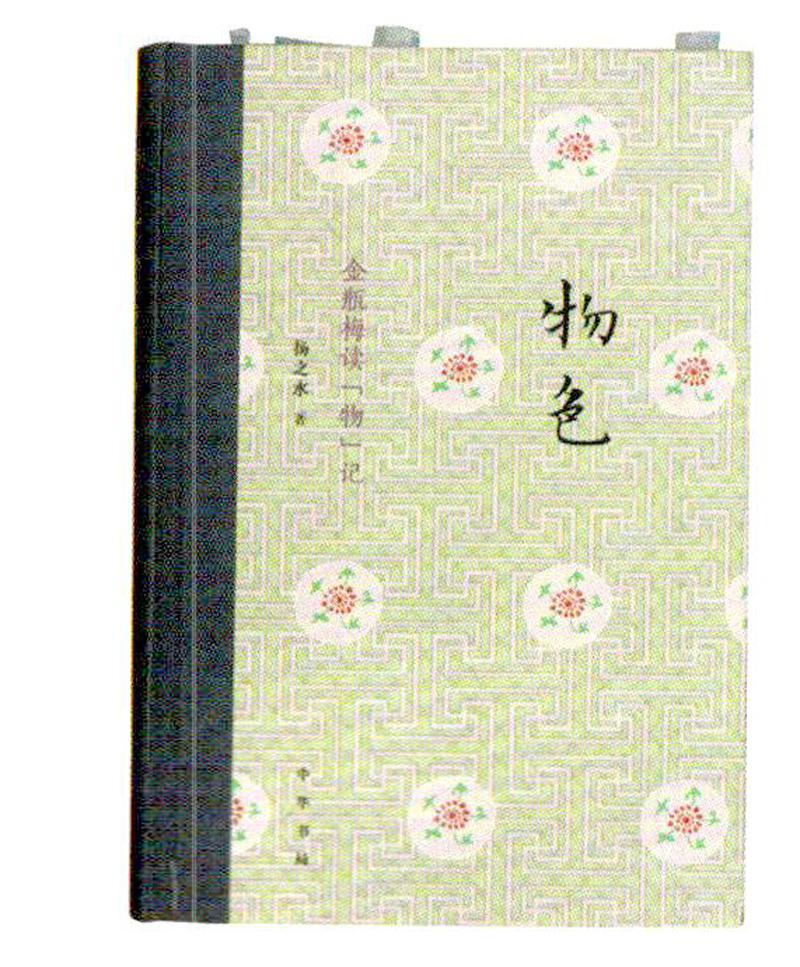
按照孙先生的要求,每研究一个问题,就要囊括所有文图资料,做一个相关专题的资料“长编”,“过去都是搜集整理出来,一个专题放进一个大牛皮纸袋子里,现在家里还有好几箱。后来都是电子文档了,调用的时候更方便,但案头工作的方法一直没有变。”
她的家也一直没有变,只是又添了一整面墙的书柜,脚上还是那双久洗泛黄的老式白球鞋,八年前拜访时她便是穿着这双鞋来帮我开门的。“还是有变化的,以前每天早晨3点半起床,现在迟了些,4点才起来。”
她惊人的产量源自专注和自律,早起打坐一个小时,便开始案头工作,早餐后写40分钟小楷算是小憩。从不午休,不看电视也不遛弯儿,因为“没那需要”,晚上9点半准时上床休息。“不出去看展览的时候,在家都是这个作息。”扬之水这两年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古代金银器史》的准备和写作上,计划用两三年的时间完成。
《物色》是她挤出时间完成的一本书,“这个是我名物研究的入口处,进去以后眼界境界就越来越扩大了,随着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初始我感兴趣的这个点还始终保持着兴趣,也就不想轻易放掉。”她积累了一本厚厚的《金瓶梅》名物研究长编,《金瓶梅词话》中提及的不少物事,她此前在《奢华之色》第二卷《明代金银首饰研究》以及《中国古代金银首饰》中都曾辨析研究过,手上的材料完全可以出一本图文并茂的词话名物词典。
但她向来不喜欢做别人做过的东西,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多年前出过一本《金瓶梅鉴赏辞典》,其中已单列了《陈设器用》,“我可以做得更细更全,再加些图,只是这样也没什么意思。”
《金瓶梅》名物研究是她“心爱的一个题目”,这一回她想要从一个自己思考得最为成熟独到的切口来呈现,“做得精一点儿”,聚焦在与叙事关系最密切,“也就是贯穿故事,跟着故事走的这些物事上。”
初衷仍然是要“解决问题”,“这也是孙先生跟我说的,他说,‘如果你这一篇文章没有问题,就只是一个叙述,你不用写,这没意思!这种文章谁都能写。勤于求知,独立思考,这是我跟老师学到的,我每一篇文章都是要解决问题的,哪怕一个很小的问题。”
“物”与“色”的关系,即一器一物与小说中人物命运草蛇灰线的关联是她这次要解决的问题,她在《物色》小引中写道,“以物色串联情色,是《金瓶梅词话》的独到之处,运用之纯熟,排布之妥帖,中国古典小说中几无他作可及。如果说作者的本意是在‘物与人的周旋中宛转叙事,那么数百年后我们得以借此辨识物色,进而见出明代生活长卷中若干工笔绘制的细节,也算没有辜负《词话》作者设色敷彩的一番苦心。”
《金瓶梅》研究汗牛充栋,自然不曾忽略小说中物事的妙用,但那些繁杂的器物究竟是何色泽质地纹样细节,没有专业知识储备是难以道明的,且看《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回——
那来旺儿一面把担儿挑入里边院子里来,打开箱子,用匣儿托出几件首饰来,金银镶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但见:孤雁衔芦,双鱼戏藻。牡丹巧嵌碎寒金,猫眼钗头火焰蜡。也有狮子滚绣球,骆驼献宝。满冠擎出广寒宫,掩鬓凿成桃源境。左右围发,利市相对荔枝丛;前后分心,观音盘膝莲花座。也有寒雀争梅,也有孤鸾戏凤。正是绦环平安殂珊绿,帽项高嵌佛头青。
扬之水说这一段“真好比是明代首饰的一个小型展销会”,“这些看似眼花缭乱的描写,辞藻之外,其实夸饰的成分并不多,且几乎都能举出与之对应的实例。”
扬之水当年不明白的“鬏髻”,是明代女子戴在发髻上的发罩。《物色》里《金丝鬏髻重九两》一文中,扬之水从李瓶儿拿给西门庆的一顶九两重金丝鬏髻起头,双线交织,一条线准确地分解鬏髻、九凤钿的质地、纹样及全套头面的插戴方式,另一条线顺着小说叙事聚焦“金”“瓶”“梅”三个女人与这几样物事的关联。
熟读《词话》,古代金银器多年的知识储备也了然于胸,扬之水落笔精准迅捷,仿佛以“鬏髻”为关键词,一键搜索,就从第二回推进至第九十五回,在《词话》堆积的海量日常场景中定格一个个瞬间——
第二回潘金莲“头上裁着黑油油头发鬏髻,口而上缉着皮金”。及至第十一同,她做了西门庆第五房,“家常都戴着银丝鬏髻,露着四鬓,耳边青宝石坠子。”
二十回,李瓶儿听西门庆说上而几房只有“银丝鬏髻两三顶”,便觉得自己那顶九两重的金丝鬏髻太过炫耀,“我不好戴出来的。你替我拿到银匠家毁了,打一件金九凤垫根儿,每个凤嘴衔一挂珠儿,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金镶玉观音满池娇分心。”潘金莲拦着西门庆,想要占些便宜,“把剩下的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凤甸儿。”
及至第九十五回,月娘从薛嫂子口中听说春梅要打几样首饰,其中就有一件前文所述的“九凤钿”,“当此之际,先前要打九凤钿的瓶儿和金莲都死了,月娘也成了寡妇,风流云散,门户萧条……”
她以丰富的文史知识和实物图片穿插其间:九两重金丝鬏髻之罕见、观音满池娇纹样之流行、九凤甸儿之奇巧,诗物互证,非常清晰。
展示一器一物的同时,她又提醒读者同到“物与色”的关系上,“《词话》作者虽然惯用簪钗之类饰物构筑情节,但从不为之寄寓诗情画意,而总是直指人心或日人欲。冷眼看世的峻利,也使得《词话》中的‘物色别呈色泽。”
在《物色》一书后记里,她表达了对于《金瓶梅》精彩纷呈的“物的叙事”的推崇——
我以为《金瓶梅》开启了从来没有过的对日常生活以及生活中诸般微细之物的描写。……白居易平朴,李贺奇幻,李商隐朦胧,温庭筠讲求字面的绮美和灵动,而笔下都有教人常温常新的物色。然而到了《金瓶梅》,此前所有的“美”,差不多都跌到尘埃,这里没有诗意也没有浪漫,只是平平常常的生活场景,切切实实的功用,成为小说中我最觉有兴味的“物”的叙事。它的文字之妙,即在于止以物事的名称排列出句式,便见出好处。它开启了一种新的,或者说是复活了一种古老的叙事方式,比如《诗·秦风·小戎》“小戎俴收,五檠梁轿。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馵”,——以“物”叙事,笔墨俭省到无一字可增减,但若解得物色,其中蕴含的丰富即在目前。
原来“满冠、掩鬓、围发、分心”都是头饰
《词话》中是这样写来旺儿的货担的,“满冠擎出广寒宫,掩鬓凿成桃源境。左右围发,利市相对荔枝丛;前后分心,观音盤膝莲花座。”
不明所以,望文生义,很容易以为这是排比夸张,哪知句句写实。《定名与相知》、《物色》两书中,扬之水将文史材料、雕塑绘画,及她在各地博物馆所看到的实物比照分解,读后令人恍然大悟,原来“满冠、掩鬓、围发、分心”都是头饰的具体名称,依照插戴部位的不同而得名,至于“广寒宫”、“桃源境”、“荔枝丛”,以及“观音盘膝莲花座”,也都是当时时髦的纹样,并无半句夸张比喻。对照她书中的大量实物图片,真真是“物”与“诗”互证,“不用再多说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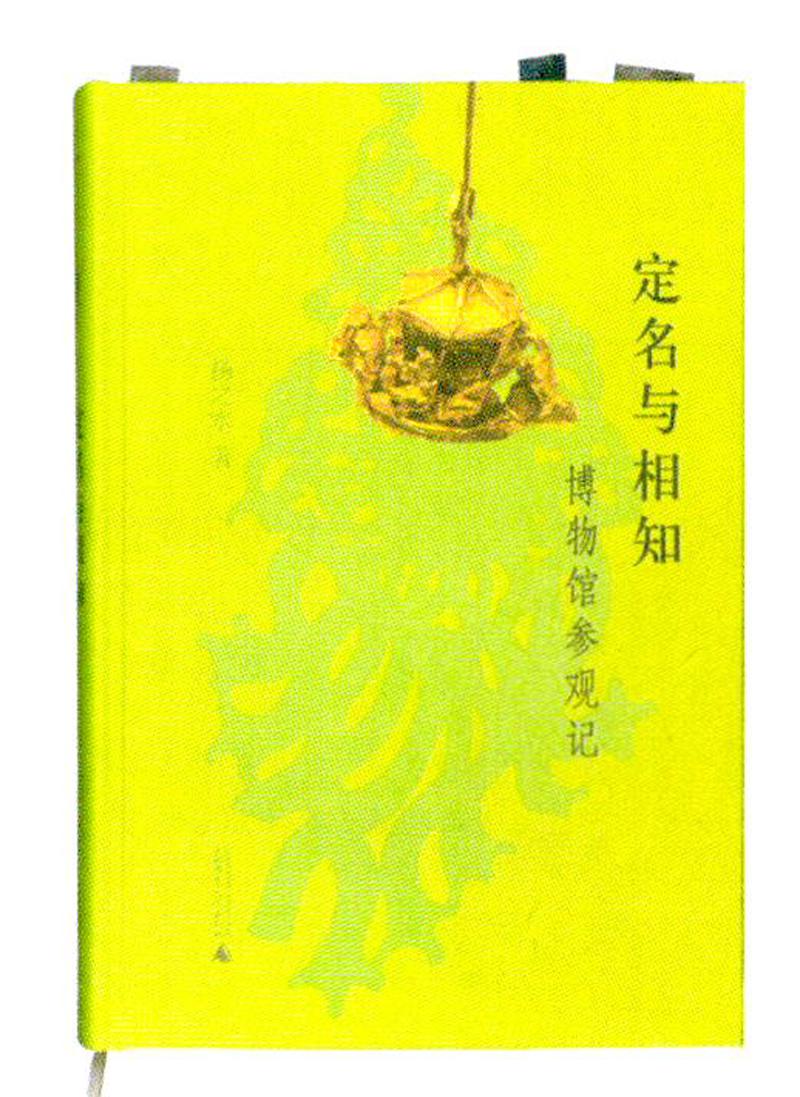
“昨天老师还在提醒我不仅要关注微小的考证,更要抓住历史的主线。”孙机先生已经89岁,思维依然敏捷,“他到现在还自己手绘制图呢。”
二十年前孙机常在博物馆里给扬之水授课,“台湾出过一本《孙机谈文物》,封面是他一个人对着佛像讲演,他实际上是在给我讲,周围围了一圈观众,这张照片用作封面时把我略去了。”
“那时的博物馆跟今天太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底下就是一个说明牌,甚至没有人经常去的地方上面落了一层土,显得死气沉沉的。还有一个是不允许拍照,这就很麻烦,当我看到一个有用的可以作为长编的图,我得站在那儿把它画下来。”扬之水的第一本专著《诗经名物新证》是孙先生手把手带着做的,“画图也是他教我的”,这本书光画图就耗费了半年时间,“画完我的视力从1.5降到了1.2,颈椎也不行了,幸亏后来可以照相。”
“老师对我寄予厚望,反复提醒我,这个问题我在《中国古代金银器史》里会关注。只是宏大历史叙事的确不是我所长,我一个人也不能包打天下,我自己知道我只能把一个一个的小问题都解决了,当其他人梳理政治史、经济史、生活史时,他接触到这些细节,而这些细节我已经给他解决了,那我不就给人铺砖铺路了吗,我这细微的工作也是有意义的!”
青年文学评论家张定浩是扬之水的忠实读者,在《定名与相知》新书发布会上,他将扬之水比作“中国文化的修补匠”, “她把很多的虚线慢慢填实,把文明当中遗漏的东西慢慢填实。这是一个非常浩瀚的学问,也可以说是绝学,人穷尽一生都很难做完,但像精卫填海一样,特别值得钦佩。”
他在《小说评论》上发表了《文学与名物》一文,讨论名物研究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镜鉴意义。词与物之间的碰合聚拢,究竟给人怎样的踏实和安宁感,张定浩在文章中以《楷柿楼集》卷六《两宋茶事》论“分茶”一节为例,让读者一窥“定名与相知”在人心中所产生的化学作用——

陆游名诗《临安春雨初霁》:“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这里的“分茶”,倘若望文生义,会草率以为就是分别给一个个杯子分上茶叶,但如此“细乳戏”三字便没有着落。钱锺书1957年版《宋诗选注》以为“分”就是“鉴辨”,后在1928年版《宋诗选注》中改正为“一种茶道”,并援引时人的诗文笔记为证。这自然已近准确,但还是不够详实和生动。扬之水遂从唐宋饮茶分煎茶和点茶两种说起。引用数十种文献和图像材料,阐明点茶方法,以及分茶即点茶之别称,而点茶之“戏”,关键在于要使茶盏表面在沸水击拂下泛起乳花,更妙者,可使汤纹水脉扩散成花草图案,这简直有点像今日咖啡制作中的拉花技术,此中要义,除了手感,还牵涉茶叶的加工方法,往往需在其中添加米粉等物,使其“调如融胶”……
他将扬之水在《楷柿楼集》里的考证辨识与《繁花》作者金宇澄在文字之外的插画进行对观,“金字澄为自己写下的文字作插图,不为写意和叙事,只是要弥补文字表述事物的不足。‘有时我即使写了两万字,也难表现一幢建筑的内部细节,图画是可以的。单纯的怀旧一定不是金宇澄的意图,他是个小说家,知道人的真实的活动与感情,需要一个具体的物的世界来安放,并通过那些物的名字来保存。”
“阅读《棔柿楼集》也能如此这般教人安静下来,知道自己和一切的人类,最终都是生活在沉默却有名字的物的怀抱.而非意见和观念的喧嚣中。”
微言一克,千钧之重
名物研究是传统训诂学的一支,研究者依据文献苦苦探索出的一个名称或是一个古代日常生活的细节,有时会被视为“常识”,受人轻视。
孙机先生也曾自谦,说自己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是本“小书”,说“我所知道的只是常识”。
扬之水却说那是一本始终滋养她的“大书”。在孙先生的治学中她看到了常识如何成为真知灼见,“曾有人称遇安师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对此极力否认。当今时代,靠了各种检索手段,也许胸罗‘百科全书并非难事。但仅凭检索而得到的知识,似乎难以避免‘碎片化,而贯通中外,融汇古今,打通文史,以求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生活有全面细致的了解,现代检索手段之外,尚别需一种思考辨析的功力,有形之‘大书,必要无形之‘大书为支撑的。”
“微言一克,千钧之重”,是她心中的治学目标。她曾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微言一克的重量:从郭在贻的训诂谈杜甫诗的校注》,很是喜欢,她在《定名与相知》一书的后记里引用了江弱水的这篇文章,“训诂学家从不废话一吨,都是微言一克,但这微言一克却是从偌大的古籍库中一本一本、一页一页、一行一行细读下来再精炼出来的,这就有了千钧的重量,动它不得。”
她对“大话”分外敏感,如同《物色》后记里所写的,“关注多年的《金瓶梅词话》,读‘物所得也不过收在这本书里的小小一束。”新书发布时,她应邀到中华书局“伯鸿讲堂”做“一器一物——明代小说中的物色”专题讲座,PPT里有一页是她节选的一篇文章,文章题为《一部金瓶梅,写尽中国古代服饰》,这篇长文曾在《中华读书报》上整版刊出,称“一部《金瓶梅》写尽天下服饰!—部《金瓶梅》集古代服饰之大成!一部《金瓶梅》就是中国古代服饰的博物馆!”她摇头,“一部《金瓶梅》如何可以写尽天下服饰?充其量也只是明代服饰,也还远不能说‘写尽,这样的表述,只能说明作者对他的评论对象以及评论对象所涉及的历史文化缺乏了解,文中的举例和评述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浮夸风也刮到了策展和宣传,“比如一年一度的正仓院展,早些年出国不方便,去看的人很少,我是2012年第一次去看的,那时没几个中国人。近年出国已经成为寻常事,特别是去日本非常方便,专程去奈良看展也很平常,我们去时经常能够看到熟人。关于正仓院特展的宣传也逐年增多,但有点褒扬过大,比如称‘这座位于奈良东大寺的宝库,保存了迄今为止种类最丰富、最全面且最有价值的唐朝艺术品,可以说想要亲见唐朝最准确、最完整、最丰富的文物,正仓院是唯一的选择。说出这六个‘最,还有‘唯一的判断,这后面得有什么样的知识背景?对唐代文物有没有全局在胸?至少,是否看过何家村与‘法门寺?你看过几个唐代专题的展览?有没有看过唐代文物图录?你说这六个‘最太高了,不可能,而且它都是传世品,跟我们出土的那些带着它当时文化信息的文物无法同日而语。评价它的时候得有对唐代文物的全局在里边,才能够判断它的价值。”
知识胶囊化、功利化的当下,她提醒匆忙的现代人不要每每满足于表面的知识和“短平快”的传播方式,“不经过深入思考而生出自己的心得,表面的知识就会永远停留在表面。”
她欣慰现在各地博物馆都在动脑筋策划吸引人的展览,“要让文物活起来”,
“实际上‘让文物活起来也是我和老师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定名与相知就是希望能够把器物放到它的生存背景中去。”
“博物馆是文物的聚英,把考古报告变成立体的便于聚焦,但展品往往脱离当日环境,虽然展板会提供很多背景资料,而且有讲解员的解读。讲解员生动活泼让你接受,有时加点噱头,但未必准确,或者根据他的理解有所发挥,这些都要通过我们自己消化、理解和辨认,所以依然需要我们的深入思考,因此读物之后仍然需要读书。”
这些年来,她的很多研究成果直接为博物馆所用,细心的读者可以在多地博物馆器物名称和说明中看到,“自己付出万千艰辛所得能够转化为公共知识,这是很教人感觉欣慰的。”
有时候,也有朋友告诉她,有些展览大段大段使用了她书中的考证、论述,却没有注明出处,“我心里是有点遗憾的,定名并不容易,我当然希望自己的知识产权得到尊重,对于策展方来说,如果注明出处,不会对他们有任何损失,反而会提升自己的‘学术专业度,对观众也是一个延伸服务,观展之后,如果想要更多知识积累,可以根据资料出处再来找书看。”
“名物是思想诗意的瞬间”,一位老友在给扬之水的信中引用了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这句话。接受本刊采访的早晨,她找出《道德经》,“你看,道经第一章就是,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這是什么?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深奥的问题,它是日常化的,每天我们都会发好几个疑问:这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但这个问题也是永恒的,宋人最初给青铜器命名时,他们会问,如今,我们也在问。在这个问题里,包含了人类最初的思考和分别的意识。”
(参考资料:《定名与相知》、《物色》、《北京青年报》所刊《定名与相知》《<李煦四季行乐图>丛考》新闻发布会节选实录。实习记者刘芮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