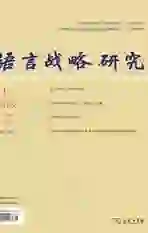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2018-05-14李英姿
提 要 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近年来越来越受到西方学界重视。本文概括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不仅对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解决问题的现实意义。西方已有的研究和经验可以给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 家庭语言政策;语言政策;理论;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8)01-0058-07
Theory and Methods in Family Language Policy Research
Li Yingzi
Abstract The study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s a new field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Western language learn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sic theories, research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y research. The study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s not only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in China, but also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problems.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western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can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domestic research.
Key word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olicy; theory; ethnography
西方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自20世纪中期诞生以来一直沿袭着关注大环境的传统,一方面官方的语言政策容易观察,另一方面这样的研究也容易产生较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也是最繁荣的阶段。Spolsky(2009)认为可以从10个领域进行语言管理,这10个互相影响的领域分别是:家庭、宗教、工作场所、公共空间、学校、立法与健康、军队、地方与中央政府、语言权利组织、超国家组织。可以看出,人们开始认识到语言政策研究仅仅依靠国家或政府行为所产生的控制力或影响力是远远不够的,逐渐突破宏大叙事,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与政策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引发更多关注,微观视角下家庭作为语言具体应用领域的规划渐受重视。
一、家庭语言政策在语言政策中的地位
家庭语言政策着力考察“在家庭范围内家庭成员之间与语言相关的明确和公开的规划,提供如何管理、学习和家庭内部语言协商的综合研究”(King et al. 2008:907)。“家庭语言政策”的说法在中国语境/汉语语境中恐怕不容易接受,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汉语中“政策”一词和英语中Policy认识和理解的不同(李英姿2016)。
一直以来,主流语言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官方政策方面。但是,不可否認,除了官方政策,非官方的、隐性的政策的标准和效果,可能对语言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并可以形成和控制语言行为(Haas 1992),这往往比官方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更有力量,更容易取得预期目标(Spolsky 2004:8)。Spolsky(2004:39)认为语言政策可以在不由权威机构发布或者明确制定的情况下依然存在,而隐蔽性的语言政策往往更持久和有效(李英姿 2013:153)。Canagarajah(2008:170)指出家庭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机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必须考虑来自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面的压力,也要考虑包括语言态度、立场、观念等在内的和语言相关的意识形态(也称为“语言文化”)的影响(Schiffman 1996)。语言意识和语言信仰可能是家庭语言政策潜藏的力量,发挥隐性语言政策的作用,不过这些意识或者信仰也不一定都转化为实践(Gibbons & Ramirez 2004)。因此与宏观的自上而下的官方语言政策相比,在家庭领域更适宜考察隐性语言政策,以及隐性与显性语言政策的关系等,从而了解语言转用或者变化的原因和过程,也有助于我们从更具体微观的层面理解语言政策。
二、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内容
(一)基本理论框架
Spolsky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早期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区分了语言政策相互关联的三个组成部分,即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语言意识是“语言及语言使用的信仰”(Spolsky 2004:5),语言实践是在语言社团中常规的和可预期的语言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指人们认为应该怎么做,后者指人们实际怎么做(Spolsky 2004:14)。语言管理指“某人或者某组织具有或者声称的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语言实践或者语言信仰而做的明确的和可观察到的努力”(Spolsky 2009:4)。语言意识由语言实践得出,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实践,语言管理可以改变语言意识,语言实践提供语言环境和语言管理的工具,同时也是语言管理的目标。Spolsky创建的三重理论框架拓展了人们对家庭语言政策的理解,对家庭领域的语言政策研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King et al. 2008),同时也促进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发展。在家庭语言政策领域,父母或者其他育儿者如何看待语言属于语言意识,父母与子女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什么语言交流属于语言实践,采取什么措施保持、传承或者放弃某一种语言则属于语言管理。
(二)研究内容
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虽然开展的时间不长,但是涉及的方面很多,在全球化和多语共存的现实语境下,可供考察的层面非常多。与宏观的语言政策研究一样,家庭语言政策尤其关注复杂的家庭语言生活状态,比如父母说不同的语言,家庭内部的第一语言与社区语言不一致,父母希望子女掌握外语、传承语或者其他语言等情况。比较早的有影响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始于Hornberger。在秘鲁的普诺地区,Hornberger(1988)考察了语言政策对学校、家庭、社区语言使用的影响。Hornberger的目的是考察官方语言政策与地方语言实践的关系,她试图回答语言保持能否被规划这样的问题。通过检视家庭、学校在政府政策背景下的语言意识和实践,Hornberger的研究显示如果缺少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自下而上的支持,那么自上而下的官方语言政策就会失败。该领域早期的研究强调语言输入的重要性,重视研究父母的话语策略,西方中产家庭儿童双语能力获得的语言环境及条件等,大多关注在家庭环境和实验室环境中育儿者和儿童之间互动的细致分析(King et al. 2008),研究多集中在第一语言习得,以单语发展模式作为一般标准,不太关注第二种语言和双语的习得情况(Romaine 1999)。
父母关于儿童语言学习的目标、态度或者意图的考察是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最重要的方面之一。King等(2008)指出,父母的语言意识反映了与语言、抚养子女相关的更广阔的社会态度和意识。他认为家庭语言政策是语言政策和儿童语言习得框架下的最好观察领域(King et al. 2008)。家庭语言政策与语言文化相关的很多辩题相关,比如意识、价值、信仰、态度、偏见、神话、宗教观念,还有和语言附带的其他文化因素(Schiffman 2006:112)。一些已有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探讨了家庭范围内外的因素如何影响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以及具体影响到了什么。比如Curdt-Christiansen(2009)对加拿大魁北克省中国移民家庭语言政策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强烈影响家庭语言政策,父母的教育背景、移民经验和文化性格也会左右他们对子女的语言选择和语言教育。Fogle(2013)研究了美国收养俄罗斯儿童的家庭这一特殊群体,在考虑情感归属和教育需求平衡的情况下,对俄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不同认识以及语言选择。Seloni和Sarfati(2013)研究了在国家官方语言政策以及自19世纪以来法语联盟学校的大环境下,濒危语言拉地诺语(Judeo-Spanish)在土耳其的犹太人家庭内部的保持情况。李国芳、孙茁(2017)通过访谈和观察加拿大的4个华裔家庭,概括了汉语、英语、汉英等几种不同家庭语言政策的类型。这一系列的研究在Sposky三维理论框架下考察父母的语言意识,涉及濒危语言保护与保持、双语教育、传承语、外语教育等问题,官方语言政策与家庭实际语言使用之间的矛盾以及出现矛盾的原因等方面也是研究的重要方面。这些研究表明父母对儿童早期的语言学习和教育的影响非常大。对应该习得哪一种语言,不同语言为什么具有不同的价值,不同家庭环境的父母如何发展双语等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也正因为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复杂性,对于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家庭场所,同时也要考察与家庭密切相关的课堂、学校、社区等场所的语言使用情况,如李国芳、孙茁(2017)就注意到了研究对象所在社区和学校的不同对家庭语言政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三、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主要方法
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方法既有量化方法也有质化方法,其中民族志方法是目前广泛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一)民族志方法
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质化研究的一種典型范式(刘熠 2015),也称定性研究。Ethnograph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ethnos和grapho,其中ethnos的意思是“人”,grapho的意思是“写”,因此“民族志”字面的意思就是“关于人的书写”。Ethnography一般译为“民族志”或者“人种志”,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民族志”。民族志源于20世纪初一批人类学家基于内部视角对某一种特定文化理解的研究。Hymes根据人们多样化的说话方式构建的交际民族学对民族志更广泛地应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语言学中的话语分析和社会学的会话分析对民族志方法也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Wolcott(2008)指出民族志方法是建立在长期从事第一手田野调查基础上的一种“看的方式”,其中心原则在于从一种冷静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研究者本身不仅作为一种基本的研究工具,同时本身也是长期亲自参与的学习者以及人们经验的解释者。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民族志方法广泛应用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交际民族学奠基人Hymes(1980)强调,民族志方法是研究者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对环境具有强烈的依赖性,所谓环境,既包括大的社会环境,也包括具体语境。现场记录、访谈转写、档案三个维度构建了一个可以互相验证的三角数据库,从而提高了研究发现的深度、宽度和可信度,实现深描的目标。看的第一个方式是现场记录,这是民族志方法的核心和关键。好的现场记录要求研究者具有很强的自我反省能力,能够反映研究者个人的假设、判断。可以通过观察者反馈提高反省能力,也叫观察者评论,包括研究者的感觉、反应、直觉、初步解释、推断、预测等(Merriam 2009:131)。现场记录通常匆匆记下,可能仅仅是一些用关键词或短语记录的时间或印象(Emerson et al. 2011:29)。离开现场之后应尽可能快地将现场记录丰富成现场报告。看的第二个方式是访谈,包括非正式的交谈记录,这些未经组织的访谈可以用作构想之后访谈的问题。访谈可以是提前准备的、结构化的固定问题。更常见的是半开放式结构的访谈,比如一对一的重要参与者或者小组形式(Merriam 2009:89)。访谈选择的形式取决于研究问题、目标、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访谈数据包括现场记录,如录音、录像以及转写等。转写的记录在必要时候应该翻译出来。看的第三个方式是档案的检验,包括文件记录和文件数据的搜集。比如对于学校语言政策研究,要收集的档案包括学校章程、教育目标、课程计划、教学大纲、学生作业、社区的人口统计学记录等。这些对语言政策文本的研究非常重要。
作为一种观察方式,Wolcott(2008:72)认为民族志带有文化解释的指向性,人们正是通过社会实践建构意义。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语言政策研究不总是理性、实用或者客观的,而是充满了意识问题,还关系到语言认同、语言态度以及语言忠诚等。人们的实际语言需要和语言态度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充满矛盾,政策执行的过程各不相同,政策执行的效果同样难以估计,语言政策难以预测或者管理的关键正在于此。民族志方法尤其适用于日常生活、机构和媒体领域的研究。传统上,民族志方法很大程度上依赖旅行、体验和互动方式获得研究数据(Hine 2000:44)。在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中,民族志方法把家庭语言政策看作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社会化过程,也就是实践、意识、态度等影响人们日常语言选择的机制(McCarty 2011: xii)。有时候这些过程伴随着官方政策,即宣言、规则和法律等,这种情况是相对容易展开研究的。Spolsky的三维理论框架肯定了家庭范围内“语言选择的力量”(Spolsky 2009:5),民族志方法即试图描述并理解这些力量发生作用的特殊进程或者机制,尤其是这些因素构成的权力或者力量。Hornberger用剥圆葱的过程比喻民族志研究过程中的多层次性,只有切开民族志圆葱(Hornberger & Johnson 2007),研究者才能了解每一个层级的细微之处以及各部分在整个有机体中的位置。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因为其独特的场域原因,有其隐私和封闭的一面,因此受制于很多研究手段和方法,其中的隐性语言政策更是不容易被发现,民族志方法則可以深入家庭内部,通过长期、细致、近距离地观察和研究,深入研究家庭这一微观领域内官方语言政策与实际语言选择及使用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从而实现语言政策研究微观与宏观的结合。民族志方法对语言权利与语言平等的高度重视,有助于我们挖掘语言多样性作为语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因此,对于家庭语言政策来说,无论从研究范式的原理还是从实际的研究情况来看,民族志方法都是一种很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民族志方法对于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意义
1. 促进语言政策研究的纵深发展
家庭语言政策将语言政策和儿童语言习得这两个以往看似独立的学科领域联系起来,是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一个新分支。传统的语言政策研究关注宏观层面而忽略微观层面,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则更关注微观层面相对忽略宏观层面,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则在弥补这两个领域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发展。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这一视角得到进一步揭示,家庭、学校、社区等政策主体在语言规划和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更容易被理解。在对教育者重新定位的基础上,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扩展了语言政策和规划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概念理解(Menken & García 2010:1),这对语言政策研究极具启发性。20世纪末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英语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传播,英语成为事实上的通用语言,法语、德语、汉语等语言也在积极谋求向外传播,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语言面临不可逆转的濒危和消亡境况。新的本土种族认同、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语言人权等概念纷纷进入语言政策研究领域。这些新情况的出现促使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必须拓展已有的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经过经典时期和反思时期,更多社会科学领域的批评和后现代理论开始出现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民族志方法致力于解读家庭语言实践深层次的意识、态度、政策等,契合语言政策研究的批判转向,也推动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2. 实现服务研究对象的研究目的
Yanow(2000:6)认为研究者不可能脱离所要研究的政策而置身事外,因此不可能不考虑研究者自身的价值、信仰以及感情等因素,而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惯用的民族志方法不可避免地混杂了做田野工作的个人经验和科学分析的主观性(李茨婷,郑咏滟 2015)。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不排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建立密切的关系,研究者可能是原住民项目中的教育者和儿童发展专家、项目负责人或者是家长、教师,而且研究者可能同时拥有多重角色。比如在中国,李宇明(1995)既是语言学家,也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汉语普通话习得长期观察记录了6年,这种自然观察法虽然不同于西方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志方法,但是对儿童语言习得及社会化的考察与民族志方法有一定的相关性。实际上,家庭语言政策更鼓励由内至外的研究,而不是由外至内的研究,即研究者本人即是研究项目中的一员。同时研究者也不回避与研究对象构成各种关系,这与语言政策研究经典时期研究者的中立、客观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
人类学家Brayboy提出了对研究对象来说“作为服务的研究”(2012:435)的观点,Brayboy指出在研究中要注意4“R”,即在尊重(respect)和互惠(reciprocity)基础上建立关系(relationship),研究者需要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影响负责(responsibility)。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体现了强烈的实用倾向,即重在解决实际问题,并最终使研究对象受益,因此可以说民族志方法是一种具有明显使用驱动(use-driven)的研究范式。这也充分彰显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旨归的研究目的,体现了学者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也是语言服务的重要表现。
(三)民族志方法的局限性
西方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目前呈现繁荣发展的态势,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其中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大大拓展了人们对语言政策研究的理解深度和广度。从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中可以看出,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问题往往是开放式的,不一定要有一个“是”或者“否”的绝对答案,也很难对已有的语言实践做出正确还是错误的简单判断。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结论一般是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得出的,比如特定国家的加拿大(Curdt-Christiansen 2009;李国芳,孙茁 2017)、土耳其(Seloni & Sarfati 2013)等,因此对于研究结论的普遍应用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不能据此认为基于民族志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是随意的或者是非科学性的。在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中,民族志方法往往结合话语分析、人口统计学等其他研究方法共同使用。这也决定了要想得心应手地运用民族志方法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需要研究者在大量实践反复操作基础上尽可能细致地观察和记录,同时具有超强的逻辑分析能力,这对研究者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
四、结 语
家庭语言政策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不仅对语言学,对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也有很多新的发现。家庭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不仅对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更具有解决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开展得时间还不长。自上而下的、宏观的、刚性的、显性的语言政策一直被关注及研究,相对而言对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家庭则关注和研究还很不够。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缩影,一样会存在语言冲突和矛盾。目前国内虽然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但是还没有更多有理记高度的实证性研究成果问世。李宇明(2015)强调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也应考虑家庭、个人、社区领域的语言问题,研究路向也更应从自下而上考虑。家庭构成了一个最小的场域,家庭是语言政策研究的起点,也是语言政策实施最有效的场所(李英姿 2015)。伴随着英语世界范围的传播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语言生活现状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比如旅居中国的国际家庭越来越多,这些家庭在子女语言教育方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比如如何保留母语,并同时学会汉语,这都应该是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需要关注的方面。同时,也有大量中国家庭因商务、留学、移民等原因旅居海外,如何在外语环境下保持汉语,如何同时获得双语能力等,都是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目前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依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话語/英语体系倾向,尹小荣、李国芳(2017)统计了近10年已有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文献,发现只有1篇文章的1位作者来自中国内地。这种情况对于全球化语境下家庭语言使用情况的把握是很片面的和不充分的。另外,在国内,民族志方法除了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使用外,还应用于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在语言学领域使用该研究方法还比较少,据裘晨晖(2015)考证,国内的外语类研究性论文提及或使用民族志方法的仅有16篇,且均处于非实证的研究现状,大部分属于介绍评价性的文章。因此,不论在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中国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都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
参考文献
李茨婷,郑咏滟 2015 《民族志研究等同于质性研究吗?》,《外语电化教学》第3期。
李国芳,孙 茁 2017 《加拿大华人家庭语言政策类型及成因》,《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
李英姿 2013 《美国语言政策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李英姿 2015 《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迫在眉睫》,《中国社会科学报》,12月22日第3版。
李英姿 2016 《中国语境中“语言政策和规划”概念的演变及意义》,《外语学刊》第3期。
李宇明 1995 《儿童语言的发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宇明 2015 《语言规划学的学科构想》,《世界华文教育》第1期。
刘 熠 2015 《应用语言学中的质化研究报告:定义、规范与挑战》,《外语与外语教学》第5期。
裘晨晖 2015 《国内应用语言学研究中民族志方法使用述评》,《语言教育》第2期。
尹小荣,李国芳 2017 《国外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综述(2000—2016)》,《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
Brayboy, B., H. Gough, B. Leonard, R. Roehl II, and J. Solyom. 2012. Reclaiming scholarship: critical indigenous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S. D. Lapan, M. T. Quartaroli, and F. Riemer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s and Designs. San Francisco: John Wiley & Sons.
Caldas, Stephen J. 2006. Raising Bilingual-biliterate Children in Monolingual Cultur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Press.
Canagarajah, S. 2008. Language shift and the family: questions from the Sri Lankan Tamil Diaspora.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2 (2), 143-176.
Curdt-Christiansen, X. L. 2009. Invisible and 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 ideological factors in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Quebec. Language Policy 2009 (8), 351-375.
Fogle, L. W. 2013. Parental ethnogteories and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n transnational adoptive families. Language Policy 12 (1), 83-102.
Gee, J. P.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Routledge.
Gibbons, J. and E. Ramirez. 2004. Maintaining a Minority Language: A Case Study of Hispanic Teenager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Haas, Michael. 1992. Institutional Racism: the Case of Hawaii. Westport: Praeger.
Hine, C. 2000. Virtual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Hornberger, N. H. 1988.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Language Maintenance.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Hornberger, N. H. and D. C. Johnson. 2007. Slicing the onion ethnographically: layers and spaces in multilingual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TESOL Quarterly 41 (3): 509-532.
Hymes, D. 1980. Ethnographic Monitoring. In D. Hymes (ed.), Language in Education: Ethnolinguistic Essays.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Johnson, D. C. 2013. Introduction: ethnography of language policy: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19, 1-6.
King, K. A., L. Fogle, and A. Logan-Terry. 2008. Family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2 (5), 907-922.
McCarty, T. L. 2011. Preface. In T. L. McCarty (ed.), Ethnography and Language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Menken, K. and O. García (eds.), 2010. Negotiating Language Policies in Schools: Educators as Policymakers. New York: Routledge.
Merriam, S. B. 2009.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Ricento, T. and N. H. Hornberger. 1996. Unpeeling the onion: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and the ELT professional. TESOL Quarterly 30 (3), 401-427.
Romaine, Suzanne. 1999. Bilingual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Martyn Barrett (e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Hove: Psychology Press.
Schiffman, Harold F. 1996. Linguistics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chiffman, Harold F. 2006. Language policy and linguistic culture. In T. Ricento (ed.),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olicy: Theory and Metho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Seloni, L. and Y. Sarfati. 2013. (Trans)national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family language practices: a life history inquiry of Judeo-Spanish in Turkey. Language Policy 12 (1), 7-26.
Spolsky, Bernard.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polsky, Bernard.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lcott, H. F. 2008. Ethnography: A Way of Seeing (2nd edition). Lanham: AltaMira Press.
Yanow, D. 2000. Conducting Interpretive Policy Analysi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eries 47.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