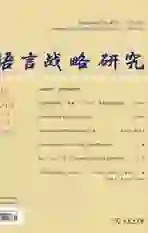汉语国际教育:“事业”与“学科”双重属性的反思
2018-05-14宁继鸣
宁继鸣
提 要 新时期,具有“事业”与“学科”双重属性的汉语国际教育,迎来新的发展和机遇期,但也是一次新的挑战和适应期。需要客观理性、审慎分析环境和政策变化带来的生存与竞争压力,从历史、发展与进步的视角,辩证反思双重属性带来的资源、问题和挑战,以及今后的发展路径。通過建构驱动模型,研究分析得到初步结论:双重属性带来的优势十分明显。但长期以来事业、学科、专业等发展指标权重不均衡不充分,造成事业(行业)发展的繁荣景象,掩盖了学科意识的薄弱、学科属性的模糊、学科建设的缺位,以至于影响到人才培养的需求和预期,影响到事业发展的基础与需要。从时代与观念意识等5个方面提出观点和看法:坚持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科学分析理性研判“走过的路”;秉承解放思想精神,深刻理解国家意志与战略的重要性;尊重学科建设规律,彰显学者与高等院校的学术贡献;强化教育事业功能,推动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建设进程;突出人才培养目标,推进顶层设计实现结构性改革调整。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双重属性;事业;学科;专业;反思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8)06-0006-11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601
Abstract The new era is a period in history which is fraught with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d poses great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both as a profession and an academic discipline, for which adaptations should be made accordingly. The pressures brought about by the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policies on its survival spur an objective, rational and discreet analysis, which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us to rethink about the resource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related to the dual qu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both as a profession and an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this reflec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In this study, a driving model is advanced to deal with what is described above. The initial implication we draw upon from the model shows that the advantage resulting from the dual qualities is obvious, and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is area. However, due to overemphasis placed on the profession,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has only shown a superficial prosperity, resulting in some problems such as weak awareness, blurring nature, and inaccurate discipline position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irstly, proceeding from the real situation, we should judge the achievements and mistakes in a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way; secondly, we should have an open mind and try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e will and its strategies; third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 academic discipline, we should value the contribution of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fourthly, we should try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by strengthening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 finally, with the aim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mind, we should try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rough a top-down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dual qualities; profession; academic discipline; specialty; rethinking
一、引 言
2018年,国家出台了两个与汉语国际教育密切相关的“指导意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并发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前者提出“加强力量建设,提高办学质量”,意味着汉语国际教育的重点从注重数量规模到注重内涵提高质量。我们理解注重内涵、提高质量的关键是其学科建设。后者提出高校要“转变发展模式,以多层次多类型一流人才培养为根本,以学科为基础,更加注重结构布局优化协调,更加注重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该意见已成为目前中国高校普遍遵循的办学理念和战略规划,深刻影响学校“资源配置与政策导向”。在这个大背景下,具有“事业”与“学科”双重属性的汉语国际教育,将迎来一次新的发展和机遇期,但也将是一次新的挑战和适应期。需要客观理性、审慎分析环境和政策变化带来的生存与竞争压力,从历史、发展与进步的视角,辩证反思双重属性带来的资源、问题和挑战,以及今后的发展路径。
二、汉语国際教育双重属性的产生和演进
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的演进,学科的属性和定位等,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做了细致的总结和分析,提出了很多颇有建树的思想和观点。在这些论述或文章中,人们可以领略到王力、吕叔湘、朱德熙、吕必松、程棠、鲁健骥、张德鑫、刘珣、邓守信、潘文国等先生在对外汉语教学初创及成长时期的思想和观点,他们的许多分析和判断,至今仍有很强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意义。2007年是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通过设置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方案,北京大学等24所培养单位开展该学位教育的试点工作。这意味着,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与专业建设开始走向新的阶段。但学者们同时注意到,与事业发展相比,学科建设相对滞后,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现象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探讨:一是对学科属性与定位的理解与判断;二是对学科研究目标与研究对象的分类与界定;三是对学科与专业发展困境与症结的反思。其中学科定位和属性的讨论最为热烈,争议也最大,涉及汉语国际教育的事业和学科双重属性及其关系问题。
许嘉璐(2012)指出,对外汉语教学转变为汉语国际教育已经7年,现在要进入一个新的攻坚阶段。新阶段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培养人才;二是转变观念;三是要有措施。他特别指出,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教育,说起来似乎只是课堂的转移和扩大,但其对教学内容、方法、工具以及评估等都带来了必须要实现的革命性改革。我们在人才培养等方面受到的局限,不是老师和学生造成的,而是与大学和院系以及学科的设立有关。陆俭明(2004,2016,2017)指出:十多年来,汉语教学,从事业的角度看,发展迅速;但从学科的角度看,进展缓慢。目前绝大多数开展汉语教学的学校,从负责汉语教学工作的领导到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学科意识普遍不强,不注重汉语教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和整体建设;不注重整合不同学科的力量为建设汉语教学学科服务。他认为,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很多问题,与有关部门对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对汉语教学的目的任务、对汉语教学总的指导思想缺乏清醒、正确的认识有关,也与我们的培养模式有关。由于体制、政策和认识等原因,汉语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不尽如人意,年轻一代教师的质量令人担忧。学科建设对于培养和培训称职的汉语教师至关重要。
在学科建设的路线和框架问题上,赵金铭(2008)提出,方向和成果是学科建设的主要标志。对于汉语国际教育来说可分为3类: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对策性研究。基础性研究要以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等原创性成果为目标。应用性研究要以反映现实教学和学习需要、能产生切实的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的技术、方法、措施为对象。对策性研究,主要以有针对性地解决汉语国际教育中的现实问题,为制定或完善相关政策起咨询作用为目标。崔希亮(2015,2018)认为,汉语国际教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它与国际上的学科体系无法直接对应,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也摇摆不定。作为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理应得到国家的重视,但无论是“985工程”“211工程”还是“双一流”建设,它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直接后果就是这个专业的发展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难以产生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因此,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非常重要。
关于汉语国际教育概念或内涵的研究与分析,在业界存在着多种理解、预期或判断,尚未达到思想统一或目标实现,但由于多种视角的切入以及不同理论和方法的采用,研究成果与发展设想不仅丰富多彩、扎实有趣,而且使人深切地感觉到几代人对事业与学术的孜孜不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其中很多观点、建议和构想可见于但不限于王路江、崔永华、周小兵、李晓琪、李向农、贾益民、王建勤、赵世举、李泉、张建民、吴勇毅、张旺熹、卢德平、朱瑞平、吴应辉、吴中伟、孙德金、王添淼等众多学者和专家发表的文献。在学者的眼中,汉语国际教育具有不同的属性和定位,以及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有一种观点,取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和高度共识,那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每一步发展,都跟国家的发展、国际风云的变幻,以及我国和世界的交流与合作息息相关”(赵金铭2006)。这个共识,既源于之前的对外汉语教学,更与之后快速发展起来的孔子学院密切相关。无论是数字统计还是经验总结,或是海内外的普遍存在与切身体验,都可以证明:汉语国际教育为培养从事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为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推动世界多元文明互学互鉴发挥了积极作用。
几乎所有的学科,都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不同程度的“焦虑和不安”,而正是这种“焦虑和不安”带来的张力与反思,成为学科建设的不竭动力和智慧源泉。但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归属不确定、体系不完整,硕博阶段的教育至今未独立成建制纳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年)》。从其大规模多层级办学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现象看上去不太正常。如果说,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找到某种原因,将之视为一个“过渡期”,那么发展至今,这已经属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不协调问题。
我们选择两组数据,对这种不协调现象进行存在、分布与推理性分析。一组数据源于教育部,反映全国开设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博士)的高等院校的情况。另一组数据来自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反映由其统筹和管理的、与汉语国际教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办学情况。
数据一。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384所高校设置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110所高校设置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2018年,北京大学等7所高校在教育专业博士学位学校课程与教学领域,试点招收汉语国际教育方向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全国42所“一流建设高校”中,有14所设置了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学位,占比33.3%;28所设置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占比66.7%。在试点招收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7所高校中,有6所属于“双一流”建设高校。
数据二。截至2017年12月,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在146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中外专兼职教师4.62万人,各类面授学员170万人,网络注册学员62.1万人。2017年,向146个国家派出汉语教师3574人,支持各省、区、市教育厅(委)和高校派出教师5001人,向127个国家(地区)派出汉语教师志愿者6306人。录取了35个国家86名中外合作培养及来华攻读学位的博士研究生(累计录取413名)和119个国家4883名孔子学院奖学金新生,其中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570人,汉语国际教育本科(含南亚师资班)439人。以多种方式,全年培训本土汉语教师117 454人次。
从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汉语国际教育的办学主体是国内高校,以及各高校的教师和学生群体;从学历层次看,涵盖了本硕博3个层次;从办学规模看,无论是当年招生人数,还是累计存量,数字都相当可观。如,2015年,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生在校人数63 933人,攻读专业硕士学位在校学生10 133人。2017年,全年在华各类孔子学院奖学金学生(学位学生)总数达到9625人。对于存在数十年、办学主体在高校、本硕博层次齐全,已培养和培训海内外各类人才数十万的学科或专业来讲,没有理由被置于“学术体制”之外。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或某种“焦虑和不安”,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发展问题,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问题,具有多重积累和叠加效应。其实人们早已发现,在这方面有一个不仅可比性极强,而且在学科属性或定位上几乎是“同源同宗”的学科或专业——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一直拥有“合法”地位。
关于何时或怎样才能成建制地进入“学科目录”,学界已经讨论了很久。“自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就不断有语言学家、教育学家、语言教学专家和教育部门的各级领导反复强调: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学科、一门学问”(李泉2010)。但正如前面所讲,这几年学科建设虽然取得“局部性突破”,但至今仍未真正进入“主流评价体系”,未能得到普遍认可的“学科或学术地位”。长期的“路线偏离”与“制度缺失”,不仅造成学科建设“乏力”,而且队伍建设“薄弱”,人才流失严重,科研水平下降。在结构和形式上,表现为本硕博体系的不统一、不完整;在内容和水平上,表现为学科理论的“松散和碎片化”,研究方法的“借用和简单化”,以及研究队伍的“单一和扁平化”。
问题在哪儿,是国家不重视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国家不但重视,而且非常重视。不仅在经费和资源方面予以大力支持,而且在组织领导、管理层级以及对外交流渠道等很多方面给予特殊关照和政策安排。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尝试回到享有荣誉的“起点”。
资料显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的正式提法,始于1988年9月第一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而以官方正式文件的形式出现,则是源于1999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文献记载,第一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意义及面临的形势,讨论中国发展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措施,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领导(晓山1988)。第二次会议结束之后,《教育部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向社会公布。对比两次会议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在“教育事业”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和强调了“国家与民族的事业”意识。《会议纪要》指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要把对外汉语教学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根据国家改革开放和外交工作的总方针,大力向世界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努力增强汉语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会议认为:“虽然11年来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国家对这项工作的要求,与国际社会日益增长的对汉语教学的多方面需求相比,我们的工作还有较大差距,有关部门、地方和学校的一些领导同志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应有高度,没有充分认识到对外推广汉语的战略意义和国家利益之所在。一些学校、单位还没有完全把这项工作视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着不重视质量,甚至把对外汉语教学只是作为经济创收的一种手段的现象。”会议强调,“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工作力度,认真解決上述问题”。可以看出,将“国家与民族的事业”赋予对外汉语教学,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其承载的使命和任务,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以利于有效统筹和配置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开放大局,服务于国际社会对汉语和中华优秀文化的需求。《会议纪要》特别提出,要“加强学科理论研究,完善学科体系,进一步推动学科建设”。由此可见,汉语国际教育从其发展初期,就已经奠定了国家与民族事业的历史基调,被赋予了国家使命、责任与任务,同时也兼顾了学科与专业内涵建设的功能与价值根基。
在问题梳理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有两组概念在汉语国际教育的演进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数十年的实践与走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一个可以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视角:一是国家与民族的事业——教育事业;二是学科建设——专业建设。
在进入讨论之前,对相关概念做一个简要分析和界定。
从本质上讲,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属于一项“国家與民族的事业”(以下或简称“国家事业”)和属于“教育事业”的提法并无不同,因为教育事业本身就属于国家事业。相较于教育事业,国家事业是一个上位概念,适用更加宽泛。在国家权力机关中,教育部作为国务院的一个组成部门,主管全国教育事业方面的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
关于学科建设问题,学界有很多讨论,也有很多观点和不同的诠释。本文遵循学界普遍接受和认可的观点予以界定和引用。《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学科建设要明确学术方向和回应社会需求,坚持人才培养、学术团队、科研创新“三位一体”。重点在于尊重规律、构建体系、强化优势、突出特色。学科建设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加强科研实践和创新创业教育,支撑引领专业建设。有学者提出,学科建设内涵可以归纳为结构性要素和功能性要素两个部分。其中,结构性要素主要包括汇聚学科队伍、凝练学科方向、搭建学科平台;功能性要素主要包括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一般认为,学科是指科学体系的分类,而专业是按职业划分的学业门类。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两者之间既相互依存,又各有其侧重点。学科建设涵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侧重于学术研究的功能建设;专业建设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应该包含于学科建设之中,但侧重于学科人才培养的功能(张炳生,王树立2012)。
在对文献和事实的研究分析中,我们发现一个对后来发展走向产生较大影响的“选择偏好”。在“事业”层面,汉语国际教育选择了更上位的国家事业,并未与具有学科资源或制度安排配置权的教育事业形成“属性契约”;在“学科”层面,则是选择了专业建设,而不是与具有学科名录所有权但理论研究色彩更浓的学科建设形成“评价契约”。从经验和效果看,这种具有“弹性”或“模糊”的选择并不是非理性的。除了政治和需求原因,也是由于专业建设的内涵和功能恰好与教育事业相适应,更加符合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发展的定位。学科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基础,专业建设有自身的任务,两者不能混淆。专业建设涉及多方面的内容,要在学科建设提供的基础上解决自己的问题。其中包括制定专业培养目标和规格、确定专业设置口径、制定专业教学计划等。这些内容是学科建设代替不了的,因为它们不属于学科建设的范畴(冯向东2002)。而这些被称之为“不属于学科建设范畴”的内容,恰恰是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的“刚需”,是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师必须承担和完成的工作与任务。
教育事业的属性和定位,是汉语国际教育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和资源保障。人们之所以更加习惯于强调其国家属性、定位和价值,一个直接原因是,在其发轫之始的主要任务是面向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在那个年代,留学生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工程,更是一项“外事任务”。“外事无小事”。因此,汉语国际教育也就很自然地被归入教育部负责“国际合作与交流,统筹管理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工作,规划并指导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司的管辖范畴,而不是负责“制定学科专业设置目录”的高等教育司,或是负责“各类高等院校招生及全国考试工作,负责各类高等教育学历和学籍管理工作”的高校学生司。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具有国家意志和属性的管理原则或出发点,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在中国的存在基础与发展路径完全不同。作为外事事务存在的事实,不仅为汉语国际教育作为国家事业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也形成了其几十年来的思想意识和实践遵循。因此,尽管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同属一个领域范畴,但汉语国际教育为何至今仍未取得同样“合法”地位的疑问,也就有了一个初步答案。当然,这个理由在今天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充分。
强调汉语国际教育的事业属性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发展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初期,采取国家意志、政府驱动、统一思想、优化资源配置的做法,是理性且有道理的,可以更好地激发与增强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巩固与加强政府的引导和掌控。事实证明,采取“上位选择”以及外事管理模式,有利于彰显国家意志,促进事业所需社会与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效率。然而,当历史的时针走进2018,人们发现,改革开放之前或初期做出的规划和设计,已无法满足新时期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亦很难适应“双一流”建设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作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开放、学科交叉、综合性强的学科(专业),一个专注于培养复合型、国际型、专业化人才的学科(专业),新时期的汉语国际教育,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过去谋划未来。特别是在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问题上,要站在新的起点新的高度,理性思考审慎判断,对于两者之间的认识和定位,不能再摇摆和犹豫,不能再放任两者之间选择性的“路径依赖”,或是普遍性的“无意识错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汉语国际教育双重属性运行模式及其得失评价
长期以来学科属性的“模糊”以及制度安排的缺位,给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带来了诸多“隐患、不安或不稳定性”,特别是目前在高校教师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由于发展空间和学术认可引起的“集体焦虑”。对于学科或专业建设来讲,关键环节就是两个:一是制度安排;二是教师队伍。学科或专业设置与否在于“制度”,学科或专业建设的责任和任务属于“教师”。但由于业界长期存在的学科与专业概念混淆、定位不明,不仅造成学科建设不知何处安身,而且已经有了部分制度安排的专业建设,也由于“责任主体”的模糊变得基础不牢、根基不稳。
双重属性下汉语国际教育是如何运行的,在运行中是如何对双重属性扬长弭短而取得快速发展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分析事业、学科、专业等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逻辑或因果关系,在本命题中,我们设A1表示“国家事业”,A2表示“教育事业”;B1表示“学科建设”,B2表示“专业建设”;H表示“汉语国际教育”。从简单线性关系看,H=A1+A2+B1+B2。但若从因果关系的视角去审视,H不再是上述各要素线性之和,而是A1、A2、B1、B2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关系”与“要素”之间不断调整合博弈的复杂过程。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环境,解释变量及其组合的权重也在不断变化。在实践中,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复杂的。本文采用简化形式,将环境(外部)因素纳入其中,建立一个一般化的汉语国际教育函数,称为“发展函数”,表示为:H=F(A1,A2,B1,B2,U1,U2),用于理解和说明各要素或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其中,H为被解释变量,A1、A2、B1、B2以及U1和U2为解释变量。U1和U2代表(A1、A2、B1、B2之外)可能影响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环境(外部)因素。U1为国内环境因素,如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战略等;U2为国外环境因素,如国际社会的汉语学习需求和教育法律制度等。在下面的分析中,重点考虑事业和学科,对环境(外部)因素暂存不议。
试将H视为一辆前轮驱动、高速行驶的大巴。A1和A2作为两个前轮,以“双轮引导驱动”的形式存在,发挥制导作用;B1和B2作为两个后轮,以“支撑保障供给”的形式存在,发挥基础作用。为了便于叙述和分析,本文将其称之为“双轮驱动模式”。如图1所示。
如前所述,在A1与A2关系中,A1为上位;在B1与B2关系中,B1为上位。表现在虚拟空间时,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A1与B1居于一侧、A2与B2居于另一侧的格局。
我们可以想象,这辆大巴在行驶中,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A1、A2动力十足,“胎压平衡、运转协调”;B1、B2结构合理,“供给平衡、各司其职”;A1、A2与B1、B2之间不仅传导过程“心有灵犀”,而且执行过程“有规有矩、职责明确”。当然,并不排除学科与专业厚积薄发、强势发展带来的“四轮共同驱动模式”。目前的实际情况是,A1的作用被有效挖掘和发挥,A2的资源未被充分调动和利用;B1因为缺少足够的能量难以支撑,“胎压严重不足”,但B2的功能与作用表现强势。由于A1和B2处于大巴的对角线位置,而作为基础和根本性支撑的A2稳定可靠,只是在行进过程中显得有些“刚性有余、弹性不足”。因此H的运行状态属于“双轮驱动、三点支撑”,可以在适当的速度或适当的负荷下平稳运行,也可以在条件许可时“百米冲刺”。这种状态在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方面都可以得到解释或验证。换句话说,只要车辆不是过于超载,或速度不是太快、路面不是太差、行程不是太远,或是乘客要求不是太高,有些颠簸现象也就成为可以容忍的“常态”,易被忽略。同样的道理,汉语国际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局部或阶段性突破,也正是A1、A2、B2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些类似于“颠簸”层面的问题,也易被“宏观大势”暂时忽略或冲淡。
纵观发展历程,汉语国际教育的组织与推动,特别是几次“关键性突破”,几乎全部来自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其中包括目前进入“学科目录”的本科专业,以及进入“专业学位目录”的硕士教育。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不是某一级“国家权力机关”或某一所“法定办学机构”,没有学科设置的权限,也没有学科建设的资源。如果用K来代表“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那么,在“行驶的大巴上”,K的策略和做法是:在A1的激励、保障和引导下,扮演A2的角色或代理行使其部分权力,与A2联手共同强化了B2的属性和定位,引导高校定向发挥了B2的功能和价值。
换一个角度看,在这个选择或实践中,由于历史和定位的原因,A2的某些资源未能实现“契约化”,连带产生或影响了B1建设的缺位或薄弱。但从执行或实践的层面看,K的策略和选择是有些无奈或理性的,是符合规矩且有道理的。因为在国家层面,教育资源的配置以及制度安排的设计,责任与权力属于教育部各有关司局;学科建设的资源配置与政策导向,更多的责任和权限在于各高等院校,而学科建设的内涵、质量和成长,则源于高校教师的理解和贡献;汉语国际教育的统筹规划与目标实现属于K。满足和实现“职业需求”目标,是K的工作首选之一,B2的功能与作用恰好与之相匹配。
汉语国际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大规模成建制、需求在外供给在内、特有的海外办学模式和社会服务形式。这种“非传统”和“双轮驱动、三点支撑”的运行特点,是造成民众、社会或相关机构对其认知程度不高,或支持力度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特殊的办学环境以及受教群体的多样性,形成了人才培养模式和就业渠道的特殊性,而学科基础与专业框架的不完整,以及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的滞后,使得各种特殊性愈加特殊。例如,从1981年教育部批准设立以培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为主要目标的“对外汉语”专业,到1985年北京语言大学等4所院校作为试点开始招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属于被“控制设点”的专业。但到了2017年,全国设置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高校达到384所,设置硕士专业学位的高校也达到110所。这种在较短时间内大规模快速发展的模式,至少带来3个问题:一是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问题;二是教师资源与合理配置问题;三是学生质量与专业定位问题。当这些问题被转移到个体、群体或社会,有些问题自然就会被放大,变成各种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如学科属性与学科地位问题、教师职业发展空间与职称评定评审问题,以及学生毕业选择与就业渠道等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与“学科”双重属性带来的优势十分明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存在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亟待解决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长期以来A1、A2、B1、B2等发展指标权重不均衡不充分,造成事业(行业)发展的繁荣景象,掩盖了学科意识的薄弱、學科属性的模糊、学科建设的缺位,以至于影响人才培养的需求和预期,影响事业发展的基础与需要。
四、对汉语国际教育及其学科建设走向的几点看法
汉语国际教育享有“国家与民族的事业”的属性与定位,其改革与建设走向,应该在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框架下,客观分析和理性研判。从事实、发展和进步的视角看,在众多不适应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由“点”到“面”再到“体”过程中出现的非“演化均衡”。在社会实践中,这种未能达到“演化均衡”的现象很多,包括思想意识、主要矛盾、体制机制、学科建设等。鉴于此,本文从时代与观念意识、国家意志的贯彻与影响、学科建设的内涵与规范、学科建设的组织与协调,以及人才培养的政策制度保障等方面谈几点看法。
(一)坚持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科学分析理性研判“走过的路”
事实观、发展观和进步观,是理解和分析汉语国际教育生成演进的重要基础,是理解和展望新时期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依据。任何事物都是动态和发展的,汉语国际教育也不例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目标和要求,因此也就有了因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不同定位和标准。例如,汉语国际教育当年的起点和现状是:数百名外国留学生,在几个被特许授权的学校里接受汉语学习教育。而当时承担主要课程的授课老师,是从北京大学等数所院校中,经过组织精心选拔、专门培训的一批人文学科背景的教师(学生),由教育部负责组建和培养的一支新型汉语教师队伍。那时,教师们普遍是在承担汉语教学任务的同时,遵循读书时的专业背景或个人兴趣从事学术研究。但伴随留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综合性大学的普遍介入,特别是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阶段,中国学生成建制地进入培养计划,教师们开始不同程度地感觉到,隐藏在汉语教学与专业研究之间的“张力”在不断增强,在“主流评价指标”的导向下,人们开始更加关注“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平衡问题。但由于“行业发展带来的繁荣景象”,以及多年形成的惯习,尽管部分教师感觉到“学科地位”带来某些困惑或不适应,但却并未形成一种强烈的意识或冲动,将自己放在“责任主体”的位置去思考,或主动承担起学科建设的主体责任。当学科建设成为“双一流”大学的基础工程与核心要素,所有人都会感觉到所在学科给职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如果远离了学科就意味着偏离了“主流学术”航道,甚至失去了进入“学术评价体系”的机会。
2005年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对外汉语教学开始向全方位的汉语国际教育转变。对汉语国际教育来讲,这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它不仅改变了办学理念和资源基础,扩大了国际国内社会影响,也影响到了办学结构与发展方向。如果将世界汉语大会视为事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历史节点,那么随之快速发展的孔子学院则为汉语国际教育开拓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奠定了一个更稳定的基础,提出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命题。从演化的结果看,这种变化对学科与学科建设,以及教师发展与职业定位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从当前社会对这个变化的理解和接受看,认识和行动显然都是不够的,人们对“六大转变”的内涵与外延,特别是对学科建设影响的认知与理解,依然是形式和表面的,并未进入“利益相关”的境界。
(二)秉承解放思想精神,深刻理解国家意志与战略的重要性
作为国家意志,“双一流”建设成为当前中国高校的办学遵循和目标要求,“四个坚持”将成为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决定资源配置导向与改革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和执行标准。杜占元(2018)指出,国家层面确定了137所建设高校,并不意味着只有这137所要建一流,而是要以此示范带动全国高校不同学科不同方面争创一流。目前,首批进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正在按照要求比对办学目标,加快办学资源的再审视再配置。尚未进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也正在按照标准和要求,实施改革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资源分配导向更明确的学科布局。在这个背景下,学科建设的标准和要求只会提高不会降低,汉语国际教育不可能“超然物外”,其学科与学科建设问题面临一次更大的挑战,存在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可能。从经验和规律看,汉语国际教育在学校“双一流”建设中的“贡献度”,学科存在的“辨识度”,学科带头人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平、社会影响力等,都将成为本专业学科与学科建设能否進入学校“主流规划”蓝图的参考依据。面对新形势大环境,转变观念、提高站位非常重要。新时期的汉语国际教育,要研究和探索怎样才能将挑战转化为机遇,获得“再出发”的能量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这已经成为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绕不过去的问题。
(三)尊重学科建设规律,彰显学者与高等院校的学术贡献
学科建设是很多学科普遍存在的共同话题,只是与它们比较,我们的学科意识和学科建设更加薄弱和不稳定,对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也略显单薄,不够深入。在诸多讨论中,与汉语国际教育多有“重合交叉”的教育学学科建设,对本专业学科建设具有较强的学习、启发和借鉴意义。龚放(2016)认为,无论是学科发展方向的凝练、学科建设重点的选择,还是学科组织模式的创新、学科建设绩效的评价,都离不开对具体学科的定位与学科特性的认知,这一定位和认知如果出了偏差,学科建设就会失焦、失范、失误,甚至荒腔走板。作者特别引用了英国学者托尼·比彻关于学科分类、学科特性以及学科文化方面的新发现和新见解。按照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2015)的研究结果,高等教育学与法学、行政管理学等应用社会科学一起,隶属于“应用软科学”,其特质是:“实用性、功利性,注重专业(或半专业)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个案研究和判断法,研究成果为规约或程序的形成。”
如此看来,汉语国际教育应该属于应用软科学范畴。换句话说,在学科建设中,不仅要从“经验话语”的角度阐述一线教师的体会和感受,更要关注和尊重此类学科所具有的特质,即“实用性”“功利性”和“注重专业实践”,用“学术话语”来诠释、论证和建构本学科“应该存在”的物质形态、知识结构与思想内涵。以研究和解决汉语国际教育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不同的语境或教学环境,面对不同群体或不同需求,如何实现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作为首要任务,而不是简单地以某种“特殊性”或“特别性”为由,简化逻辑判断、忽略理论方法、泛化学术概念,或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探寻和构建一个逻辑严密、范畴特殊、边界严明的学科理论体系为唯一的目标或标准。当我们探讨学科建设问题时,应该向学界普遍认可的观念、范式和内涵要求看齐,与学界普遍遵循的规则、标准和贡献要求接轨。在这方面,对学科(专业)建设负有主体责任的教师不可以回避,资深学者或知名教授“个人创造力”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
(四)强化教育事业功能,推动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建设进程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承载的使命和职责,是实现新时期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学科属性、定位与内涵等学科建设的动力来源和资源基础。根据其官方网站,其承载的使命和职责,特别是其主要职能几乎全面覆盖了汉语国际教育的内涵与任务,是汉语国际教育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最坚实的资源基础、最广阔的办学空间。
根据中央《关于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队伍建设是一项核心任务。新时期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扮演的角色,既是事业发展的责任主体和建设主体,也是学科与专业建设最重要的推动者和组织者。专业建设的动力基础和功能价值源于培养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人才,其发展必将对“支撑引领专业建设”的学科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带来更大的挑战。如果说,当前“专业建设”的主要推动来自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那么在“双一流”建设对学科问题提出更高要求之后,一个较为理想的预期是:教育部有关司局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落实学科建设的“属性契约”与“评价契约”;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对学科建设的关注发生针对性变化,成为新时期学科建设最重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引领和推动学者与高校为此做出基础性、全方位的贡献。
(五)突出人才培养目标,推动顶层设计,实现结构性改革调整
坚持内涵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多层次多类型一流人才,是“双一流”建设对学科的根本要求。但从当前学科框架和实践效果看,汉语国际教育本硕博学位层级设计与人才培养目标之间存在不完善不协调现象。问题是结构性的,不仅有研究生阶段的问题,也有本科生阶段的问题,而且本科阶段存在的问题影响更大。在这方面,有教育理念相对滞后的制约,也有历史积累、社会接受与改革成本等问题,不是“修修补补”可以解决的,需要得到国家“政策制度”层面的设计、支持和保障。
针对人才培养,特别是国际汉语教师培养内容与能力分级等问题,笔者曾以语言的基本属性为理
据,提出一个基本假设:一名称职的国际汉语教师,应该具有良好的“汉语素养与汉语教学能力,以及文化素养与文化传播能力”。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本硕博学位层级设计与人才培养目标之间的框架性建议:本科阶段更加注重“基础与理解能力教育”;硕士阶段侧重于“专业与应用能力教育”;博士阶段则应将“研究与建构能力教育”视为主要任务。
因此,汉语国际教育本科阶段的课程安排和培养目标,是以“汉语素养和文化素养为主干的通识教育”,要求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的层级要求和目标,具有专业特色、专业知识和专业属性的知识体系,而不是当前“过于功利或实用性”的设计与安排。其设置原则应该有利于促进学科建设和提升本硕博教育阶段的识别度,有利于学生毕业时跨学科选择研究方向,有利于拓宽就业渠道和职业选择范围。
研究生阶段,按照“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两个发展方向进行规划、设计和安排。遵循办学规律,明确培养目标,采用不同的办学模式和办学路线。在“专业学位”建设方面,方向要更加集中,方案更具针对性,融入更多教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理论方法,体现出更具操作性的职业化特点。培养目标更加明确,培养计划更加实用,培养体系更加完整。按照《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精神,完善汉语国际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形成完整的、涵盖硕博层级的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体系,以利于更好地服务于事业发展。这不仅是专业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也是为学科建设搭建的一个平台工程。
在“学术学位”建设方面,则应该更加开放,更具广泛性、拓展性和科学性,表现出更加显著的学科知识体系特征。特别是在博士阶段,实施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鼓励和支持“人文社科”学院增设与汉语国际教育相关的学科与专业方向,以双方合作或相对独立的方式,共同享有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资源,开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以及多元人才培养计划。要敢于破除各种“学术篱障”,勇于接受各方“天外来客”,不盲目追求本专业“自娱自乐或包打天下”的极端办学思想。只有宽口径、广基础,才能吸引和集聚更多跨学科、跨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才有能力、有智慧去面对并解决汉语国际教育发展中,诸如“汉语国际教育‘当地化”(李宇明,施春宏2017)、“海外学习者低龄化”(李宇明2018)等各种绕不过去但又非常重要的、“学习内容可能涉及中国高校所有学科”的众多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搭建并完善学科建设的主体结构与整体框架,实现“人才培养、学术团队、科研创新‘三位一体”的建设要求。
在这個问题上,应该有这样一种预期和自信:当“开放办学”成为一种自觉,当“社会参与”成为一种现实,汉语国际教育之事业发展与学科建设的愿景,不仅可以实现“演化均衡”,而且可以进入全方位适应外部环境或条件的“四轮或全轮驱动”模式。或许,这是新时期“学科建设”的一种选择或必由之路。
五、结 语
历史将证明,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作为一项“国家与民族的事业”,汉语国际教育再次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但与之前不同的是,新时期的汉语国际教育不仅要继续做好“事业发展”这篇文章,还要担负起“学科建设”这个重担。士不可以不弘毅,秉承着中华文化的敬事传统,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崔希亮 2015 《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定位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崔希亮 2018 《汉语国际教育的若干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杜占元 2018 《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中国教育报》10月23日,第1版。
冯向东 2002 《学科、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高等教育研究》第3期。
龚 放 2016 《把握学科特性 选准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中国高等教育》第9期。
李 泉 2010 《国际汉语教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李宇明,施春宏 2017 《汉语国际教育“当地化”的若干思考》,《中国语文》第2期。
李宇明 2018 《海外汉语学习者低龄化的思考》,《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陆俭明 2004 《增强学科意识,发展对外汉语教学》,载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编 《第三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科技联合出版社。
陆俭明 2016 《汉语国际教育学科性质与汉语教师应有的素质》,《华夏文化论坛》第2期。
陆俭明 2017 《认清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积极培养称职的汉语教师》,《国际汉语教学研究》第4期。
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 2015 《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晓 山 1988 《中国召开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许嘉璐 2012 《继往开来,迎接汉语国际教育的新阶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张炳生,王树立 2012 《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研究》,《中国高教研究》第12期。
赵金铭 2006 《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推广》,载李泉主编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赵金铭 2008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述略》,《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责任编辑:朱俊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