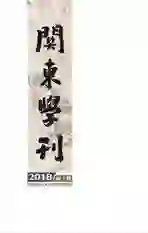论《花间集》中的色彩
2018-05-14王慧刚
王慧刚
[摘要]《花间集》中有大量色彩词的使用,尤其是金、红、绿三色,使用频率非常高,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些色彩词大多都用来描写女性,如果说《花间集》大量描写女性的内容促成了“词为艳科”的观念,那么,可以说,浓艳的色彩是“词为艳科”最直接的视觉感受。当然,具体到每个花间词人,其色彩词的使用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这些差别也导致人们对花间类型风格的评判,因此,色彩词的使用是《花间集》研究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当然浓艳的色彩与晚唐五代的社会风气也是分不开的,这也是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
[关键词]花间集;色彩;风格;女性
《花间集》是后蜀赵崇柞编纂的一部词集,一共收录了十八位词人五百首作品。除了其表现爱情相思、离愁别恨的共同性内容,给人印象较为深刻的还有词中随处可见的色彩。有研究者做过相关统计,“《花间集》共收录词作五百首,对色彩字的使用高达千次,平均每首词使用两至三次,说明花间词人对色彩的表现情有独钟”。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曾云:“《花间》字法,最著意设色。”本文即就《花间集》的色彩问题作探讨分析。
一、色彩与女性及“词为艳科”的关系
《花间集》中的色彩运用是比较多的,诸如金、红、朱、赤、绿、翠、青、碧、银、紫、黄、白、粉、黑等,但使用频率比较高的集中在金、红及绿色系上,美术学上有所谓三原色,即红、黄、蓝,那么金、红、绿也可称为花间词的“三原色”,而且如果把这些色彩词的搭配对象做一整理,即可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大量的色彩词都用在了描绘女性形象上。杜甫在《丽人行》中写道:“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稳称身。”诗人在表现这些丽人的体态之优美、衣着之华丽上,就使用了鲜艳富丽、金碧辉煌的色彩。我们也试看《花间词》中女性的打扮装饰。首先就是头上金光闪闪的发饰,比如钗、钿、簪等,试看几例:
金雀钗,红粉面,花里暂时相见。(温庭筠《更漏子》)
妆成不整金钿,含羞待月秋千。(韦庄《荷叶杯》)
众中依约见神仙,蕊黄香画贴金蝉。(张泌《浣溪沙》)
碧罗冠子稳犀簪,凤凰双飐步摇金。(和凝《临江仙》)
小鸳鸯,金翡翠,称人心。(顾敻《酒泉子》)
其次是精美的服饰:
新贴绣罗孺,双双金鹧鸪。(温庭筠《菩萨蛮》)
云解有情花解语,窣地绣罗金缕。(韦庄《清平乐》)
春满院,叠损罗衣金线。(薛昭蕴《谒金门》)
叢头鞋子红编细,裙窣金丝。(和凝《采桑子》)
金色代表富贵,通过“金色”来表现女性的富丽是常用的一种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花间词呈现富丽堂皇的艳丽风格,但过多地使用也“适得其反地导致雕绩质实的弊病和穷形极相的小家子气。”所以李冰若说:“本欲假以形容艳丽,乃徒彰其俗劣。正如小家碧玉初人绮罗丛中,只能识此数事,便矜羡不已也。”这样的评价不无道理。
除了“金”色,再就是“红”色了,把“红”色与女性联系起来是再自然不过了,我们常说红颜知已、红粉佳人即是明显的例证,因此花间集中我们可以看到:
须知狂客,拚死为红颜。(牛希济《临江仙》)
红粉相随南浦晚,几含情。(和凝《春光好》)
红腮隐出枕函花,有些些。(张泌《柳枝》)
黛怨红羞,掩映堂春欲暮。(顾敻《酒泉子》)
还可以看到头上的红花、舞起的红袖、身穿的红裙:
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温庭筠《菩萨蛮》)
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韦庄《菩萨蛮》)
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鸭儿。(皇甫松《采莲子》)
可以说和女性有关的一切几乎都能与红色结合起来,比如流下的眼泪称为“红泪”:“坐看落花空叹息,罗袂湿斑红泪滴。”(韦庄《木兰花》)所盖的被称为“红被”:“红绣被,两两间鸳鸯。”(牛峤《梦江南》)所处的居室称为“红罗帐”:“晓来闲处想君怜,红罗帐,金鸭冷沉烟,(毛熙震《小重山》),女性所居的楼也称为“红楼”:“红粉楼前月照,碧纱窗外莺啼。”(毛文锡《何满子》)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再举出。
说到“绿”色,诗词中常见的有绿草、绿树、绿阴之类,但在《花间集》中形容女性也离不了“绿”。比如“闲抱琵琶寻旧曲,远山眉黛绿。”(韦庄《渴金门》)“绣帘垂篆簌,眉黛远山绿。”(温庭筠《菩萨蛮》)等。“传统观念中,女性面部最性感的部位不是嘴唇、双眼,而是眉。……晚唐五代女性画眉主要用黛——一种青黑色的颜料。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云:‘前代妇人以黛画眉,故见于诗词,皆云“眉黛远山”。”,当然这里的“绿”应该解释为“黑”,因此女性的黑发也被称为“绿云”“绿鬟”,试看:“绿云高髻,点翠匀红时世”(牛峤《女冠子》),“绿鬟云散袅金翘”(毛熙震《浣溪沙》)。
南朝江总妻有《赋庭草》诗:“雨过草芋芋,连云锁南陌,门前君试看,是妾罗裙色。”借裙、草同色,希望行人睹景思人,不忘旧情。《花间集》中也常有绿罗裙之意象:“记得绿罗裙,处处恋芳草。”(牛希济《生查子》),“焦红衫映绿罗裙。”(李殉《南乡子》)。
还有一个与绿相关的色彩词也应指出,那就是“翠”,翠的本意应为翠鸟,后来也指绿色,《花间集》中“翠”出现了106次,大多与女性相关,如女性的饰物:翠钗、翠翘、翠钿;女性的头发、眉毛:翠鬟、翠云、翠黛、翠颦、翠蛾;女性的屋室及物品:翠帷、翠幄、翠屏、翠帘、翠据等,女性也被称为翠娥,如“翠娥争劝临邓酒,纤纤手,拂面垂丝柳”(韦庄《江城子》),“一点凝红和薄雾,翠娥愁不语”(牛希济《谒金门》)等。
举了以上例词不单是为了说明《花间集》中色彩与女性的密切关系,还想进而阐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色彩的运用与女性的描写对“词为艳科”观念的促成。
“词为艳科”是一种比较通行的说法,但“它并非古人说的一句话,从词学文献可以证实是现代词学家胡云翼先生于1926年出版的《宋词研究》中关于宋词基本内容所作的理论概括”。但这种观念的形成却是在唐宋时期,有研究者认为:“词体的‘艳科性质是由‘花间派词体观念所决定的。”因为早期的民间词“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而“言闺情及花柳者,尚不及半”。直到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的出现,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词为艳科”的“艳”主要是内容方面的界定,即写艳情,《花间集》主要就是描写男女之间的恋情,而着重点又主要在女性身上,多写上层贵族女性日常生活和服饰容貌,这也影响了后世词作的主流内容及婉约词的正宗地位。除了在内容上的“艳情”,其实还有另一种含义就是“表达上的‘艳语”,,使用炫人耳目的色彩无疑是“艳语”中最惹人注目的部分,这种现象尤以“花间鼻祖”温庭筠表现得最为明显。事实上,诸多学者早已作出过评价,近人李冰若评温曰:“其词艳丽处,正是晚唐诗风,故但觉镂金错彩,炫人眼目。”(《花間集评注·栩庄漫记》)夏承焘则说:“温庭筠词的特色:一是外表色彩绮靡华丽,二是表情隐约细致。”更有研究者认为温庭筠“以他的艳词创作直接开启了晚唐五代香艳的词风,并且奠定了词以婉约为正宗、词为艳科的正统地位。”而从其所举例子来看,色彩的艳丽是温庭筠艳词的首要关注点。
从上文举例可以看出,好用色彩、多写女性不仅是温庭筠词个人的特点,而且是整个《花间集》十八位词人的共同特点,因此“词为艳科”观念的形成虽然不能说是《花间集》的创作起到了决定作用,但至少是起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而大量的色彩运用又是“词为艳科”之“艳”的最直观的视觉感受。“艳”的本意即为色彩艳丽,在表现艳情的内容时刻意使用艳丽的色彩不能不算是一种常见的也可以说是成功的手段。詹安泰在其文中说:“为此等词者,色、味、声、情种种,无一可以忽略,大抵色须鲜妍明艳,味须隽永浓至。”因此可以说,正是因为大量色彩词的使用,使得《花间集》中的女性显得富丽明艳,而大量以这类富艳女性为表现内容的《花间集》促成了“词为艳科”观念的形成,人们在强调“词为艳科”的艳情性内容的同时,最先关注的恰恰是那些色彩斑澜的艳语。
二、色彩的运用与花间词的风格类型
通过色彩刻画女性的艳丽并促成“词为艳科”观念的形成,这是花间词人运用色彩艺术的相同性,但如果具体到每位词人,那么其色彩运用还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也导致人们对花间风格类型的判别。
比如作为花间领袖的温庭筠和韦庄,虽然韦庄的词“在抒写内容上亦不外男欢女爱、离愁别恨和流连光景之类,基调也是‘软性的、宛曲柔美的,与温词无本质差别”,但还是有更多的人指出二人的不同,顾宪融《词论》:“世以温韦并称,然温浓而韦淡,各极其妙,固未可轩轾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飞卿,严妆也。端已,淡妆也。”并把二者作为两种风格流派的代表,比如蔡嵩云《柯亭词论》:“自来治小令者,多崇尚《花间》。《花间》以温、韦二派为主,余各家为从,温派*艳,韦派清丽。”浓与淡、*艳与清丽,可能包含了诸多方面的不同,但通过温韦词作的比照以及前人对二者的评价,则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色彩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对他们风格的评判。
首先要举出的一种情况就是:同样是艳情词,表现男女相思离别的作品,使用色彩尤其是明艳的色彩,比如金、红、绿等就容易浓艳,这一点温词尤为显著,上文已作过论述,而少用或不用此类色彩则会趋向清丽,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温庭筠的《梦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这首小词写思妇登楼怀人,对女性只交待“梳洗罢”,却没有对其本身作更多的描绘,更没有写她是否穿戴色彩艳丽的服装头饰,因此显得空灵疏荡,在以浓艳为主的温词中别具一格,因此有学者说,“或谓温词之风格乃是精美及客观,极浓丽却无生动的感情及生命可见。并举其《菩萨蛮》及《更漏子》为证。然则其《梦江南》(“梳洗罢”)‘无生动的感情及生命耶?‘画屏金鹧鸪是飞卿语,‘斜晖脉脉水悠悠又是何人语?”色彩的运用影响浓淡的评价甚至可以出现在同一首词中,比如温庭筠的《更漏子》: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此词写离情,上片用较多的色彩词,如玉炉、红蜡泪、翠眉等来形容女性的容貌及居室环境即显得浓丽,被认为是“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七)下片梧桐细雨,衬托离情,没有色泽则显疏淡。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八谓:“‘梧桐树(略)语弥淡,情弥苦,非奇丽为佳者矣。”唐圭璋先生也说此词“浓淡相间,上片浓丽,下片疏淡。”
当然我们引用上例不是为推翻温词浓艳风格的断语,因为此类作品在温词作品中相对较少,只是想证明色彩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浓与淡的评价。而韦词被认为疏淡清丽也就是在色彩的运用上与温词不同,比如那首非常有名的代表作《荷叶杯》: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
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小词伤今怀昔,情感真挚,纯用白描,不见色彩,被人评为“语淡而悲,不堪多读。”(许昂霄《词综偶评》)这可能是温浓而韦淡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其次,同样的色彩如果所搭配的对象不同,那么给人浓艳或清丽的感受也是不同的。
通过作品比照,大致可以说,如果用色彩搭配的对象是人物,尤其女性,则会显得浓艳,而如果色彩描绘的是景物,则效果感受就会不同。比如韦庄《菩萨蛮》: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还家,绿窗人似花。
有红楼、金翠羽、绿窗等众多色彩,但因为不是直接描写女性装饰,被唐圭璋先生评为“韦词清秀绝伦,与温词之浓艳者不同,然各极其妙。”(《唐宋词简释》)而另一首《酒泉子》:
月落星沉,楼上美人春睡,绿云倾,金枕腻,画屏深。
同样为韦庄所写,因写美人之绿云、金枕,色彩艳丽,就与温词境界相似了,若评为疏淡则显然不妥。为更好地说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
事实上,仅仅从色彩使用频率来看,温韦二人是非常接近的,我们仍选取使用较多且色彩感较强的金、红、绿为代表作一比较,温词分别为29次、16次、12次;韦词为22次、12次、10次。《花间集》收温庭筠词66首,韦庄词48首,温词比例分别为43.9%、24.2%、18.2%;韦词比例分别为45.8%、25%、20.8%。如果不考虑色彩的搭配对象,我们甚至可以说韦词比温词更加艳丽,但事实并非如此,为节约篇幅,这里仅选取“金”色为例。原因有二:一是金色词无论在温词还是韦词中都是最多的;第二,温词之所以给人以*艳之感,就色彩词来看,主要是运用了大量的“金”色词。比如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评曰:“飞卿惯用‘金鹧鸪‘金鸂鶒‘金凤凰‘金翡翠诸字以表富丽,其实无非绣金耳。十四首中既累见之,何才俭若此?”唐圭璋曾批评其曰:“余则谓飞卿词亦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但碎拆下来,亦皆为零金剩壁。”那么同样使用“金”色最多的韦庄为何没有得到类似的评价呢?这也正是本文需要分析的。
通过总结归类,我们发现,在温词金色共使用29次,其中与女性服饰、头饰,包括用品等明显无关的只有5次:
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杨柳枝》)
金缕毵毵碧瓦沟,六宫眉黛惹春愁。(《杨柳枝》)
两两黄鹂色似金,袅枝啼露动芳音。(《杨柳枝》)
竞把黄金买赋,为妾将上明君。(《清平乐》)
玉连环,金链箭。(《蕃女怨》)
剩下的24次中,其中22次则正如李冰若所说乃“金雀钗”“金缕凤”“金鹧鸪”等富丽的女性饰品。还有2次是与女性有直接关系的,比如居住环境“金堂”,女性所用物品“金鸭”(香炉之类)。当然“竞把黄金买赋”中的“金”并非代指金色,亦可去掉。
而再去比对一下韦庄即可发现很大的不同,韦词中金色直接涉及女性饰物的只有4首5处:
云解有情花解语,牢地绣罗金缕。妆成不整金钿。(《清平乐》)
金似衣裳玉似身,眼如秋水鬓如云。(《天仙子》)
绿云倾,金枕腻,画屏深。(《酒泉子》)
锦浦,春女,绣衣金缕。(《河传》)
其余的或形容物品的珍贵,如金杯:“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菩萨蛮》),“今日送君千万,红缕玉盘金镂盏”《诉衷情》)或物件的富丽,如门额:“细雨霏霏梨花白,燕拂画帘金额”(《清平乐》);或形容柳丝初春淡黄之色:‘旧落谢家池馆,柳丝金缕断”(《归国遥》),“野花芳草。寂寞关山道。柳吐金丝莺语早”(《清平乐》);甚或形容男性所用之物,如“白马玉鞭金辔,少年郎”(《上行杯》),“狂杀游人,玉鞭金勒。”《河传》)这些作品中的“金”色也许给人带来富丽之感但绝不是浓艳,因此,是否可以说,浓艳是浓之色与女之艳结合所带给人的一種直觉感受,韦庄之词虽也写女性之艳情,但少用浓艳之色特别是“金”色描绘其容貌,正如唐圭璋先生所说:“端已写人,不似飞卿一一刻画,而只是约略写出一美人绰约之状态”,所以给人以清丽之感。
另外的红、绿之色同样适用于上述规律,即与女性搭配,如红粉面、红泪、红袖、红袂;绿鬟、眉黛绿等会稍显浓艳,而与景物搭配,如杏花红、红芳、绿槐、芳草绿等更显清丽。
当然还应当指出的是同样是给人以浓艳之感,不同的色彩词引起的感受程度是不同的,比如《花间集》中常见的金钗与翠钗、金钿与翠钿、金缕与红缕、金霞与红霞等,金色以其独特的贵金属之色及代表的富贵的社会意义“抢占”了人们的第一视觉感受。
色彩是如此重要的影响到人们对温韦二人的评价,并进而影响到《花间集》其他词人的流派归属。这里想以李冰若的《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为例作一简单论述。因为“在其汇笺的《花间集评注》中,以《栩庄漫记》的形式表述已见,……几十年来,在《花间集》及五代词的研究中,《栩庄漫记》一直扮演着‘引渡之舟的角色”,上文论述已有引用,在这部书里李冰若将《花间集》分为三派:,《花间集》词十八家,约可分为三派:镂金错彩,褥丽擅长,而意在闺筛,语无寄托者,飞卿一派也;清绮明秀,婉约为高,而言情之外,兼书感兴者,端已一派也;抱朴守质,自然近俗,而词亦疏朗,杂记风土者,德润一派也”,即以温庭筠、韦庄、李珣为三派之代表,但他又说:“李德润词大抵清婉近端己”,因此如果笼统一点,我们根据李冰若的评价可以将花间词人分为温韦两派,而其分派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是“引入画论中的‘设色概念,做出……区分”,即温派浓艳,韦派清丽。
上文我们较为详细对比了温韦二人“金”色词的不同,得出浓艳是“浓之色尤其是金色与女之艳结合所带给人的一种直觉感受”这一粗浅结论,我们试着对比两派其他词人,就会发现,李冰若在评价温派词人(包括牛峤、欧阳炯、和凝、顾复、魏承班、毛熙震)时几乎用了同样的字眼:“浓艳”,而这些词人“金”色词的使用特别是用来形容女性的比例都非常高。惟一例外的是阎选,没有直接的金色词来形容女性,但我们也注意到作者虽评其为“颇近温尉一派”,却没有用“浓艳”一词形容,而是用“侧艳”,阎选词存八首,作品中确有如“粉融红腻”“鬓叠深深绿”“泪飘红脸粉难匀”之类的艳语,这倒反而说明了金色与女性影响到“浓”艳的关联是如何的紧密。
再看韦庄派,作者评价这些词人时常用的字眼是“清”“雅”,明确表明近于韦庄的有皇甫松、薛昭蕴、张泌、牛希济、孙光宪、李珣。这些人使用在女性身上的“金”色词明显少于温派词人,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张泌,但从绝对数来看,也仅有5次,因此李冰若给其的评价是“张子澄词盖介乎温韦之间而与韦最近”。
另有三位词人李冰若并没有明确说应归入哪一派,比如毛文锡,在评其《赞浦子》(锦帐添香睡)时说:“繁丽似飞卿”(《栩庄漫记》),词中确有金炉、翡翠、锦帐之类的字眼,但这类作品比较少,李冰若评价较多或认可的却是其“质直”“匀净”的特点,显然不属温派。鹿虔庡的“秀美疏朗”与尹鹦的“似韦而浅俗”似乎与韦庄更为接近,从色彩的使用上更能说明这一点。
综上,我们用了较多的篇幅对花间二派的色彩运用主要是“金”色作了比较,不管李冰若的评价包括判断是否有偏颇,我们想表明的是色彩的运用确实有较大的影响力。
如果给本小节作一结论,是否可以这样表述:色彩的运用与搭配对象会影响人们对词风的评价,如果色彩运用较少或者色彩所描绘的对象是自然风物,那给人的印象则是清雅或明丽的感受;但如果色彩搭配的对象是人物,尤其是女性,那么就有所区别了。就《花间集》来看,使用较多的为金、红、绿、翠等色彩,其中红色主要描写对象有两种:女性与红花,因为诗词当中一直有以花喻女性的传统,因此可以说红色词的使用至少是很大程度地影响到了《花间集》的艳情性,而对于“金”色词的使用则影响了“浓艳”或“清艳”的判别,至于“绿”“翠”包括其它色彩则是补充,当它只是形容自然景物时偏向清丽,当其配合“金”“红”描绘女性时则偏向浓艳。
三、色彩与感官的刺激及世俗时代的相融
色彩的运用和时代风气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还是先来看“花间鼻祖”温庭筠那首有名的代表作《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孺,双双金鹧鸪。
这首小词写了什么呢?无非是一位女性起床梳洗时的娇慵姿态,全词把妇女的容貌写得很美丽,服饰写得很华贵,体态也写得十分娇柔,仿佛描绘了一幅唐代仕女图。
而如果我们真的对照一下唐代唯一存世的仕女画作品——周防的《替花仕女图》,图中那些贵族妇女的装饰与服饰,比如她们发髻上的金钗、玉饰,甚至插的牡丹花、额前的金钿、浮起红晕的脸庞、红色的罗裙或披风、手拈的红花等等,你就会惊叹于温庭筠词作的写实风格。
沈从文在其《中国服饰史》中认为:“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讲究的用金缕蹙绣……腰系金花装饰的钿镂带……脸上无例外地用黄色星点点额……还有一种贴脸的‘茶油花子,有花鸟诸般图形,平时盛在小银盒内,用时取出,呵气加温,就可贴作面靥,盛行时满脸都是大小花鸟。五代后期还讲究浓眉上翘的倒晕蛾翅眉,头上满插用金、银、玉、象牙或玳瑁制成的小梳。”对比我们之前论述的色彩尤其是金色与女性装饰及服饰地描写,什么“金鹧鸪”“金鸂鶒”“金雀钗”“翠钿”“翠靥”等,可以说,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集》只是如实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服饰与装饰。
然而这种服饰穿着并非到晚唐五代才开始流行,那为什么到晚唐五代才更多地得以展现呢?这可能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时代风气。李泽厚在其《美的历程》中说:“这里(指晚唐五代)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主题已完全不同于盛唐,而是沿着中唐这一条线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晚唐五代)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区别到底何在呢?实际上这乃是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狭小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时代风气的转向把人们的视野拉回到小小的闺房,开始着重关注女性的穿着与装饰,忽略了事功的追求与心境的开阔,剩余的是官能的享受与视觉的刺激。
比如温庭筠生活的唐宣宗时期,虽然史书上称唐宣宗“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新唐书》),并把这一段时期称为“大中之治”,但还是留下“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假其(温庭筠)新撰密进之”的记载。温庭筠的14首《菩萨蛮》,是最具代表性的风格艳丽的作品,不能不说一定程度上是迎合皇帝的兴趣取向而作的。而唐宣宗之后的“懿(宗)、嘻(宗)当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继”(《新唐书》),他们对宴会、乐舞和游玩的兴致远高于国政,饮酒作乐、酣歌艳舞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他们的表率作用下,整个官场、社会都弥漫着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风气,这里不妨引用两首韦庄的诗作为例证,一首是表现唐懿宗咸通时期的社会风气,题目即《咸通》:
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
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一首是表现唐嘻宗时期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家中盛大宴会场景的《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
满耳笙歌满眼花,满楼珠翠胜吴娃。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间富贵家。
绣户夜攒红烛市,舞衣晴曳碧天霞。却愁宴罢青蛾散,杨子江头月半斜。
而到了《花间集》的产地——西蜀,这种风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是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南方出现了一批诸如成都之类高度发达的富丽城市,如韦庄一首词写成都风貌说:
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蝉金雀宝髻,花簇鸣档,绣花裳。(《怨王孙》)一方面是君王的喜好对士人的影响,如蜀主“王衍浮薄,而好为轻艳之辞”,其《醉妆词》云: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樽酒。
这是其享乐奢靡的最好展现,时代风气如此,文人只好追而随之,比如毛文锡,事蜀主王建,官翰林学士,因政治上渴望有所作为,积极进谏,反而被排擠贬滴,甚至全家被抄。“心灰意冷,不再渴望政治上有什么作为了。人后蜀,他专以小词供奉内庭,与时风同流合污。于是与欧阳炯、韩琮、阎选、鹿虔扆一起,被时代称为‘五鬼。”
以温庭筠为“花间鼻祖”的十八位词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大量地描写女性,在描写女性的时候又大量使用明艳的色彩,正是那个时代“性情渐隐,声色大开”(沈德潜《说诗晬语》)的需要,济世抱负的无望、时局动荡混乱使得自上而下沉靡于眼前的快乐和感官的刺激,这可能就是《花间集》色彩尤其醒目惹人关注的社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