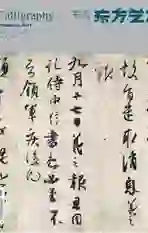书法史学何以“一家独大”?
2018-05-08祝帅
祝帅(博士、北京大学研究员)
闫晓姣(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闰晓姣:当今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凸显出许多问题。在2009年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上,刘恒先生提出的一个观点后来经常被人引用,那就是当前书法史、论研究局面失衡,呈现出一种书法史研究“一家独大”的局面。的确,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书法史与书法理论的研究并驾齐驱,到近二十年来,书法史的研究成果突飞猛进,相对于书法史,书法美学、教育学等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少。你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祝帅:这是目前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书法史发展的速度超过理论和批评,我以为无可厚非,其中有一些深层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新出土的资料越来越多。整个学术界新出土的资料不断涌现,甚至我们都可以说上世纪末以来新出土的材料对于书法研究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二十世纪的出土材料。其中不乏一些意外的收获,比如说曹操墓、海昏侯刘贺墓,各种新出土的石刻、文书材料,更不用说现代高校竞相收藏的简牍,如清华简、北大简等,并且至今还未被完全整理。2010年我去吐鲁番博物馆参观,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博物馆,它的收藏序列里面有文书一类,并且文书的数量相当可观,甚至有更多的文书还未被整理展出。此外,不只是无名氏书法,也包括一些著名书法家的作品和资料,很多是此前书法史上没有记载的,比如1997年出土颜真卿的《郭虚己墓志铭》,还有2009年出土的《冯承素墓志铭》等。对这些新出土材料的考释、辨伪、研究,毫无疑问适合用史学而不是理论的方法来进行。
第二个原因是学术潮流的影响。在今天的二十一世纪,整个文、史、哲学科相对边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相对好一些的就是史学。一方面,这是因为整个学术界的兴趣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美学热”转向了具体而微观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海外中国史学研究得到了很大的进展,这方面以前我们很少关注。八十年代谈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是郭沫若、范文澜、邓广铭、周一良这些人,但今天毫无疑问最炙手可热的中国史学家是美国的汉学家。这样的变化,使得史学相对保有一定的活力,也使得书法史研究可借鉴的东西比较多。
第三个原因是书法教育的蓬勃发展。教学和课程设置的需要,客观上使得对书法史的研究出现了一种需求,即大量需要书法史的教材,这也使得从事书法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多起来。这也是促使书法史成果数量增长的原因之一。
闫晓姣:既然书法史发展如此迅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否也应该由此带动和促进书法理论的发展?据我所知,当代许多书法理论家为此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探索。越來越多的理论家抛弃了对于书法史的就事论事,或考据,或编写年谱,转而探索书法研究的内在理路。他们最关心的不是生卒年或收藏地,而是“问题意识”。而在研究方法上,书法史和书法理论互为补充,这些探索本身是否能够让书法理论有所提升?
祝帅:我并不认为今天书法理论的研究毫无进展。我们今天的书法理论研究和八十年代的书法理论研究不一样。表面上看今天的书法理论研究数量少,但是今天的书法理论研究在质量上比八十年代的书法理论研究有提升。对于八十年代的书法理论研究也不能过于美化。虽然成果很多,但是有价值的成果非常少。八十年代的书法理论研究,照搬哲学、文学理论研究的痕迹比较明显;书法美学重复建设,缺乏思想原创性;谈书法文化的文章大多大而空,言之无物。尽管成果的数量不如史学那样集中,但应该看到书法理论在新世纪以来也是有所发展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书法史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关注理论,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理论的需求。这说明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甚至历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问题化的倾向。过去的书法史研究看的“是什么”,现代的书法史研究谈的则是“为什么”。如祁小春的《王羲之十七帖汇考》,不是做一部“十七帖注释”,而是研究诸如“晋代人的手札为什么第一行几月几号写的特别大,后面写的特别小”“十七帖为什么没有几月几号”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建构。像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提出“冲击一反应”模式,我自己写的《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中就加以了借鉴和利用: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本书法学术史的著作,但其实提出了“西学东渐促使中国书学发展转型”这一理论议题。又如李慧斌的著作《宋代制度视阈中的书法史研究》在史学研究中借鉴了“祖宗之法”“唐宋转型论”等前沿理论。这些成果都使得历史研究中理论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理论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历史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了。
第二,是关于书法本体阐述机制的研究。这方面成果数量少,但质量高,以邱振中教授的系列研究成果为代表。邱振中在二十一世纪以来发表了几篇非常重要的成果。尤其是《人书俱老:融“险绝”于“平正”》和他正在撰写的通过形式分析方法对字结构研究。这两篇文章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方向一一不是照搬哲学,而是探讨书法本体研究的阐释方式。这有些像美术史学史上李格尔和潘诺夫斯基所做的工作,即把美术史学从一般的哲学人文科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和传统的历史学、哲学拉开距离的独立的学科。既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显然它就不能全用哲学的理论,要有美术史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美术史家寻找到的和哲学不一样的方法就是图像志一图像学。哲学、文学研究的是文本,哲学、文学研究方法叫做解释学,或者诠释学,解释文本有什么深刻的含义。中世纪以降,解释学最早是研究《圣经》的学问,后来又用到文学和哲学的解释上,就是说文本的意义并不是你看到的字面的意义,文本的背后有它非常深刻的象征、隐喻含义。这些象征含义和隐喻含义是需要通过专业的解读才能看出来的。只不过潘诺夫斯基提出的是我们研究的不是文本,是图像。从类似民族志描述性的图像志,到阐释性的图像学把绘画中图像背后所隐含的内涵列举出来,对图像进行深入分析,阐释其内涵。同时,美术史也借鉴了哲学中的另外一套方法,就是形式研究。一方面,通过图像志一图像学阐释作品的内涵,另外一方面关注作品的形式本身,从形式的构成、节奏、韵律、到后来的平面构成、视觉构成的研究,都被吸收到美术史这个学科来。康德早在《判断力批判》中就提出形式自身的纯粹审美价值,美术史学科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以后,形式分析就不再由哲学家来做,而由艺术史家、心理学家来做了。为什么说李格尔、潘诺夫斯基这些人在美术史上这么重要,因为他们把图像学明确为美术史的研究方法。为什么说贡布里希、阿恩海姆重要,因为他们将形式理论引入美术史研究。他们都让美术史越来越体现出独立的研究价值。因为美术史这些独特的资源和哲学不一样,所以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书法史、书法理论也想有这样的思想,也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在理论建设上就不能像八十年代那样照抄照搬哲学、文学,而应该走出自己的路,寻求书法本体的阐释路径。邱振中同时在思想史和形式研究两方面展开思考。在思想史方面,他在“人书俱老”“字如其人”两个陈述上展开思考,揭示看似两句简单的阐释背后隐藏的深刻含蕴。在形式研究方面,他在思考书法的形式分析方法能够给传统的形式研究补充什么样的内涵。在对书法材料的研究中如何使用形式研究的方法,对于美术史界来说还是一个难题。最近我看到巫鸿在《空间的美术史》一书中提到,美术史空间分析的方法应该运用到书法研究中,但显然他没有关注到邱振中的系列成果。邱振中对《乙瑛碑》《张迁碑》等碑帖中的相似笔画和字结构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形式理论研究创新,要比整个美术史研究领域借鉴形式研究的难度大得多。
所以说在书法理论方面虽然数量少了,但质量在提高。现在很多研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做书法史,但是对理论的东西认识越来越比八十年代深化了。八十年代很多人大而空谈美学、文化,到了今天,一方面和历史结合起来,一方面和书法的形式研究结合起来,把书法理论做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独立于文史哲,也独立于美术史。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积累性的重要的工作。这些重要工作的成果可能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星星之火。
闫晓姣:近年来,关于书法出版的研究渐次增多。这是因为人们注意到对于碑帖的论调影响了二十世纪甚至至今书法史,其中不乏有些陈词滥调以及立场偏颇的论调。清代以来对碑的热爱,一方面由于出土石刻越来越多,为许多书法理论家提供了新鲜的材料。另一方面,自清中叶开始,书家们对篆、隶、正书的兴趣不逊于对阁帖的热爱。伴随着碑学之兴,碑帖走向了彼此融合的道路,显现出各自的优势与风格,期间既互为补充,又相互排斥。如清代的碑派书家,虽聚焦于碑版,但早期大多受《阁帖》侵染。他们将碑体写出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对帖的使转的熟练把握。因而我们今日所谓的碑派书家,实际上多数是碑帖兼融的书家,只是各自侧重点不同。这一点上,清代书论偏重于碑,而二十世纪的书法理论已经理清了碑帖彼此的审美范畴。在此基础上,你认为怎样在“碑帖二分”之外来描述和把握二十世纪以至当下的书法风格?
祝帅:的确,近年来书法研究还有一个取向,那就是从社会科学的理论中借鉴了越来越多的内涵,书法出版就是这种书法社会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关于碑帖的研究就和社会科学里的传播学、出版史、出版理论的研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传播学里面一些关于编码、解码、虚拟、复制的理论,对我们分析书法中的碑帖的认识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一个前沿的倾向就是,书法理论对于书法出版的研究开始借鉴传播学的理论来反思我们过度依赖媒介的后果。这方面我也写过文章,也是这些年来书法史和书法理论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书法出版目前渐次形成一个学科热点。一个关于古代书法出版物的研究,例如关于刻帖研究举办了多次专题研讨会,包筠雅关于四堡书法出版物的研究和方波关于明代类书的研究也发表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另外一个是关于版刻书法的研究,祁小春写过版刻书法研究的重要著作。书法出版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给我们思考碑学与帖学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过去,康有为提倡碑学,原因之一就在于“帖学大坏”。但今天情况不一样了,精美的印刷品和电子图片,似乎扫清了我们学习帖的技术障碍。可事实如何呢?传播学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虚幻的,这是我们和传统社会一个很大的不同。与传统社会面对面的交流相比,现代社会损失了很多真实性和情感。传播学家霍尔有个“编码与解码”的理论,提出现代的传播技术和传播工具是一种编码工具,法兰克福学派的先驱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就提出,原作是有神韵的,而复制品无法传达这层神韵。它是经过现代复制技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而出现的,今天再精美的印刷品、电子文件放大一看,也逃不过油墨、像素、点阵。也就是说,其实你看到的是一个模拟的影子,一个虚假的幻像。我们以前是对照刻帖拓片或原作去临摹,今天对照的是编码解码后的影像去临摹,这将会产生一系列想象不到的后果。二十一世纪初,陈振濂曾撰文反思展厅的后果,反思“展厅效果”。近些年来,学术界开始反思印刷的后果,看着好像根据很高级的印刷或电子范本临帖就更接近于原作了,实际上很可能恰恰相反。今天很多人写“二王”,看似写二王很像,但就是缺少神韵。因此,借助传播学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对今天的“技术风”提出更深刻的反思。
闫晓姣:二十世纪对于书法的理解与古人有诸多不同,这种转变受到了印刷的制约,字如其人的品评范畴。印刷厂内调色取决于出版科工作人员的审美,往往一幅闲远雅致的书法作品,被制作成有着清晰轮廓,充满严肃感的书法作品。这样出版物提供给大众的感觉完全又是另一种審美。曾经专门访寻到了位于甘肃成县的《西狭颂》,需通过锁链到达悬崖半壁之上,所见刻石真容令人惊异,绝非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印范本所体现的那样“粗旷雄强”,更多的感觉却是“圆润细致”,这种圆润一体现在一千九百多年的半玉化峭壁凸显出的润泽,二则由于字的大小匀称,章法中见书韵,满壁高古之气。这种“细致”更多的是从篆隶线条边缘所体现出来的线质具有强烈的细腻感。也就是说,无论从笔法、墨法或章法来看,印刷品与原作的差距甚至颠覆或者误导了一批书法学习者,印刷的临摹范本中是否提前注入了出书人员们审美的不同因素。对此,书法史研究应该如何应对?
祝帅:这也是通过媒介的后果之一。放大缩小这是二十世纪才有的。举个例子,《经石峪》-直在,二十世纪以前的没有人去学,但是二十世纪以来,很多入学《经石峪》如李瑞清、李叔同等都从中受益。因为二十世纪照相制版印刷技术可以轻易的放大缩小。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的,就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书法史里形成的一种新的研究趋势,暂时可以叫做“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清代以前,包括二十世纪上叶,书法史写作主要是根据文献研究来写作的,祝嘉的书法史就是这样。但现代学术非常重视实地调查。在此影响下,书法研究中也形成了一些新的学科,比如书法地理学,现在包括德国学者雷德候在内的一批人都在从事书法地理研究,他们通过“访碑”等形式关注书法在环境中的呈现。还有书法人类学。人类学的方法就是民族志和田野调查。二十一世纪以来关于书法人类学的调查越来越多,邱振中主持的兰亭论坛中好几次谈到日常书写的问题,也有很多书法人类学调查的文章。日本学者关于书法人口的调研,我自己到军营、书法之乡展开的调研等,都属于此类。人类学田野调研的方法也是为了摆脱单纯依赖印刷品与文献的弊端,即不只关心书法名家名作,也关心书法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这种研究取向,也是受到了文化史等“新史学”的影响。此外,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也给书法史研究提供了启发。人类学、地理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越来越多的在书法学得到应用,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书法史的写作范式。
闫晓姣:我们知道你主要从事书法学术史的研究。那么,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如何来描述和把握二十一世纪以来这些年书法研究领域的学术进展?
祝帅:二十一世纪中国书法研究有很广的取法视野,可以说是建筑在三种书法研究传统基础之上的。这三种传统分别是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日本的书法史研究以及欧美的书法研究。这三种学术传统共同支撑起二十一世纪最初二十年中国书法研究的面貌。中国传统方面不必说。日本方面,八十年代我们对日本书法知之甚少,大概只有陈振濂翻译的榊莫山《日本书法史》、卢永璘翻译的中田勇次郎《中国书法理论史论》等著作。但现在通过留学日归来的一些学者的引介和国际交流,以及对内藤湖南、西川宁等日本学者著作的译介,使得“京都学派”等日本书法研究被中国所熟知。关于西方,八十年代我们只关注到蒋彝、林语堂等人,而近年来,外国人对中国书法的研究越来越多,雷德候、柯律格、乔迅、石慢、倪雅梅等海外汉学家的书法研究为国人所关注、译介,因而西方的书学传统也进入到中国书法研究的视野。但是,学术传统的传承借鉴是一个方面,如何在传承和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融合与创新,提出新的理论范式、流派和方法,还是摆在书法研究同仁面前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