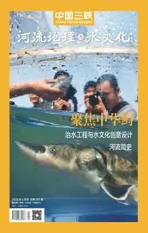保护这条鱼,故事还在讲述
2018-04-26孙钰芳制图李雨潇编辑吴冠宇
◎ 文 |孙钰芳 制图 | 李雨潇 编辑 | 吴冠宇

刚出生几天的中华鲟幼苗 摄影/黎明
电影《大鱼海棠》讲述了一个女孩冲破困难与阻碍,帮助一条拇指大的小鱼成长为大鱼,并使它回归大海的故事。中华鲟的研究和保护,与这个故事有着相似的感动,几代科研人员攻破一个个技术难题,使得小小受精卵成长为大鱼,放它们回到长江、东归大海。36年的研究,第60次放流,保护这条鱼,故事还在讲述着。
中华鲟人工繁殖及保护历程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华鲟是大型经济型鱼类,据统计,1972年至1980年期间,长江全流域成年中华鲟的年均捕获量为517尾,相对稳定。1981年,葛洲坝截流,当年湖北一省捕捞中华鲟800多尾,是多年平均捕捞量的5.5倍,1982年捕捞量更是高达1163尾。过度捕捞使中华鲟的数量大幅减少,这引起了国家主管部门的关注。1983年,国家禁止中华鲟的商业捕捞,并严格限制人工繁殖科研用鱼。
1982年3月8日,水利部发文成立了三三〇工程局水产处(中国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前身),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完善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技术,并进行实验性生产,网捕中华鲟过坝,使鲟鱼在上游产卵场孵化幼鱼,开展中华鲟生态习性的研究”。这是我国第一个与大坝建设有关的鱼类人工繁殖放流研究机构,正式开启了中华鲟人工繁殖与保护的的大门。
1984年,科研人员将从葛洲坝下捕捞的成熟亲鱼运到黄柏河基地,利用雄鱼脑垂体催产成功,孵出20万尾鱼苗,开启第一次放流。
1985年,中华鲟人工繁殖技术中,利用人工合成激素代替脑垂体进行催产实验获得成功,从此,不必为获得脑垂体而捕杀野生中华鲟。
1984年至1987年,共催产21尾中华鲟,成功18尾,这四年共放流各种规格中华鲟77.7万尾。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并于次年3 月施行,中华鲟被列入我国首次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定为一级保护物种。
1995年,中华鲟研究所在国内率先突破大规格幼鲟的培育技术,将规模化培育幼鲟的成活率提高到70%以上,幼鱼的成活率大幅度提高。
1997年,符合中华鲟营养需要的人工饲料研制成功,使幼苗不依赖饵料进食,这大大提高了中华鲟培育的数量和放流鱼种的规格。
2000年,中华鲟活体无创伤取卵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结束了为繁殖而牺牲雌性亲鱼的历史,这使亲鱼在产卵康复后又可重回长江。
2009年,世界上第一尾全人工繁殖的子二代中华鲟在中华鲟研究所三峡坝区基地诞生,当年,产后亲鱼的康复技术成熟。
此后,全人工繁殖连年获得成功。
中华鲟全人工繁殖研究的成功,使得中华鲟的物种保护摆脱对野生中华鲟资源的依赖,并使大规模人工增殖放流成为可能,为保护中华鲟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华鲟放流现场,两名抬不动中华鲟大鱼的小志愿者,模仿大人,抬着中华鲟保护宣传海报,走向长江边 摄影/柳向阳
60次、500多万尾,放流由粗放走向科学
从1984年第一次中华鲟放流至今,已有34个年头,总计60次,累计放流各种规格中华鲟500多万尾。回顾放流史,中华鲟的物种保护技术、监测跟踪技术不断更新、改进,由最初的粗放型放流转变为更加精准和科学的放流。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华鲟放流,放的是“水花”。“水花”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实是身长1厘米左右、刚出膜的中华鲟鱼苗,由科研人员在船上用盆倒进江中。虽然放“水花”是当时国际上的流行做法,但由于鱼苗太小,这种形式的放流,无法监测,更无从知晓这些鱼苗是否能够逃过天敌和自然环境的考验顺利地存活下来,再加上没有标记技术,无法将其与野生中华鲟区分开。现在放流的中华鲟平均约长70厘米,这种大小的中华鲟躲避自然天敌的能力强,放流后存活率高。鱼的个体在变大,放流的方式也由用盆倒入江中,逐渐演变成今天我们看到的从滑道进入长江。
同时,放流的中华鲟梯队结构也在调整,使放流更加有针对性。2016年至2018年放流,都选取的是不同年份繁殖的不同规格的鱼,这样的放流梯队种群优势大,遗传多样性丰富。今年四月是第60次放流,此次放流的中华鲟共500尾,其中7龄和9龄的大鱼有60尾,都是雄性,这是为了调节中华鲟种群雌雄性别比例失衡的现象。
很多人会问,这么多年这么大数量的中华鲟放到长江里,到底有多少能到达河口?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中华鲟研究所不断研究更新了中华鲟监测追踪技术。


供图/中华鲟研究所
目前,放流的中华鲟身上有体外T型标、PIT标记和声呐标记三种,这是见证“追鲟”技术逐渐成熟的几个标记。
最初放流只在中华鲟体外打一个T型标,上面印有研究所的联系电话和鱼的身份编号,如有渔民误捕,可以据此判断是放流的鱼,如果鱼受伤也可联系研究所及时救治。但是这种标记功能有限,且很容易脱落,时间长了,便无法识别。
2007年时,PIT标记开始用于放流的中华鲟。这个标记位于鱼背上,识别距离短,只有误捕后通过扫描才能识别,放回长江后无法跟踪。但此标记不易脱落,长期有效,如有中华鲟在海洋生长达到性成熟并返回长江繁殖时,可以通过扫描PIT标记鉴定。
为了对中华鲟进行持续跟踪标记,2014年,中华鲟研究所科研人员开始在部分放流的中华鲟体内植入声呐标记,通过标记追踪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可以对各江段中华鲟的数量变化、游速差异等等进行了解、分析,探寻个中原因。这种标记一般打在100厘米以上规格的鱼的腹部,其接收范围约1000米,当鱼游经接收器接受范围可以自动记录接收信号时间,从而推测中华鲟洄游过程。从2014年到2017年,中华鲟研究所在长江干流上设置的监测断面从9个增加至17个,监测覆盖更加密集。
今年的中华鲟放流监测跟踪技术较之往年又有了改进。往年的声呐标只有两到三个月的有效使用期,监测时间短。今年的声呐标为十年有效使用期,如果在一些即将成熟能进行生殖洄游的中华鲟身上植入这种声呐标记,那么就很有可能在它洄游时监测到。今年放流的中华鲟中植入十年声呐标记的共有50尾,全是雄性中华鲟,雄鱼相对雌鱼来讲性成熟期短,这样就有可能尽量早地监测识别到洄游中华鲟。
中华鲟监测追踪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让我们能逐步解答公众有关中华鲟的提问。“根据近年的追踪数据看,大鱼一般20天左右就可以游到河口,放流的鱼到河口的成活率约为53.7%。” 中华鲟研究所水生态修复研究室副主任姜伟博士介绍。
多种标记手段相互补充,使得“追鲟”工作有迹可循。这些数据的汇总也有利于后续研究,为中华鲟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长江大保护,开启种群恢复的希望
古老的中华鲟历经沧海桑田,从远古走到现代,它见证了地球的变迁和人类的诞生。虽然中华鲟人工繁殖技术日臻成熟,但其生存现状不容乐观。
在葛洲坝下游产卵场,2013年至2015年三个年份未监测到中华鲟产卵。2017年,同样是只监测到中华鲟洄游来到产卵场,但是没有监测到它们产卵。那么中华鲟不远千里从大海洄游到葛洲坝,到底有没有产卵?如果产卵了为什么监测不到?姜伟博士解答了这个问题:一是,中华鲟的雌雄比例严重失调,根据2008年科研捕捞监测的数据显示,雌雄比例为7∶1,现在十年过去了,这一比例根据推断可能还会加大,这样即使雌鱼洄游,没有雄鱼刺激也无法产卵。二是,洄游的中华鲟数量本身很少,例如去年只监测到22尾,这样小众的数量本身的产卵总量小,监测到的概率也就小。第三,中华鲟即使产卵,卵分布在江底的面积只有几十到上百平米,呈细长条状,与面积巨大的产卵场相比,面积很小,不易监测。
从长江口洄游到产卵场近一年半的时间,成年中华鲟是不摄食的,它在海洋中进食、生长、积累脂肪,为它溯河洄游做能量准备。近多年来,近海开发、过度捕捞使得底栖生物减少,影响到中华鲟的摄食,没有足够的食物会影响到中华鲟的脂肪积累,进而影响了它在溯河洄游中的性腺转化,在抵达产卵场后,自然会出现鱼卵质量差、数量少、甚至不产卵的情况。加之,航运、污染、误捕等因素,中华鲟生存情况严峻,种群繁衍岌岌可危。
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一些小小的希望。2014年葛洲坝产卵场虽然没有监测到中华鲟产卵,次年,却在长江入海口发现了上千尾中华鲟幼苗,这表明中华鲟可能在长江的其他江段产卵,也可能在葛洲坝产卵场产卵,并未监测到。2017年,同样在河口发现了野生中华鲟幼苗。
与其他种群的功能性灭绝相比,中华鲟无疑是幸运的,保护这条鱼的故事,已经讲述三十六年,如今“长江大保护”的提出,让未来还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下去。姜伟博士说:“我们寄希望于未来长江全流域以及近海生态环境的改善,整个大环境恢复好了,只要有人工种群在,中华鲟就能继续繁衍,即使数量增长速度缓慢,但依然会是恢复野生种群的希望,毕竟野外的大环境有着无限可能。”
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共分布鱼类416种,其中纯淡水鱼约350种。有约177种为长江特有种。保护长江水生生物,修复水域生态,事关长江经济带的健康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长江大保护为中华鲟种群恢复开启了希望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