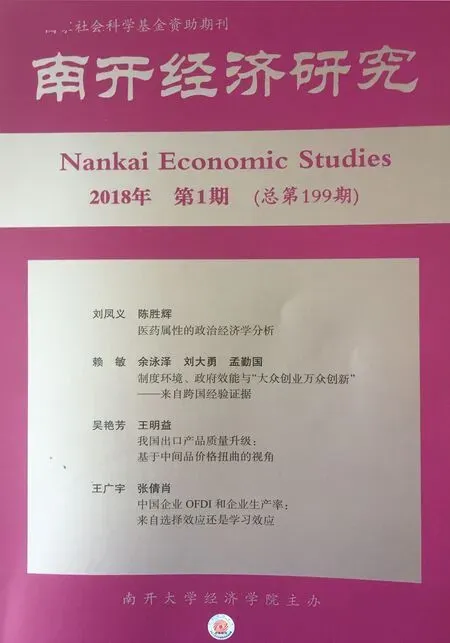进口行为与企业生存
——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2018-04-25李淑云许家云
李淑云 李 平 许家云
一、引 言
企业发展不仅关系到企业经营者及工人的切身利益,从宏观上看还关系到国民收入、就业水平及社会稳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言而喻。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出了致命弱点:中国企业的生存时间普遍比较短暂,特别是中小企业。据国家工商总局2013年的《全国内资企业生存时间分析报告》显示:有近五成企业年龄在 5年以下,且企业成立后 3年至 7年为退出市场高发期。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深,我国企业不断融入国际市场,贸易活动日趋活跃。这虽然为我国企业生存发展带来机遇,但也给予我国企业一定冲击,特别是目前中国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企业生存压力加大。因此,如何提高企业生存概率、稳固企业生存发展,不仅是企业经营者首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政界及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话题。
据商务部贸研院2016年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形势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和重要设备等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如,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达 2.46万亿元,同期增长 1.4%,。企业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使用这些高科技产品能够提高自身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那么,企业对这些高科技产品的进口能否降低企业生存风险?该《报告》还指出,我国对大宗商品进口量持续增加而进口价格普遍下跌,不仅节约外汇支出,且为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收益。如,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铁矿石增长 9.1%,,原油增长 14%,煤增长 15.2%,铜增长11.8%,;同期,我国进口价格指数总体下跌5.3%,。近年来,用工成本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税收增加都困扰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大量原材料的进口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能否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延续企业生存?进口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企业生存?此外,由于企业在研发水平、融资能力、企业规模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且企业进口的产品也因产品类型、产品来源国的不同,产品在技术含量、产品质量等方面也存在异质性。那么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是否受企业异质性或产品异质性的影响?迄今为止,鲜有学者对上述问题给予解答。
本文着重从上述问题出发研究进口与企业生存之间的关系,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往研究并未充分重视到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本文从企业进口角度出发,研究进口①本文研究的企业进口行为指的是企业对投入品的进口,不考虑企业对消费品进口,仅包含资本品进口与中间投入品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其次,将进口行为划分为进口倾向、进口强度和进口持续时间三个维度,更全面地检验进口行为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再次,本文针对企业异质性及产品异质性两个方面深入考察进口对中国企业生存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研究旨在为我国微观企业降低生存风险、延长生存时间提供解决路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生存分析最早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研究中,随着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展,逐渐被经济学家应用于经济领域。Jovanovic(1982)最早将生存分析模型引入企业生产领域,发现企业规模及年龄相对大的企业其生存风险相对更低。随后各国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利用生存模型对影响企业生存的众多因素展开研究。比如,Audretsch(1995)、Coad等(2016)认为研发活动能够提高企业存活概率;Ferragina和Mazzotta(2014)研究了企业所有制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发现相对内资企业,外资企业所面临的生存风险更大;Stucki(2014)、Görg和Spaliara(2014)探究了融资约束对企业生存的影响;而Toraganlı和Yazgan(2016)研究了汇率变动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并指出,实际汇率的变动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存活概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企业生存引入国际贸易领域,但大多关注在企业出口行为对企业生存的影响,鲜有学者关注到进口行为的影响。例如,Bernard和Jensen(2007)对美国、Baldwin和Yan(2011)对加拿大及Görg和Spaliara(2014)对英国的研究都发现企业的出口行为能够显著地降低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于娇等(2015)利用中国企业数据研究发现,总体上企业出口行为有助于提高企业生存概率,但是过度出口也会对企业生存产生负面影响。Namini等(2013)对智利的研究却发现,出口虽然在一定程度提升企业的生存概率,但是随着出口范围的扩大,企业生存概率降低,而中间品进口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生存概率。López(2006)认为,出口企业只有在同时进口中间投入品时才能提高企业生存概率,出口活动本身并不能降低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López(2006)的研究凸显了企业进口行为的重要性。接着,Gibson和Graciano(2011)针对智利的研究也发现相比非进口企业进口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更低。由此可见,如果忽略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可能会造成企业出口行为与其生存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出口对企业生存作用的高估。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本文将进口影响企业生存的机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口数量效应。企业对投入品进口可以节约生产成本,为企业实现持续经营创造成本优势。一方面较之国内市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更为激烈,同类产品企业成本加成较低,因此从国际市场上引进的中间投入品或资本品的价格可能比国内市场上更低,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Wagner,2013);另一方面企业对国外多样化投入品的引入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迫使国内同类投入品价格降低(Gibson和Graciano,2011),进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同时,企业因使用国外处于世界知识和技术前沿的中间品,可以从中学习新知识和先进技术,促进企业改善生产活动(Bas和Strauss-Kahn,2014),进而降低企业生存风险。企业对国外投入品进口量越大,就可为企业节约越多的生产成本,同时获得技术外溢效应也越大。因此,企业进口数量扩大有利于降低企业生存风险。
第二,产品种类效应。企业进口的投入品和国内投入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进口投入品种类的增加丰富了当地企业生产投入的种类(Ethier,1982;Halpern等,2015),拓展了企业异质性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降低了企业生存风险。Fernandes和Paunov(2013)研究发现,企业对国外先进机器设备及投入品投资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新产品的产生和企业存活率的提高。
第三,产品质量效应。生产高质量的产品需要高质量的投入(Hallak和Sivadasan,2013),企业进口的投入品包含着国外先进的技术水平(Blalock,2007),一般比国内投入品的质量高,因而进口高质量的投入品能提升企业的产品质量。产品质量越好,企业市场信誉就越高,产品质量是企业立足于市场的根本和保证,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源泉。此外,Manova和Zhang(2012)认为,多产品企业内部不同产品间的质量差异是生产投入品间的质量差异造成的,企业产品质量差异拓展了产品价格区间及消费者选择范围,为企业持续经营创造条件。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1。
研究假设1:企业进口行为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存风险,且随着企业进口数量的扩大、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及进口产品质量的提高,进口企业的生存风险逐渐降低。
此外,进口还通过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引致出口,进而降低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延续企业生存。首先,进口能提升企业生产效率进而降低企业退出风险。企业生产率体现着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在市场上的生死存亡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生产率水平。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的一些学者从微观企业层面运用实证分析法探究了企业进口与其生产率之间的关系(Amiti和Klonings,2007;Halpern等,2015;李淑云和慕绣如,2017),尽管研究对象和估计方法存在一些差异,但这些研究基本都支持进口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的观点。因此,进口能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进而延续企业生存。其次,企业进口可以引致出口(张杰等,2014)或扩大出口企业生产范围(Feng等,2017),进而降低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企业从事出口活动,一方面企业面对的消费者及产品需求更加多元化,分散单一的国内市场需求波动风险,提高企业存活概率;另一方面出口能够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因在不同产品周期可以通过向不同市场扩展销售量来规避风险进而延长企业的生命周期(Hirsch和Lev,1971;于娇等,2015)。此外,企业出口还可以减少不可抗力(如政变、自然灾害等)给企业经营带来的风险,降低了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许家云和毛其淋,2016)。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2。
研究假设2:进口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引致出口或扩大出口范围进而降低企业生存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进口产品因产品用途、产品来源国的不同,产品在技术含量、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异质性产品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效应可能不同。例如,Löof和Andersson(2010)认为,并非所有来源国的产品都能提升企业生产率,相比从其他国家进口,从知识密集度更高的 G7国家进口,企业生产率获得了更快的提升;Feng等(2017)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会受到进口来源国的影响,相比非OECD国家,从 OECD国家进口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的进口行为与企业生产率、出口之间密切相关,同时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又影响到企业生存。因此,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可能会受产品来源国的影响。其次,进口产品因产品用途不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而不同类型的投入品在技术含量、产品质量等方面也具有显著差异,因此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可能会受进口产品类型的影响。再次,由于企业自身在研发水平、企业规模、融资能力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可能会受到企业异质性影响。因此,我们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3。
研究假设3: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效应受到产品异质性及企业异质性的影响。
三、数据处理、企业生存与风险函数估计
(一)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0—2013年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统计库的合并数据。本文将样本做了以下筛选:(1)删除成立时间无效的企业;(2)删除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总计、固定资产净值大于企业总资产的企业;(3)删除主要财务指标缺失的企业;(4)删除就业人数小于8的企业;(5)删除同一年出现一次以上及无法识别编号的企业。本文使用的第二套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的产品层面交易数据。本文对企业每年的进口数据进行加总处理,即将企业进口数据加总为企业每年年度数据。本文参照余淼杰等(2015)的研究,采用两种方式合并两套数据,根据企业名称匹配及通过企业邮政编码和最后7位电话号码进行匹配,为保证匹配样本中尽可能包括更多企业,本文同时使用以上两种匹配方法,只要企业通过其中任何一种方法匹配成功,就将其纳入观测样本。关于企业生存的计算本文参照于娇等(2015)做法,对样本进行以下处理:(1)选取自 2000年新成立的企业,去掉了左删失观测值;(2)剔除2013年首次出现在数据库中的样本①本文研究的是 2000—2013年持续存在的企业,但是我们无法获知在这研究区间之外的企业的生存状况。如果企业在2000年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么本文无法获知该企业自成立至2000年期间的生存状况,若忽略这个情况就会出现左删失问题。为此,本文选取自 2000年起新成立的企业,去掉了左删失观测值。若企业在研究周期结束时(2013年)仍未退出市场,则又出现右删失问题,而生存分析方法可以更为准确地对含有右删失数据的样本进行估计。另外,本文剔除了观察期最后一年首次出现在数据库中的样本,其生存时间仅为 1年并且为右删失值,容易对估计结果造成干扰(于娇等,2015)。。
此外,考虑到企业进口行为不是随机的,可能是企业“自我选择”的结果(Löof和Andersson,2010),本文首先使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方法②采用近邻1:2匹配。对样本进行匹配以解决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然后,选取匹配成功的样本数据采用 Cloglog生存分析模型进行估计,以考察企业进口行为对企业生存的影响③限于篇幅,匹配过程及匹配效果可通过扫描本文二维码后点击“附录”查看。。
(二)企业生存与风险函数估计
本文参照Namini等(2013)、于娇等(2015)计算方法将生存时间定义为企业i出现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且持续存在直至退出的时间,当企业i在第t年存在而在t+1年消失时即为退出市场④査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调 对象是全部的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这意味着某一企业在数据库中消失的原因,除了真正的倒闭之外,还有可能是由于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规模降到了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规模以下(2010年之前(含 2010年)企业经营规模为 500万元以上,2010年之后企业经营规模变为 2000万元以上)。对此,我们借鉴马弘等(2013)的方法使用企业的所有制类型、营业状态和出现在样本中的初始年份来进一步识别企业的退出、存活状态。如果一个国有企业从样本中消失,直接定义为消亡,而如果一个非国有企业从样本中消失,只有它上一年为非运营状态时才定义为消亡。。本文首先选取生存函数分析法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存分布特征进行初步探讨。企业的生存函数被定义为企业持续经营时间超过t年的概率,表示为:

其中,T为企业保持存活状态的时间长度,hk为风险函数,表示企业在第t-1期正常经营条件下在第t期退出市场的概率。进一步,生存函数的非参数估计通常由Kaplan-Meier乘积项的方式给出:

在上式中,NK表示在k期中处于风险状态中持续时间段的个数,Dk表示在同一时期观测到的“失败”对象的个数。本文采用Kaplan-Meier估计式初步考察进口对企业生存持续的影响。
图1描绘了进口企业与非进口企业生存持续时间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显示进口企业与非进口企业生存时间存在显著差异:相对非进口企业(im=0),进口企业(im=1)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的位置较高,这表明与非进口企业相比,进口企业的生存持续时间相对更长。由此,本文推断,企业的进口行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生存风险,延长企业生存时间。

图1 进口企业与非进口企业的Kaplan-Meier曲线
企业对投入品的进口是否越多越好,过度进口是否对企业生存造成负面影响?为了检验这一疑问,本文对进口企业按进口强度(进口价值/企业总产值)大小①根据按进口强度大小进行排序,高于进口强度平均值的为高进口强度企业,低于进口强度平均值的为低进口强度企业,进口强度为0的为非进口企业。划分为高进口强度企业(dimc=1)和低进口强度企业(dimc=2),再与非进口企业(dimc=3)做对比,采用Kaplan-Meier估计进一步考察进口强度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图2中Kaplan-Meier生存曲线表明,与低强度进口企业相比高强度进口企业的生存时间更长,这说明企业进口行为能够降低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且企业进口强度越高,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越小。

图2 不同进口强度企业的Kaplan-Meier曲线
图1和图2仅是初步描述企业进口与企业生存持续时间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由于Kaplan-Meier估计方法未对影响企业生存特征的其他因素加以控制,用此方法得出的进口影响企业生存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颇。因此,为了更准确地考察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在下文中对影响企业生存特征的其他因素加以控制,利用Cloglog生存分析模型进行更为严谨的估计,并用Weibull、Cox生存分析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模型设定与指标构建
(一)模型设定
利用回归的方法我们可以进一步检查多元连续或分类自变量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并且可以将影响企业生存特征的其他因素加以控制,使进口对企业生存的估计结果更加可靠,本文借鉴Esteve-Pérez等(2013)的做法,进一步采用Cloglog生存模型估计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二)指标度量
为考察进口行为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借鉴国内外已有文献的方法,同时考虑到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年龄及其所属行业、所有权性质、地区等其他因素,本文设定公式(3)中影响企业i生存的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核心解释变量:企业进口行为,本文分别从进口倾向(im)、进口强度(de import)和进口持续时间(timport)三个维度衡量。若企业参与进口则定义进口倾向为 1,反之为 0;进口强度表示为企业进口总额与总产值的比值;进口持续时间为企业i从进入国际市场直至退出进口市场(中间无间断)所经历的时间。
2.控制变量:依据既有的相关研究,实证模型中,本文考虑了可能对企业生存产生影响的相关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生产率(lnLP),用劳动生产率取对数表示;企业盈利能力(profit),用营业利润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来衡量;企业规模(size),用从业人员数取对数衡量;企业年龄(age),用当年年份与企业开业年份的差取对数衡量;出口强度(dex),用企业出口交货值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表示;此外,还加入反映企业所有制特征的国有企业虚拟变量(soe)和外资企业虚拟变量(foreign);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用来反映企业竞争程度,采用二位码行业中企业市场占有率的平方和的对数值表示;融资约束(finance),以利息与企业固定资产的比值表示;企业负债率(debt),用企业负债总额与企业当年总产值的比值衡量;年份、省份、行业虚拟变量。
3.机制变量:为检验进口影响企业生存的作用渠道,我们还需要计算进口产品价值量、进口产品种类及进口产品质量三个指标。
(1)进口数量。本文从海关数据库中通过加总整合得到每个企业每年进口的产品总价值(计价单位为美元),并按照 2000—2013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度汇率均值将其折算成人民币计价进口总值,再按照各地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为 2000年的可比价数额。
(2)进口产品种类。按照Bas和Strauss-Kahn(2014)的做法,我们定义企业进口产品种类数为国家—产品对,也就是说,来自于不同国家相同 HS编码的产品记为不同的产品种类。
(3)进口产品质量。本文采用 Hallak和Schott(2011)的方法计算企业的进口产品质量。具体地,采用进口数量对进口价格做回归取得残差来衡量产品质量。企业层面的产品质量指标表示为:

其中,valueijt为企业进口的 j产品的贸易价值量,而表示企业进口的所有产品的价值量。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选取匹配成功的共 388308个样本,其中实验组样本为 168757个,控制组样本为219551个,采用Cloglog生存分析模型估计进口行为对企业生存的影响。表1汇报了进口倾向对企业生存的检验结果。表1第1列和2列利用2000—2013年的数据检验了进口倾向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其中第 1列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变量im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企业参与进口活动可以降低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第 2列加入全部控制变量,检验结果可见,进口倾向的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这说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考虑到2010年往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统计口径等问题可能对检验结果造成影响,本文使用 2000—2007年的数据做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见表1第3至4列,结果显示,进口倾向对企业生存的影响系数符号及标准误大小未发生本质性改变;而表1第5至6列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Cloglog离散时间模型的估计结果相比,进口倾向对企业生存的影响系数符号及标准误大小也未发生本质性改变。总之,表1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出Cloglog离散时间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很高的稳健性。

表1 进口倾向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二)进口强度与进口持续时间
上文较为严谨地验证了企业参与进口活动可以降低企业生存风险,延续企业生存,但是这一结果仅反映了进口活动对企业生存的平均效应。接下来,我们有必要探讨企业进口是否越多越好?是否存在使企业生存风险降为最低的最优进口强度?进口持续时间是否越长越好?
我们将进口强度由低到高排序,并按四分位数为临界点将企业进一步划分为四种类型(deimτ,τ=1,2,3,4)。im×deim1表示低进口强度实验组,im×deim2和im×deim3表示中进口强度实验组,im×deim 4表示高进口强度实验组。在同一回归模型中可以通过比较估计系数的大小识别出能使企业生存风险最低的最优区间。表2中第 1列显示,im×deim1、im×deim2、im×deim3及im×deim 4的影响系数都为负,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影响系数的绝对值有先变大后变小的趋势,其中im×deim3 的影响系数最大,说明进口强度对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呈现非平稳特征,并非进口强度越强,其对企业风险的抑制效应就越大,当进口强度处于[0.0341,0.11645]之间时,对企业生存风险抑制效应最强。但是,因四个交互项系数大小变化不大,进口强度与企业生存风险之间的“正U型”关系不太明显①从不同进口强度分位数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进口强度第三、四区间的影响系数是大于第一二区间的影响系数的,表明进口强度越高,企业生存风险越低,这与图2中Kaplan-Meier曲线估计结果一致。。
接着,本文在模型中加入进口强度及进口强度的平方项,以检验进口强度与企业生存风险之间是否存在“正U型”关系。表2中第2至3列结果显示,进口强度一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是二次项的影响系数太小。这表明,进口强度与企业生存风险之间虽存在“正 U型”关系,但是只有当进口强度达到足够大时(约大于 0.718②本文利用样本数据计算得出,使企业生存风险变大的进口强度的拐点大约为 0.718,在除去进口企业中的极端值外,进口强度超过0.718的仅有3533家,仅占样本中进口企业总数的2.09%。),才出现使企业生存风险变大的拐点,这与不同进口强度分位数的估计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企业如果过多依赖进口会削弱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动力,不利于企业长期生存发展;二是企业过度进口,长远看来会造成我国企业对国外投入品过度依赖,而国外企业因拥有技术垄断势力,在信息不对称性情况下可能对国内进口企业索取高价,增加企业生存风险;三是我国企业过度进口,造成我国对外依存度过高,企业生存发展极易受到国际政治局势动荡或金融危机的冲击,企业经营不确定性风险加大。表2中第 4列检验的是进口持续时间对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口持续时间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企业进口行为持续时间越长,越有利于延续企业生存。
本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2第5至第8列。稳健性检验结果和Cloglog离散时间模型估计结果相比,进口强度、进口持续时间对企业生存的影响系数符号及标准误大小有所改变,但是未发生本质性改变。此外,鉴于各协变量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本文借鉴了于娇等(2015)、Görg和Spaliara(2014)的处理方法,选用进口相关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进一步消除内生性偏误。在进一步消除内生性偏误后,检验结果依然稳健①检验结果可通过扫描本文二维码在“附录”中查看。。

表2 进口强度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三)作用机制检验
上文研究发现进口能够降低企业生存风险,那进口通过哪些渠道降低企业生存风险?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本文将进口影响企业生存的作用机制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包括数量效应、产品种类效应、产品质量效应;间接效应为进口通过影响企业生产率和出口进而降低企业生存风险。下面本文将进口影响企业生存的传导机制进行量化,并对进口影响企业生存的作用渠道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中直接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进口产品价值量、进口产品种类、进口产品质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随着企业进口产品数量的扩大,产品种类的增加,进口产品质量的提高,企业生存风险逐渐降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将进口产品数量、进口产品种类、进口产品质量加入同一模型后,发现三种效应中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系数最大,其次是进口产品种类的,而进口产品数量的影响系数最小。这表明在进口作用于企业生存的三种直接机制中,产品质量效应起着主导作用。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得以生存,需要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或技术革新,企业对于产品创新不仅包括对新产品的研制还包括对原有产品的改进与换代,而对新产品研制往往投入成本大、风险高且收益小,尤其是在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中,大多数企业对新产品创新是对现有产品改进而非创造全新产品。企业进口投入品种类的增加及产品质量的提高为改进现有产品创造条件,拓展企业新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而延长企业生存时间。表3中对间接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出:加入间接机制的交互项后,与表1基准回归结果相比,im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变小,这表明两种间接效应是存在的;进口与企业生产率的交互项及进口与出口强度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企业进口行为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引致出口进而降低企业生存风险,延续企业生存。

表3 进口影响企业生存的影响机制检验(Cloglog方法)
六、进一步研究
前文的研究仅检验了进口影响企业生存的平均效应,未考虑企业异质性和进口产品异质性的影响。由于企业自身在研发水平、企业规模、融资能力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且企业进口的产品在产品技术含量、产品质量等方面也具有显著差异,那么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效应可能会受到企业异质性及产品异质性影响。下面,本文将分别从企业异质性及进口产品异质性两个方面深入考察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异质性影响。
(一)企业异质性
1.企业研发水平
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可能会受企业研发水平的影响。企业新产品价值一方面体现了企业的研发水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因此,本文将企业新产品价值由低到高排序并按四分位数为临界点,将企业进一步划分为四种类型,在模型中加入进口与新产品价值分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以检验进口对不同研发水平企业的生存风险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4中第1列。估计结果显示:进口与研发水平三个分组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im∗lnrd_q)的估计系数符号均显著为负,随着企业研发能力的提高,im∗lnrd_q 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变大。可能的原因在于,“进口中学效应”的发挥不是仅靠企业简单地进口大量的、种类繁多、质量更高的投入品,还依赖于企业自身的研发水平和对技术的吸收能力。一般来讲,企业研发能力越高,企业对技术吸收能力越强,企业从进口中获益更多,进而延续企业生存。
2.企业融资能力
近年来,企业融资约束在贸易活动中的作用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相对非进口企业,进口企业参与进口活动需要额外垫付一定的沉没成本,因此企业融资能力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进口行为。表4中第2列考察了进口对不同融资约束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三个交叉项(im∗finance_q)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且有变大趋势,说明进口对融资能力强的企业生存风险的抑制效应最大。可能的原因在于企业融资能力越强,企业越倾向于进口,进而降低企业生存风险。
3.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差异也是非常典型的企业异质性特征,本文将企业生产规模分为四等组,在模型中加入进口与企业规模的交叉项,以检验进口对不同规模企业的生存风险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4中第3列。估计结果显示:三个进口与企业规模分组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im∗lnsize_q)的估计系数符号均为负,且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三组im∗lnsize_q 的影响系数逐渐变大,这表明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进口对企业生存风险的抑制效应变大。
(二)进口产品异质性
1.产品类型分组
本文考虑到进口投入品因产品用途不同可以划分为很多种类,而不同类型的投入品在产品用途、产品技术含量、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可能会受产品异质性的影响。BEC分类采用三位数编码结构,把国际贸易商品分为 7 大类,19 个基本类。其中,BEC 代码为“111”、“121”、“21”、“22”、“31”、“322”、“42”、“53”属于中间产品;“41”、“521”属于资本品。考虑到中间产品又包含很多种类,本文按 BEC 分类标准将中间产品进一步细分为三大类,其中“111”、“21”、“31”为初级中间投入品(m1);“121”、“22”、“322”为加工型中间投入品(m2);“42”、“53”为零配件(m3);因资本品仅包含“41”、“521”两个门类,且中国企业对“521”运输设备的进口数量很少,因此本文对资本品(mk)不再进行细分。表4中第4列为不同类型的进口产品对企业生存异质性影响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所有进口产品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所有进口产品都能降低企业生存风险。值得注意的是im∗ mk的系数大于三种中间品的影响系数。这说明资本品的影响效应要强于中间品的影响效应;三种类型的中间品中,零配件对企业生存风险的抑制效应最强,其次是加工型中间产品,而初级型中间品对企业生存风险的抑制效应最小。其原因可能是:与中间品相比,企业资本品的进口对提升企业生产率、盈利能力能起到直接促进效应,而企业生产率是其生存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盈利能力是其生存的基础,因此,进口资本品对企业生存风险的抑制效应最强;三种类型的中间品中,零配件的质量水平最高,拥有的技术含量最多,对企业生存风险的抑制作用最强;加工型中间品因质量水平及技术含量居中,因而对企业生存风险的抑制效应居中;而初级型中间品因其质量水平及技术含量最低且进口产品种类单一,对企业生存风险的抑制效应最小,但企业对初级产品的进口能弥补国内生产要素不足的劣势或者节约企业生产成本,也能降低企业生存风险,延续企业生存。
2.产品来源国分组
鉴于不同来源国的产品可能对企业生存产生差异化影响,本文将企业按进口产品来源国进行分组检验,分为从 G7国家进口(g7)、从 G7国家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进口(dexg7)、从欠发达国家进口(ding)。检验结果见表4中第 5列,结果显示,im∗g7、im∗ dexg 7、im∗ ding的影响系数都显著为负;从影响系数大小来看,im∗g7的影响系数最大,其次是im∗ ding,im∗ dexg7的影响系数最小。这说明不论是从发达国家进口还是从欠发达国家进口产品,都有助于降低企业生存风险,但是从G7国家进口的产品对企业生存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而来自除 G7国家之外其他发达国家的产品对企业生存风险抑制作用最小。可能的原因在于,从知识密集度更高的 G7国家进口的产品,其技术含量及产品质量水平比其他国家的高,从而更有利于降低企业生存风险,延续企业生存时间。

表4 进口倾向对企业生存影响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法深入探讨了企业进口行为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第一,企业进口活动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存风险,且随着进口强度的增大和进口持续时间的增长,企业生存风险逐渐降低。企业进口强度虽然与企业生存风险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但是目前至少有95%,的企业并未达到使企业生存风险上升的拐点。第二,本文还检验了进口影响企业生存的具体途径:直接效应下,企业进口产品数量的扩大、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及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降低企业生存风险,其中进口产品质量起主导作用;间接效应下,进口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引致出口或扩大出口范围进而延续企业生存。第三,本文分别从企业异质性及进口产品异质性两个方面深入考察进口对企业生存的异质性影响。企业自身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进口对企业生存风险的抑制作用会受到企业研发水平、企业融资能力、企业规模的影响,随着企业研发水平的提高、企业融资能力的增强及企业规模的扩大,进口对企业生存风险的抑制效应变大。产品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资本品及中间品中零配件对企业生存风险的抑制作用较强,其次是加工型中间品,而初级型中间品对企业生存风险的抑制效应最小;不论是从发达国家进口还是从欠发达国家进口产品,都有助于降低企业生存风险,但是从G7国家进口的产品对企业生存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
本文的研究为我国现阶段“促进口”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首先,中国企业进口时在注重产品多元化的同时也要注重产品质量,进口高质量投入品是获得生产率提升、延续企业生存的有效途径。其次,当前中国政府在调整进口政策时,应鼓励企业增加对先进机器设备、关键性零配件等高科技产品的进口以加快中国企业的技术升级。再次,我国应该加快完善进口政策,搭建更多平台鼓励企业投入品进口,尤其是鼓励企业多从知识密集度高的G7国家进口,在加大高技术含量投入品进口同时,也要注重企业自身吸收能力的提升。
[1]李淑云,慕绣如.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进口产品异质性的新检验[J].国际经贸探索,2017,33(11):77-92.
[2]马 弘,乔 雪,徐 嫄.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消失[J].经济研究,2013(12):68-80.
[3]魏 浩,赵春明,李晓庆.中国进口商品结构变化的估算:2000—2014年[J].世界经济,2016,39(4):70-94.
[4]许家云,毛其淋.中国企业的市场存活分析:中间品进口重要吗?[J].金融研究,2016(10):127-142.
[5]于 娇,逯宇铎,刘海洋.出口行为与企业生存概率:一个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5(4):25-49.
[6]余淼杰,李 晋.进口类型、行业差异化程度与企业生产率提升[J].经济研究,2015(8):85-97.
[7]张 杰,郑文平,陈志远.进口是否引致了出口:中国出口奇迹的微观解读[J].世界经济,2014(6):3-26.
[8]Amiti M.,Konings J.Trade Liberalization,Intermediate Inputs,and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Indonesia[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97(5):1611-38.
[9]Audretsch D.B.Innovation and Industry Evolution[M].Cambridge:MIT Press,1995:81-99.
[10]Baldwin J.,Yan B.The Death of Canadian Manufacturing Plants:Heterogeneous Responses to Changes in Tariffs and Real Exchange Rates[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11,147(1):131-67.
[11]Bas M.,Strauss-Kahn V.Does Importing More Inputs Raise Exports?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France[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14,150(2):241-75.
[12]Bernard A.B.,Jensen J.B.,Redding S.J.,et al.Fir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7,21(3):105-30.
[13]Blalock G.,Veloso F.M.Imports,Productivity Growth,and Supply Chain Learning[J].World Development,2007,35(7):1134-51.
[14]Coad A.,Segarra A.,Teruel M.Innovation and Firm Growth:Does Firm Age Play a Role?[J].Research Policy,2016,45(2):387-400.
[15]Ethier W.J.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2,72(3):389-405.
[16]Esteve-Pérez S.,Requena-Silvente F.,Pallardó-López V.The Duration of Firm-Destination Export Relationships:Evidence from Spain,1997-2006[J].Economic Inquiry,2013,51(1):159-80.
[17]Feng L.,Li Z.,Swenson D.L.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s: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7,106:20-36.
[18]Fernandes A.M.,Paunov C.Does Trade Stimulate Product Quality Upgrading?[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2013,46(4):1232-64.
[19]Ferragina A.M.,Mazzotta F.FDI Spillovers on Firm Survival in Italy:Absorptive Capacity Matters![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14,39(6):859-97.
[20]Gibson M.J.,Graciano T.A.Costs of Starting to Trade and Costs of Continuing to Trade[C].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2011,23.
[21]Görg H.,Spaliara M.E.Financial Health,Exports and Firm Survival:Evidence from UK and French Firms[J]].Economica,2014,81(323):419-44.
[22]Hallak J.C.,Schott P.K.Estimating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 Quality[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1,126(1):417-74.
[23]Hallak J.C.,Sivadasan J.Product and Process Productivity:Implications for Quality Choice and Conditional Exporter Premi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3,91(1):53-67.
[24]Halpern L.,Koren M.,Szeidl A.Imported Inputs and Productiv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5,105(12):3660-703.
[25]Hirsch S.,Lev B.Sales Stabilization through Export Diversification[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71:270-77.
[26]Jovanovic B.Sele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y[J].Econometrica: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1982:649-70.
[27]Lööf H.,Andersson M.Imports,Productivity and Origin Markets:The Role of Knowledgeintensive Economies[J].The World Economy,2010,33(3):458-81.
[28]López R.A.Imports of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Plant Survival[J].Economics Letters,2006,92(1):58-62.
[29]Manova K.,Zhang Z.Export Prices Across Firms and Destinations[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2 ,127(1):379-436.
[30]Namini J.E.,Facchini G.,López R.A.Export Growth and Firm Survival[J].Economics Letters,2013,120(3):481-86.
[31]Stucki T.Success of Start-up Firms:The Role of Financial Constraints[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13,23(1):25-64.
[32]Toraganl N.,Yazgan M.E.Exchange Rates and Firm Survival:An Examination with Turkish Firm-level Data[J].Economic Systems,2016,40(3):433-43.
[33]Wagner J.Exports,Imports and Firm Survival:First Evidence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Germany[J].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13,149(1):11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