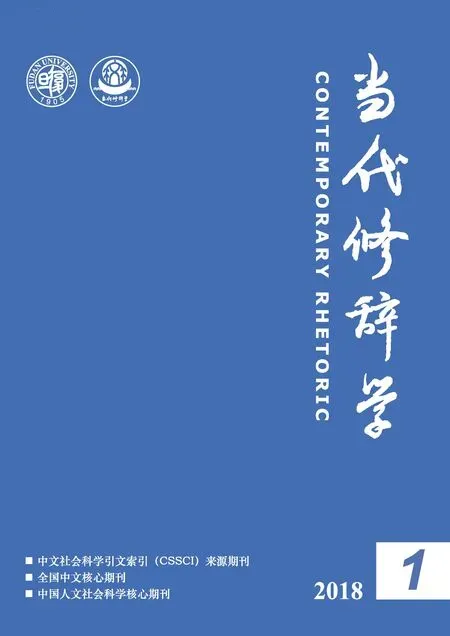当代新兴构式“我A,我B”研究*
2018-04-11温锁林
温锁林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市 300387)
提 要 本文专门研究当代新兴构式“我A,我B”。根据构式的句法和语义特点,概括其构式义为:宣告并凸现群体活动中主体自我的感知与行为的交织并存状态。在此基础上,文章通过分析构式对进入变项成分的句法限制与语义压制,展示了构式的表意机制。最后,对构式的表意特点进行了简要的总结。
近年来,以“我节约,我光荣”“我运动,我健康”等为代表的框式结构“我A,我B”在报刊上被广泛使用。因其话语意图明晰且字句简短有力,通常用于标语口号、宣言号召等,如“我单身,我自豪”“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我承诺,我服务,我创新,我超越”。这些话语与其他标语口号的最明显的区别是,以彰显活动参与者“我”的方式来进行宣传与造势,因而更能起到号召、呼吁、鼓舞宣传、吸引眼球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只有刘禀诚(2008)关注过该格式,刘文从标题格式的角度指出了进入格式A、B的句法属性,标题结构的凝练性所造成的格式中受事宾语隐含和词意偏移等特点,还重点分析了“我A,我B”格式所表达的多种复句关系。不过,刘文并未将该类格式作为一个构式进行整体研究,因而未能把握这类话语以并列关系为最显著的语义表达,更没能概括出该构式的构式义。从“我A,我B”话语方式所采用的并列表达格局来看,该格式将人们按常规理解的多种语义关系一律指定为并列关系,这种整齐划一的强行处置正是该构式最显著的表意特点。而刘文却认为“我A,我B”结构可表达“顺承、递进、因果、并列、转折”等语义关系,忽略了的恰恰是构式整体最为彰显的并列关系。
本文拟从如下角度进行研究:
1. 作为一种新兴构式“我A,我B”的句法特点及其构式义;
2. 构式对进入变项成分的句法限制与语义压制;
3. 构式独特的表意机制;
4. 构式的表意特点。
一、 “我A,我B”构式及其构式义
1. “我A,我B”构式
“我A,我B”构式在形式上有几种变体,大体上可分为双项并列式与多项并列式两类。双项并列式以“我A,我B”为代表,构式中只包含“我A”“我B”两个并列关系的小句,此类双项并列式在该构式中最为常见,可视为该构式的典型。请看如下实例:①
(1) a. 此次庆祝活动为其半个月,包括“我健康,我美丽”女性户外趣味运动会、厨艺大赛……活动。(《河南日报》2014.03.08)
b. 至于发布者,无外乎“我选择,我喜欢”之类消费宣言,名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与普通意义上的广告媒体别无二致,都是旨在发布信息、引导消费。(《新民晚报》2013.08.29)
多项并列式是构式中包含了多于两项的并列小句,形成“我A,我B,我C,…”的多项并列。根据并列项的数目,又可细分出三项并列式(“我A,我B,我C”)、四项并列式(“我A,我B,我C,我D”)和多项并列式(“我A,我B,我C,我D,…”)三个小类。②下面各举两例:
(2) a. 在济南街头,记者看到这样一幅标语:“我当兵、我光荣、我受益”。(中国东平·兵役服务,2013.09.19)
b. 本次运动会的举办,旨在进一步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弘扬“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的风尚,……(人民网·青海频道,2014.01.16)
c. 坚持激发党员活力,设置党员先锋岗,开展以“我参与、我承诺,我奉献、我光荣”为主题的党员承诺活动,……(人民网·党建频道,2013.11.18)
d. 吉水县举办2012年中小学生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比赛体现“我阳光、我健康、我运动、我快乐”的主题,全县13个代表队参加角逐。(《江西日报》2012.12.13)
e. 近年来,大化瑶族自治县……,围绕“我诚信、我选择,我诚信、我受益,我诚信、我光荣”这一主线,把创建“诚信计生·幸福家庭”工作融入人口计生工作全过程。(人民网·广西频道,2013.07.29)
f. 献血者们都怀着“我献血、我健康,我献血、我快乐,我献血、我光荣”和“奉献、人道、博爱”的大爱之心,为襄樊的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人民网·健康卫生频道,2013.02.03)
这些多项并列式,不论是三项、四项或多项并列,都是在双项并列式的基础上增加并列项形成的,而且表达的都是并列的语义关系,差异在并列项的多寡,因此,完全可以把双项并列式“我A,我B”作为典型构式进行研究。根据邵敬敏(2011)关于框架结构的界定,以上例(1)、(2)各句中的“我A,我B”均为框式结构,结构中前后并列的小句相互照应,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框架式结构,具有特殊的语法意义和特定的语用功能,使用起来,只要往空缺处填装合适的词语就可以了。因这类结构是在近十几年来才形成并广泛使用的,本文将其称之为新兴的并列构式。该构式在形式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结构上的框式化。“我A,我B”由不变成分和可变成分组成。两个固定的框架成分一律为第一人称代词“我”,做小句的主语,起着为小句的表述定位和标记的作用;两个变项A和B 均由单词充当。根据这种框式结构的特点,“我A,我B”可以看成是“双项双框式”③构式。结构上的高度框式化排除了任何对框架成分变动的可能性,如果将其中一个“我”替换成“你”,或是换成复数形式“我们”,或是在任何一个小句主语“我”后添加判断词“是”或别的动词,都会改变构式的框式属性,导致“我A,我B”构式的解体。因此,诸如“我创新,你满意”“你安全,我放心”“我是党员,我自豪”“我做乌鸦,我快乐”“我坚强,我感恩,我会更出色”等表达式均不能算作“我A,我B”构式。刘禀诚(2008)正是因没有看到“我A,我B”的构式特性,所以没有明确构式中的变项必须是单词充当的特殊要求,将一些由短语充当变项的小句,诸如“我反思,我能反思”“我写我事,我抒我情”“我声唱我心,我手写我心”等也看成“我A,我B”结构,使得结构内部驳杂不纯,也使得本来具有形式与语义匹配的构式失去了统一的鉴别标准。
2) 较强的能产性。该构式的架构模板可被无限复制,这种能产性充分显示,“我A,我B”作为一种独立表意的“形式—语义匹配体”的构式模板,在语言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获得了某种专属性的注册商标。
3) 构式的压制作用。构式的压制作用具体表现在句法限制与语义压制两个方面。句法限制是显性的,而语义压制则是隐性的。我们看到,尽管动词、形容词、区别词和名词都可充当构式的变项,但是,它们的准入条件必须是单词的身份,这种显性的句法限制表明,充当变项后的成分其原有的句法核心功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如及物动词均不能带宾语、状语,且不能加入与动词相关的时体成分(下例a、b);形容词不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下例c、d);区别词不再表示属性(下例e);名词则不再单纯地表示事物(下例f)。另一方面,变项显性的句法限制又是语义压制的风向标,观察可知,这些变项都经历了隐性的“指称化”的语义演变,即变成了与词类相关的活动或事件的指称。请见下例:
(3) a. 我选择,我喜欢(《华西都市报》2005.09.27)
b. 我欣赏,我追求(人民网·教育频道,2008.08.06)
c. 我健康,我快乐(人民网·游戏频道,2014.01.17)
d. 我充实,我自信(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09.16)
e. 我绿色,我低碳,我环保(《济南日报》2010.08.13)
f. 我单身,我贵族(《中国妇联新闻》2012.07.12)
有关变项在构式中的句法限制与语义压制的详细讨论,请见下文的2.1。
根据以上三点,我们认为,该构式中的框架成分或是构式变项如上的特点,都不能直接从已有的其他结构中推导出来,这是该构式作为一个特定的表意单位的形式表征。那么“我A,我B”的构式义到底是什么?下面我们将结合该构式的形式特征予以展示。
2. “我A,我B”构式义
构式本身虽然具有意义,但是构式的意义并不是其组合成分语义的简单相加,而是由构式作为一个形义匹配所表达的整体意义。但是,我们在强调这种自上(构式)而下(构式成分)的构式义表达特点时,一定不能忽略自下而上的构式义的形成特点,即构式的组成部分或要素对构式义所做的贡献。因此,要理解“我A,我B”的构式义,必须把自上而下的整体把握与自下而上的意义解读结合起来,这是构式研究中必须贯彻的一条重要原则(温锁林、 张佳玲2014)。我们发现,该构式在句法上的几个显著特点正是我们追踪构式义构成的最佳线索。
1) 构式采用的并列复句表达框架。这是该构式在形式上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我A,我B”构式虽对已有的并列复句进行了句法上的改造,两个变项必须是单词就是这种改造最明显地体现。但改造后的构式在形式上仍然保留了并列复句的基本特征,即用逗号来标记两个小句之间的并列关系。这种形式特征是构式义最直接的语义标签,所以,并列关系是“我A,我B”构式义中最显著、最基本的语义表达。
2) “我”使用的唯一性与特殊功能。我们认为,构式中“我”的功能表现在主体凸显与宣告功能两个方面。先看其主体凸显功能。众所周知,人称代词“我”在一般情况下,表示“个人商标”,用作上下文和实际情境的连接(田海龙2001)。然而,“我A,我B”构式中的“我”,往往不代表说话者个人,实际上,它暗含了一个群体、一类人。请看:
(4) a. 通过加大生态环保知识宣传普及力度,我市市民环保意识逐年提升,“我环保我光荣”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人民网·安徽频道,2013.09.06)
b. 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营造出“我廉洁我光荣”的良好氛围。(人民网·安徽频道,2011.08.02)
c. 服务的宗旨意识焕发出来,广泛形成了“我光荣、我争先”的思想共鸣。(《中国共产党新闻》2012.05.07)
d. 以“我创新、我绽放”为主题的北京邮电大学第五届大学生创新成果展示交流会暨创新论坛近日开幕。(《科技日报》2013.05.30)
很显然,上述各例中的构式均用于群众性活动的标语口号,因为是群体活动,按理构式中小句的主语应该都用“我们”,至少不应该排斥,但是,构式却一律以“我”为视点,对“我们”一概排斥拒绝。仅从句法与语义的角度看,这种限定是无理据的,因而是不可预测的,但是,从构式的强制作用来看,以“我”为视点的表述,不仅是构式的“语义标签”,而且具有特定语用功能:将“我”定位为表述的主体,着眼点是群体(“我们”)中的个体(“我”),“我”被置于前景从而得以凸显,“我们”被处理为群体背景起着衬托前景的作用。构式通过凸显个体的方式来反映群体活动,从而极大地增强标语口号的号召力和宣传效果。据此,凸显主体自我应该是构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对比:
(5) a. 我工作,我快乐(《经济日报》2006.05.08)
b. 工作着,快乐着(《吉林日报》2004.10.28)
c. 工作并快乐着(《电子资讯时报》2003.03.20)
上例三句皆表示“工作”与“快乐”这两种活动的并列共存关系,不同的是,a句中采用了“我A,我B”构式,两个小句均以“我”为表述的主体,自我的身份在话语中被着意凸显,b、c两例突出的是“工作”与“快乐”的并列状态,而呈现状态的主体并未明确定位,处于被淡化的地位,需要靠语境才能被激活与确定,这是b、c两例在基本的语义构成上与a句的显著差异。
再看其宣告功能。由于“我A,我B”构式多用于群众性活动的标语口号、倡议宣言等,它是凸显个体的方式形成的群体活动的宣言,是个人化了的集体话语,它放大了个体参与者的感受与状态,增强了标语口号的号召力和宣传效果,所以该构式具有显著的宣告功能。
3) 变项A、B语义的状态化
前文指出,变项A、B在构式中受到了句法限制,进入构式变项位置的成分必须以单词的面貌出现,而且充当变项的成分都失去了该词项原有的核心句法功能。这些句法限制的背后推手,来自构式对变项语义的改造,即变项在语义上都变成了与其词义相关的活动或事件所呈现的“状态”。状态化是变项句法功能的丧失后在构式中获得的语义补偿。
根据“我A,我B”构式语义上呈现出的如上的三个特点,本文将该构式的构式义概括为:“宣告并凸现群体活动中主体自我的感知与行为的交织并存状态”。
下面,本文将结合“我A,我B”构式的构式义来描写与分析该构式的表意机制与特点。
二、 “我A,我B”构式表意机制
要了解“我A,我B”构式的表意机制,必须从构式对变项A、B的特殊要求入手。上文提到,构式的变项A、B以单词为常态,这种特殊的句法要求一定来自构式语义表达的需要。所以,考察进入构式的成分的句法与语义特点,是了解构式表意机制的第一步。
1. 变项A、B的句法与语义性质
1) 变项A、B均为形容词
(6) a. 我诚信,我光彩(《人民政协报》2014.07.04)
b. 我诚信,我吉祥(人民网·浙江频道,2014.03.15)
以上实例中的变项A、B均为性质形容词,按理,性质形容词最容易接受程度副词修饰。但是,进入构式后的性质形容词,在构式的强力压制下,不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也就是说,形容词原本表示性质的程度属性被压制与淡化,而其词性中并不显著的状态性则被激活与强化。状态化与描述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当这些语义上被状态化的性质形容词用于小句谓语的位置时,小句的主语“我”也被认同为状态呈现的主体。以例(6a)为例,构式表达出的是“我是诚信的,我也是光彩的”之意。可见,充当变项的形容词在句法的显性限制(去程度化)背后,语义上其实经历了一个隐性的“状态化”的强化过程。
2) 变项A、B均为动词
(7) a. 我创新,我成就(人民网·江西频道,2012.05.12)
b. 我热爱,我追求,我需要(人民网·文化专题,2007.01.10)
以上例句中变项均为动词,它们在构式中也受到了句法限制。这种限制具体表现为不能带状语和时体成分,即便是及物动词也不能再带宾语。句法功能的显性变化说明,构式中的动词其及物性与时间性的句法功能被弱化与消解,与这种句法功能变化相伴随的是语义上出现的某种细小变化。我们看到,在构式的压制下,动词的语义也由陈述转为指称,即指称某个动词所代表的活动与事件呈现的“状态”。小句主语“我”也被认同为活动或事件的相关状态的呈现主体。联系例(7a)出现的语境,可以清晰地看出充当变项的动词在构式中的语义变化:
(7a’) 该公司还开展“学身边劳模,展青春风采”“我创新,我成就”和“小事做起、奉献爱心”等各种各样的活动,鼓励员工刻苦学习和不断创新。(《人民网·江西频道》2012.05.12)
“我创新,我成就”表达的是,在某个活动中“我属于有创新性的与有成就性的个体一类”,明显地是一种对“我”进行评价与分类的宣言与口号,而不是要陈述“我创新什么与成就什么”这些具体的内容。
3) 变项A、B为不同词类的混搭
充当变项A、B的虽然以形容词、动词为主,但也有名词、区别词做变项的不少用例。因此,形成不同词类混搭的构式自然也以形、动间的混搭为主,形、动与其他词类的混搭为辅。先看形、动混搭:
(8) a. 我工作,我快乐,我微笑,我享受(手机看新闻,2011.03.02)
b. 我磨砺,我阳光,我成长(精品学习网·建军节,2013.08.06)
c.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人民网·辽宁频道,2014.08.23)
再看形、动与其他类的混搭:
(9) a. 我风度,我信赖(搜狐网·男人频道,2010.02.09)(名、动)
b. 我热爱,我参与,我奋斗,我冠军(《保定晚报》2012.07.24)(名、动)
c. 我单身,我自豪(《广州日报》2013.11.11)(名、形)
“我A,我B”构式中大量存在的由不同词类混搭的变项清楚地表明,同一个构式中两个小句中的变项,尽管由不同的词类担当,但构式作为一个形式与语义相匹配的特定的表意整体,一定要对进入变项的句法与语义进行强力的整体化改造与处置。否则,不同词类的句法属性与语义性质就会不相容、不协调,从而造成构式的解体。构式对充当变项的成分的准入条件限制就是,无论变项原来是什么词类,都得在句法上光杆化,为其语义实现“状态化”扫除句法的障碍,可见,这种句法上的高度同一化处理还是语义上的要求与拉动。动词的“去时体化”、形容词的“去程度化”、名词的“去数量化”以及区别词的“去修饰化”等句法处理,都是语义上“状态化”转变的外部表征。
4) 变项A、B为非单词形式
还有一些变项A、B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单词。比如,下例划横线的变项均为动宾短语:
(10) a. 我抒情,我言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07.02)
b. 我有责,我尽责(人民网·福建频道,2014.02.17)
c. 我排队,我让座,我文明,我快乐(人民网·陕西频道,2013.11.11)
从纯句法的观点看,这些“我A,我B”结构似乎不符合构式对变项必须是单词的规定。但是,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看,这类话语无疑是对“我A,我B”构式刻意模仿的结果。我们发现,这些充当变项的成分都是双音节式动宾短语,从外形上看与双音动词非常相像,更何况,汉语中的动宾式双音词(“备战、出厂、收工、求和”等)与动宾短语本来也难以截然分开。再从结构的构式义来看,这类动宾短语做变项的结构与“我A,我B”的典型构式(变项由单词充当)并无二致。故而,本文将上述由动宾短语做变项的构式看作“我A,我B”构式的变异形式。
“我A,我B”构式还有一类由语素充当变项A、B的变体。这类构式中的变项A、B非常特殊,是将一个词一分为二拆开之后,再把拆开的两个语素置于变项位置形成的。例如:
(11) a. 我求我索(《人才开发》1994.03)
b. 我见我闻(《华文文学》1986.02)
c. 我娱我乐(《现代文学(初中读写版)》2005.08)
上例中变项A、B实际是由双音复合词“求索、见闻、娱乐、行动”拆分而得。这种把双音节词拆分成不成词语素并赋予它们以词的句法与语义作用的做法,似乎是违背语法规律的。但这种不合常规的“以语素为词”现象在构式“我A,我B”中却得以合法化,且这种拆分后的语素在构式句法与语义的引导下,仍然能大体表达出原词(拆分前)的意义。可见,构式的压制作用既表现为对变项句法上的限制,也表现为对变项句法功能的引导与释放,使得不成词语素临时衍生出词的用法与功能。这让我们清楚地感觉到了构式的力量。
2. 构式的表意机制
“我A,我B”构式的表意机制集中地表现在两个“强行的改造”上,即对变项A、B 的本身的句法与语义性质的强行改造和对“我A,我B”两个小句的语义关系的强行改造。2.1中已经具体描述了构式对变项A、B本身的句法与语义性质的改造,因为构式所要呈现的是行为主体的状态而非某种具体的活动与事件,所以构式对变项的句法与语义必然附加了允入条件。同时,构式所表达与凸现的是行为主体的感知与行为的“交织并存状态”,故而,构式一定要有所作为,把分句间既有的逻辑关系的表达习惯进行清一色改造,使之背景化,而将新的并列关系通过构式的推力使之前景化,并成为小句关系唯一的解读。我们发现,被背景化了的语义关系有多种多样,下面将以具体的例子来做具体的还原与解说。
1) 因果变并列。按照普通的表达与理解习惯,有的“我A,我B”两个小句间的语义关系应该用因果关系来表达,但在构式中被强行处理成了并列关系,原来的因果关系被背景化。
(12) a. 我献血(因),我光荣(果)(人民网·社会视频,2013.06.15)
b. 我选择(因),我无憾(果)(《北京晚报》2014.01.07)
c. 我奉献(因),我幸福(果),我快乐(果)(《中国妇运》2006.10)
d. 我承诺(因),我践行(因),我光荣(果)(中国共产党新闻网,012.01.09)
e. 我学习(因),我收获(果)/(因),我成长(果)/(因),我快乐(果)(《黑龙江教育》2005.12)
上面背景化了的因果关系尽管复杂多样,有的是一因一果(a、b),有的是一因二果(c),有的是二因一果(d),有的是连环因果(e),而构式却可以完全置这些常规的逻辑关系于不顾,统统加以统一的改造,用并列的方式重新呈现出来,充分地显示着构式的表意“新质”。
2) 条件变并列。即把一般按条件与结果关系理解或表达的关系处理成并列关系,被背景化的条件关系又分多种情况。如:
(13) a. 我学习(条件),我成才(结果)(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10.18)
b. 我学习(条件),我充实(结果),我有为(结果)(人民网·蚌埠政府网,2013.04.26)
c. 我服务(条件),我存在(结果),我创新(条件),我发展(结果)(《中国远洋报》2002.08.09)
d. 我坚持(条件),我拼搏(条件),我胜利(结果)(人民网·关于我们,2006.08.23)
a句“只有A,才能B”是被背景化了的条件关系,因为“学习”是“成才”的必要前提条件。b句被背景化了的是“只有A,才能B、C”,“学习”是前提,“充实”和“有为”是这一前提的结果。c句被背景化了的是“只有A,才能B;只有C,才能D”。一个人只有“服务”,才能表明你的“存在”;只有“创新”,才能“发展”。d句背景化了的是“只有A、B,才能C”,按常规表达,d句应该说成“我只有坚持,只有拼搏,才能胜利”。不过,在构式语义的压制下,上述这些多种条件关系都被披上了统一的并列关系的语义外衣,而作为常规条件关系的表达则被驱逐与淡化,只能凭借人们的理解习惯而浮现于构式义的背景之中。
3) 递进变并列。还有的“我A,我B”构式,其间的两个小句关系在常规的话语中一般都是以递进复句来表达的,而进入构式后,这种递进关系也全部被背景化处理,由构式统一化为显性的并列关系。例如:
(14) a. 我支持,我践行(《大河报》2014.03.03)
b. 我有责,我负责,我尽责(人民网·手机看新闻,2014.02.27)
c. 我承诺,我服务,我创新,我超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07.11)
上述例子中的被背景化了的语义关系其实都是“不仅A,而且B”这样的递进关系。a句的常规的语义关系应该是“我不仅支持什么,而且还要践行什么”;b句的三个小句之间按常规表达应该是“对某事,我不仅有责,而且还要负责,更要尽责”;c句的常规表达是“我不仅要作出某种承诺,还要服务好,更要做到创新和超越”。
4) 转折变并列。有的“我A,我B”构式,前后两个小句的变项,在语义上都是隐性的对立矛盾关系,因而两个变项共现时,在人们的表达习惯中似乎早已根深蒂固为转折关系,但在构式的强力指引下,也被改变成了并列关系。如:
(15) a. 我卑微,我快乐(《中学生天地》2003.01)
b. 我懦弱,我自豪(人民网·动漫频道,2013.04.25)
c. 我单身,我骄傲(人民网·游戏频道,2011.05.04)
d. 我温暖、我厚重,我纠结、我闷骚(《广州日报》2014.01.12)
按照常理,一个地位“卑微”的人,心情很可能是压抑而非“快乐”的,所以说成转折性“我虽然卑微,但我很快乐”是一种常态的表达;同理,“懦弱”之人很难“自豪”起来,故而说成“他虽然懦弱,但却很自豪”才能反映这种矛盾关系;“单身”的人毕竟与大众文化传统习俗(即人到一定年龄应该成家结婚)不太相合,在心理上也很难真正“骄傲”起来,因而说成转折性的“我尽管单身,但我很骄傲”比较适合人们的表达习惯;一个“温暖”而“厚重”的人,本不应该有“纠结”与“闷骚”之感,用“我虽然温暖、厚重,但我感到纠结而闷骚”是常态化的表述。不过,上例中,这类常态化的转折复句都被背景化,在构式的强制作用下表达成了并列关系。
当然,在上面提到的常态化表达中,复句关系的解读可能不止一种,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与理解而见仁见智。比如,例(15c)中的“单身”与“骄傲”之间,因为立足点或文化环境的不同,理解为“因为我单身,所以我骄傲”这样的因果关系也未尝不可。也许正是被背景化了的语义关系本来可能多种多样,而在“我A,我B”构式中却被处理成清一色的并列关系,这种变多样性关系为单一的并列关系的解读的强行语义拉动,或许是构式真正吸引人们竞相效仿的一种原创性动力。
三、 “我A,我B”构式的表意特点
“我A,我B”构式首见于1999年由乒乓名将孔令辉为安踏运动鞋所作的一句“我选择,我喜欢”的广告代言,自此,“我A,我B”话语方式风靡全国。至今,其使用覆盖了文章标题、标语口号、群体活动的主题宣传及广告用语等多个领域。需要是创造之母,特色是构式的生命。作为一种新兴的话语方式能够一炮打响并多年来一直走红,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一定与其特有的表意特点有关。
1. 简洁性与丰富性的统一
构式“我A,我B”是以广告语出现的,后来被广泛地用于标题、口号等。构式的这些使用语域充分地利用了其形式简短与表意核心突显的特点,用最精简的结构装载了丰富的信息,是构式在表意上的一大突出特点与优势。正如前文所示,虽然构式通过表层的语义压制,使得两个小句间只留下了唯一的并列关系,但是,在构式背景化了的语义当中,仍然不时地浮现出人们常规的语义识解,正是这些表面被压制了的语义内容,极大地放大和丰富了构式的语义内涵,抬升了构式的地位。
寓复杂语义于简洁表述当中,在构式对变项的句法与语义的改造中也同样得以体现。在进入构式后,无论是动词、形容词、区别词还是名词,尽管它们原来的词性各异,但是一旦处于变项的位置,它们原有的词类功能都被“洗白”,以统一的状态化的特性呈现。不过,被“洗白”后的词项,其原有的语义仍然呼唤着人们的识解记忆,这是构式表意上寓复杂语义于简洁表述之中的又一特点。可以说,正是这种显性的句法限制与语义压制的矛盾而造成的构式表意上的奇特性与简洁性,吸引着说写者与听读者的注意力,才使得构式具有了独特的表意优势。
2. 言者视点与旁者视点的统一
所谓言者视点,就是从说话者自己的角度来观察与表达;而旁者视点,则是从旁听者的角度来观察与表述。任何语言中都存在这两种表述视点的差异,比如同一个说话者在指称同一对象时可用言者视点的“我妈”和旁者视点的“你大娘”。当言谈对象不是指代人或物,而是陈述一个活动或事件时,旁者视点就会演变为行者(即具体活动或事件的实施者、行动者)视点。
“我A,我B”构式就其使用语域而言,较多地用于群体活动的标语口号,广告用语和文章标题等场合,很少用于会话中说话者的自我表白。但构式中一律以言者“我”的视点来组织小句,巧妙地把言者视点转换为行者视点,把群体的视点转换为自我个体的视点。众所周知,汉语中用于群体性活动的宣传口号,一般采用非主谓句来表达,如“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献身教育,做时代先锋”等即是,或是采用行者视点的主谓句表达,如“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小红帽为您服务”等即是。“我A,我B”构式通过表达视点的转换,实现了两个隐藏,两种凸显。一是把实际的言者,即活动的组织者与发起者的身份隐藏起来,而把行动者(即活动的实际参与者)的角色凸显出来。二是把言者的主观意愿(主动地号召与鼓动)隐藏起来,而把行动者的参与意愿(主动地宣告与表白)凸显出来。构式话语利用了表达视点的巧妙转换,放大了群体活动的自我参与度与主观意愿性,所以才具备了彰显个性、突出自我认同、展示自我价值的语用效力。
“我A,我B”构式在当今开放多元的社会土壤中孕育,在自我意识急剧膨胀的个性化文化中诞生与成长,它以独出心裁的个性化的话语方式装点了现代汉语构式的宝库,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富特色的语言创造。
注释
① 本文的所有例句都来自人民网,引用时在不影响意思的前提下对较长的文字进行了裁剪。
② 作为某种群体活动的号召、标语口号,或是产品广告词,“我A,我B”构式中所含的并列项以两三项的最为常见,使用起来也能做到中心明确、主题突出。一旦构式的并列项超出四项,就会造成多中心,反而会损害构式的宣传鼓动效果。有家企业的口号就是九项并列的“我A,我B”构式:我思考,我学习,我充实,我追求,我丰富,我工作,我快乐,我白领。(深圳隆邦资讯发展有限公司:www.yjbys.com/company/ /2490292.html 2012.02.19)
③ 邵敬敏(2011)把汉语的框式结构概括为四个类型(双项双框式、单项双框式、双项单框式和单项单框式),其中“双项双框式”中的“双项”是指有两个前后可变项,“双框”是指有一前一后两个不变项。据此,“我A,我B”构式中,前后两个可变项“A”与“B”(“双项”),两个小句的主语“我”为起定位与标记作用的不变项(“双框”)。所以,应该看成是框式结构中最为典型的“双项双框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