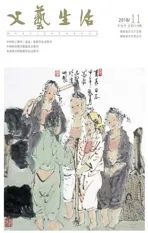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心灵历程
2018-04-08梁俊
梁 俊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一、前言
苏轼(1037-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苏轼不单是一个诗、词、文、书、画兼擅的文艺全才,而且是一个兼通儒、释、道的学者和思想家,他的多方面的文化创造和贡献使他成为象征性人物。
苏轼一生多波折。他于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纵观苏轼一生,获罪被贬黄州为其人生重大打击时刻。然而,总结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心灵历程,可以看出他面临人生逆境的处世态度是人生宠辱平常事,任他风浪起,心态要端平,朋友广结交,私仇摆一边,心胸常开阔,乐天不悲观。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都是非常适用的,值得我们借鉴。
二、黄州在苏轼生平经历中所占的意义
(一)苏轼黄州之前的心态
苏轼出生于一个儒家思想浓厚的家庭,从幼年起,苏轼受其父影响,有志于做一个经世济民的儒家子弟,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进士之前这一阶段,苏轼对于政治十分乐观,又正值风华正茂。
而苏轼中进士之后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苏轼心中不止有了走好仕途的志向,更是产生了渴望改变朝政的想法,也为他后来遭受种种磨难埋下伏笔。
(二)黄州事件对苏轼心态的意义
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府谏官李定、舒、何正臣三人,以《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三卷,今已佚)为主要“罪证”,摘录了二、三十篇诗文,指采取了断章取义的手段,指控苏轼“触物及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乌台诗案》)”因为审案是御史台负责,又因为御史台种植了很多古柏,栖有数千只乌鸦,故御史台又称乌台。也因为如此,苏轼这桩诗案史称“乌台诗案”。①苏轼到黄州,是他从生死线上刚逃脱出来,从政治深渊中刚爬起来后,到达人生转折的第一站。使他“魂飞汤火命如鸡”。
在《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中,作者以“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的孤鸿自喻,表达自己突遭厄运、惶恐寂寞而又孤苦无告的心境。《西江》(世事一场大梦)传达自己无辜被贬,在落叶秋风中感受人生短哲、空幻、正义难容于世的种种况味。②
被贬黄州这一重大事件,使苏轼政治上陷入绝境,心理饱受摧残,生活困窘不堪。
三、苏轼黄州期间心态如何变化
(一)挣扎徘徊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到黄州。黄州是个“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的蛮荒之地。且不得参与公事,这对于仕宦之人来说,几近于流放。
“湿薪如桂米如珠,冻吟谁伴捻髭须”(《浣溪沙·半夜银山上积苏》),“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江城子黄昏犹是雨纤纤》),这形象地写出了苏轼作为一个失意文人士大夫的凄凉无奈。“吟”字之前加一“冻”字,吟本无所谓冷暖,置一“冻”字,寒意即出,似乎苏轼在咀嚼体味这人生之凄凉。而坐是“孤”坐,“谁伴”即无人伴,这透露出了苏轼心里的寂寞与孤独。这些字眼传递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信息:词人贬黄之时,生活上、心灵上都是很“失意苦闷”的。
(二)积极求索
体味了人生如此多的“失意”之后,苏轼虽然觉得人生虚幻,但并未因此而沉沦,而是在心灵上做着积极的求索。东坡的失意苦闷之情逐渐演化为坦然超旷之态。经过了各种思考与思想的磨练后,苏东坡在黄州形成了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是其人生观的最终表现形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态度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颓唐之病。即使在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他也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自适的人生态度:“莫听穿林打叶音,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闲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他比较完整地表现出由积极进取转而压抑苦闷又力求超脱自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
(三)觉悟超然
从被贬黄州以后的苏轼的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形成了一种更为超脱达观的人生哲学。贬谪心态中最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部分,是个人痛苦解决之后思想境界的升华,对后代士人的影响尤为深刻。这种终极意义的哲理集中表现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将对于人生诸种问题的思考作了超妙绝伦的解答,注入了对人生最深沉的思考:“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此赋先是触景生情,生出古今如梦功业难久,人生渺小年命不永,与求仙无望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生失意、生命无常的苦闷与感喟。继而又对这人生之大困惑作出超然的解答。既看到生命流逝,又看到其常住不尽有永恒的价值存在,故无所慕无所憾恨。物各有主,人有定分,惟与江上之清风明月适值相遭,取之于自然而形成恬淡自适之审美人生,从哲思与历史的高度审视个体生命的存在,获得一种超脱旷达快乐的人生观。
四、苏轼心态转变的原因分析
(一)哲学思想的救赎
到黄州的后两年多时间里,苏轼从思想到创作都有了质的飞跃。儒家入世思想使苏轼陷入困境,他开始以佛老思想作为自己在逆境中的处世哲学,把它作为恢复心理平衡的手段。
纵观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词赋之作,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思想变化的复杂性。他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把儒、佛、道二家哲学结合起来。外道内儒和外儒内道常被用来定义苏轼的人格和精神特点,概括了他的官场人格和文化人格。儒家的进取之心,是他一生的追求,是他生命的底线,但道家的无为而治亦是他全力追求的。它们缺一不可,是并立的。在他身上,儒家宗旨和道家的理论是放在人平两端等量的人生指导思想,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内外之别。在朝的时候,人平就偏向儒家的宗旨。放逐的时候,人平就偏向佛老思想。“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是苏轼的追求,他也是一直这么来平衡自己的得意和失意的。修身和治心并不互为表里,是他生命里同样重要的两个原则。
(二)在友爱与对故乡的思念中寻求生存的温情
看清世情的苏轼,凭借着超然、豁达的胸襟,超然于世外,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和文学上的洒脱。
苏轼居黄期间爱与异人交往。这些人不好功名富贵,脱俗超尘,特立独行。如“阳狂垢污,寒暑不能侵。常独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止”(《张先生》)的张先生;独好法书、名画、古器、异物,遇有所见,脱衣辍食求之,不问有无”(《石氏画苑记》)的石康伯;李泽厚说:“这也许就是苏轼的理想化了的人格标本吧。总之,不要富贵,不合流俗,在当时“太平盛世”,③居黄期间,苏轼对自己以前对仕途的过于执著感到后悔,他感到人生中追求的不应只是虚无的功业。他朦胧的感受到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生命才是士人应该追求的。
苏轼在黄州承受的不仅是精神上的痛苦,还有生活上的困厄,他在给自己的弟子秦观(答秦太虚书》中写道:“初到黄,康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苏轼就是在这种境遇下,无奈地走向朴素的劳作,去与自然会晤的。而这种劳作和会晤反过来又成为一剂烫贴心灵伤口的良药。
他为当地农人设计如何筑水坝、建鱼池、植树造林、播种稻谷。他琢磨各种各样养生的菜肴,这些菜肴,日后成为名菜流传至今。在劳动之余,他更喜欢来到城中,随意找个小酒馆喝上几杯,舒缓一下身心这种苦中有乐、安道苦节的生活,的确令人既感动又心酸!在东坡看来,远离官场的喧嚣与无耻文人的倾轧,得到的是身心的完全解放,两者相比,还是后者合算。即使是有一时的苦忧,也会随风而逝,不会挂碍于心。
五、苏轼黄州心态对我们的启发
苏轼一举登上文坛极顶,其底蕴极为深厚,对文学创作、对人生、对处世处事,极富有挑战性和启迪性,是很值得人们借鉴的:
(一)豁达豪旷、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苏轼在谪居黄州期间,乃至他的整个人生,表现出的一种人生态度就是,豁达豪旷、随遇而安。苏轼经历了多次俯仰起落,可以说尝够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可再怎么样他都能做到及时地、想方设法地调整心态、调整生活方式、调整自身在社会上的坐标位置,使自己容膝而安、乐得其所。他谪来黄州之前是当大官的,身处社会上层。“乌台诗案”使他一夜间成为阶下囚,几乎送命。之后被贬到黄州。他一到黄州,就很快调整自己,上至知府,下至小商小贩、渔樵庶民都可以结交为好朋友。他还说他在黄州饮用的长江水,半是峨眉雪水,我又是峨眉人,这里与我的故乡一样,又何必归故乡呢人生在世,谁都会遇到一些顺心的事或不顺心的事,都会碰到平坦或坎坷,这就需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在不少的情况下,人可以跟这跟那过不去,但千万不能跟自己过不去。自安自适,以待日后东山再起。要坚信:太阳偏西甚至夕阳西下,但过十来个小时之后,又会从东方升起,当空而照。
(二)真正的、超凡的才学和见识,其源泉在黎民百姓的生活之中
苏轼在黄州一举登临文坛极顶,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黄州真正放下了官架子,融入了黎民百姓之中,脚板踏到了土地上。在黄州,他调整心态,自适自安,靠的是黄州的父老乡亲。他写作的不少名篇佳作的灵感和素材,还是从黄州的父老乡亲及其质朴无华的生活中而来。这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苏轼在黄州的写作实践告诉我们:超凡的才学和见识来源于群众的生活之中。任何想有作为的人,都需要练功底,而首先要练就的功底,就是与群众交知心朋友的功底,了解和熟悉民众生活的功底。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苏轼虽然屡遭打击迫害,丢官被逐,但是他自始至终并未苟且偷生,消沉遁世,而是很好地融入人间天地,豪迈从容,给所贬之地带去了文明教化,为当地人民所崇敬热爱。这应该是儒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与佛道忘我无我、空静澄明境界相互杂糅融和的结果。苏轼的精神魅力也正在于此,这也是后人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
注释:
①林语堂.苏东坡传[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214.
②杜勍妹.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及思想[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03).
③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