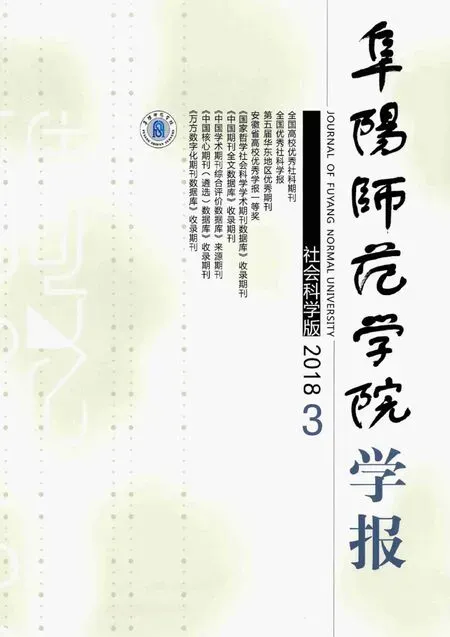《约伯记》与《庄子》死亡观比较
2018-04-04张齐
张 齐
《约伯记》与《庄子》死亡观比较
张 齐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约伯记》和《庄子》分别是各自民族的经典智慧文本,都对死亡有着特殊观照。两者在死亡之因、死亡之果以及由此而反观生命的态度三个方面均有可比性。《约伯记》将死之因归结为人的罪,死亡的结果是骨肉朽坏,成为阴魂,远离上帝;《庄子》将死之因归为不可知之“命”的作用,死亡的结果是以气化的方式重新回到大道运行之中。由此也产生了对生命态度的差异:一者敬畏谦卑,一者逍遥自由。这两种异质文化死亡观的比较,有助于人们通向一种对于生命更为整全的理解。
死亡观;《约伯记》;《庄子》
有生必有死,关于人生哲学中任何问题的探讨,最终都离不开死亡这终极视域的观照。以生观死,死亡自有其不容忽略的意义;以死观生,人对生命的认识也会刷新。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之中,以古希伯来民族的《约伯记》(1)和古华夏民族《庄子》为代表的经典智慧文本,对各自民族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两者对人的生命有着极为精透的探析,对死亡问题投注了极大的关心,并作了极有特色的解答。我们拟从死亡的产生根源、死后的存在状态以及由此而对生命产生的不同态度,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死亡指的是因衰老疾病等不可抗拒因素的生命终结,他人或自己刻意造成的生命终结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一、死之因:罪与命
死是相对于生而提出来的,生死问题总是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开。包括《约伯记》在内的《旧约》,无论其中的文本内涵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却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中心,亦即上帝耶和华,对上帝的信仰也决定着他们的生死观。从《创世记》以来的文本都一再强调:耶和华乃是拥有绝对生命的,是生命之源、万物之本,他是生命的创造者、赐予者和呵护者。《约伯记》的生命观与《创世记》一脉相承:“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伯12:7-10)
上帝的工作当然是值得称颂赞美的,只有生命才配得上上帝的荣耀与赐福,甚至只有生命才能与上帝有联系。受此观念影响,人们不会盯住死亡和冥界不放,而多注目于现世的存在。于是,对于现实生活幸福的追求便成了人们始终不渝的目标。这一方面固然由于自身生存的需要,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此乃衡量是否蒙上帝悦纳的标准。现世的生存,不但注重个体生命的延续(即“享大寿数”“日子满足而死”),也要求族群生命的旺盛(生养众多,儿孙满堂)。如若早夭或绝嗣,对于个体而言,当然是一种遭难,倘作更深层的溯源,也表明个体与上帝关系的紧张。无论如何,均非人所愿见的。
不可否认的是,不管人的寿命有多长,生时对上帝有多虔诚,现实的生活有多幸福,他们终归是要死的。因着始祖时期亚当和夏娃的犯罪,人类陷入永恒的堕落当中,罪使死亡如影随形地伴着人类。“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3:19)上帝的宣判将人类永远钉在了罪的耻辱柱上,而作为罪的后果便是生命的终结。人皆有一死,无论贫富贵贱。正如约伯所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完全人和义人他都灭绝。”(伯9:22)由此,死亡作为罪的结果,而具有必然性。
在庄子那里,死亡也具有必然性。不过庄子并没有将这必然性归之于上帝的主宰意志,而是将其归之于“命”,所谓“死生,命也”。一般而言,“命”观念在古代中国思想中,有两种意义:一则表示主观命令,一则表示客观限定。“前者可称为‘命令义’,后者可称为‘命定义’。”[1]72前者必然蕴涵着主体的意志及价值抉择,后者则不必然如此,而往往指向那些无法为人力所左右的客观因素。
在庄子哲学中,也在不同维度上论及“命”,其中大多是指后者而言,强调“命定义”,代表着一种不可知的必然力量。《大宗师》篇末,子桑向子舆谈论自己之所以如此贫病交加的原因时说:“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子桑认为,造成他如此窘迫状况的根源,不在父母,不在天地,而是不可捉摸、不得而知的“命”。
由于“命”具有必然性,所以要求人无条件地遵从。“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为父,而身犹爱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而身犹死之,而况其真乎!”人之有死生,正如天之有昼夜,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世俗之人,只知以君王为贵,尚且愿意为其付出生命的代价,却怎么不知遵循那万有之本根——大道的安排呢?“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捍矣,彼何罪焉!”在阴阳造化面前,就好比面对父母之命一般,生死皆自然必然,不可抗拒,只能遵从。任何妄求长生和擅自轻生的行为都是为庄子所弃绝的。
两者都将死亡视为人生之必然,但《约伯记》将其归之于上帝意志的结果,死亡带有鲜明的惩罚意味;而《大宗师》则视其为天地间阴阳变化的正常现象。对于死亡终极原因的不同追溯,导致二者在对待生死的态度上也大相径庭:一者悦生恶死,一者善生善死;由此牵引出人生态度的差异:一则谦卑敬畏,一则逍遥自由。
二、死之果:魂与化
既然凡有生命之物是必死的,对死亡意义与结果的探讨便成为顺理成章的话题。当然,由于死亡具有不可知性,这种探讨实际上最多只是一种基于经验的猜想。但不管如何,人类总怀有对未知事物莫名的兴趣,这兴趣使得他们对于死亡的触探也动力十足。
从《旧约》中,大致可以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对于死亡结果及死后状态的看法,这种看法也同样渗透在《约伯记》中。其中尤以约伯所论居多,约伯的陈述夹杂着强烈的个人主观情绪,他的朋友们对此多有批判,而涉及到死亡的看法时,这些朋友根本未加反驳,故而基本上可将约伯的死亡观视作彼时彼地人们的共同观念。
古希伯来人的丧葬习俗一般是将逝者埋葬在深坑之中。世人都能明白所观察的事实是,人死之后,其尸身终将毁损。“若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伯17:14)肉体为虫子噬咬吞吃,必将面临毁灭。尽管如此,约伯认为,人死后并不是彻底地消失或不存在,还将以另一种形式(阴魂)在阴间或下界生活。他们在那里处于十分虚弱的状态,“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伯30:23)人死后同归一地,名曰“阴宅”。“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兢。”(伯26:5)希伯来人设想的阴间所在,即“大海以下”“深坑之中”,对于习惯生活在干旱陆地上的古希伯来人而言,这自然令人万分恐惧害怕。“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伯10:22)这说明阴魂的居住环境极为恶劣,其存在状态也十分虚弱。
死亡是一“往而不返”的不可逆事件,“人死了岂能再活呢?”(伯14:14)“海中的水竭尽,江河消散干涸。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仍不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伯14:12)阴魂与活人世界断绝了任何联系,“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认识他。”(伯7:9-10)“他儿子的尊容,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伯7:21)他与自己的故土、家庭、亲人相互隔绝,彼此不知对方状况。对有信仰者而言,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死后的阴魂与上帝也难以沟通。“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我却不在了。”(伯7:21)这赌气似地吁求也暗示了死人与上帝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更意味着人一旦死亡,其冤屈更无法平反。“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伯16:21-22)这里表达的仅仅只是一种愿望,实际情况则是死后无法与神辩白。既然如此,他生前无缘无故而遭的苦难也无法得到补偿。如此一来,人无论生时还是死后,所有的希望都将断绝:“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等到安息在尘土中,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闩那里了。”(伯17:15-16)
这样,死亡在《约伯记》中作为上帝惩罚的结果,不仅是个体生时价值的消泯:“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伯12:2)也是其生时种种关系的断裂,包括与活人、故土,乃至上帝。总体看来,《约伯记》中尚无后来《新约》中那种明确的灵魂拯救与肉体复活思想。约伯的朋友以利户的发言:“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伯33:28)似乎暗示了救赎与复活的存在,但他的发言有许多学者认为是后来添加的,与原文整体脉络及观念并不契合[2]67-68。约伯也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伯19:25-26)但约伯的这种说法与其说是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勿宁说是一种殷切的期盼。此外,也有学者根据原始经文指出:“在这个上下文中,救赎主的文本是错误的。”[2]64所以,在《约伯记》中,死亡被认为是不可逆的,死后的存在更多地被赋予了凄凉不祥的意味,这无疑是为所有生物所厌弃恐惧的。这就与庄子对死亡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差异。
庄子也认识到死亡是一种必然和自然的现象,但他并未赋以死亡贬义。庄子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广阔视角俯瞰人生,将宇宙的运动及万物的生死成毁视为气的流行转化,从而消解了死亡的残酷意味,赋予了死与生齐一的地位,甚至隐隐然有抬高死亡价值之势。
一般而言,在任何时代,大众的普遍心理必然是悦生恶死,尤其庄子那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战国时期更是如此。庄子正是要破除这种对于死亡的恐惧心理,“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庄子·齐物论》)生是如此痛苦,安知死后不会快乐,或许死后还会后悔当时的恋生呢?以至在《至乐》篇中,庄子甚至借髑髅之口道出了“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的“死之说”(2)。
仅仅只是一种推测,远远不够说服人,庄子至少得给出理论上的证明。“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庄子·至乐》)这就从生命的产生和形成解释了生死的本质。在他看来,这世界原本无生、无形甚至无气,其后在“芒芴之间”忽而生“气”。此气贯通宇宙,“通天下一气耳”,天地万物处于一气流转变化之中。生命的产生和消逝皆是一种气化过程,气聚则生,气散则死,虽有生死之别,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论》),所谓此之生,乃是彼之死,所谓此之死,乃是彼之生。其为气也则一而不异,故生与死本质上是相通的。
由此,不管是生是死,都不过是气化过程中的一种现象而已,而且重要的不是这种现象,而是气化过程本身。这种对于气化过程的强调,使得庄子也不再注意人与物的差异。“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庄子·大宗师》)人的形体不过是转化的千万种可能性之一,而每一种转化都是一种崭新的体验,所以大可不必执著于人形。“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庄子·大宗师》)人的死亡正是结束人形的特定存在、开启无限转化的门窍,正因为如此,它反而变得无比令人期待。“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鹄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庄子·大宗师》)
在这里,庄子以一种近乎戏谑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的铺陈排比,消解了肉体的毁坏乃至生命的消逝所带来的残酷属性。在无尽的转化之中,不仅人体与万物,甚至是天地间所有的事物,莫不是相续相生的循环,一物之形化为另一物之形,至于在何时何地化成何物何形,则是完全未知的,充满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整个宇宙都处于不断地重构和更新的过程中,它也使得人们对于任何具体形态的执著都变得可笑,包括作为人的形态而存在的生命。“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庄子·大宗师》)毕竟,万事万物都逃不脱转化的命运,但这命运并没有使庄子产生紧张压迫感,反而在深刻体认之后,而催生了一种奇诡的超越自由感,这就是随时俯仰、任运推移、与化为一、所在皆适的人生态度:“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庄子·大宗师》)
三、以死观生:救与游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伯5:7)“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苦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伯14:1-2)苦难是人生在世的常态体验,而在《约伯记》的语境中,死亡无疑是最大的惩罚,是最为深重且不可逃脱的苦难;但另一方面,由于死亡的不可逆性,它也意味着在世苦难——甚至是幸福的彻底终结。人生的一切差异性体验:贫富、贵贱、祸福……都将因为死亡的到来而不复存在。
如果人生的一切差异都通过死亡得以消除,那么这既是受苦义人的一种幸运,又是其最大的不幸。虽然苦难通过死亡而终究消泯,但生时遭受的冤屈却始终得不到申诉,由此产生的必然是对生命的深切失望。对有信仰者而言,最直接的后果便是产生对上帝公义的怀疑,乃至于对上帝存在的怀疑。即使上帝的意旨与智慧我们无从知晓,报应的法则并不能用来衡量上帝,即使凭凡俗人的智慧无法得知善恶究竟是什么,但一个邪恶的或对这世界善恶不闻不问的上帝,却丝毫不值得人崇拜。尽管文本之中约伯向上帝屈服,但这远不能说服读者。对于任何一个稍具理性的信仰者来说,一个非道德或超离道德的上帝,是不可思议的。仅仅这样一种猜想,已让人感觉十分不安。毫无疑问,《约伯记》的作者负有消除这种不良倾向的责任。
《约伯记》文本即将结束之际,在面对上帝的质问之后,约伯的沉默是意味深长的。这种沉默并不意味着约伯对上帝大能威权的屈服,这种解释更会使上帝陷入以强凌弱的不义责难之中,何况上帝自有与其位格相匹配的出场方式,他也并非要故意以此威吓约伯。向约伯显现的上帝所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其真正答案也并不值得关注。已经有为数众多的学者指出:上帝的发问仅仅涉及宇宙自然秩序,而对人世道德秩序却不置一辞,这是否合理?但在这里,问题的答案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问题背后的真正意涵。
上帝发问最为显著的作用,便是彰显了人类以外的无限广阔的未知领域。在这领域之内,甚至还存在两种强大无比的猛兽(比希莫特和利维坦),“显示了超越人类认知和掌控的可怕力量,不过在上帝的宇宙中,它们仍允获居某处。它们不具任何功用,无法驯服。但他们仍处于神圣的掌控之中”[3]93。甚至在《约伯记》文本的开头,那个想要故意挑拨神人关系的撒但,貌似咄咄逼人(神),其实最终也还是受上帝掌控。这意味着,在人类未知的世界中,上帝仍然有着无上的威权,他的意旨和律法无往不利。依此类推,死亡对于人类而言,也完全是一个绝对未知的世界。由此,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上帝的律法在死后的世界是否依然有效?抑或生时虽受冤屈,但上帝在人死之后终将有公义的审判?置身于宇宙洪流之中,人类不过是偶然翻起的浪花,何时涌现,何时平息,源于何处,流向何方,人无法做出准确的推测。因而上帝对约伯的质问:“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伯38:16-17)便不至太过蛮横无理。文本之中虽未明示,但约伯的沉默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这种死后公义的可能,而这正是世俗中受苦受难的众生所期待的。
对此,可能的解决办法便基于死亡观的转变,即在无限广远的时间历程中(包括死后的存在),人(包括其灵魂)仍受德行业报法则的钳制,由此便有了恶人受罚的地狱与善人受赏的天堂,但这种救赎与复活的思想在《约伯记》创作的年代似乎并未产生。可以想像,作者也无力颠覆传统的神义论,因而不得不安排约伯在现世重新得到福报。基于这种死亡观的视角,也可以解释为何《约伯记》会有那么一个令人颇感奇怪的结尾——耶和华加倍赐福给约伯,也不难理解为何在《约伯记》的开头,耶和华与撒但打赌,耶和华同意撒但试探约伯,但却一再要求“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伯1:12)、“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伯2:6)。因为对一般读者而言,他们很难理解约伯沉默的真正意涵所在,于是今生的救赎与赐福便成为他们对上帝必然的祈求,如若没有来世的寄托,这祈求只会更加强烈。因此,时刻对上帝乃至对一切生命保持敬畏谦卑便成为必然。
在庄子那里,没有上帝的概念(虽然他爱用“造物者”“造化”这样的称谓,但这只是对道的一种拟人表现,而非认为“道”具有上帝那般的人格和意志),宇宙中的一切皆处于转化之中,故而其哲学的核心工作,乃是对事物相对性不遗余力地破解。“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如此一来,伦理道德上的善良与邪恶、人生经验中的苦难与幸福、生存与死亡,其间原本存在的巨大差异性均被消解。
庄子根据人是否具有超越事物的相对性,将其分成两类:一类为汲汲于世俗利益的普通人;另一类则为突破了俗世一切限制的真人,或曰至人、神人、圣人、真人。对于普通人而言,了解生死齐一的道理,就等于知晓了所谓的“命”,就能够以安时处顺的态度对待死亡。“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庄子·大宗师》)生时以天地大道为宗,能够养身全生,尽其天年。死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会人为地求生避死,更不会恶死恋生。无论面临何种情境,都不会有极大的情感波动,这样便能在精神上获得一种自由和满足感。这种安命观念不是去否定、也不是深化“命”之必然性给人生带来的困境,它表现为对这种必然性的顺从,试图以顺从的态度来克服死亡带来的恐惧不安。
但思辨的论证是远远不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还需要有特殊的精神修炼方法。这就是“忘”的工夫,在《大宗师》里具体表现为“坐忘”与“见独”:
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生不死。
“坐忘”与“见独”的修养工夫,消除了对事物具体形态及存在方式的执著,消泯了它们的界限与规定,从而使包括我在内的万事万物通而为一。达到这种境界的人,被称作真人、圣人。庄子用了一个颇有意味的词来形容这种境界——“游”。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鱼之“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譬喻,才能获得最为真切的理解。“相濡以沫”是指生之胶著与困窘,而“忘”不仅是指精神脱去的粘滞与纠缠,也暗含死亡的意味(“亡”与“忘”具有词源学意义上的相通关系)。只有相忘以后,才能够自由自在地畅游于江湖之中。在此,“游”乃是对破除了窒碍与束缚,而最终获致的那种无拘无束状态最为贴切的描绘。在此种状态之中,“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不计较得失,不关注祸福,不在乎生死,甚至连上帝的存在与否也不重要。正是在此意义上,庄子在其生命中的至亲之人(妻子)去世时“鼓盆而歌”,才能得到谛当的理解。
结语
《庄子》之齐一生死,自有其积极意义,但也不能忽视其中隐含的疏漏。为了论证生死一如,庄子往往有矫枉过正之嫌,虽然以“善生善死”为其最终结论,实际却极易导出“悦死恶生”的倾向,以死亡为真正解脱,而忽视生命的价值,逃避其应尽的义务,虽则这义务在庄子那里看来类似赘疣,然而生命的社会现实维度却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抹灭的。此外,庄子所描绘的生死齐一的高妙境界,只有至人、神人、圣人、真人才能臻至,而这境界对于世俗众生而言却永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生时能否得到有力的保障,更是死后也能否有好的归宿。于是,一个全能的主宰意志(诸如上帝)的设定,对于苦难中的芸芸众生便有其必要性。在这方面,如《圣经》中《约伯记》之类的文本便有相应的启示作用。不过,如前所述,《约伯记》并不像后来的福音书那样,有着明确的救赎希望。在《约伯记》中,死后的世界被设定为一片虚无。若只以此为据,苦难与冤屈的人们,便只有盼望在今生得到拯救,而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毕竟约伯与上帝的相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享有的待遇,即使上帝无时无处不在,也并不是每个义人都能在生前享受福报(尽管为着福报的信仰并非真正的信仰,为着福报的道德也并非真正的道德,但福报的预设却是必需的)。通过比较,可以看到,《约伯记》与《大宗师》死亡观虽各具特色,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失,这或可启示引导我们通向对生命更为整全的理解。生命本具备无尽的庄严神圣,亦承担着无穷的烦恼苦难,同时也希冀着无限的美好幸福。
注释:
(1)本文主要参考《圣经和合本》,上海基督教两会,2008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约伯记》中故事的主人公约伯及其朋友,均非以色列人,但这并不意味《约伯记》不属于以色列民族。正如Roland E.Murphy所指出的:“它是一部以色列的智慧书,它仍然在这样的智慧的视角内。”参Roland E.Murphy著《生命之树:圣经智慧文学之探索》,段素革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52-53页。
(2)《至乐》篇中这则骷髅寓言的真正意旨,历来注家聚讼纷纭。甚或将此排斥在庄子思想体系之外者亦不乏其人;也有学者试图证明其并非“厌世”“乐死”,而是“以死劝生”。(参黄克剑:《〈庄子·至乐〉髑髅寓言抉微》,《哲学动态》,2015年第8期,第45-51页)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段文字给人的最直接印象,的确是“乐死恶生”。
[1]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Roland E.Murphy.生命之树:圣经智慧文学之探索[M].段素革,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3]Richard Clifford.The Wisdom Literature[M]. Abingdon Press.2011.
A Comparison betweenandunder the View of Death
ZHANG Qi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s one of the most classical wisdom texts in each nation, bothandhave unique opinions on the death phenomenon. They can be compared in three aspects: the causes and the results of death and how to live under the view of death. In, the cause of death is the sin of human beings, the result of death is the putrefaction of the body, although it may exist in the form of ghost somewhere, it is separated from the God.regard the cause of death as the(命) that human beings can't understand. As the result of death, human beings transform into(气)and return to the circulation of(道). Influenced by their respective death view, the attitude to life are also very different. The former taught us abasement and reverence, the latter taught us(逍遥)and freedom. This comparison of two kinds of death view from very different culture, can help us understand our life more comprehensively.
death view;;
2018-02-23
张齐(1988- ),男,湖北襄阳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美学,中国哲学。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8.05
B223.5
A
1004-4310(2018)03-0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