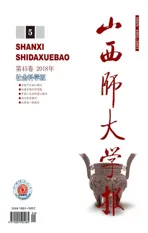论元杂剧婚恋剧对唐传奇的再创作及其原因
2018-04-04王理超
李 成,王理超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元杂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借鉴吸收唐传奇这一叙事文学的现象,长期都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其评论与阐述从元代就已经开始。前人关于元杂剧的婚恋剧对唐传奇继承的研究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立足于婚恋小说与戏曲,宏观地研究二者关系,如程国赋的著作《试论唐代婚恋小说的嬗变》(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从唐传奇的角度出发,研究唐传奇婚恋题材的故事在后世作品中的嬗变;其次,专注于研究某一部名家名作或者某类热门题材的嬗变,如吴波的《从〈柳毅传〉到〈柳毅传书〉柳毅形象的嬗变》(《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凌茜的《〈莺莺传〉到〈西厢记〉的继承与发展》(《剑南文学》2011年第3期)等,分别就《柳毅传》《莺莺传》的改编进行比较。此类论文非常丰富,大多聚焦于婚恋题材名篇;再次,侧重研究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成因,如程国赋的《唐代小说嬗变的成因探讨》(《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1期)和朱玲的《唐传奇与戏曲的发展》(《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等,此类论文多着眼于唐传奇对整个后世戏曲作品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元杂剧,他们总结的原因都是宏观角度的共性;最后,有专门研究不同体裁作品在艺术表现上的不同,如储著炎的《抒情的本色性——试论唐传奇与元杂剧爱情题材作品的内在联系》(《文学前沿》2007年第1期)、王珂珂的硕士论文《论元明清戏曲对唐宋传奇的改编》(苏州大学2011年)等,注重从作品的艺术特色、体裁类型等方面阐述二者在形式上的联系。本论文通过吸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将现存的以唐传奇为蓝本改编而成的婚恋类元杂剧进行系统的总结,并从具体的作品内容出发,阐述其再创作的文本动因、时代动因和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本文拓宽视角,以素材、形象、情节三个创作要素为基点,从两个角度,即历时的唐传奇小说艺术的传播角度与共时的元杂剧作家、观众的接受角度,经纬相织地分析元杂剧婚恋剧对唐传奇的继承;从历时的唐传奇小说艺术的传播角度看,唐传奇婚恋故事素材的丰富性、人物性格的鲜明性、情节结构的奇幻性,都成为元杂剧的婚恋剧继承唐传奇进行再创作的重要原因;从共时的元代杂剧作家、观众的接受角度看,唐传奇的婚恋小说题材被元杂剧继承,一是唐传奇婚恋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满足了元代文人作家的精神需求,二是唐传奇婚恋故事情节符合元代观众的审美趋向。元杂剧的婚恋剧对唐传奇的继承,既是唐传奇小说艺术成熟后传播的结果,同时也是元杂剧创作的需求。在传播接受过程中,唐传奇扩大了其在民间的传播与影响,元杂剧则找到了可借鉴的本事基础,这是元杂剧以唐传奇婚恋故事进行再创作的文学思想与艺术价值。
一、以唐传奇婚恋题材为蓝本再创作的元杂剧
元杂剧借鉴、吸收唐传奇题材进行创作的现象受到了历代学者的关注。元代开始就有学者追索杂剧源流,元末人陶宗仪即把唐传奇认定为元杂剧的渊源: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1]370
元人陶宗仪追溯故事题材流变的线索:唐传奇、宋戏文、金院本、元杂剧是一脉相承而来的,唐传奇被认定为元杂剧的渊源之一。明人臧懋循在其《负苞堂稿》卷三《弹词小记》中提及:“近得无名氏《仙游》《梦游》二录,皆取唐人传奇为之敷演,深不甚文,谐不甚俚,能使呆儿少女无不入于耳而动于心,自是元人伎俩。”[2]67他也认为元代的戏曲多有改编唐传奇之作。清代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中提到,唐传奇与元杂剧都以叙述新奇的故事为中心,认为戏曲不过是有声的小说。近代开始,研究者对于二者在题材上的传承与袭用认识更加明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元、明人多本其事作杂剧或传奇,而影响遂及于曲。”[3]211虽隔数百年,但元杂剧的确在创作上接受与发展了唐传奇。
根据徐调孚所著《现存元人杂剧书目》一书统计,现存完整的、以婚恋题材的唐传奇为蓝本的元人所作元杂剧共十一部,占唐传奇改编的元杂剧剧目的二分之一。可见,元杂剧作家在改编唐传奇时偏爱爱情婚姻题材。这些改编而来的婚恋题材剧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奇幻恋情的婚恋剧:以唐传奇《柳毅传》人龙之恋为本事,尚仲贤改编为《洞庭湖柳毅传书》、李好古改编为《沙门岛张生煮海》;以唐传奇《离魂记》人鬼之恋为本事,郑光祖改编为《迷青锁倩女离魂》;以唐传奇《云溪友议·玉箫》两世姻缘为本事,乔吉改编为《玉箫女两世姻缘》。
第二类,现实题材的婚恋剧:以唐传奇《柳氏传》为本事,乔吉改编为《李太白匹配金钱记》;以唐传奇《李娃传》为本事,石君宝改编为《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以唐传奇《莺莺传》为本事,王实甫改编为《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白朴改编为《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以唐传奇《长恨歌传》为本事,白朴改编为《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以唐传奇《唐摭言·王播》为本事,王实甫改编为《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以唐传奇《玉溪编事·侯继图》为本事,李唐宾改编为《李云英风送梧桐叶》。
《洞庭湖柳毅传书》与《沙门岛张生煮海》两部元杂剧改编自同一部唐传奇《柳毅传》,但二者风格各异。《洞庭湖柳毅传书》基本继承《柳毅传》因“义”而情的主题,敷演书生柳毅去洞庭湖传书解救龙女三娘,最终与其结为夫妻的故事;而《沙门岛张生煮海》则将矛盾的主体转化,变矛盾的双方为封建的家长势力与追求爱情的青年男女:书生张羽与龙女琼莲心生爱慕,而龙王得知此事后百般阻挠。张羽用仙姑所赠银锅煮海,使龙王最终屈服,将龙女嫁与张羽。《沙门岛张生煮海》在题材的改编上做出了更为明显的创新。
《迷青琐倩女离魂》基本继承了唐传奇《离魂记》的故事情节,敷演倩女因爱而魂追书生王文举,陪伴文举进京考中状元,历经艰苦终成连理的故事。书生王文举曾与张倩女有婚约,但因文举父母双亡,家势衰落,倩女之母逼迫王文举赴考中第后才可娶亲,张倩女情急之下灵魂追随王文举同去,而倩女的肉体却卧病在床,直到王文举科举中第,带着倩女的灵魂归来,魂魄与肉体才合而为一,二人团圆结局。
《玉箫女两世姻缘》则丰富了唐传奇《云溪友议·玉箫》的故事情节与人物设置。乔吉在元杂剧中增设了鸨母这个反面角色,以及鸨母以科举为由赶走韦皋,韦皋和玉箫约定得中后来娶她的故事情节。改编之后的故事人物更加丰富,故事矛盾更加尖锐突出,起到了强化戏剧效果的作用。
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与白朴《董秀英花月东墙记》是以唐传奇《莺莺传》为本事进行改编创作的两部元杂剧,二者均对唐传奇《莺莺传》“始乱终弃”的结局进行了改写:《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中书生马文辅与董秀英相爱而私自结合,最终冲破阻挠得以团圆;《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中白衣书生张生与崔相国之女崔莺莺一见倾心,历经波折与反复,冲破以老夫人为代表的门第观念与封建礼教束缚,最终喜结连理,有情人终成眷属。《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将原来《莺莺传》中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改为喜剧,大团圆结局的设置,不仅符合元杂剧观众的审美趣味,更是元杂剧作家改编唐传奇的创新之处。
其他,如《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等元杂剧婚恋剧均对唐传奇的婚恋故事题材有所接受,同时又加以不同程度的创新。
由此可见,唐传奇为元杂剧婚恋剧的创作提供了较多的故事材料,元杂剧作家以这些故事材料为蓝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重新创作。
二、元杂剧以唐传奇婚恋题材进行再创作的原因
唐传奇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是标志中国文言短篇小说成熟的里程碑。唐传奇在主题题材、体制语言等方面充分吸收了前代文学的养料,发展成为既有故事情节,又有人物形象的创新性小说。由于不朽的艺术魅力,唐传奇受到后代作家的一再追步。元杂剧明显地继承了唐传奇的故事题材,其中婚恋题材的唐传奇是元杂剧吸收和借鉴的主体。元杂剧继承婚恋题材的唐传奇,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 元杂剧以唐传奇的婚恋故事为素材的原因
唐传奇与元杂剧的文本均以“故事”为中心,叙述性是二者的共性。这样的文本特点必然要求二者的创作都要以大量精彩的故事为素材。因此,唐传奇丰富而成熟的婚恋故事素材就自然地对同样需要故事充实文本以满足市民审美心理需求的元杂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单从以男女婚姻爱情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这部分唐传奇来看,其故事素材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这为读者展示了丰富的艺术世界,同时为元杂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婚恋故事素材。例如,同为神怪类型的婚恋故事,《柳毅传》是描写书生柳毅去洞庭湖传书解救龙女三娘的故事,《离魂记》则讲述张倩娘以魂魄追表兄王宙并最终团圆还魂的故事:一个男性解救女性,两人因恩情产生感情;一个女性追随男性,二人为真情不离不弃。虽然在题材上二者都属于婚恋类作品,但两部唐传奇在思想主题、情节演绎、形象塑造等方面均体现出不同的特色。《柳毅传》描写与歌颂的是以“义”为主导的人性美:男主人公柳毅“闻子之说,气血俱动”[4]321,自称“义夫”,救龙女于急难而不求回报;女主人公洞庭龙女“脱获回耗,虽死必谢”[4]321,龙女的语言与人物性格,同样显示出受恩而知报的“义”的主题。男女主人公的结合以“重义”为前提,恩情成为爱情的基础。可见,作者意将理想化的“重义”主题赋予到人物性格中,以美好的精神品质反映主题内涵。相比之下,《离魂记》表现的主题,更多的是为真情而反抗包办婚姻,爱情是男女主人公结合的基础。王宙与张倩娘真挚相爱,遭遇困境时,倩娘不畏艰辛以魂相追,“徒行跣足”[4]297,“须臾至船”[4]298,而男主人公王宙见此情形,亦欣喜若狂,“执手问其从来”[4]297,可见二人感情亲密真切。小说以超现实的形式成全了二人的爱情,主旨在赞颂青年男女勇敢追求爱情的精神品质,这与《柳毅传》“重义”主题有所不同。
不仅在主题上有所区别,《柳毅传》与《离魂记》在情节设置方面也各有特色。《柳毅传》的情节围绕男主人公柳毅的行踪展开,小说写他归家遇龙女,传书洞庭宫,解救龙女受礼遇,娶龙女成眷属。作者的笔,犹如摄影机的镜头,始终对准这个人物,情节以男主人公为线索,结构紧凑,主线明朗。《离魂记》则以女主人公张倩娘为视角,情节起伏多变。从二人“常私感想于寤寐”[4]297,到受家长阻拦是一个节点;从倩娘离魂出走,至船相见,又是一个转折;从蜀中生活五年到“俱归衡州”[4]298,故事达到高潮并获圆满。一波三折的情节设计,讲述了六十多年的故事。由此可见,《柳毅传》与《离魂记》二者虽都以大团圆为结局,但个中曲折,实有差异,情节视角的一男一女,情节节奏的一快一慢,这些富有变化、区别度大的故事素材为元杂剧的创作提供了可借鉴与创新的原材料。因此,以唐传奇《柳毅传》为蓝本,元杂剧作家分别改编为《洞庭湖柳毅传书》《沙门岛张生煮海》两部作品;以唐传奇《离魂记》人鬼之恋为本事,郑光祖改编为《迷青锁倩女离魂》,感人至深,流传甚广。这些元杂剧在思想主题,情节结构上多借鉴于唐传奇。
此外,唐代传奇作家还将以前小说较少涉及的现实社会的世俗爱情生活作为表现的重要内容,在艺术上也独具魅力,同样为元杂剧提供了可再创作的丰富的原材料。例如,同为以现实为题材的婚恋故事,《莺莺传》表现的是书生与表妹的民间爱情故事,《长恨歌传》以宫廷帝王妃子的爱情为题材,描写的是玄宗在位时,诏命高力士宫外选妃而得杨玄琰女并封为贵妃的故事。《莺莺传》与《长恨歌传》的故事取材于不同的社会环境,演绎的是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物之间的爱情故事,形形色色,丰富多彩。元杂剧作家们直接借鉴唐传奇的这些具有现实性的婚恋故事素材,分别以《莺莺传》《长恨歌传》为蓝本,改编为元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李云英风送梧桐叶》《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可见,唐传奇的故事情节富于变化,故事素材丰富多样,从人间到神怪,从民间到宫廷都有涉及。可以说,唐传奇创造了一个缤纷多彩的艺术世界,这一大批感人至深,意蕴深刻的故事,鲜活且富有新意,流传影响甚广,这为元杂剧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借鉴,为元杂剧作家在婚恋剧的创作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很多元杂剧作家在创作婚恋剧时袭用唐传奇的故事素材,有的仅对故事细节进行完善补充。
唐传奇婚恋故事素材的丰富性及其广泛长久的影响力成为元杂剧继承婚恋题材唐传奇进行创作的重要原因。
(二)元杂剧以唐传奇的人物为主人公形象的原因
唐传奇的婚恋故事提供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群体,诸如风流的文士、知情重义的女子、勇于担当的文官武将、贪财的鸨母、鄙俗的商贾,乃至像汉文帝、唐玄宗等帝王形象,这些群像在历代的传承中深入到读者的内心,长久地震撼着后世,成为后世文人反复摹写的对象,并直接影响了元杂剧的文学艺术创作。元杂剧以唐传奇婚恋故事中的人物为主人公形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唐传奇婚恋故事的人物形象能满足元代文人的精神需求。元代的文士阶层被社会秩序冷落,他们困在难以维持文士尊严又不甘沦为市井细民的尴尬处境中,“往往混为编氓”[1]26,辗转飘零,委顿流落。苦闷的文士无处宣泄,便在文学的幻想中求索精神满足。唐传奇婚恋作品中有许多可亲可敬的女性形象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元杂剧作家,即元代文人的视野中,她们敢于冲破束缚,追求与文士的真情,她们青睐文士的才华、珍视与文士的感情,这些人物的性格特质给予了文士精神上的慰藉,文士的价值通过这些女性得到体现,引起了元代剧作家的精神共鸣与创作欲望,因此作家在元杂剧创作中更加确认与强化了这类女性形象的赏才学、慕真情的性格特质。这类人物,如风月场中的李娃、贵族公子的婢女韩玉箫等,她们为了文士大胆作为,成为元代文人反复抒写的对象。唐传奇中的李娃是风月场上的老手,她与荥阳生开始只是某种交易关系,但她渐渐发现荥阳生对她一片痴情,“厥后心常勤念,虽寝与食,未尝或舍”。[4]344李娃知重公子的情谊,报以一句:“我亦如此。”[4]344这是对文士真情的肯定。她虽有负义行为,日后却时常自责,并为了荥阳生高价赎身,帮助他恢复地位、成就功名。在此,作者借助真诚实意、有胆有识的女子对文士的倚重,表现出了文士的地位与才能。元代文人正是看中李娃形象知重文士的特质,才将其人物形象搬入元杂剧的创作中,继续让她给精神郁闷的元代文士以精神慰藉,同时使得戏曲成为人的天性释放的最佳艺术形式。
又如,婢女韩玉箫也表现出对文士的至死不渝。韩玉箫与文士韦皋是主仆关系,在相处中渐渐产生真情,但韦皋在离开江夏时不敢带她同归,留下玉环作为信物,韩玉箫苦等而死。他们的真情感动阴司,让玉箫重生,二人终得团圆。韩玉箫对文士韦皋的执着真情是此篇唐传奇的闪光之处,元代文人杂剧作家看到玉箫女对文士的知重,便将此人物形象引入到元杂剧的创作中,肯定了韩玉箫坚贞而重情的精神,借助戏曲的艺术形式为失落的文士们提供肯定自身价值的有力证明。
2.唐传奇婚恋故事的人物形象能对民众产生艺术感染力。唐传奇中丰富的人物形象,不仅有不甘屈服、为自己幸福而不竭追求的女性,如张倩娘、李娃等,还有反抗压迫,拥有侠义精神的男性,如柳毅、荥阳生等。这些形象都对民众产生了感召力,读者希望看到这些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演绎传奇的故事,因此,元杂剧继续以这些人物为主人公形象进行再创作。例如,《柳毅传》中的柳毅形象民众极为喜爱。他身上具有热心助人、解人危难等美好品质,符合民众心理需求,市民阶层乐于接受。柳毅富有深厚的同情心与强烈的正义感,当他听说龙女的遭遇时,立即表示深切的同情,并愿意为她传书,解救她于危难之中。当他接受龙女父母的款待时亦没有丝毫居功自傲,完全是君子的表现。在婚恋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作者继续将此类人物的这一特质确认、强化,塑造出同样具有美好品质,民众喜爱的男主人公形象。正是由于《柳毅传》中塑造的柳毅形象具有可挖掘性与再创作价值,才使得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塑造的张生形象再度焕发光彩。民众往往对具有美好品质的仁德之士喜闻乐见,这反映了民间的一种追求真善美的心理与情绪。元杂剧作家正是基于民众中形成的接受习惯,围绕民众的接受标准来选取婚恋剧中的人物形象。因此,唐传奇婚恋故事中民众喜闻乐见的人物群象成为元杂剧作家创作借鉴的主体。承袭、发扬这些具有美善精神的人物形象,昭示着民众与演出市场影响在杂剧创作中的作用。
另外,元稹在《莺莺传》中塑造的崔莺莺形象同样是民众喜闻乐道的艺术形象:她情感丰富,却又含蓄娴静,她也备受封建社会和礼教的束缚,渴望自由爱情,但又甘于接受“始乱终弃”的悲惨遭际。正是这样矛盾复杂的性格,莺莺这一角色才显得生动鲜活,有血有肉,令人同情。王实甫注意到了这一特殊的人物形象,在《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中更加强化了崔莺莺在爱情中的谨慎而又大胆叛逆礼教,勇于追求真情的性格,通过五本跌宕起伏的戏文,扬弃了唐传奇中的糟粕,改变了莺莺的悲剧命运,塑造出更加丰满而真实的叛逆女性形象。可见,元杂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注重吸收借鉴唐传奇婚恋题材作品的艺术形象,并给予加工和丰富,使之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这恰恰是因为唐传奇塑造的人物形象内涵丰富且对民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以唐传奇婚恋故事情节为元杂剧创作题材审美趣向的原因
唐传奇中的婚恋故事情节在流传过程中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虽然时代在变化,但民众对美好爱情执着追求的兴趣点仍在延续,因此,由唐传奇改编而来的婚恋剧目自然地拥有了广大的受众心理基础。由于市场化,市民化的需求,杂剧作家创作要迎合观众的审美趣味,所以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得不考虑民众的评价态度以及当时的社会心理。唐传奇中凝聚着的民众由纷乱而渐趋稳定的情感趣味与审美观念是元杂剧作家可以直接汲取的养料。诸如唐传奇中的民众钟爱的崇尚和合的大团圆式结局、才子配佳人的套路以及好人好报的价值观念等,这些可借鉴的程式化的情节因素,使得元杂剧作家热衷于在改编时化用婚恋题材唐传奇中的情节,表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来获得广大观众的认可。由唐传奇改编而来的婚恋题材元杂剧的情节之所以易于受到观众喜爱的具体原因有如下两点:
1.现实化的故事情节能够反映市民生活。市民阶层在经过宋代的萌芽期之后,在元代逐渐形成壮大,他们随着城市工商业的繁荣而产生。市民群体的产生壮大,要求有以反映他们生活及价值观为中心的文艺作品产生。又由于他们是元杂剧的主要受众,所以,元杂剧作家多受市民观众审美趣味的影响,创作符合市民口味的元杂剧作品。而唐传奇婚恋题材作品中具有生活化气息的故事情节正与市民观众滋长的追求声色、重视人性追求的审美趣味不谋而合。尤其是唐传奇中描写现实生活中婚恋故事的作品,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与观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十分接近,由此而改编的元杂剧在舞台搬演时,如同一个万花筒,观众在其中可以找寻自身的影子,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还能看到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因而成为元杂剧作家可以直接汲取的养料。例如,由唐传奇《李娃传》改编的元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敷演了妓女李亚仙与书生郑元和曲折爱情故事。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洛阳府尹之子郑元和与妓女李亚仙一见钟情;郑元和花光资财后沦落街头,其父知道后觉得有辱家门,对其痛加杖责;李亚仙将郑元和救治,并助他考取状元,最终二人成为美满夫妻。故事以妓女和书生的爱情故事为题材,吸引了以追求声色为乐的市民观众,生活化、曲折化的故事情节更易引起市民观众的情感共鸣,故事描写的家庭关系,男女关系等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现实生活,自然受到追捧与喜爱。由此可见,唐传奇现实化的故事情节能够契合市民观众的生活,让观众从中寻觅许多现实性的问题。唐传奇这种“接地气”的风格特点符合市民观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趣味,因此得到了元杂剧作家自觉的接受。他们将这种风格的唐传奇改编之后搬演于舞台,使得文字生动立体,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接受。正是唐传奇作品的这种“现实性”情节符合元代民众审美趣味,才使元杂剧作家热衷于对其进行大量改编。
2.虚实结合的奇幻性创作特征能够吸引观众视线。除现实化的故事外,还有一些唐传奇婚恋故事在创作上逐渐摆脱了史家叙事法的影响,加入虚构、夸张的情节,由虚而实,虚事实写,显示出小说艺术创作的自觉。这类唐传奇因故事情节的传奇性而受到读者的喜爱,也为婚恋题材元杂剧创作的情节设置提供了借鉴,元杂剧作家予以继承与改编。例如,《离魂记》中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主要情节都是虚幻的,张倩娘以魂魄追表兄王宙并最终团圆还魂,想象大胆奇特,作家只在结尾处附带介绍了传闻的出处、来源,强调故事的真实可信。众多奇幻恋情的婚恋作品皆为此类,不必一一列举。可见,唐传奇的创作立足于“奇”,内容奇异,情节曲折,辞藻华丽动人,适合进行改编之后搬演于舞台。李渔曾评价元杂剧:“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5]15由此而言,元杂剧的创作追求与唐传奇相似,也极力追求故事情节的传奇色彩。唐传奇这种戏剧性很强的婚恋题材故事,时刻在制造矛盾、冲突,充分注重情节结构,自觉地运用艺术想象,将奇特之人、灵异之事再现于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中,非常容易进行改编进而吸引观众。这种虚实结合的奇幻性创作特征能够紧紧抓住读者与观众的视线,因此奇幻性较强的婚恋题材的唐传奇作品改编性强,改编难度小的特点,既为元杂剧婚恋剧创作的情节设置提供了借鉴,又容易吸引读者与观众的视线。这种借鉴表现在元杂剧中,如《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以实写为主,但也有《草桥店梦莺莺》的梦境描写,生动地抒写了张生与崔莺莺别后相思之情。又如《迷青琐倩女离魂》在《离魂记》的基础上以王文举与张倩女分别之后,倩女的魂魄追逐王文举进京赴考的情节,在奇幻的超现实的情节中,把倩女与文举渴望与追求爱情婚姻的理想展示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与情感冲击。同时,具有时代性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理想在元杂剧婚恋剧作品中得到集中展示,并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总之,唐传奇作为“一代之奇”的比较成熟的叙事文体,给后世元杂剧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人物、情节等方面的有益借鉴,在婚恋题材作品上显得尤为突出。丰富的婚恋故事素材、典型的艺术形象以及与市民观众相符的审美趣味是元杂剧继承唐传奇而进行创作的重要原因。
三、元杂剧对唐传奇婚恋题材再创作的价值
元杂剧以唐传奇的婚恋故事为借鉴进行改编与创新,可以看出二者的亲密关系。其价值有三个方面:
(一)思想价值
元杂剧的婚恋剧在以唐传奇为蓝本进行再创作时,并没有完全因袭唐传奇婚恋故事的思想主题,而是加以改造使其富有新的时代意义,使改编后的元杂剧在唐传奇婚恋故事基础上具有了更丰富的思想价值。例如,以元稹《莺莺传》为蓝本再创作的《西厢记》,作者并没有直接因袭元稹始乱终弃“善补过”[4]356的主题思想,而是赋予作品新的思想内涵:《西厢记》中的张生有情有义,有始有终,对崔莺莺负责到底,在功名遂成之后按照约定迎娶旧时的恋人过门,赞颂了“重爱情,轻门第”的主题思想,“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6]1025。可见,剧作家王实甫取用唐传奇的婚恋故事进行创作时,将具有时代性的思想内涵蕴含于故事之中,大力宣扬了文人士子尊重女性、知情重义的美好品德,肯定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这使得《莺莺传》不再只是风流士子的故事,而是增添了肯定知识分子价值的作用,可以说元杂剧《西厢记》丰富了唐传奇《莺莺传》的思想内涵。又如《曲江池》中的李亚仙。李亚仙与《李娃传》中的李娃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形象,李娃是有意勾引郑生,使计骗光其钱财后离他而去,很难说李娃对郑生有爱情的存在,更不必说其抗争性。而李亚仙则是一个勇敢追求爱情的形象,她自己赎身供养郑元和,助其高中,与其私自结为夫妻,一路走来,对爱情坚持和努力。可见,在元杂剧的婚恋剧中,男女主角对爱情的追求更加真诚、炽烈,对封建礼教束缚展现出更强烈的抗争性,这是前代作品中少有的思想,对后世文学的婚恋爱情题材作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元杂剧再创作的过程中,同一题材的故事思想性更加饱满,内涵更丰盈,更具有时代特色与思想价值。
(二)文学价值
元杂剧以唐传奇婚恋题材进行再创作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剧本题材、形象塑造、叙事模式三个方面。
首先,元杂剧作家在创作婚恋剧时借鉴唐传奇中的婚恋故事题材,使得改编后的唐传奇故事以元杂剧这种新的文学样式继续产生了更广泛的文学效应。唐传奇丰富而成熟的婚恋故事素材为元杂剧提供了故事题材蓝本,对同样需要故事充实文本的元杂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杂剧作家在创作时对婚恋题材的唐传奇故事细节进行完善补充后搬演于舞台之上,使得这部分唐传奇的传播空间扩大,传播范围更广,进而在民众当中产生了更广泛的文学效应。
其次,元杂剧塑造了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婚恋题材的唐传奇中塑造的丰富的人物形象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元杂剧婚恋剧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同时,元杂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注重对艺术形象给予加工和丰富,使之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这又使得唐传奇中的人物形象在元杂剧创作与表演中焕发出新的艺术光彩。
最后,元杂剧的婚恋剧丰富完善了唐传奇的叙事体制。元杂剧婚恋剧所接受、取用的唐传奇婚恋故事已不是在生活中直接取用的素材,而是具有一定叙述形式的文本,那么,它们在接受唐传奇的故事题材时,唐传奇的叙事模式就必然会潜移默化地为元杂剧作家所使用,从而影响婚恋剧的叙述体制。这种叙述性话语的借鉴,丰富了元杂剧的艺术表现形式,使得剧作家在设置时间、空间时可以凭故事需要自由切换,情节结构可以做到幅度广而密度松,演员使用这种叙述性话语时可以随意跳出虚拟故事直接与观众接触。同时,元杂剧在采用唐传奇叙述性话语模式时,也融入了诗词的抒情元素,婚恋剧的宾白部分为散文形式的叙述体,演唱部分为韵文形式的抒情体。韵散结合的叙事模式,组合出新的艺术效果,这也使得唐传奇单一的叙事模式在元杂剧的叙事体制中得到了完善与丰富。同时,元杂剧戏曲艺术中程式化、虚拟写意性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成为中国古代戏曲的重要形式特征。
(三)传播价值
元杂剧与唐传奇在社会传播方面起到了互相促进的作用。一方面,当唐传奇的婚恋故事被元杂剧重新敷演时,其中丰富的故事素材、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委曲生动的故事情节都给予元杂剧以思想与艺术上的影响,丰富了元杂剧婚恋剧的题材内容、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情节,让元杂剧的发展有了可借鉴的实在基础;另一方面,元杂剧婚恋剧承袭唐传奇的作品与题材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唐传奇的接受群体,促进了元代以及后世更广大的群体对唐传奇婚恋故事的了解熟悉。元杂剧通过形象直观的演绎,直接地以视、听的方式作用于观众,使得一部分不接触文本的民众也受到了感染与熏陶。清代焦循对农民观剧的情形有所记述:“天既炎暑,田事余闲,群坐柳阴棚下,侈谭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7]225元杂剧这种文艺形式因受民众欢迎而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戏曲文化环境中,唐传奇的婚恋故事被改编为元杂剧,就获得了更多的接受者,由此也扩大了唐传奇在民间的传播与影响。可以说,元杂剧是唐传奇与民众扩大连接的一种很好的传播载体。
陈文忠先生曾阐述诗歌的意义为:“今人的重新思考和再阐释,并非意味着阐释史从此终止,它也只是无尽阐释史的一个环节……优秀作品是读不尽说不完的。”[8]5用它来说明唐传奇的“意义整体”也同样适应。唐传奇婚恋题材作品的丰富内涵与意义同样需要在理解的历史进程中去逐渐挖掘和展现。而元杂剧的婚恋剧正好成为唐传奇婚恋题材作品在新时代被再创作、再阐释的艺术新载体,它将唐传奇的意义与内涵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挖掘和丰富,这不仅使得唐传奇的内容与艺术风貌得到保存和流传,更使一些元杂剧的创作有了本事基础,二者的关系不仅是互相映照,彼此成就,而且共同促进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小说与戏曲中婚恋作品的交融,丰富了婚恋题材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唐传奇小说的婚恋题材,为元杂剧婚恋剧的借鉴、改编奠定了基础,影响了元杂剧的创作题材;元杂剧婚恋剧在接受唐传奇婚恋题材的基础上,又创新发展,赋予婚恋剧以新时代的思想元素,使其更具有思想解放、歌颂爱情自由的主旨,在情节结构与叙事方式上丰富了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爱情题材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为后世叙事文学小说、戏曲婚恋题材作品所接受与借鉴(如《西厢记》对《红楼梦》),对后世婚恋题材作品的创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