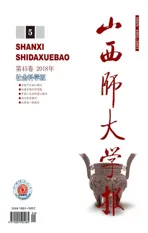近代转型期的“国民”话语建构
2018-04-04罗崇宏
罗 崇 宏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一、引言
本文中的“转型期”是借鉴了张灏的“转型时代”时间划分、梁启超的“过渡时代”的概念规定以及耿云志的“转型期”而命名。张灏认为,“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5年初前后大约3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1]3;梁启超在1901年6月26日的《清议报》上发表的文章《过渡时代论》中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2]710;而耿云志的命名则更加笼统,“从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就进入近代转型期”[3]3。可以看出,这些知识分子所说的“过渡”大体在1900年前后20或30年的时间段。本文要讨论的是“改良”与“革命”语境下的国民话语建构问题。不过,这两种几乎相对的国民话语,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革命”话语逐渐占据主流,且大有淹没“改良”话语言说之势。有鉴于此,本文把“转型期”暂且设定为1895—1911年这一时间段之内。
众所周知,话语的转型主要源于言说主体和言说语境的转移,并由此引起对话语言说对象的重构。在传统的“臣民”时代,言说主体是君主与封建知识分子,而封建知识分子又大致有两种言说,一是作为主流话语的贯彻者和“传声筒”,把“君主”的意志付诸文字并进行话语强化,在话语实践上倾向于“以君为本”;另一种是具有“平民”情怀的知识分子则将话语视角移向社会底层,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倡导名副其实的“以民文本”。
然而,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语境当中,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实质上是“不在场”的,即便是在知识分子的话语场中,“民”也是被管理、被作为政治调解的对象,而不具有离开统治模式的独立主体性,因而也是“第二性”的。总体而言“民”对国家、社会更多的是在尽义务,而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权利。
到了近代,随着启蒙现代性被译介到中国,一批有着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在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中“人”在社会变革中的关键性作用。于是,拥有话语权的近代知识分子重新塑造了有别于“臣民”的“国民”形象:“国以民为重,故称国民”,“国民对于国家,必完全享有国家的权利,也必要担任国家的义务”。[4]179—180基于对“国”的认识,这里不是把“国”视为一个统治型的王国,而是所有民众共同参与的“国家”。这样“民”自然成为“国”的主体,其地位从依附转移为自主。因此我们说从“臣民”到“国民”的话语转换既是“现代性”的客观要求,又是启蒙知识分子不断言说的结果。本文中我们一般把“臣民”到“国民”转换的关节点认定为1900年前后,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前后,近代“国民”概念的命名正式从“臣民”变成了“新民”“国民”等初具现代性意涵的“国民”语义场。尽管从概念史来看,某一概念突变和断裂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时间点,但不能否认新的话语系统强制性地把“臣民”以重新命名的方式改造成了“新民”和“国民”等。
二、“国民”话语的现代转型
可以说,从“臣民”到“国民”的现代转型是由不同时代的语境与言说机制所致。但是作为国民话语“指示器”的“国民”这一语词,其使用含有某种偶然性与随机性。黄克武在论述中国近代用以表达新观念的新语汇时认为,其语汇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从西方传教士的书刊中所创造的新词汇,一是当时留日学生从日本引进的日译新名词,双方或采音译,或从中国古典著作中汲取灵感来创造新词,且两者之间互有交流”[1]462。不过,近代“国民”概念的出现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金观涛认为由于近代使用“国民”用语比较早,甚至“日本的‘国民’一词也很可能来自中国”[5]85。早在1833—1837年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一书中就出现了“国民”用语:
所以强调“国民之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远近异形,要其水源则一”。[6]13
到了1843年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也提到“国民”一词:
道光二十七年,民叛,国王逃避于英国,国民又自专制,不复立君矣。[7]1217
显然,这些“国民”用语与近代的“国民”概念尚有很大不同。金观涛在《观念史研究》一书中也对“国民”概念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检索“数据库”可以看到,把中国人称为“国民”发生在甲午后。这意味着“国民”越出儒学经世致用的范围,成为民族国家的组成单位。更准确地说,“国民”作为公共意识的一部分,是1900年中西二分二元论意义形成后的事;用其指涉中国人,则表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国家主权是由国民权利合成。[5]85
可见,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现代意义上的与“国家”相关联的“国民”概念是出现在1900年之后的,而在这之前特别是洋务运动期间,“‘国民’大多用于指涉外国人,极少出现用来指涉中国人的例句”[5]85。因为“国民”概念的生成与“国家”密切相关,“而‘国家’一词的使用,也是在1895年后突然增加了”[5]242,从金观涛在《观念史研究》一书中所列的“‘天下’、‘民族’和‘国家’使用次数(1860—1915)”曲线图可以看出,1900年是“国家”这个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5]242。
不过,“国民”话语的现代转型不仅仅与“国家”相关,与之相关的新的“民”概念的生成也功不可没,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语义场,即“国民”的现代语义场,包括民、新民、公民、族民、庶民、平民等。
这样就有必要对“国民”语义场里的新概念作一简单的区分。本文里“国民”话语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国民”与“族民”相类似,在法律上“国民”近似共同体内的所有成员的概念。但“国民”与“族民”也有很大区别:国民对应的英语词是Nation,而族民则是People;国民是“共住同国之民众”,有参政权,族民是同种族之民众,属于人种学之意义,没有法人资格;国民只能住在同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国家不能有几种国民同时存在,但是族民则可以分属几个国家。[8]111“国民”与“平民”也不相同,侠少在《国民的国家》中认为:平民(Plebeians)起源于罗马王政时代及共和时代,是与贵族相对的词,不是国内人民一切平等,“盖平民者,即吾国古代所谓庶人”,“国民者,则统君主贵族平民而言也”。[9]113—114显然,文中认为“国民”是一个平等的概念,而“平民”则指的是阶级色彩比较明显的的底层人民。再就是“国民”与“人民”的差异,“人民者,无数之个人也。国民者,则人民之全体”。[9]113—114这样言说似乎还没能够把他们区分清楚,侠少在《国民的国家》中继续对它们进行甄别,“国民者,为统一的意思,而称人类之多数为国民”,“国民者,法人也;人民者,自然人也。国民者,法律上之无形人也;人民者,事实上之有形人也”[9]115—116。当然“人民”的概念也是有变化的,如自延安后期始,“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中特指在其意识形态阵营之内的人群,与之相对的则为敌人。看来“国民”是与“国”紧密相连的,有“国”才有“民”,是在“国”意义下建构起来的一个法律概念;而“人民”则没有与“国”紧紧绑定在一起。
可见,“国民”之所以与“族民”“平民”“人民”概念有所区别,主要在于“国民”是法律上的、有国家意识、有平等意识的现代概念,是基于启蒙现代性话语之上建构起来的概念,同时也是建立在现代法治国家之上的政治话语。而“国民”概念的这些现代内涵,都是转型期的时代话语在对“国民”进行言说的过程中不断赋予其特定意义的结果。
三、“改良”与“革命”派的“国民”话语建构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古今交替、东西碰撞的时代,各种思想流派交织在一起。于是,一些知识分子各自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基于不同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提出了不同的“国民”话语。在这个多声部混响的话语场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话语斗争:改良派的“国民”话语和革命派的“国民”话语,它们均源于现代意义上“民”的话语,但由于对社会走向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实现现代社会所采用的不同实现方式而形成了不同的话语体系。简单地说,“‘革命’被等同于政治结构的激烈变革,它与暴力密切相连,并与‘改良’相对立。”[9]
当然,“改良”与“革命”的不同言说,最直接的理论渊源还是基于人们对于Revolution的不同理解,即“改良”与“革命”。具体地说“革命”派大致延续了中国传统的“革命”话语,即把它等同于暴力的政治行为方式。这种“暴力”式的“革命”言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逐渐成为主流,如毛泽东也曾经说过,“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10]17。而“改良”派对Revolution的理解与这一概念的“理论旅行”密切相关。梁启超在《释革》中说:“‘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11]可见,梁启超发明的“革命”概念,“其实已经脱离了暴力手段改朝换代的中国传统‘革命’的语境,而带有强烈的日本色彩,并与西方和平演进的革命意义相融合”[10]。之所以说梁启超所说的“革命”是他自己的发明结果,是因为“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12]35。因此,梁启超在日本译文“改革”“革新”的基础上,采用“变革”来翻译Revolution[10],也即祛除“暴力”语义之后的“改良”。
另外,秦力山以一种描述性的方式对“改良”和“革命”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
今试有一物于此,其全体尚未破坏,而有一部分之丧失或糜烂,吾人为弥补之,或更易之,使成一完全之物,是之谓改良。有一物于此,其全体皆腐败,或腐败其大半,今欲修补之,反不如更张之,其资力益神,于是乎弃此而另置一物,其义直同于革命。[13]140
可见,“改良”是在“原物”的基础上“修补”,使之成为“完全之物”;而“革命”是弃一物而“另置一物”。显然,这个“物”指的就是“改良”与“革命”话语中的“社会制度”。
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他们的“国民”话语言说主体大都是近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在吸收了经日本中转而来的源于西方的“被译介的现代性”之后,用西方的“公民”(Citizen)改造中国传统的“臣民”概念,而“公民”话语中的核心概念是“民主”(Democracy)。这个“民主”概念自日本“旅行”到近代知识分子那里之后,一方面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或“贵民”的理想有所对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如三权分立、地方自治,宪法等,从而在近代知识分子那里被整合进现代“国民”概念之中。
重要的是,尽管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话语分歧源于对“革命”概念的不同语义选择,但是在铸造现代“国民”形象的言说中却表现出不谋而合的情况。从总体趋势上看,他们对于“国民”的言说呈现出始而有异、渐次趋同的情形。也就是说,他们的“国民”话语中常常包含大致相同的关键词,如1901年刊登在《国民报》中的《说国民》一文就详细地列举了与“国民”相关的几个关键词:权利、责任、自由、平等、独立等。
其一,改良派与革命派都倡导健全的“国民”要有权利。近代知识分子之所以大力鼓吹权利,原因在于他们所构想的传统“臣民”是没有自主权利可言的,而现代“国民”一旦失去了权利,他们很可能会退回到“臣民”的行列之中,而徒具奴隶的根性。
秦力山将“权利”视为“国民”与“奴隶”的重要区分,“所谓国民者,必有参政之实权”[14]62;不仅如此,“权利”属于国家也属于“国民”,邵力子在《主权在民》中认为“共和国之主权,当然属于国民全体”[14]。当然,权利之于现代健全“国民”的生成还体现在其“功效”上,1903年发表在《直报》上的《权利篇》一文也认为“可以救吾民之质格、打破礼法之教者,无他,吾只恃权利思想”[15]。可见,权利的巨大“功效”在于救“质格”、破“礼法”,其目的可以“全”人之本性,权利甚至与宗教、政治等同等重要。
然而,中国人只知道“食色”的重要性,却不知权利能够维持人性的健全。而权利的作用一是强制,二是竞争。“竞争者,富强之兆也”;“强制者何?制人不制于人之谓也”。人如果没有权利则会受制于人,那么人性自然就不会健全,更有甚者“不能制人者必为人所制”。而权利的实质就是“人之本分也”[16]344。那么,倘若国民有了“权利”又当如何呢?权利能够全人之本性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以与他人竞争而强制他人者也”[18]。可见,权利不光是法律意义上的东西,更是塑造健全之“国民”的重要部分;不光能够不受制于人,更有甚者能够“强制他人”。
不仅如此,革命者陈天华在强调国民的权利的同时还强调其义务,“何谓义务?义务的话,犹言各人本分内所当做的事,所当负的责,通皇帝、官长、国民都是有的。”国民“当以义务向皇帝、官长要求权利,不可抛弃权利,因就不尽义务。义务的解释如此。”[4]180陈天华的义务概念更多还是倾向于权利,通过义务来实现更多的权利,并且他还提出实现国民权利的几个必要条件:学问、武力、合群和坚韧。[4]197而汪兆铭则将“权利”与“义务”并举,“有权利义务,此国民之真谛也”[17]。当然,革命派对于“权利”强调的最强音者当属孙中山。在1905年的《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明确地把“民权”作为其三大主义之一;然后孙中山又在1905年秋发表的《与汪精卫的谈话》一文中提出:“革命以民权为目的……革命之志在获民权。”[18]
此外,“国民”的权利问题还应该包括男女平等的权利,也即女子要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各种权利,这也是“国民”与“臣民”的重要区分。“臣民”被认为是男尊女卑时代的产物,而“国民”则是男女平等时代的话语。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此有较为详实的言述:
窃谓女之与男既同为人体,同为天民,亦同为国民。同为天民,则有天权而不可侵之,同为国民,则有民权而不可攘之。[19]
近代由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所“制造”的“国民”已经深入人心,然而许多文本尤其是官方的许多条文中实际上还是把男女区别对待,就像邵力子所说:“从法律上去看,许多条文,都是把女子屏在‘国民’或‘人’以外的。”[20]就是说,如果女子不能享有更多的权利,那么她们就被排除在“国民”之外,那“国民”也就退回到“臣民”的言说之中。
其二,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国民”话语都是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将国民与国家想象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1]39。
改良派知识分子认为,作为政治话语的“国民”与现代“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国民”的主体性体现在它是“构成国家之实体”,梁启超就认为“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22]309。不仅如此,“国民”与“奴隶”的区分也表现在与“国家”的关联上:
凡立于一国之下,而与国家关系休戚者,则曰国民;立于一国之下,而与国无关系休戚者,则曰奴隶。[23]
我们说“国民”与“臣民”的不同在于其既有义务又有“权利”,而这个“权利”也必须与“国家”相勾连才能够实现。对此梁启超有更详实的言述:
一曰:国民者,人格也。据有机之国家以为其体,而能发表其意想,制定其权利者也;二曰:国民者,法团也,生存于国家中之一法律体也。国家有完全统一永生之公同体,而此体也,必赖有国民活动之精神以充之,而全体乃成。故有国家即有国民,无国家亦无国民,二者实同物异名也。[2]452
可以看出,“国民”是“国家”的“精神”和“人格”,“国民”的权利也要在“国家”的法律中得到保证。同时立国也是立民,只有创立了“现代”国家,才能塑造“现代”的国民。此外,梁启超还用“人格”把“国家”与“国民”连接起来:
人格云者,谓法律上视之为一个人也。而国家者,则最高最大之团体,而具有人格者也。[22]
梁启超认为“国家”与“国民”具有相同的“人格”,这就使“国家”成为“国民”的团体。这种对“国家”的认识与中国传统观念完全不同,“国家不是领土,不是君主,也不是社会中任何一个家庭或者社会本身,而是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独立实体”[24]。这种具有法人意义的“独立实体”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的意涵,诚如英国学者约翰·麦克里兰(J.S.McClelland)所说“国家要中立,必须与社会分开”[25]328,与社会分开保持“中立”性的国家既不偏向传统的君主、贵族,也不偏向其他人。在这种国家 “语境”中才能“制造”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
与改良派稍有不同的是,革命派知识分子更多的是把“民”视为“国”的“民”或把“国”视为“民”的“国”,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革命者陈天华就是从“民”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来阐述“国民”概念:
何谓国民?没有国之时,一定必先有人民,由人民聚集起来,才成了一个国家。国以民为重,故称国民。国民的讲法,是言民为国的主人,非是言民为国的奴隶。[4]179
“国家”是由“国民”聚集而成的,并且能称之为“国民”者,民必须是国家的主人而非奴隶。同样,戊戌变法之后的秦力山以“国”为基础来言说“国民”,“划一土于大地之中界,而命之曰国;群万众于一土之中域,而区之曰国民。”[13]45也即有“国”才有“国民”。廖仲恺则是以“所有”“所治”“所享”等词强调“民”与“国”的关系,认为“中华民国就是‘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的国家”[26]。杜亚泉也有类似言论,“国家者,国民共同之大厦。我国民生于斯,聚于斯,而不可一日无者也”[27]130—131,也就是“国家”是“国民”生存的“大厦”。而邵力子更是从“国本”的层面论证“国民”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他在《和平会议开幕》一文中说“国本何在,在于国民”[28]86。
然而,近代中国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以及外来列强的入侵,无论是革命派抑或是改良派都有“无国感”或“无国民感”的焦虑。对此王汎森有很好的概括:
在革命派方面,主要是从种族主义观点出发而得出无国的结论,他们抱怨过去两百多年间中国是被异族所窃据,看来有国,其实是 “无国”……另外一种“无国”的感叹,则是从现代国家(Nationstate)的角度发出的,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朝廷”,没有“无国”。[29]169—170
可见,至少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前,深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革命派认为,由于“国”被异族“所窃取”,“国家”实际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因而在这种“排满”意识的驱使下,革命派此时的“国民”概念是把满族排除在外的。另外,革命派的“国家”特别强调一种现代意识,否则只能称之为“朝廷”。这种“无国”感意味着无现代国民可言,同时也成为近代知识分子建构现代“国民”的思想基础。
其三,改良派与革命派都以“命名”的方式“制造”出“国民”的概念。作为言说主体的精英知识分子,把“命名”作为制造“国民”的重要方式。常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命名的过程便是赋予其意义,对其进行书写的过程,也是由世界的物质存在转化为知识客体的过程”[30]232。可以说,命名也是一种权力和意识形态表征,同时也是制造意义的基本前提。由前文可知,尽管“国民”用语自古就有,但是现代“国民”显然是被融入了诸如权利、责任等现代性要素的新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为今用、概念“旅行”本身也是一种重新命名或再概念化。
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常常以“国民”来命名各种刊物和团体。改良派的命名包括1902年创刊并命名的《新民丛报》以及1910年的《国民公报》等;以“国民”命名的团体有“国民公会”等。同样,革命派所创办的以“国民”命名的报刊杂志包括1901年的《国民报》、1903年的《国民日日报》以及1919年的《国民》杂志;革命派还将自己的政党取名为“国民党”,同时把他们所从事的革命定性为“国民革命”。秦力山甚至在《〈国民报〉序例》中以下定义的方式来命名“国民”:“能尽其责而善其事,则其地治,其国强,其民有完全无缺之人权,可表而异之曰国民。”[29]45这些命名都体现了当时的“国民”话语所带来的影响。
四、结语
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国民”言说趋同的原因有很多,从总体上看,近代知识分子虽然存在“改良”与“革命”的分野,但实际情形也没有那么泾渭分明,这既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处于共同的“转型期”的时代语境,从而对“国民”表现出大致类似的话语诉求:“革命与立宪,要非绝对的名词也。夫立宪为专制改良的政体,而革命者,即所以求此政体之具也。求共和立宪以革命,求君主立宪亦以革命。”[31]沈松侨更明确谈到两派的共同出发点,“两派人士,取径固有参差,策略不无轩轾,原其本心,要皆以塑造深具权利、义务观念,享受自由、平等,并能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之中国新‘国民’为旨归”[32]711。另外,这种趋同也源于一些知识分子意识的“摇摆性”,比如“改良”派的主要代表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后期就表现出明显的“革命”倾向,并因此不惜与其老师康有为决裂;秦力山的经历也很具有代表性,在中国近代史上秦力山“活动于戊戌维新运动前后至辛亥革命初期,都属于维新运动中的激进派,而在变法失败后又不同程度地走上了革命道路”[29]1;还有早年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赞成维新变法的章太炎,在1900年之后从维新梦中惊醒,“强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33]前言1—2。
事实上,当时的很多“改良”派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后几乎都被“革命”话语所收编。当然,改良派与革命派在“国民”话语言说的侧重点上还是有明显差异的,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部民”与“国民”进行对比,所强调的是“国民”的国家意识;而《国民报》中的《说国民》一文则把“国民”与“奴隶”比较,更注重的是“国民”的“权利”意识。更具代表性的是上文所提到的孙中山在“三大主义”中对于“民权”的强调。这些从某种意义上昭示了后来“国民”话语的两种不同发展路向,即“一个从国家意识阐释国民,一个从民权本位强调国民,以后发展出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两种歧路”[2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