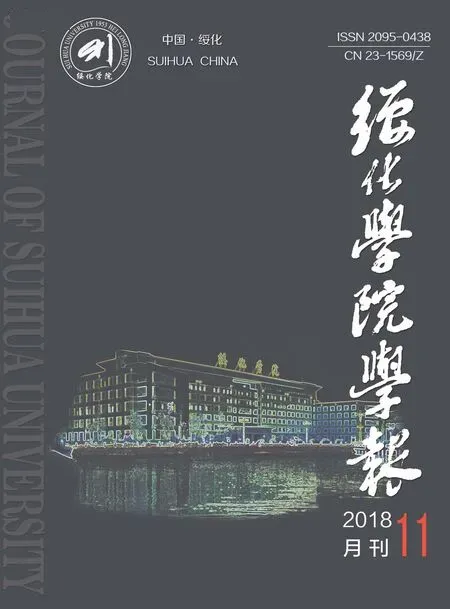徽州民间采茶舞的文化人类学解析
2018-04-03史一丰
史一丰
(黄山学院艺术学院 安徽黄山 245041)
舞蹈是人体在时间和运动中不断展示艺术美的表演形式。表演者通过不断的人体位移和肢体变换表达内心情感,析解作品的艺术内涵。因而,舞蹈作品及其演绎与人在其中发挥主导密不可分,从而表现着舞蹈表演艺术和其作品的文化特质。对于人类文化的解释,梳理前人的研究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张文勋等著的《民族文化学》导论中就人类“文化”这一定义进行了探讨,指出了文化不论是包含与人相关的一切包罗万象的创造还是仅指人的精神世界,还是两者互相交错,纷繁复杂的界定,都是现有世界上对文化的解释,都有其科学性,只是界定的视角和界定者的定位不同罢了。我们所理解的文化,从形式看是包含物质与精神创造,从实质看,则是对人们有某种支配意义,且为人们所认同(包括遵循、依托)的模式、符号、观念等。[1]也就是说,以人们所认同的模式、符号、观念作为外在表象,且具有内在依托的这类形式上表现为物质和精神的创造才是我们所要理解的人类文化。所谓模式、符号、观念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所谈论的舞蹈艺术就是以人体来表达的一种肢体语言、一种人体的符号。所以,考察舞蹈首先要了解相关的人(创作者、表演者)及其文化,在将舞蹈作品置于该特定的文化景观之中,来解析人的创作、人的表演的文化功能。笔者选取徽州民间采茶舞作为研究视点,正是因为徽州这块土地有着浓厚的地域文化,有其独特的文化叙事,且在表现形式尤为多样。已有的徽州艺术内容丰富、形式各异。雕刻、版画、民歌、戏曲、舞蹈等皆带有“徽州味道”的烙印。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审视徽州民间采茶舞,我们不光是要让徽州民间舞蹈艺术永放光芒,更是通过去枝打叶,再现徽州民间舞蹈背后的文化内涵,可以这么说,作为文化的徽州民间采茶舞是徽州人创造的一种地方艺术形式。
一、徽州民间采茶舞的文化背景
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境内崇山环绕,平原较少。当地农村主要种植适合山区生产的农植物为主,茶叶是徽州一带农耕的主要作物。每年清明前夕,是茶农当年第一次采摘时节。明前茶价格颇高,但是产量相比较低,又因为是当年的头一次摘采,所以,徽州各地的菜农都要举行一个简短的采摘仪式。徽州的富硒、祁门、歙县等地都有类似采摘节。主要内容各地都差不多,简单的仪式多为燃放鞭炮、地方领导致辞即罢,一般在祁门一带还有茶农穿上青花帆布衣裳,背起竹篓跳起《采茶舞》。又一说是《采茶扑蝶舞》,据《祁门县志》“舞蹈”条目记载:“《扑蝶舞》原名扑蝶灯,是流传在西乡彭龙村的一种民间舞蹈。最初在元宵闹花灯时表演,……表现人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喜悦心情。”[2]《徽州戏曲》一书中记述:“采茶有《采茶歌》、《扑蝶舞》。”[3]在实地调研中,祁门县茶农对《采茶舞》的解释为因清明时节茶树地中偶有蝴蝶飞过,茶农在摘采同时偶有扑打蝴蝶之事,所以在舞蹈中带有扑打的动作。笔者认为,《采茶舞》或说《采茶扑蝶舞》都是摘采茶叶这一农事活动的艺术再现,舞蹈中带有扑打蝴蝶的动作更能够体现茶农摘采的惬意和对茶叶丰产的喜悦。
徽州民间采茶舞的产生,各地地方志都没有清楚的记载,然而,在调研中,茶农的都说从老一辈开始,每年开采时节或者采摘闲时,茶农都要跳采茶舞,主要的动作多为模仿摘采茶叶的动作。问起何意之时,茶农的解释为祈盼当年茶叶丰收,也为采摘之间休息娱乐之用。调研中还发现,祁门的采茶舞多为边唱边跳,故而,在祁门农村《采茶舞》也称《采茶歌》。说为演唱其实是口语化的吟诵,以当地方言为主。贝林特指出:对于与歌唱结合在一起的舞蹈——这是最早、最普遍的参与性艺术——来说,社会性表现得更深刻,它深深得嵌入了每一种人类文化之中。[4]在徽州一带,尤其是祁门县和徽州区富硒乡这两个茶叶主要产区,采茶舞不仅在每年茶叶开采时作为节目来表演,农闲时、节庆时,当地老百姓都跳采茶舞作为娱乐、健身的手段。地方文化部门在每年参加省市的文艺演出、群星奖比赛中,以采茶舞为主要创作基点,排练了许多带有地方泥土气息的舞蹈搬上舞台,把乡土舞蹈的文化创新做到了淋漓尽致。笔者认为,徽州民间采茶舞的产生虽没有文字的详细记载,但是从其存在的普遍性和表演的通俗性来说,植根于泥土并形体相传是毋庸置疑的。
二、作为文化特质的徽州民间采茶舞
文化特质是组成文化最基本元素之一。以文化特质为核心,通过文化功能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构建了文化丛。厦门大学周显宝教授指出文化特质具有四个特质,首要的一个特质是:每种文化特质一定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单位,并有其自己的特点和意义,而不与其它的文化特质混淆。[5]我们可以将徽州采茶舞视作为文化特质,把徽州民间音乐文化看作为文化丛,两者都置于徽州文化这一文化系统中来审视。徽州民间采茶舞包含表演者用方言吟唱、模拟采茶的肢体动作、穿插于中间的扑蝶动作。这就涉及到了徽州方言、徽州民歌、徽州习俗等文化子系统。
就徽州方言来说,“十里不同音”是对徽州方言各地迥异的真实写照。所以,徽州一带民间采茶舞表演时的演唱(也可称作为吟唱)大有不同,多半是演唱用的方言不同。笔者在多年的徽州民歌调研中,搜集了歙县、绩溪、祁门、石台等地采茶歌多首,通过对演唱者音频的梳理和比照,即使是雷同的歌词,听起来也大相径庭。所以考察徽州民间采茶舞的表演又能展示出徽州不同地域方言的特色。
就徽州民歌来说,上述提到的徽州民间采茶舞在表演时还带有调子吟唱,因徽州各地习俗、方言等多有不同,故而,调子(民歌)的旋律也有许多变化。比如,歙县的《采茶歌》曲调平缓,歌词多为闲聊型,而祁门一带的《采茶歌》旋律变化起伏较大,高音出现的频率也较多;歌词除了闲聊之语外,还多有表达采茶之辛苦,祈盼丰产的话语。笔者认为,茶叶产地的地理面貌不同也是造就徽州民间采茶舞中演唱调子各异的主要因素。祁门一带群山连绵,接连不断,必然造就调子高亢、旋律变化起伏。
就徽州习俗来说,采茶舞多是在明前茶开采之前的仪式活动中表演。徽州各地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就祁门一带来说,采茶舞在闲暇时成为茶农娱乐、健身的载体。这在徽州其它地方很少见到。在调研中不难发现,在当广场舞流行的当下,祁门一带的中老年妇女还结合采茶舞的部分舞姿,编排出有声有色、婀娜多姿的群众性舞蹈。
作为文化特质的徽州民间采茶舞,我们暂且不论它的舞蹈动作是否专业、是否优美,不与杨丽萍、黄豆豆的舞蹈进行纵向比较,也不与赣南采茶戏中的舞蹈元素横向对比,徽州民间采茶舞一招一势、一唱一吟,谈不上大气磅礴,意向宇宙,多为含蓄、低调,略带有羞涩感。既把采茶这一农事活动体现得栩栩如生,也彰显出徽州文化哺育下的徽州地域民风淳朴、理性求真的徽州文化内涵。
三、徽州民间采茶舞的文化功能
在西方人类学发展史上,英国功能学派的诞生及其学说的影响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该学派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主要代表人物。该学派否定了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都源于进化论思想和传播论思想,也就是否定了进化论学派和传播论学派有关人类发展的学术主张。他们主张人类学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存文化或社会的分析和说明上,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对其社会都是有功能的,……。[6](P102)英国功能学派将人类学研究从古典主义过渡到现代主义,把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从“扶手椅”带向了田野,追求实证研究是英国功能学派的倡导的主要研究方法。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表格》成为当时直至现在仍然为文化人类学研究起到主导作用。
具体到文化功能的解析,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文化起到什么的样的功能?什么样的文化表现形式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曾列出了10种功能,分别是风俗、仪式活动、类别性称呼、宗教信仰、巫术、思想、道德、艺术、娱乐和游戏等。[6](P115-116)就徽州民间艺术文化来说,以徽州民间采茶舞为文化特质,结合徽州民间采茶舞在每年明前茶开采之前举办的仪式活动中模拟采茶忙碌的景象和茶农时而扑蝶的愉快场景的这一娱乐且又带有祈盼之意的功能,共同构建了徽州民间舞蹈艺术文化丛。从表现形式上看,虽然只是一个模拟采茶这一农事活动的舞蹈,但是,它隐含着茶农的一种祈盼丰产的意愿所在。因而,该舞蹈有神化的色彩、也有信仰和巫术的成分。尤其摘采的这一动作,表面上看到的是将茶叶采到竹篓中,事实上收获的是茶农一年的辛苦劳动和对丰收的喜悦之情。同样是舞蹈,舞台之上的肢体表现重在展现人的肢体艺术之美,而田野之中的肢体语言所表现的是憨厚的茶农淳朴的意愿。功能总是意味着某种需求的满足,从最简单的进食动作到领圣餐的圣礼操演都是如此。[7]将徽州民间采茶舞置于徽州文化中予以审视,它所能起到的文化功能当属于娱乐的功能,也伴有巫术、仪式活动和民间信仰等因素。主要是茶农为了满足其对当年茶叶丰收的祈盼之意愿。我们说,茶农的这一期望是朴素的,采茶舞的一招一势也是都来自于农事活动,所以,民间文化所能起到文化功能是对老百姓生产生活鼓舞的一种内在驱动力。
文化人类学研究已成为对非西方小规模社会文化研究的主要视野,经过诸多文化人类学家的开拓和发展,当下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更为宽泛,研究的程度也更为深入。以人的艺术研究为例,不同社区、族群的文化艺术形式各异,且都代表着本社区、本族群的特有文化。选择其中任意一个方面作为揭示本文化特色的切入点,无论是音乐也好、舞蹈也好、绘画也罢,都可以将其内在的文化特征呈现出来。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介入徽州民间采茶舞的研究,是接通了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音乐学、舞蹈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精髓,在徽州文化这一文化景观的视阈内,把徽州民间采茶舞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质与其文化功能结合在一起,既注重舞蹈取材、编创、表演的文化背景,还强调了人在舞蹈表演中所呈现出的外在与内隐的表现,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