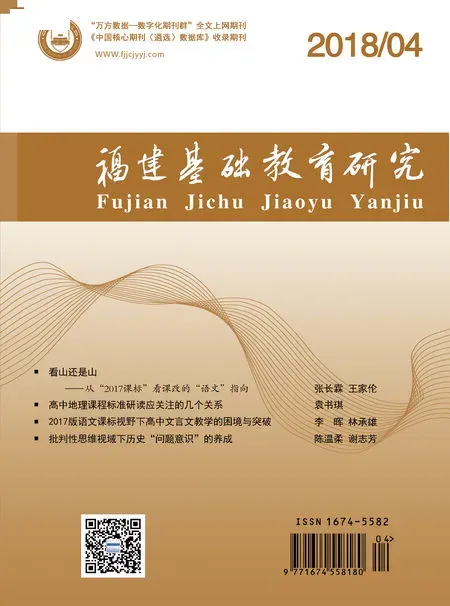课堂转型从空间转换开始
——班级学习共同体的座位安排探讨
2018-04-03郑艳红
郑艳红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上海 200000)
(郑艳红,上海大学附属中学高级教师,上海市第三期班主任带头人郑艳红工作室主持人,上海“学习共同体研究院”指导委员会委员)
日本东京大学佐藤学教授在《学校见闻录——学习共同体的实践》中指出:“以黑板与讲台为中心,每一个人排排坐在单向排列的课桌椅上,教师以教科书为中心讲解传递的同步的教学方式,在欧美各国正在进入博物馆。”[1]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展开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黑板和讲台从教室中消失,秧田式的课桌椅变成四五个人围坐的桌子。课堂空间座位的变化背后是从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转向以“学”为中心的教学;从“个人学习”转向“协同学习”。这场静悄悄的革命在我国悄然进行,“学习共同体”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课堂场景。
一、从“灌输中心教学”向“对话中心教学”转变
2001年,教育部发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强调,新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是要实现从“灌输中心教学”向“对话中心教学”的转变。灌输中心的教学是把学生作为被动接收的容器,学生端坐在座位上,认真地听、认真地看、认真地思考,认真地回答教师提出的各种问题。有经验的教师还不断向学生提出要求:上课思想要集中,思维要跟着教师转,和教师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可是,现实中的学生似乎不太愿意配合教师的教学,他们会认真听讲却不愿意与教师互动,他们会端坐在教室里思绪却四处游走。灌输中心的教学者认为传授课本中已有的知识就是学习,认为能熟记并能运用课本中已有知识的学生就是优秀的学习者。把知识的传递误认为学习,学生们逐渐丧失学习的兴趣,逐渐“逃离课堂”。
佐藤学教授提出:“所谓学习,是同客体(教材)的相遇与对话;是同他人(伙伴与教师)的相遇与对话;也是同自己的相遇与对话。”他提出:“学习原本就是合作性的,原本就是基于同他人合作的‘冲刺与挑战性的学习’。业已懂得、理解的东西即使滚瓜烂熟,也不能称为‘学习’。”[2]学习共同体的课堂教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话型实践”。学习是同客观世界的对话,同他者的对话,同自我的对话的实践。“真正的教学应当是‘知识的建构’;是教师引导学生同教科书对话、同他者对话、同自己的内心对话的活动;是合乎学科本质、基于‘相互倾听关系’而展开‘挑战性学习’的活动。”[3]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对话就没有学习,没有教学。
二、课堂空间座位变化让对话性沟通成为可能
戴尔克认为:“教学活动是在一定的物理环境中进行的,这一环境在某些十分重要的方面制约着学生学习与发展之可能性,环境这一舞台一旦搭起来,则于此上所进行的演出活动便已部分地被决定了。”[4]座位的不同安排对学生的学习存在较大的影响。
1.秧田式座位
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小学课堂座位编排呈秧田式:讲台置于教室块状空间的正前方,讲台下面是整齐排列的座位。教师习惯站在讲台前,学生只能看到教师的上半身。教师在黑板上板书、播放幻灯片,在讲台和黑板这块极其有限的空间里不断转动着身体。教师在教室的前面,学生面向教师,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教师的讲解上。这种课堂空间模式不断地强化教师“教”的中心。教师和学生都学会了“选择性倾听”。教师不会倾听学生的话,只会选择倾听自己需要的答案;学优生不会倾听学困生的回答,只会倾听教师的讲解;学困生既不会倾听教师的话语,又不会倾听同伴的话语,逐步丧失学习的兴趣。秧田式的座位方式使课堂成为“一言堂”,课堂教学的建立不是学生的主动参与建构。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逐步形成了僵硬的关系。
佐藤学教授指出,“同客观世界的对话、同他人的对话、同自我的对话的三位一体的活动,其基础就是基于柔和的声音和身体交往,基于‘倾听关系’的对话性沟通,具体的做法是所有的教学(小学三年级以上),由四人组成的小组展开协同学习”。传统的秧田式座位不改变,课堂的转型难以实现。
2.让学生面对学生
台湾林文生博士在《共同体的实践密码》讲座中提出,空间的力量是很大的,空间的变化会优于教材的力量。林博士用梅洛龙蒂的知觉现象学来解释: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走到一个吃着奶嘴的小男生跟前,互相认真地看一下,然后互相换奶嘴,又赶紧吐出来。孩子比较喜欢看到伙伴的身体,而不是大人,这是“知觉的优先性”。学生个性的展现是通过群体互动而展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孩子年龄越大,越不愿意举手发言。班级如果组建了相互倾听的同伴关系,弱势的学生,至少有一位同学在听他说话,不至于让他“逃离学习”。从纵向的师生互动转向横向的生生互动,这是同伴之间的“互为主体性”。学生喜欢这个群体,进而共筑一个温暖幸福的班级,这是“公社群性”。
在林文生博士的学习共同体实践课上,笔者担任了观察员,近距离观察了一位学习共同体课堂初体验的低年级学困生的变化。课堂呈U字型排列,学生面对着学生而坐。教师在U字型中间灵活走动,靠近学生的身体,柔软的声音和手势,都在营造一种平等合作的氛围,关注每一位孩子,努力构建他们良好的伙伴关系。笔者重点观察的一位男孩子,前半节课热衷于做各种与学习无关的小动作,后半节课,他慢慢向同伴表达自己的想法,先是一个词,再到一句简单的句子。他在和同伴的交流中,慢慢地进入文本,和同伴分享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虽然这节课他没有站起来回答教师的问题,但是,在一个接纳倾听他的同伴面前,他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课堂结束后,他主动和我打招呼,“这个小木偶太有趣了,太好玩了。这个语文课也很有意思。老师再见。”孩子变化的背后,是课堂空间的变化所带来的生生关系、师生关系的变化。
三、课堂空间座位的转变
课堂的物理环境能有利于积极学习,也能破坏积极学习。有时候,将课桌稍作调整便可创设不同的学习环境。即使是传统的课桌也可以组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布局。
1.U字型
U字型是一种能用于多种教学目的,多个年段的座位布置。学生有阅读或写作的桌面,能容易地看到教师或者其他视觉媒体,相互之间能面对面联系。学生结对也很容易,转过头就能形成两两同伴关系。如果转过身去,还可以和后面的两位同学形成四四关系。教师的活动空间很大,可以灵活走动,关注每一位学生。
U字型座位的摆放,让笔者的高中语文课堂实现了“学教翻转”。面对高一新生,笔者提出改变一下座位方式,学生一脸迷惑。笔者在黑板上画了U字型座位排放,同学们快速搬动课桌椅,一会儿就形成了新的座位方式。由于班级有40人,我们在U字型的左右两端、U字型底部各摆放了两排桌椅,同学们面对面而坐,稍一转头,就可以和旁边的伙伴组成两两倾听关系。变成摆设品的讲台被移到教室前方的角落里,同学一抬头就能看到黑板和多媒体屏幕,没有任何的遮挡。学生想要公开发表,可以自由灵活地来到U字型的中间,围坐在边上的同伴微笑地看着展示的同学,整个课堂洋溢着温暖信任的气息。这时候,笔者往往坐在教室一角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或者索性坐在学生的座位上,用心地倾听“同伴”的话语,往往前一批同学分享完,后一批同学急着起来分享,学生也忘记了教师的存在。学生的发言给了笔者很多启发,笔者在串联学生的发言中,深入了对文本的理解。U字型座位排放所带来的温暖、开放、自由的感受,深受师生的喜爱。
U字型的方式也同样适用于低年级的学生。对于一年级新生,首先要建立师生倾听关系,然后再是生生倾听关系。U字型座位的排放,让教师充分关注到每一位孩子,孩子和孩子并排坐在一起,不用再看着同伴的后脑勺,吃力地追随教师的身影。U字型座位的排放,让孩子的坐姿更加灵活自由,不用死板地按照原来的背挺直,双手平放在桌面上。笔者曾经到上海世博家园小学听过芮莹老师给入学半个月的一年级新生上的一节语文课,座位呈U字型排列,孩子感觉教师时时在自己的身边,时刻受到教师的关注。教师的身体或前倾,或下蹲,都是为了更好地和孩子建立倾听关系。教师不再当众点“不受规矩”孩子的姓名,而是很自然地摸摸孩子的头,拍拍孩子的肩,巧妙把孩子游离的注意力再引到课堂中来。在课后研讨时,观察员提到由于学生人数众多,依然有教师关注不到的孩子,比如U字型两端、教师背后的处于座位“死角”的孩子。芮莹老师充分听取了浦东发展研究学院陈静静博士的建议,把U字型中间的空间缩小,加长加多U型底部的位置;U型两边分成两半,中间空出通道;在课堂中间设置观察员点评环节,表扬倾听关系好的孩子,激励更多的孩子进入到温暖、润泽的倾听场域。
2.小组摆放形式
笔者在高中阶段和学生一起研究实践学习共同体多年,经历了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三人小组、四人小组等变化。笔者所任教的高中班级一般有四十人左右。小组协作学习,多少人为宜?一开始,我们考虑到教室空间不大,就把班级人数分成八组,每组五人,两个课桌并列排放在一起,四个课桌两两相对摆放,还有一个课桌摆放在四个课桌的下端,就像会议室的主持人的座位。四位同学两两相对而坐,一位同学正对着黑板而坐。在协同学习中,学生慢慢地发现,面对黑板而坐的学生,有的成了探讨的中心人物,有的却成为被忽略的对象。一旦五人中有一人掌控话语权,另外的组员就会感觉到不平等,从而失去探讨的兴趣。一旦五人中有人游离在探讨之外,小组间的倾听关系就不能很好的建设。于是我们进行了改革。
我们把面向讲台的第五个桌子撤掉,变成四人小组的排放形式,学生两两相对而坐,既能构成良好的两人倾听关系,在遇到冲刺而挑战性难题时,又能形成很好的四人倾听关系。小组间的倾听关系建立了,但是在小组上台展示的时候,由于班级中有十个小组,有些组与组之间座位摆放不合理,造成通道狭窄,小组成员不能灵活地到台上与全班同学分享,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也很难关注到教室后排的小组。于是,我们将小组与小组座位错落排放,让组与组的间隙更大,教师能自由地穿行在各组之间,观课的教师坐在学生旁边,也不至于感到拥挤。四人小组座位排放,给有稳定倾听关系的中高年级学生解决冲刺而挑战性问题,提供了可能。
班级的人数并不都是整数,四人分组后,可能会出现落单现象,于是就出现了三人小组和六人小组。三人小组,学生与学生的距离近,探讨方便,也是比较好的一种座位摆放方式,如果教室空间大,学生人数少,可以考虑。可是,三人座位排放方式也有缺陷。学生体验下来,不足之处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三人中如果有一人在探讨时不积极,很容易“落单”;二是在解决冲刺挑战性问题时,三人的思维碰撞不够。学生们在摆放座位时,有时候会出现六个人挤在一起不愿意分开,我们体验下来的优点是人多热闹,探讨更自由。可是不足之处更大。一是六人小组距离很远,很多时候探讨在两两间进行;二是六人共同体探讨,为了让对方听到,声音必须放大,有种闹哄哄的感觉;三是课堂探讨的时间有限,六人很难平衡话语权。
3.课堂空间座位的灵活摆放
座位的摆放,可以按照课堂的需要灵活调整。我们可以摆放成“团队风格”,将课桌围绕教室组合,从而有利于教师与团队互动。也可以让座位围城半圆形,这样就没有学生背对着教室前面。组合几张桌子形成会议桌式的布置,这种布置可以将教师的重要性最小化,而将学生的重要性最大化。或者可以去掉课桌,将学生安排成圆形。没有桌子或椅子,可以让学生产生最直接的面对面互动。还有“同心圆风格”、爆炸式分组、肩章式分组、礼堂式等等,座位的摆放可以根据课堂的需要灵活设置。
21世纪是“课堂革命”的世纪。课堂不变,教师不会变;教师不变,学校不会变。课堂的转型并不体现在公开课、研究课中,而是扎根于日常课堂教学改革实践。教师在课堂这块专业发展的沃土上,对传统的座位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在课堂中构建相互倾听、合作学习的关系,保障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权”,让每一位学生获得真正的学习与成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实现一场“静悄悄的宁静的革命”!
参考文献:
[1]〔日〕佐藤学.学校见闻录[M].钟启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8.
[2]〔日〕佐藤学.学校的挑战[M].钟启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0.
[3]钟启泉.课堂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6.
[4]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