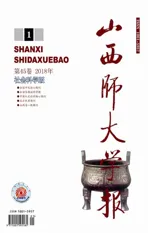论儒学与中国科学之关系
2018-04-03廖启云毛建儒
廖启云,毛建儒
(太原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太原 030024)
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的角度说包括儒学、道学、墨学等,从狭义的角度看则专指儒学。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儒学自身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具体地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等创立了儒学。到了两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把儒学确定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董仲舒本人就是一个大儒,他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在此之后,有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它们虽然发展势头强劲,且广为流行,但它们从未取代儒学的主导地位。时间推进到宋明,儒学又产生了新的形态,这就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儒学、道教、佛教的融合,这就是学界所说的“三教合一”。“三教合一”当然是以儒学为主导,因此称为儒学的新形态。
进入20世纪以后,儒学虽然遭到两次大的批判,即五四运动的批判和70年代的“批林批孔”,但儒学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它或者作为意识形态存在,或者流行于民间。不管是哪种情况,儒学在中国社会一直具有很大影响力,儒学仍然是中国人的道德依据和行为准则。
从20世纪90年代起,儒学又开始了新的复兴,而且复兴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对儒学的新的复兴,当然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面对分歧,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这就是儒学与中国科学是什么关系。具体地说,儒学是有利于中国科学的发展,还是不利于中国科学的发展。五四运动为什么要 “打倒孔家店”,其原因之一是儒学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这个问题目前仍没有定论,仍处于争论之中。儒学要复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儒学与中国科学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在历史的不同时段,儒学对中国科学的作用是不同的,对不同的科学分支,儒学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我们的探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题目:儒学与中国古代科学、儒学与中国近代科学、儒学与中国现代科学。
一、儒学与中国古代科学
儒学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关系,既不能单纯用肯定也不能单纯用否定来概括之。事实上,有很多学者不是这样做的,也包括国外的学者。他们要么肯定儒学的作用,要么否定儒学的作用,他们为此还争得一塌糊涂。他们的观点包含一定的真理,但只是片面之真理。
儒学的经世致用,有大用,也有小用。关于大用,《大学》中曾明确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2这就是说,儒学的大用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靠讨伐和杀戮,而只能靠修身。修身得有规则,于是儒学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儒学道德体系后来被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在儒学看来,只要三纲五常做到了,便会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目标。
儒学重视大用,但他们对小用也不是漠不关心。这里的原因在于大用需要小用,大用离不开小用。科学就是小用。作为小用,科学对大用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每一个朝代为了表示自己属正统,都把颁布历法作为重要的任务。而历法与天文学紧密相关,于是天文学对大用就产生了积极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大用的一部分。其二,天下太平需要让人民有吃、有喝、有穿、有住。而吃、喝、穿、住的解决依赖科学。例如,种地就离不开历法、离不开天文学。除了天文学以外,还需要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这就使科学又进入大用的视野。其三,天下太平还需要有身体健康的人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防病、治病。这里防病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传染病的预防,有时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而防病、治病需要有相关的医学知识。其四,天下太平还有一个保护国家的问题。而要保护国家,就得有“利器”。要获得“利器”,就需要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其五,天下太平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怎样才能处理好天人关系。“天人合一”的畸形发展就是占星术。占星术在中国古代很流行,也很管用。因为皇帝在世人面前可以胡作非为,但他却怕“天”,怕“天”的惩罚。而占星术需要天文学,需要天文观察。这也使科学从小用转变成大用。
由于大用需要小用,小用与大用相联,这就使小用受到社会的关注,受到国家的重视。拿天文学来说,“大约公元前两千年,就有了天文台的设置。到秦始皇的时候,宫廷中‘候星云者至三百人,皆良士’。”[2]161“中国皇家天文台不但规模庞大, 而且持续时间之久, 也是举世无双。与此相对照,在欧洲,国立天文台17世纪末才出现。在伊斯兰世界,一个天文台的存在,没有超过30年的,它常常是随着一个统治者的去世而衰退。唯独中国,皇家天文台存在几千年,不因改朝换代而中断。”[2]162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天文台被纳入政府机构,天文台的工作人员属政府官员。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当时天文台属秘书省管辖,由四部分组成:编历:63人;天象观测:147人;守时(管理漏刻):90人;报时(典钟、典鼓):200人。主持天文台的太史官职为从五品,相当于今天的局级。
这样问题就比较清楚了:天文学尽管是小用,但它与大用紧密相联,因此它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具体地说,天文台被列入政府机构,天文台的工作者成为政府的专职人员,天文台的管理者属政府官员,天文台的修建由政府负责,天文台的经费由政府提供。这一切为天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平台,并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仅就古代而言,中国的天文学硕果累累,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例如,《竹书纪年》中载有夏桀十年(约公元前1580年)“夜中星陨如雨”,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流星雨的记载。[3]4《春秋》中记载了我国公元前722年至481年间的37次日食,其中32次据推算是可靠的,这是世界上最完整的上古时期的日食记录。[3]19《汉书·五行志》载:“河平元年(公元前2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是世界上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3]40
儒学对科学的积极作用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大批儒士加入科学研究的队伍。这当然是儒学的副产品。我们知道,儒学的目标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实现这些目标,特别是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就得读书。因为只有通过读书,才可能进入官场,才可能在官场担任重要职务。而这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否则“治国、平天下”就是一句空话。正是基于此,中国古代流行两句话:“门从积德大,唯有读书高”。这里的“读书高”,过去往往理解成读书可以做官,实际上儒家有更高的目标——“治国、平天下”,做官只是一种中介。当然,读书后来被“异化”了,其表现就是做官成了最后的目标,甚至是唯一的目标。
儒士要进入官场,就得考试。考试指的是科举考试。由于儒士甚多,而科举高中者甚少,这就使大多数儒士名落孙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转向。在转向中,有相当一部分儒士进入科学的领域,并开始从事科学研究。当然,他们的科学研究不可能是纯科学研究,而只能是应用科学研究。因为他们要维持生计、要养家糊口。这一点不同于古希腊。古希腊从事科学研究的是奴隶主,他们不愁吃、不愁穿,没有生计问题,因此他们的科学研究大多属纯科学研究。在纯科学研究中,他们的目标是求真,至于求用他们是不怎么关心的。这是古希腊科学的特色,正是这种特色,使中、西科学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当然,除了在科举考试中失败的儒士外,还有一些成功的儒士也进入科学领域。所谓成功的儒士,就是他们通过科举考试顺利地进入官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官场中也很顺利,即做到了很大的官。他们虽然为官、虽然以官为主要职业,但他们在业余时间也从事科学研究,并且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例如,宋代的苏颂,23岁中进士,此后他当过地方州县的长官,担任过中央政府中礼、吏、刑、工等部的官员,最后官至宰相。他编撰了《图经本草》,收录了前代本草著作中从未录过的103种草药,这些药物都是当时民间行之有效的单方验方,并成为此后主流本草著作的主要内容。[4]10他领导制造了水运仪象台和假天仪,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其次,就是文章的内容。乍一看,似乎也未尝不可;细思量,则让人生疑。比如,中秋节,他罗列一些从古到今的名人赏月轶事,到了春节,他又搜寻出古人如何过年的传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春、夏、秋、冬四季歌写毕,再接着写二十四节气,拉拉杂杂地写些个无关痛痒的陈词滥调。今年发表了,明年连改都不用,仍可发表。
但儒学对科学的消极作用也不能视而不见,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儒学的焦点在“治国、平天下”。要“治国、平天下”,就得当官,于是官就成了儒学的追求。这后来发展成为官本位思想。这种思想以官的大小来衡量人的价值,甚至衡量物的价值。这不仅把大批人才吸引到官场,而且还造成了官场的腐败。至于科学,这不在儒学的焦点之内,从事科学活动的儒士,要么是迫不得已,要么是兼职,这就严重影响了科学的发展。二是儒学看不起工匠,他们耻于与工匠结合。这与儒学“君子不器”的观点有关。这里的“器”实际上就是技术。而科学离不开技术,没有技术的支撑,科学就不能很好地发展。这一点已被西方的近代科学所印证。西方之所以有近代科学、有近代科学的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三是儒学太讲实用,而科学主要是一种求真的事业。在这一点上,古希腊人有他们的独到贡献。古希腊人把求真当做科学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他们发展出古希腊科学。古希腊科学在古代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在理论化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超越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达到它的水平。中国则不同。由于儒学太讲实用,中国科学的理论化程度较低,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像欧几里得几何那样的理论体系。结果是,中国的科学只能低水平徘徊,只能随着“实用”亦步亦趋。这样的科学没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这样的科学只能依赖“一条腿”走路,这样的科学最后肯定要落后。这里的“最后”是指近代。到了近代,西方科学突然加力,并迅速发展起来。中国科学则缓缓而行,没有大的起色,更没有大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学的落后是必然的,而且落后的程度越来越大。
二、儒学与中国近代科学
如果说中国古代科学还与西方科学有一拼,到了近代,中国科学却远远落后了。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所谓近代科学,是西方的独特产物。近代科学是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开始的。在此之后,伽利略创立了地上力学,开普勒创立了天上力学。牛顿把天上力学和地上力学统一起来,建立了经典力学体系。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是近代科学最重要的成就,也是近代科学区别于古代科学的最重要的标志。
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因此中国科学只有古代形态,而没有近代形态。我们现在说中国科学落后,主要指它没有实现从古代到近代的跨越。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肯定与儒学有关。这样,儒学对“中国没有近代科学”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儒学的一个“死穴”,是评判儒学与科学关系时无法绕过的一道“坎”,正是这道“坎”,后来把儒学推到了“风口浪尖”。
但在中国和西方未猛烈碰撞之前,儒学与近代科学的关系还被遮蔽着、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就不同了,因为西方列强不断侵略中国,中国则在反抗侵略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战败的结果,不仅要赔款,还要割地,当然还有一些相应权益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志士仁人在反思,在反思中国御敌的良策。在这个方面,魏源最早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思想。李鸿章则指出:“查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 方足夺其所恃。”[5]108“师彼之长,去我之短, 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5]109冯桂芬也指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5]109
魏源等人的思想,概括地讲就是要学习西方的技术,特别是西方的物化技术。正是这种物化技术,才使西方强于中国,才使中国被动挨打。魏源等认为,通过学习西方人的技术,就可以改变中国技不如人的状况,就可以使中国战胜外国的侵略,就可以使中国再次复兴。但这个目的并没有实现,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一是中国腐朽的封建制度,中国腐败的统治集团。这阻挠了对西方技术的引进和学习。二是技术只是表层的东西,技术的基础在科学。因此要学习西方的技术,就得首先学习西方的科学。后一点已被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了。例如,严复就提出要学习西方的科学与科学方法。
上述两个问题,都与儒学有关。因为在儒学的基础上,既没有发展出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就产生了对儒学怎么看的问题。具体地说,是肯定还是否定。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与此同时,又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这实际上是对儒学的否定。“德先生”是民主,“赛先生”则是科学。民主和科学,正是儒学所缺乏的,这是“打倒孔家店”的原因,这是否定儒学的原因。这种否定当然有片面性,但却切中了儒学的弊端,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心声。这种心声集中到一点就是:救亡图存,复兴中华。
在以后的岁月中,对儒学的评价反反复复。在这种评价中,儒学与科学的关系至今仍观点林立、争议不断。这里关键是近代科学。如果说在古代,儒学对科学的积极作用还有迹可寻,有时“迹”还表现得很大、很明显;但就近代科学而言,儒学则没有扮演任何直接“角色”,儒学基本是“局外人”,儒学也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近代科学是在西方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是西方的一种独有现象。
当然,近代科学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例如,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古希腊文化的复兴、阿拉伯科学的涌入、中国三大发明的吸纳,等等。可以这样说,西方的近代处于“漩涡”之中,各个方面的因素激烈碰撞,不断综合融合,最后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也包括中国因素的作用。但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因素,特别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除了古希腊文化外,还有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实际上是这两种文化的结合。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结出了近代科学之果,并且这个“果子”越长越大。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儒学在科学上的最大问题是:在它的基础上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因为近代科学还被应用到技术层面,并极大地推动了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又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使西方迎来了繁荣和富强。与西方相比,中国则远远落后了。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落后了,最重要的是在经济质量上也落后了。西方又把经济上的优势转化为军事上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侵略中国,中国只能被动挨打,中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三、儒学与中国现代科学
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但中国要自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又是不可能的。这就迫使中国人去学习西方的科学。最初的学习,基督教的传教士是中介。例如,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西方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李善兰则与伟烈亚力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后九卷。当然,由于传教士不是专业的科学家,因此他们带到中国的科学不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
学习西方科学的另一个途径就是留学。在西方国家留学,可以接触到最先进的科学,特别是可以接触到处于科学研究前沿的科学家。后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可以使留学生知道什么是科学研究、怎么搞科学研究。有些留学生还直接进入科学研究过程,并获得了一定的、甚至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正是依靠这些留学生,依靠这些留学生在中国国内的“传、帮、带”,才使西方的科学传到中国,才使西方的科学在中国扎根。
西方的科学,从古代、近代、直到现代,有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科学,是一股脑儿学,即古代、近代、现代的科学通通学。当然,中国人更多的是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因为西方科学已前进到现代阶段。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才能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才能在科学上有所作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的近代科学也现代化了。例如,牛顿力学应该属近代科学。但牛顿力学产生后,很多科学家围绕牛顿力学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这使它更加全面、更加精确,这使它应用的领域更加广泛、更加普及。因此,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科学,更多是从现代开始的、即从现代科学开始。这就有一个儒学与中国现代科学的关系问题。
现代科学是中国人从西方学来的,因此现代科学属“舶来品”,而且现代科学基本上取代了中国古代科学。这里的“基本”,是说还保留了中国古代的一门科学,这门科学就是中医。其他中国古代科学则已不复存在。然而就是中医这门科学,也受到质疑。因为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医不是科学。中医到底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讨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医不符合西方的科学规范,按西方人的观点,中医不是科学,至少不是严格的科学。
这就是说,中国现代科学是西化的结果,而且除了中医以外是全盘西化。但儒学却不能西化,至少是不能全盘西化。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西化的科学与儒学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核心在于:科学的精髓在求真,儒学的精髓则在求用。求真和求用有时是一致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却存在矛盾。以求用为标准,会遏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不利于科学的相对独立的发展。
儒学还有一个问题是它的官本位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而且还影响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中国人是学而优则仕。这也包括科研人员。本来,科研人员应该终身从事他们的职业,他们应该以他们的科研活动为荣,他们应该把科研成果的获得作为他们的价值追求。然而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有点科研成果,就想着去当官,就以此为资本去争官。如果当官与他们的科研活动有关,那还问题不大。因为他们还没有离开科研活动,他们的科研活动还可以继续进行。但目前存在最大问题是:大量的科研人员被推到官的位置,而且他们所当之官与他们的科研活动毫无关系。这样他们就不再从事科研活动,他们也没有时间从事科研活动。这就使一个又一个科研人才夭折,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科研领军人才。这造成了科研人才的巨大浪费,并严重影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问题是: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根本不适合当官。他们抛弃自己的科研活动而进入官场,他们陷入日常事务而不能自拔,他们处理不了人际关系,他们面对各种挑战束手无策,他们心力衰竭、疲于奔命。这导致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这既是他们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
在中国科学界还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某某某留在国外继续搞科学研究,他所获得的科学成就可能还会更大。这里除了科学研究的连续性外,剩下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儒学、中国的科研体制,不利于科学研究的进行。中国的科研体制在不断变化,这是向西方学习和自我创新的结果。中国儒学的核心层面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某些方面则更加负向了。例如,官本位的思想,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科研领域也不例外。这样,中国儒学原本与现代科学就不相适应,再加上它的畸变,就更不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了。
这表明,儒学与中国现代科学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从现代科学引进之初就存在,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如果对这种矛盾做一个概括的描述,那就是:现代科学产生、发展于西方,其载体是西方文化。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不同的精髓、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气质。因此儒学不能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至少是部分不能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这个原因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使中国现代科学仍然落后于西方国家。例如,就诺贝尔科学奖来说,基本上被西方科学家垄断了。21世纪以来,日本在这个方面有较大的斩获,它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数量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则只有1人,这就是屠呦呦。当然,外籍华人中有一些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譬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崔琦等。但这反倒暴露了一个问题:西方文化更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
四、结语
这就是儒学与中国科学之关系。这种关系概括地讲就是:儒学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在儒学的基础上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儒学与中国现代科学存在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
怎样解决儒学与中国科学的矛盾,显然不能采用五四运动的方法。事实上,五四运动的目的并没有实现。因为儒学是中国人的根、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要否定它是不可能的。即使官方否定,知识界否定,它仍然在人民间“游荡”,它仍然作为道德规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这就有一个如何协调儒学与中国科学关系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一是把儒学与科学分割开来。这是一种划界的方法,即儒学管价值问题、管伦理道德,科学则致力于对客观世界规律的探索。划界不可能是绝对的,但通过划界,可以减少儒学与科学的矛盾。二是在儒学中增大求真的成分。儒学的特点是求用。当然儒学中也有求真的成分,但求真的成分较少。这就需要扩大求真的成分。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中国科学的发展。三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称之为“科学的文化”。其特点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并始终坚持这个目标。四是对在儒学基础上衍生出的“官本位”思想,不仅要坚决批判,而且要设立相应的制度消除它。这是一颗毒瘤,这个毒瘤已严重影响到中国科学的发展。
求真和求用是一对矛盾,西方文化中也存在这样的矛盾。具体地说,在西方文化中,古希腊文化代表求真的一方,基督教文化代表求用的一方。这两方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最后则融而为一,实现了协调、平衡。正是这种协调、平衡,推动了西方科学的发展。中国要学习西方,要努力实现求真与求用的协调、平衡。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增大求真的成分。因为求真的成分太少了。不仅如此,求真还被求用遮蔽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增大求真的成分,必须培植求真的精神。
[1] 李志敏.四书五经[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9.
[2] 席泽宗.科学史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 潘永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事记[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7.
[4] 汪前进.中国古代100位科学家故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5] 武吉庆.中国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