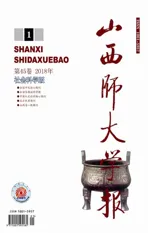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宗教信仰与教徒改造
——以山西平遥路候村、双口村为考察中心
2018-04-03马维强
马 维 强
(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太原 030006)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在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也着力肃清国外势力在资金、组织及思想意识上对中国宗教的影响。基督新教内的控诉运动、革新运动是国家针对宗教界上层精英分子“宗教是超政治”观念的回应与治理。经过这些运动,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揭开的近代传教运动时代至此终结。[1]天主教的革新运动、反帝爱国运动和肃反运动及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的成立使天主教会基本完成自身身份的转变及重构,走上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2]外来宗教的本土化改造在积极有力地向前推进。随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国际领域意识形态的紧张对立,以及一些神职人员的激烈言论和传教活动的活跃,国家对乡村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转变为约束限制,宗教信仰成为有悖于国家意志的思想意识和活动,削弱其在乡村的传播和影响成为乡村宗教工作的重要内容,许多教徒的言行被一一加以审视,如何入教,入教之后有哪些活动,是否进行了传教,是否宣讲了基督、天主教教义和发表了相关言论,等等,都需要进行“交代”。
学界关于新中国之后的宗教研究在时段上主要集中于对1950年代的讨论,对集体化时代的专项研究目前还付诸阙如。这些成果以论文居多,专著较少,尤其是关于国家与乡村教徒及宗教信仰互动关系的探讨更为少见。①本文以村庄档案为资料基础,结合对村民的口述访谈,从乡土社会和普通教徒的微观视角出发,以区域性的实证性研究来探讨教徒身份对村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及他们的经历体验和思想变化,并透过教徒的信仰揭示和反思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改造。
路候村天主教于1801年左右由田姓传入,晚清四代时建起天主堂及钟楼。四代田文都神父编纂很多教理、教义、译述著作,如《炼狱圣月》《古迹家训》等,在全国各教区都有流散,声名远播罗马教廷。20世纪30年代,田家生意衰落,教徒也逐渐减少,相关宗教活动渐少。新中国之后,田家七代田恒群成为路候村天主教爱国会代表。除了田姓外,路候村的天主教徒还有范姓。范云贵一家于1906年从祁县教徒村——九汲村迁来,三代范柏慈先后在汾阳、孝义等地当神父。路候村天主教徒在1920年左右人数最多,达到130人上下。1964年, 16岁以上的天主教徒29人,基督教徒11名,共23户40人,占到总户数612户的3.8%,总人数的1.8%。“四清”运动开始后,路候村的天主堂于1966年被生产大队占用。*参见《路候工作队关于宗教工作简结汇报》、《道备宗教讨论会情况和发言记录》,1966年8月28日,路候村庄档案, 编号DBC10-4-1、 DBC-11-3-1,藏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以下同。与路候村相邻的双口村没有修建教堂,在1966年时16岁以上的教徒包括天主教徒1户4人,耶稣教徒6户13人,共17人,占双口村总户数516户的0.013%。除王彪1户是由路候田姓受洗的家传天主教外,其他人在1945—1953年由本村王光宗、柳中桓及其妻介绍入耶稣教。*《天主基督教档案》,1966年,双口村庄档案,编号XYJ-9-1-1、XYJ-9-1-2;《参加耶稣教人员的名单及其情况》,双口村庄档案,编号XYJ-5-14-2;《生产大队宗教人员登记花名》,1965年12月31日,双口村庄档案,编号XYJ-7-15-2,藏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这两个村庄的宗教徒在村庄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可成为集体化时代国家治理非教徒村庄的教徒及宗教信仰的一种类型。
一、宗教信仰:身份政治的一个负相关*这里的负相关主要指村民因教徒身份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负面影响,如在参军、上学、加入党团、参加村庄公共管理活动等方面受限。
在集体化时代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民的宗教信仰及其活动受到较多约束。在对乡村宗教传播和教徒的改造工作中,国家主要从组织、活动、言论上限制宗教信仰,并组织教徒对其展开思想斗争。这使宗教徒不仅在信仰上,而且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受到诸多压抑,宗教信仰因而成为影响信徒日常生活及其是敌是友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路候村、双口村的天主教徒以家庭世传为多,从出生即跟随父母自然信教,同时教徒一般多在教内结婚,在乡村人际交往中占重要地位的血亲、姻亲关系对于天主教徒而言就多限制于教徒圈内,如路候村田姓、范姓教徒都是如此。双口村王彪家从祖先信仰天主教后,通过配婚,大部分亲属也都是天主教徒,其姑母家、岳母家、妻舅家、妹夫各家也都是天主教徒。*《回村四类分子王彪个人档案——专政对象登记表》,1966年7月9日,双口村庄档案,编号XYJ-4-8-6。与天主教徒相比,基督教徒几乎没有家传入教,而多由亲戚朋友介绍成为基督徒。
无论宗教徒因何种动机入教,他们在集体化时代的言论和行为都受到了较多约束限制。一般而言,教徒不被允许加入党团组织,参军、上学也要受到限制。*在路候和双口村中,只有一个路候信天主教的女孩——亮子的女儿入了团。参见访谈资料记录,访谈对象:樊林刚,男,74岁,平遥县路候村人。访谈时间:2010年7月24日。访谈人:马维强、李保燕。双口村耶稣徒柳尚明曾于1961年至1966担任大队统计,参见双口村庄档案,编号XYJ-9-5-8。田秉惠虽然符合国家对于征兵的年龄要求,但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而被拒之门外。*《天主教徒小组讨论发言摘录——田秉惠发言》,时间不详,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3-2。宗教徒日常的做弥撒(做礼拜)、念经、领圣体、会餐、帮助神父(传教士)开展相关仪式活动、传播显圣的言论、劝人入教等一切与宗教相关的活动都不被允许,都需要参加讨论会进行自我交代和相互揭发。至于神父(传教士)的言行和社会交往更是被关注和限制的重点。
神父范柏慈就被揭发在1962年组织白桦、杜松庄共150—160个教徒过圣诞瞻礼节误工一上午;在1965年秋忙时,其弟媳劳动回来后生火拉风箱做饭,范不让做饭而是让念经。*《天主教徒小组讨论发言摘录——田恒群、范春波发言》,时间不详,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3-2。这些因与国家强调集体利益、农业劳动生产至上相悖而受到揭发。不仅如此,范还做弥散“剥削”教徒,支持“三天三夜天黑”谣言,给教徒“圣火”“圣蜡”,违反政府政策给未成年儿童“领洗”。范因此而被集中到榆次参加神职人员集训班,并在1966年10月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有关范柏慈的个人材料》,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6。范柏慈,路候村人,解放前主要在汾阳、孝义担任本堂,1953年后在汾阳眼科诊疗所工作,1955年被逮捕,1956年底被释放后在眼科诊疗所和医院工作,1963年后因患高血压回村养病,未再返回汾阳。参见《范柏慈交代罪恶材料》,1967年1月13日,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6-1;《范柏慈个人履历》,时间不详,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6-6。其他教徒也因参与了相关的宗教活动而受到“斗争”。田大勇曾因在汾阳辅助神父在后贺家庄、杨家庄、田家庄组织“公教进行会”被大队干部关了七个晚上。*访谈对象:韩清媛,女,81岁,平遥县路候村人。访谈时间:2013年8月16日。访谈人:马维强、(日)佐藤淳平。戴帽子的宗教徒受到严格的监控和管制,斗争激烈时他们甚至被拉到大队戏台上公开批斗。他们每天早晨四五点就起来低着头打扫街道,一直干到七八点,行动被严格管制,外出活动必须请假。*访谈对象:田美凤,女,50岁,平遥县路候村人。访谈时间:2013年8月16日。访谈人:马维强、(日)佐藤淳平。
在路候和双口村戴上帽子、成为“阶级敌人”的宗教徒中,只有田文刚是由于参与圣母军及天主教“闹事”活动而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其余教徒或者是地主、富农成分,或者是由于参加伪政权、有历史血债如出卖八路军干部和相关人员,或者发表了违背国家意志的言论而戴上历史反革命、右派、坏分子帽子,成为被管制的对象。尽管宗教思想、言论和相关活动不是宗教徒成为国家“专政对象”的唯一原因,但仍然是他们被划定为黑色政治身份的重要因素。
朱育方于1945年加入耶稣教,是双口村的传教士,曾因在村中当了3个月伪特派员而在1954年被划为“历史反革命”,戴帽管制三年。他于1962年冬至1964年春先后在屯留、沁源、侯马教徒家中做礼拜,祁县、徐沟、汾阳、孝义、临汾、太原的教主都去过他家。朱育方还在平遥的乡镇传教,并宣扬“教会受压迫,教徒应为教会舍命背十字架”“教徒不要爱世界,而抛开世界爱主”等言论。朱的言论和行为被评定为含沙射影对党进行攻击,企图煽动教徒反对党的领导,不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在1966年重新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回村四类分子朱育方个人档案》,双口村庄档案,编号XYJ-4-7-1至4-7-3。双口的耿学岸同样宣扬类似的“反动”言论,并在斗争会上公开说共产党是替天行道,又说土地改革是圣经上有的,因而在1966年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双口大队四清委员会关于给耿学岸戴坏分子帽子的处理决定》,1966年7月10日,双口村庄档案,编号XYJ-3-23-1。
教徒的信仰及其宗教生活由于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对立而受到约束打击,尽管这种自我经历体验和社会实践活动“既不是意识形态式的宣言,也不是那些教义的实践,而是他们的政治行为本身。不是党派式的意识形态政治,而是着落在每一个个体的体验和性情中的,由每个人最本己的伦理生活和生存处境生发的,一种政治生活”[3]229。但显然,这样的“政治生活”在意识形态紧张对立的时期已经超越了“国家政治”,是对国家政权的威胁。由此,与其说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加强了对基层的治理,莫不如说国家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加强了对个人、对民众“身体”的改造,使“个体人”向“国家人”转变。
二、爱国与信教:国家的信仰改造
“普世性是需要通过地域性来体现的”[3]2,“如果基督教信仰所传播的是一种普适性的教义或精神,那它必定能够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或中国化”[3]3。这种地域性、本土化除了需要与地域风俗、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有机相融外,更首要的应该体现为爱国,认同党的领导,积极维护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信教与爱国并不矛盾,两者可以融合共存。但在意识形态斗争紧张和警惕西方文化侵略的前提下,信教对党和国家的权威、革命道德及社会秩序和国家管理构成了威胁。
1964年冬“四清”运动开始后宗教徒的公开活动更加受到约束。[4]885—8861965年太原天主教事件在教徒内部产生较大影响,引发教徒的情绪波动,社会秩序产生动荡,平遥县统战部召开教徒代表会,召集各村宗教代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学习及登记教堂财产,并在榆次召集汾阳教区和榆次教区的神职人员进行集训。*《范柏慈交代罪恶材料》,1967年1月13日,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6-1;《揭发田恒群的信》,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6-3;《范柏慈自我交代》,1972年12月15日,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6-12。路候、双口村召开普通教徒及不信教群众的宗教讨论会,揭批宗教信仰及神职人员的活动。
在公共空间话语的表述中,宗教教义的唯心主义违背了唯物主义观点。至于宗教对世俗生活的干预,如宣扬“偷粮食要偷集体的才没罪,偷个人的有罪”的观点与国家强调集体利益至上的观念相冲突。*《路候工作组揭批天主教问题有代表性的发言记录——田恒群补充交代》, 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3-2。神职人员发展教徒即是争夺青年下一代,腐蚀未来的国家基石。通过阶级话语的表述,国家对宗教信仰在村庄的“政治”地位和性质予以评定,约束规范着宗教徒的思想及活动。
村庄的宗教信仰改造工作主要由驻村工作队领导大队干部安排实施。路候村与双口村的实践活动大致相同(以下论述以路候为主)。路候工作队根据上级工作团的指示,确立了“打头、挖根、清底”的六字方针,从政治定性、组织管理、思想削弱和信仰冲淡四个方面展开对宗教信仰的改造。在组织上也加大了力度,以工作队队长抓宗教为主指挥全面工作,其余四名工作队员分别深入到教徒集中的二、三队,边工作边劳动,边发动群众揭发问题。大队党支部除全面抓宗教斗争外,七个支委中确定了副书记和治保专门负责。*《路候工作队关于宗教工作简结汇报》,1966年8月28日,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4-1。
加强组织、提高工作队员的思想认识、明确工作内容和目标后,更重要的是对教徒的组织动员。工作队一方面组织信教与不信教群众进行关于“四清”的政策、性质等的学习,并着重给信徒讲解党对宗教的政策和太原等地发生的天主教事件情况;另一方面组织教徒进行“大讲天主教历史‘反动’本质,大揭天主教‘罪恶’盖子,大忆天主教在路候150余年的‘罪恶’事实,大诉天主教给教徒造成的‘苦难’”的“四大”活动,并在此基础上组织教徒进行自我揭发。工作队还根据上级指示开办了教徒训练班, 从1966年7月24日晚开始,大约持续进行了10天,每晚两个或两个半小时。16岁以上的40个教徒中除外出、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及范柏慈等6人未参加外,其余的人都分别参加了集训。*《路候工作队关于宗教工作简结汇报》,1966年8月28日,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4-1。
在这种学习和讨论中,教徒对于国家的宗教改造政策逐渐具有了清晰的认识,并明了改造工作的关键是使信教群众阶级归队,将斗争矛头对准教内“头头”,从而团结多数,孤立少数。路候还专门针对国民党书记长(教徒)田树林、传教士范椿祥、会长田恒群等五人展开了斗争。*《路候工作队关于宗教工作简结汇报》,1966年8月28日,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4-1。据村民回忆,工作队对天主教和戴帽分子相对比较宽容,目的是动员群众划清界限,从内部瓦解组织者,树立典型,影响他人,使他们认识到只要相信党,揭发罪行,自己是有机会的。*访谈对象:樊林刚,男,74岁,平遥县路候村人。访谈时间:2010年7月24日。访谈人:马维强、李保燕。村民认为路候村对宗教徒的斗争基本没有血债,相对平和。*访谈对象:刘云福,男,78岁,平遥县路候村人。访谈时间:2009年12月21日。访谈人:马维强、李保燕。
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器具既是开展相关活动的工具,也被认为是宗教信仰的象征符号。工作队将天主教堂收归大队挪作他用,动员教徒上交或者没收圣书、圣像、搧布、念珠、祭衣、十字架等用品,并以毛主席像作为替代物,在教徒家中、院中、墙上分别写上毛主席语录,组织教徒学习《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实践论》等内容。教徒还被陆续不断地送往县城参加榆次教区神职人员的自我批判,参加祁县、平遥、汾阳等地的斗争大会,参观县天主教历史展览、去往太原实地参观。地委宗教宣传队在路候做宣传活动,演出电影《地下航线》和《阿娜尔汉》,同时有两位神父宣讲自身的切身经历、活动和思想。*《路候工作队关于宗教工作简结汇报》,1966年8月28日,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4-1;《路候大队关于宗教工作进展情况》,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5-4。
除了对宗教徒的动员外,普通民众也被组织起来进行学习讨论。工作队召开了针对全体社员的动员大会以及党、团员、贫协会、队贫协小组及知情、知事人的大、中、小型座谈会议,同时还深入群众进行个别访问。教外群众利用地头、饭场进行相关讨论。*《路候宗教讨论会情况和发言记录》,1966年8月28日,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3-1。总之,无论是教徒还是非教徒,都需要针对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义和活动展开讨论,深化认识。
国家通过公共空间中的阶级话语塑造及对教徒信仰的治理改造,在村落地域空间里形成了约束限制宗教信仰的紧张氛围。从村庄结构和权力关系来看,宗教观念及由宗教信仰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在路候、双口村不足以主导乡村生活,但无论上帝是否在世俗旁边绕行,世俗是要将上帝置于对立面而予以否认的。[1]304国家对宗教信仰的约束限制根源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对立促成的“革命”而非“改良”的思维逻辑,也根源于思想观念领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三、守与变:乡村教徒的因应
在集体化时代后期,宗教信仰及活动受到更加严厉的限制。国家希望将宗教徒对天主、耶稣的精神崇拜置换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认知与接受,对党、国家和集体的忠诚与支持。对于教徒而言,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观念置换必然需要经过一番煎熬与斗争,而与此相应的实践活动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转变。
尽管自“四清”运动开始后宗教徒的活动已被要求停止,但晋中地区1966年近三个月的集中调查显示,活跃在本区的基督教组织形式多样、活动小型频繁。*《中共晋中地委宗教工作领导组关于全区基督教基本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1966年6月17日。这里的基督教主要指基督新教。天主教徒的活动也同样存在。教徒们将相关的仪式活动由公开转入秘密,由集中转向分散,其中不乏在家设经堂、聚众念经者,也有将神父偷偷请到家中做弥散,他们在内心里依然坚守自己原有的信仰。双口天主教徒就认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被一直灌输唯心论的迷信观点,虽然唯物论观点教育了自己,使自己不再是反革命天主教的忠实信徒,但自己仍然是个半信半疑的天主教徒。*《王彪对于自身天主教信仰的检查》,1966年3月27日,双口村庄档案,编号XYJ-4-8-9。范柏昌1952—1953年被捕,释放后到教堂少了一些,认为自己(与宗教信仰)逐渐脱离了关系,但思想上总半信半疑的。*《杜松庄路候大队宗教讨论记录——范柏昌发言》,1966年3月3日,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1-1。宗教徒不放弃信仰,一方面源于对圣母、耶稣信仰的心理认同,另一方面源于对不信仰天主、得罪了天主将会受到惩罚下地狱的担忧。
放弃信仰就是罪恶的言论在宗教徒中不断弥漫,各地天主“降罪”和“显圣”谣言的盛传更加深了宗教徒的恐惧心理,使一些原本就不坚定的退教者更加游移不定。1964年到处都有“4月15日天主要降罪,15—17日天黑三天”的谣言。韩清媛的教徒外甥告诉韩,神圣瞻礼日前后要黑暗,需要点洋蜡,且给了圣才能点着,如不圣洋火就点不着洋蜡,还说他们那里已经连洋蜡都买不到。韩清媛将此消息告诉韩美君,两人买了洋蜡、洋火,并让范柏慈给圣。*《天主教徒小组讨论发言摘录——韩清媛发言》,时间不详,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3-2。“天黑三天”的谣言也传到王彪家。王彪在检讨书中写道:“1964年4月12日,我妹夫韩金川来到我家,对我说清源六合村天主教显圣迹,4月15号、16号、17号左右要天黑三天,还说我是半信半疑的人,如不回头天主就要罚罪我,我家里大的病,小的病,病下一家家,说我现在应该回头了,要热心求天主,不然的话到那时要受到天主的惩罚,比不信的人罪还大。我当时仍有唯心观点,在困难中被迷信思想战胜了,我便说这该怎好?韩金川说给你四支蜡烛两盒火柴,叫你到那时祈求(用)。语出亲人之口,他也是为我好,使我不信中又信,疑惑不定。……当时我也是想做实验,如真有天(主)从今以后我就信,要是假的从后就不信啦。”*《王彪对于自身天主教信仰的检查》,1966年3月27日,双口村庄档案,编号XYJ-4-8-9。
一方面,谣言的不断传播使退教的教徒感到恐慌,怕受惩罚下地狱,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转变信仰,揭批神职人员和教徒的活动。在社会舆论和传播媒介话语的表述中,在神父等教职人员现身说法、自我反省批判的示例下及现场观摩斗争会的体验中,许多教徒或主动、或被迫放弃宗教信仰,转而运用“革命”话语揭批宗教活动,检讨自身“错误”,揭发周围的宗教徒。神父、传教士、教会会长作为宗教的“头”与“根”成为被揭批的主要对象。
许多教徒扭转以往“宗教信仰只是简单的信仰问题”的认识,在讨论会、座谈会上表达自己对天主教本质的看法,并且在公共空间舆论中逐渐形成了对神父和天主教的系统批判话语。以往信仰甚深的教徒也开始发生转变,韩清媛就是一例典型。工作组刚开始讲解天主教的教义和神父的腐化活动时,韩清媛依然对天主笃信不已,认为那是神父不守教规,为非作歹,天主教不能饶恕他们。自己只是念经、听天主的话,又不跟着他们做反动事情,谁犯罪谁受惩罚。让她揭发问题时,她或者说我们不识字,妇女家哪能知道别人的事情,谁也不肯说他们干些什么;或者干脆说管他谁怎样,反正自己不办坏事,谁说啥做啥可不知道。清媛这样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被工作队认为是受天主教毒害甚深的表现。但当她到平遥县城听了榆次神职人员的自我检查和参加了平遥神职人员的斗争会后,思想陡然发生了变化,一改以往沉默不语的消极抵触,大胆揭发自己阻止儿子参加党团的事实及神父和其他天主教徒的相关言论及活动。*《路候工作队关于宗教工作简结汇报》,1966年8月28日,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4-1。
除了在公共空间和检讨书中的揭批检讨外,许多教徒从行动上与宗教信仰决裂,交出进行宗教活动的工具,在个人日常生活空间中用“红色”象征符号取代了宗教信仰的象征物。刘如玲主动将圣像扯坏烧掉,范春波主动召开教徒会,田秉光的女人甩了圣像,惊得邻居家听见像响雷一样的声音。前述态度发生巨大转变的韩清媛主动把十字架取下,扯了圣像,挂上毛主席像。*《工作组总结》,1966年4月1日,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1-6;《宗教座谈会——韩美君发言》,1966年3月5日,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1-3。经过一番“斗争”后,路候村有23个教徒已经放弃了信仰,其他半信的有9人,一般的有3人,还有5人仍然虔诚。*《路候工作队关于宗教工作简结汇报》,1966年8月28日,路候村庄档案,编号DBC-11-4-1。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教徒的思想转变过程和内心的激烈冲突。在集体化时代,国家以社会主义理念和各种手段塑造乡村公共空间,并深入到私人空间中,国家对宗教信仰的治理显然对信徒个人的内心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有的人因此彻底放弃了宗教信仰,转而向国家意志靠拢,有的却不然。许多宗教徒虽然写了退教书,也揭发了一些相关的宗教活动及自我反省批判,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真正放弃了宗教信仰,认同国家对于宗教信仰及其活动的政治定性与价值评判?抑或他们向国家表示放弃信仰乃是争取生存空间的策略选择?
四、结语
在集体化时代,革命日常化和生活政治化的特点突出。如果说50年代国家对宗教信仰的改造集中在宗教组织、制度、运作机制及精英分子层面,六七十年则已经将治理的重点扩展到乡村基层普通教徒的日常宗教生活及思想观念中。在“政治挂帅”的意识形态和语境下,国家将“宗教”和“爱国”都纳入政治的范畴之内,两者成为非此即彼的对立面。国家希望能消解宗教信仰在乡村的影响,完全占领教徒的精神世界,而事实上,“信教”与“爱国”的结合是个人宗教信仰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一个平衡点,精神认同与政治认同可以融合并存,宗教徒“天主的好儿女”与“国家的好公民”的身份可以合二为一。
尽管“爱国”的含义和内容被政治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坚持宗教信仰就可以不爱国,信仰自由应该被置放在制度的范畴内。不过,扎根于民间的信仰文化尤其是埋藏在心底的、头脑中想象的“看不见”的宗教信仰并不容易被唯物主义的思想观念所替代,对于精神世界的改造显然无法依靠群众运动式的治理来实现。一方面,“运动”方式的过激往往使事实无法得到全面呈现,其“正向”的方面几乎被完全忽略,容易对被揭批对象造成伤害和压抑紧张,也无法引导其发挥“正能量”;另一方面也使治理的重点发生偏差,更多关注具体事象,而无法集中在对宗教内部制度及运作体系的本土改造上。
在路候、双口这样的非教徒村庄中,当宗教徒在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中面临国家意识形态的约束,原本微弱的宗教关系更加遭到削弱和淡化,仪式的取消弱化了教友们的集体认同,以致人们放弃宗教信仰而形成了断裂。这种断裂不仅是思想信仰上的断裂,更在深层次上造成了宗教教育和实践的边缘化和个人化。[5]241在充分认识到多元文化的并存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建构的意义的前提下,如何才能使宗教信仰走出自闭保守,在个人和组织层面上实现私人领域与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和谐统一是关键问题。
[1] 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运动与基督教史论[M].香港:道风书社,2012.
[2] 陈铃,陶飞亚.从历史视角看梵二会议与中国天主教会[J].世界宗教研究,2012,(6).
[3] 吴飞.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与生活[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
[4] 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平遥县志[B].北京:中华书局,1999.
[5] (英)王斯福.帝国的隐喻[M].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