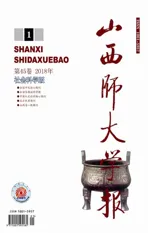十九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探析
——基于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的诠释维度
2018-04-03田宝祥
田 宝 祥
(首都师范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48)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至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被正式提出。就思想的内涵而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一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进理论成果,而就思想的渊源来看,其理念可追溯至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在价值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其坚实的思想文化依据。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需要以生态哲学的眼光来综合认识和把握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的发展,为此,不仅需要实践创新,还需要理论更新,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切先进理论成果,还需要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与儒、道智慧。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如何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有效的理论互动,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的基本内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新理念主要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和谐,二是可持续发展。从本质上讲,生态问题的中心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从人类文化、伦理价值的角度出发,反思并应对工业时代以来人类由于大肆追求资本积累而导致的环境污染、能源破坏、资源匮乏等自然危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工业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是自然世界的破坏和人的异化。海德格尔则进一步指出,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有二:一是科学技术的扩张,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蔓延。因此,在考虑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时,绝不能一味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是要双向考虑、综合判断。也就是说,在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保障动、植物等其他生命体以及整个自然界不受额外之伤害,而只有当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和宇宙获得了某种动态的平衡,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才有可能,这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的价值初衷。
此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对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而言,其意义是深远而非凡的。习近平早在2013年考察海南时就曾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之后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又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政治问题。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习近平更提出“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着力解决雾霾等一系列问题,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包括物质文化生活方面更高要求,而且也包括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方面的更高要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还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可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主要在于解决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在于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儒家的生态哲学:“天人合一”与“生生不息”
当前所讨论的生态问题,还原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语境之下,即天人关系问题。天人关系在儒家的哲学体系当中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生生不息”的认识论。
儒家所论之“天人合一”,并没有多少神秘主义的色彩,而是一个内涵丰富、层次分明的观念系统,确切地说,其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在结构上是有序的。从哲学上讲,人既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反过来,包括动物、植物乃至整个生命世界、自然世界即构成人的认识对象和实践对象,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天、地、人三者是天然统一、不可分割的;于农事生产的层面讲,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乃“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1]41之结果;于生命绵延的层面讲,生、老、病、死乃“与天地合其德”“与鬼神合其吉凶”[1]41之结果;于道德修养的层面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33,“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44,理想人格的形成,即同时秉有“天格”之自强不息与“地格”之厚德载物的品质。宋儒后来讲“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和”[2]132,与原始儒家一贯的“天人合一”观念已大为不同,之所以如此说,主要还是受到道家“天人一体”思想的影响。原始儒家言“合一”而不言“一体”,乃是基于人的道德主体性之立场。思、孟认为,“合一”是一个可追求、可实现的结果,而这一结果的获得往往需要一个发展与努力的过程,这便是人的道德实践以及孟子所强调的“大丈夫”之道德承担,若是一味讲“一体”,那过程的意义必然会被消解。由此可见,在儒家的视阈里,“和”与“合一”既是实然,又是“应然”,其事实中本就包含着价值,无论是出于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都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儒家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一以贯之的观念有二,即“仁”与“和”,此二观念不仅作用于日用伦常层面,也作用于生态价值层面。孟子讲“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3]948,乃是说儒家的“仁爱”本质上是一种由“亲亲”到“民”、再到“物”的伦理关系;从结构上讲,它更似一个由圆心向外逐层展开的同心圆,只是这个圆心并非“我”,而是由我所构成的血缘共同体。因此,仅就道德实践的意义而论,儒家的“仁爱”要比墨家的“兼爱”更为切实、有效。“和”的观念亦如此,《论语》谈“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4]935,谈“礼之用,和为贵”[4]46,即指向人伦关系层面;孟子谈“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3]251,荀子谈“万物各得其和以生”[5]309,即指向天人关系层面。可见,儒家的“和”,不仅有“和合”之意,还有“和生”之意。《国语》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6]470,《周易》讲“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1]265,“天地之大德曰生”[1]245,“生生之谓易”[1]229,《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7]1632,《孟子》讲“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3]54,皆是说天地即自然,生生不息之“仁德”即天地之基本特质。这就要求人一方面在心灵上体认天性、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另一方面在现实中修炼自我、扩充德性、承担责任。
在儒家看来,“君子”人格的养成与“圣人”之道的实现,最直接的途径就是摆脱物质性,提升精神性。《周易》讲“生生”之德,张载讲“为天地立心”,朱熹更讲“仁者,天地万物之心”[8]2440,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天地之心、自然之德何以可能?从现实性的角度来讲,天地之心本质上还是人心,亦由人心所显现,但此心非彼心。在孟子看来,人心的最主要功能在于道德本性的无限扩充,人心既可以体认万物,也可以包容万物,所谓“生生之德”“天地生物之心”,主要是就这一意义而言。可见,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中流砥柱,始终都具有浓烈的人道主义关怀,无论是在内在道德与外在实践的路径探索上,还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追问上。
三、道家的生态哲学:“道法自然”与“万物一体”
邵雍曰:“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可以说,天人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无论是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还是主张“天人一体”的道家,皆以天人问题为根据而展开其理论系统。儒家认为天人之间可互通、可对话,主要是基于人的道德主体意识以及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道家认为天人本就一体,并强调人与生命万物具有先天的平等性,则主要是基于超越现实与自我的意识以及自然主义的价值立场。
道家讲“万物一体”,讲万物平等,主要是基于《老子》一书与“道法自然”的思想。“自然”一词在《老子》一书中出现最多,内涵也最丰富。《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64王弼注:“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安全,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10]213就《老子》全书而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疑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精妙概括,从逻辑上讲,老子最终要表达的思想也是“人法自然”。在老子看来,“道”乃宇宙万物之本原,“自然”则是宇宙运转、万物生息的最高价值,“道”是基于本体论与存在论意义而言的,“自然”则是基于认识论与工夫论意义而言的。“自然”之价值即无为而无不为,或曰不妄为、不做多余之处理、顺应自然之发展而发展。《老子》还讲:“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9]137在老子看来,“道”生万物而“德”育万物,其方式无非是顺应自然而不干预,如此,则万事万物方能各秉其气、各安其性、各修其命、自在自为。
老子提出“自然”的价值之后,庄子又提出了“齐物”的思想。“齐物”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1]38,一方面强调万物的平等,另一方面又强调万物之间的和谐共处。庄子还在“齐物”的基础上延展出两种新的思想:一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二是“无用之大用”。《庄子》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已。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11]324由此可见,“物无贵贱”的思想背后所蕴含的其实是一种超越的相对主义价值,而唯有基于这一价值,才可以进一步推出“万物莫不大”“万物莫不小”“万物莫不有”“万物莫不无”之结论。在庄子看来,所谓高低、大小之分别,皆由“物”的视角所产生,但基于此视角所做出的判断,往往是有局限性的,因此也是不准确的。庄子认为,唯有“道”的视角才是宏观的、无偏差的,在“道”的视阈下,无论是具体而个别的事物、还是普遍而整体的世界,皆是残缺不全的。换而言之,与道的永恒性、无限性相比,万物也就不再有美丑、贵贱之分,既是“齐一”的,也是平等的。
如果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体现的是庄子价值论层面的思想,那么“无用之大用”则体现的是庄子认识论层面的思想。庄子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11]86“有用之用”指自然为人所用的那部分价值,“无用之用”指自然本身所内在具有的那部分价值,显然,较之自然的“有用之用”,庄子更注重自然的“无用之用”。也就是说,庄子基本上反对“利用自然”,而主张“因任自然”。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然习惯了用直觉的经验和系统的知识去判断一个事物是否有用,从伦理学的角度讲,这正是功利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泛滥的表现。事实上,一味追求“有用之用”,必然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外界,最终导致自我意义的丧失;二是为达到各种目的而放逐“机巧之心”,致使原来的生态平衡被破坏。在庄子看来,万物本质上是平等的,“大用”“小用”“有用”“无用”等观念的形成,完全是人们的功利心和目的欲作祟的结果。庄子以为,只有在工夫境界上实现“无待”,才能把握“物无贵贱、万物齐一”的真谛,也就是说,对物质实体的无所欲、无所待,是精神上实现自在逍遥的必要条件。
四、从“生生不息”“道法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如果将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儒、道两家之思想无疑构成了这一整体的二元。儒家以“人”为本位,用人伦解释“天”,从而使“天”人格化;道家则以“自然”为本位,主张顺应自然并把握其自生、自为之内在法则。儒家以人道主义为价值立场,主张将道德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即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领域一直扩展到人与万物的自然关系领域;道家则以自然主义为价值立场,主张从人与自然的对立状态回归到人与自然的一体状态。由此可见,虽然儒、道两家的出发点不同,所采取的理论路径也不同,但“殊途同归”,他们在天人关系或者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终极理念是基本一致的。
可见,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其实是关于价值的哲学。也就是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其实隐含着“生态”抑或“自然”这一价值主体本身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一方面,“生态”乃一可循环系统,本身具有基本的调适与修复功能;另一方面,“生态”系统内部所蕴藏的资源,分可再生与不可再生两种,由于人类社会的大肆索取与无度掠夺,那部分不可再生的资源势必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大隐患。因此,不该想如何介入自然、改造自然,应该去想如何恢复自然、还原自然,而恢复自然、还原自然的前提则在于了解自然、体认自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讲,人、植物、动物、水、空气,作为自然界的物质存在,一方面它是真实可感的,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它又是动态的、普遍联系的,而非孤立的、静止的。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研究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元素在结构中的分布以及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追求“和合”的美学境界。
综上所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与中国古代生态哲学在价值上、认知上最为契合。以儒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与道家“天人一体”“道法自然”诸观念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生态哲学,不但能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而且可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这一主体之“两翼”,配合其发展出更为深刻、更切近中国文化土壤的生态伦理思想。如果说让精深而圆融的中国古代哲学从文言文与经学的樊笼里走出,并鲜活于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一直以来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理论难题,那么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新理念以中国古代生态哲学尤其是儒家“天人合一”与道家“道法自然”的视阈作深度之阐发与有效之推进,无疑是为解决这一理论难题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法。
[1] (宋)朱熹撰.周易本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清)焦循撰.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 徐元浩.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 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 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 (宋)吕惠卿.庄子义集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