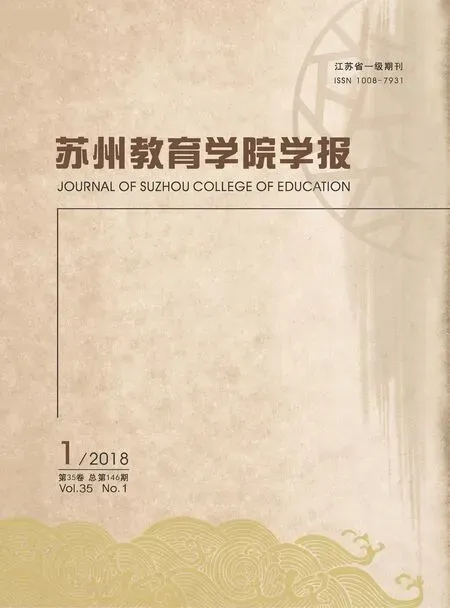略论陶渊明《饮酒》诗题的典故及其寓意
2018-04-03沼口胜李寅生
沼口胜 著;李寅生 译
(1.京都文教大学 文学部,京都 宇治 611-0021;2.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一
生于晋末宋初的诗人陶渊明(365—427)创作了以《饮酒》为题目的二十首五言组诗,关于其中的意图和理由,历来有一些不同的解读①。本文将对此进行重新解释,并对以往不同的观点进行研究,但限于篇幅的关系,只能谈一下笔者的愚见及其相关理论根据而已。
《饮酒》诗前五十五个字的“序”是以下论述不可缺少的文字,故将其全文展示如下: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1]86-87
上面的序文,是作者闲居无聊在秋夜倦怠的饮酒醉余之作。以这个序文来说明《饮酒》诗的整体特征,是否完全相符呢?
正如有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在二十首诗中,与饮酒有关的诗并不超过半数,剩下的并未谈及饮酒。再如,组诗的内容主要涉及王朝交替的迫在眼前的生存问题,所以作者叙述的是以古人为榜样,表达甘愿作为隐者而固守穷节的思想。作者围绕出仕与归田问题,对时代与自己做了深刻的反思,并寄托了觉醒后的孤独与达观。首章“哀荣无定在”与终章“羲农去我久”处于相对应的位置,配以相互呼应的内容。
从上面例子来看,如果把这组诗看成是与作者饮酒嗜好相关联的话,那么它就不是单纯的饮酒诗了。序文谈到的“饮酒”,不正是作者借此来表达复杂、隐微的感情吗?换言之,在内容复杂深奥的组诗中,几乎每首都暗示了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精神状态。序文看起来较为
① 关于以《饮酒》作为诗题,历来的说法大致有三:第一,按《饮酒》序文所言,是作者在实际的饮酒中为其所作的组诗而确定的题目。第二,从序文及“其二十”末尾二句的内容来看,为借“饮酒”之名来叙自己的感怀。第三,在《文选》第二十九卷中,从题为“杂诗”的“其五”“其七”二首的题目来看,它原本是作者题为《杂诗》的,后人改作《饮酒》。单纯,但实际上题意深刻且隐晦。
依笔者愚见,诗题“饮酒”大概出自两种不同的典故。其一是汉代焦赣(字延寿)所撰并传下来的《易林》(十六卷)①最早的记录是《隋书》“经籍志•三•子•五行”中的:“《易林》十六卷,焦赣撰。梁又本三十二卷。” 关于焦赣的字,《汉书》“儒林传”载:“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唐颜师古的注是:“延寿其字,名赣。中的一个繇辞;其二是《周易》中的一个爻辞。关于《周易》中的“饮酒”一词暂放于后面研究,先对《易林》中的“饮酒”一词进行考察。此外,在陶诗《乞食》和《拟古》其一也引用《易林》中繇辞典故,对于这一问题,请参阅笔者的其他论文②笔者拙文:《论陶渊明〈拟古〉九首其一的表现手法及其寓意》(《中国文化—研究与教育,汉文学会报50号》,大塚汉文学会1992年6月出版)、《论陶渊明〈乞食〉诗的寓意》(《中国文化—研究与教育,汉文学会报51号》,1993年6月出版)。。
二
笔者认为,陶渊明“饮酒”诗题的典故出自《易林》繇辞中的如下二首:
六月采芑,征伐无道。张仲方叔,克胜饮酒。(离之坎)③焦赣:《焦氏易林》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六月采芑,征伐无道。张仲方叔,克敌饮酒。(小过之未济)④焦赣:《焦氏易林》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对比这二首繇辞,可发现第四句的第二字是不同的。但从“克胜”“克敌”同为具有“胜敌”之意来看,二首则为同一繇辞的重复。
下面对这个繇辞的内容进行研究。四部丛刊本(乌程蒋氏密韵楼藏影印元本)《易林》附载的“旧注”(“旧注”者不详)如下:
《六月》、《采芑》,皆诗名。六月,建未之月也。时猃狁内侵,宣王命尹吉甫帅师伐之,有功而归。诗人作歌,以叙其事。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六月而出师者,以猃狁之故也。采芑之诗,言蛮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军行采芑而食,故赋其事。张仲,吉甫之友。是时燕饮,张仲在焉。⑤焦赣:《焦氏易林》附载之“旧注”,见四部丛刊本,乌程蒋氏密韵楼藏影印元本。
由“旧注”的解释,进而敷衍繇辞内容的话,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六月》《采芑》诗均为《诗经》小雅中的诗篇,所吟咏的是征伐无道的夷狄之事。夏六月,面对北方猃狁的不时入侵,周宣王命尹吉甫为大将进行征伐,归国庆功后咏《六月》之诗。此外,南方蛮荆反叛后,宣王命方叔进行征伐,故而咏《采芑》之诗。在征伐猃狁得胜而归的宴会上,吉甫之友张仲和与吉甫一起参战的方叔等文武大臣聚集在一起,举杯庆贺胜利。所以,由上面的繇辞可大致推测出“饮酒”诗题的典故出处了。
事实上,在东晋安帝司马德宗统治后期,实权人物刘裕统兵在外,在征伐鲜卑慕容部的南燕、羌族姚氏的后秦和平定卢循之乱时,刘裕吟咏《六月》《采芑》二诗,把自己的军事行动比喻成宣王征猃狁、伐蛮荆,史书和当时的诗赋作品都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按史书记载及诗赋作品所述,刘裕对外出兵都被比喻为周宣王的南征北伐。《晋书》“恭帝纪”所载,安帝之弟司马德文时,刘裕被拜为远征后秦军队的先锋,在途经战乱后的洛阳时,他奏请朝廷修复晋朝王陵,朝廷答应了他的要求:
刘裕之北征也,帝上疏,请帅所莅,启行戎路,修敬山陵。朝廷从之,乃与裕俱发。[2]
“启行戎路”一句,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晋义熙十二年(416)二月中,“琅邪王德文请启行戎路”[3]3686的记事所附的元朝胡三省所注:“《诗》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3]3686《诗•小雅•六月》是“赞美宣王时代尹吉甫北伐猃狁获得胜利的诗”[4]诗有 “元戎十乘,以启先行”之句,由此可知,刘裕的北伐是自比为宣王的。
傅亮曾随刘裕征战,《宋傅亮从武帝平闽中诗》云:“鞠旅扬城,大蒐徐方。旅旌首路,元戎启行。弭楫洪河,总辔崇芒。”[5]1139诗中的“闽中”疑为“関中”之误。对此,逯钦立认为:“逯按:宋武帝有平关中姚秦事,无平闽中事。闽,闗之讹。”[5]1139与陶渊明同时代的谢灵运在其《撰征赋》中也引用了宣王征猃狁之事。在这篇赋中,作者叙述了自己作为天子特使慰问指挥北伐的刘裕之事,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载之曰:
惟王建国,辨方定隅,内外既正,华夷有殊。惟昔《小雅》,逮于班书,戎蛮孔炽,是殛是诛。所以宣王用棘于玁狁,高帝方事于匈奴。然侵镐至泾,自塞及平。[6]1745
在上文中,作者谈到了最早扰乱中国秩序的戎蛮部落,以及周宣王征伐猃狁吟咏《六月》之事。在这里,宣王北伐被刘裕看成是自己北伐的先例。刘裕把自己征伐后秦比喻成宣王北伐,在史书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宋书•刘穆之传》记载:
故左将军、青州刺史王镇恶,荆、郢之捷,克翦放命,北伐之勋,参迹方叔。[6]1308
“荆、郢之捷,克翦放命”是指刘毅讨伐司马休之、鲁宗之之事;而“北伐之勋,参迹方叔”则是把征伐后秦有功的王镇恶比喻为随宣王征伐猃狁的方叔。在上述资料中,都把刘裕征伐后秦比喻成了宣王征伐猃狁之事了。刘裕平定卢循之乱和征伐南燕、后秦的所谓南征北伐,当他吟咏《六月》《采芑》之诗时,把自己的军事行动比喻成宣王征猃狁、伐蛮荆已是很明白的事了。
源于这个史实,陶渊明根据《六月》《采芑》的内容并引《易林》中的繇辞:“六月采芑,征伐无道。张仲方叔,克胜饮酒”中的“饮酒”一词,陶渊明的《饮酒》组诗中寄寓了对征伐后秦凯旋归来而沉醉于胜利之欢的刘裕的复杂情感。《饮酒•序文》有“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之句,在晋宋禅代之前,作者已寓有对黑暗时政的不愉快之意了。继之的“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一句,虽说是表现了秋夜无聊的孤独饮酒之态,但其中所蕴含的寓意又是什么?解释这一点的关键是“饮酒”诗题的深层次的其他典故,亦即《周易》中的一个爻辞,具体而言即“未济”卦的“上九”爻辞。
三
《周易》只有一处使用了“饮酒”的爻辞及其小象,即“未济”卦“上九”的爻辞及其小象: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7]500-501
作为“饮酒”诗题的典故的考察对象,即是上面爻辞中的“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一句。那么,这则爻辞在“饮酒”诗题中的典故寓义是什么呢?
“未济”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卦象的意义是值得注意的。众所周知,“未济”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处于第六十四的位置上,六爻分别表示阴阳失正、事业未成之意。《隋书•经籍志》录三国吴人虞翻所著《周易注》九卷,今见收于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中。虞翻解“未济”卦云:“济,成也;六爻皆错,故称未济也。”①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陶渊明对此应该是熟知的。如按此说,以这个“未济”卦的位置和卦象推测,《饮酒》诗的创作时间应是义熙十四年(418)的秋天,其所象征的东晋王朝的状况,陶渊明应是有所考虑的。
即《周易》六十四卦中的最后一卦“未济”,是与东晋王朝将亡的安帝治世相对应的;再如六爻中处于天子之位的“五”为柔顺之阴,与柔弱的安帝相对应;处于大臣之位的“四”为刚强之阳,与安帝手下的权臣刘裕相对应。前面的爻辞象征了后面的人物命运。
这里看一下“六五”和“九四” 的爻辞。“六五”的爻辞是:“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7]500这没有问题。但“九四”的爻辞:“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7]499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九四”爻辞中的“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是指殷高宗在盛怒之下征伐北方的鬼方(商、周时期居于中国西北方的少数民族),经过三年时间的征讨,逐渐平定叛乱而获得天子赏赐之事。位于“未济”之前“既济”卦的“九三”爻辞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7]492殷高宗讨伐鬼方,经过三年而取得胜利之事。按此说,“未济”卦的“九四”爻辞也是指殷高宗讨伐鬼方之事。
从上面所看到的殷高宗讨伐鬼方,和前面《易林》繇辞中的周宣王征伐猃狁,以及刘裕征伐后秦,三者所征伐的对象都是北方的种族,征伐的时间都是三年,而且都因战功而受到了赏赐,就这些方面而言,他们的征伐有着类似之处。
那么,“未济”卦“上九”(“上”位象征着上皇、隐退之士、隐者等)的爻辞“有孚于饮酒,无咎”[7]500一句有什么意义呢?陶渊明又从中领悟到什么呢?
在陶渊明之前众多的《周易》注释中,关于上面爻辞的解释,有前面谈到的虞翻和王弼二家。虞翻之说是从卦象、卦变上解释爻辞,但对爻辞的意义却不做说明,只把“孚”字解释为“信”意而已。因而,关于“上九”的“有孚于饮酒。无咎”的爻辞,在陶渊明之前所能看到的解释除王弼的《周易注》之外而无其他。王弼的解释是:
未济之极,则反于既济。既济之道,所任者当也。所任者当,则可信之无疑,而已逸焉。放曰:“有孚于饮酒。无咎也。”①王弼:《周易注》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唐孔颖达等《周易注疏》对王弼这段话做了解释,其“未济”卦《正义》曰:“‘有孚于饮酒。无咎’者,上九居未济之极,则反于既济。既济之道,则所任者当也。所任者当,则信之无疑,故得自逸饮酒而已。故曰‘有孚于饮酒。无咎’。”②孔颖达等:《周易注疏》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正义》对王弼注的解释大致如此,即“上九”处在了“未济”卦的终极位置,但不久又返回到了“既济”卦的位置。“既济”卦的六爻均为“正”,在世事中表示适应各种地位的人。尤其是居于“五”的位置能够获得为政者的信赖,所以居于“上”位的隐退君子则可安心地饮酒逸乐了。根据这些说法,“有孚于饮酒”一句的“有孚”有对为政者的信赖之意,而所谓“饮酒”则可当作逸乐之意来解释了。所以在对上面王弼所注的“有孚于饮酒”的爻辞的解释中产生了新的理解,因此,陶渊明便可能选取其中的意义了。
谢灵运有《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诗》,收录在《文选》卷二十“公宴”中。这首诗是作者在义熙十四年(418)九月九日于宋公刘裕主办的鼓城戏马台宴会上,为退隐故乡会稽山阴(今绍兴)的尚书令孔靖(字季恭)送别时所作。此外,谢灵运的族兄谢瞻也有同题诗,也收录在《文选》卷二十中。谢灵运诗云:
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凄凄阳卉腓,皎皎寒潭洁。
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鸣葭戾朱宫,兰巵献时哲。
饯宴光有孚,和乐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万群方悦。
归客遂海隅,脱冠谢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乐阕。……[8]960
诗中的“圣心”,唐代刘良的注云:“感圣心,谓感天子之心。”①六臣注:《文选》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谢瞻的诗中也有“圣心眷嘉节”[8]957之句。从作诗的场合来看,“圣心”之语是用于宋公刘裕的。把刘裕比喻成天子、并赞扬其主办的宴会的是第九、十句“饯宴光有孚,和乐隆所缺”的对句。对此二句唐代李善的注释是:“《周易》曰:‘有孚于饮酒。无咎。’《毛诗序》曰:‘鹿鸣废,则和乐缺矣。’”[8]960由此可以看出,“饯宴光有孚”出自“未济”卦的“上九”爻辞,“和乐隆所缺”出自《诗经•小雅•六月》“小序”中的“鹿鸣废,则和乐缺矣”②毛亨:《毛诗注疏》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而唐代张铣对第九句的注释则是:“光明,孚信也。言饯宴之理明朝廷有信也。”③同①。信赖朝廷,则能安心逸乐,进而寿于太平之世,这可能就是写作这首送别诗的原因吧。如按此说,谢灵运诗句“饯宴光有孚”便能够使用“上九”爻辞中王弼的注释了来解释④关于“饯宴光有孚”一句,请参照以下诸家的解释:叶笑雪选注:《谢灵运集校注》,古典文学岀版社1957年版;花房英树译著:《文选》(诗骚卷)三,见《全释汉文大系28》,集英社昭和49年(1974)版;顾结伯校注:《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森野繁夫译注:《谢康乐诗集》(卷上),白帝社平成5年(1993)版。。
对陶渊明而言,和所看到的谢灵运的例子一样,是在王弼对“有孚于饮酒。无咎”的爻辞的注释中对《饮酒》有了新的理解,许也可能适用于不同的方向而已。如果是前者的话,《饮酒》的诗题表现了对当时的为政者即形式上的天子(安帝)而实际上是对宋公刘裕的信赖,具有寿于逸乐的太平之世的寓意。然而如前所述,典出于《易林》繇辞的《饮酒》诗题,又具有征伐后秦凯旋而归的刘裕及其统治下的时势之寓意;而序文中的“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一句,又暗寓了作者对时势的厌恶感,典出于《周易》爻辞的《饮酒》诗题的寓意,与王弼解释的侧重是不同的。那么,究竟应该倾向于哪一种说法呢?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他所表现的是乐天不疑的态度。作于义熙元年(405)出世归田之际的《归去来兮辞》结尾之句即是其中的一例。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1]161-162
这里所表现的是陶渊明在人生的余年回归故乡田园和自然的自适,进而表现岀不畏死亡的觉悟了的人生态度。在写完这篇文章二十二年之后的刘宋元嘉四年(427),即在作者去世前两个月时所作的《自祭文》中,也谈到了乐天的态度:
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
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1]197
作者在上文中叙述了归田后的自适之乐,回顾自己的一生,他认为是“乐天委分”的。这个“乐天委分”中的“乐天”之语,与《归去来兮辞》中的“乐夫天命”之语具有相同的意义,《自祭文》的“识运知命”的意义也就由此而明白了。《归去来兮辞》与《自祭文》中的“乐天”之语,正如前辈诸家所指出的那样,是出自《易经》“系辞上传”的“乐天知命故不忧”⑤孔颖达等:《周易注疏》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一语,东晋韩康伯对此语注曰:“顺天之化故曰乐也。”⑥同⑤。唐孔颖达等疏曰:“顺天施化,是欢乐于天。识物始终,是自知性命。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终,任自然之理,故不忧也。”①孔颖达等:《周易注疏》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陶渊明乐天知命即顺从天命的态度当源于《周易》中的思想。
这里就《自祭文》中“乐天委分”的“委分”进行研究②需要指出的是,安立典世在其论文《陶渊明〈自祭文〉“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考》(《中国文化—研究与教育,汉文学会报52号》;《九江师专学报》2000年4期,李寅生译)中,对“乐天委分”的“分”的解释是以郭象《庄子注》为依据的。。所谓的“委分”即是肯定上天赋予自己的命数,并顺从之。换言之,就是要相信自已,相信自己的根源大概就是信赖天命吧!
笔者把所见到的陶渊明如上的精神态度和“有孚于饮酒。无咎”的爻辞关联起来进行解释的。即“有孚”是对天命的信赖,此事是上天赋予自己的或相信自己的,具有自信的意思。因而,逸乐自适便有了“饮酒”一词的意义,如果这样有效果的话,大抵也就成了不惧怕灾难和罪过的“无咎”一词了。
对“有孚于饮酒。无咎”一句爻辞作如上的解释,是否出现于陶渊明之前呢?就笔者所见,不是这样的。但在陶渊明之后的解释,却与此非常类似。宋代程颐的《伊川易传》(四卷)中的解释,就与此极为相似:
九以刚在上,刚之极也。居明之上,明之极也。刚极而能明,则不为躁而为决。明能烛理,刚能断义,居未济之极,非得济之位,无可济之理,则当乐天顺命而已。若否终则有倾,时之变也。未济则无极而自济之理,故止为未济之极,至诚安于义命而自乐,则可无咎。饮酒,自乐也。……有孚,自信于中也。……③程颐:《伊川易传》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对上面程颐《伊川易传》的解释,笔者认为④笔者的观点参考了本田济著《易》(新订《中国古典选》,朝日新闻社昭和41年[1966]2月版)的一些解释。,“上九”是刚毅(刚爻)、贤明(上卦离为“明”)之意,按道理是可以做出冷静判断的,但居“未济”之极,并没有取得“济”的地位,也无可济的道理,只是作为未济的终极而已。此处贤明、刚毅的“上九”,其否定的状态为极,并且又很快回复到原位,换言之只有乐天知命,一心一意以至诚安天命,自乐则可无咎了。所谓的“有孚”,是因自信在其中,所以“饮酒”才会得其乐。
对“上九”爻辞“有孚于饮酒。无咎”一句,把王弼的解释与程颐之言相对照,就会发现其不同之处在于“有孚”一词,前者解释为对为政者的信赖;而后者则解释为信赖天命、且安于此才会有自信。两者的差别并不很大。
如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程颐致其高足谢湜的信中所言:“《易》当应先读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⑤程颐:《伊川易传•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易》应当用王弼的注本。此外,本田济也认为,《伊川易传》的解释方法,与王弼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⑥参见本田济著《易》。。对“上九”的爻辞,陶渊明的解释与程颐的解释是相似的,他们基本依照了王弼的解释方法。
由以上考察可以看出,《饮酒》的诗题典故,是与焦赣《易林》的繇辞复合而成的,所用的是《周易》“未济”卦“上九”的爻辞,其寓意是以至诚安天命,和其所产生的顺从、自适的精神态度。因而,由《饮酒》诗序文“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便能够解释其诗中所寓意的精神态度了。
四
通过以上的考察,笔者认为,《饮酒》的诗题是由两种不同的典故构成、由不同寓意复合而成的词汇。具体而言,其一是典出于汉代焦赣所撰并传的《易林》繇辞:“六月采芑,征伐无道。张仲方叔,克胜饮酒。”指刘裕征伐后秦凯旋,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实现晋宋禅代的义熙十四年(418)秋的形势;其二是典出于《周易》“未济”卦“上九”的爻辞“有孚于饮酒。无咎”,指在上述的晋末时势中,作为隐者的作者所寓意的以至诚安天命,和其所产生的顺从、自适的精神态度。
《饮酒》的诗题虽如上面内容所表现的那样,但这个诗题的寓意并不难解。从《易林》繇辞的典故上看,它表面上只是为建立大功凯旋归来的刘裕祝寿之意;而从另一《周易》的爻辞来看,按王弼注所言,它表现了自己信赖为政者而寿于逸乐太平之世的意思,并沒有什么危险的感觉。从这些意义上看,花费细致的功夫所确定下来的诗题,正是作者谨慎心情的反映。
《饮酒》诗题的典故及其寓意正如上所述,一般而言,组诗的内容当与此呼应。然而事实上,组诗所暗示的内容是作者已意识到了晋宋禅代的形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纷争,其结果是读者看到了作为隐者的诗人所具有的自信。这方面的内容,由于篇幅限制,现仅略述一二而已。
《饮酒》其十七“幽兰生前庭”和其八“青松在东园”二首,具有托幽兰和青松来表现作者心目中理想人物的寓意,而这个人物是义熙十一年(415)三月刘裕讨伐司马休之时在休之府中任录事参军的韩延之的可能性较大。韩延之曾在刘裕幕下做事。刘裕爱其才,在开战之前曾写密信劝其归降旧主,但韩延之在给刘裕的回信中,谴责其不行道义,表明了他与休之共命运的意愿。后来韩延之逃往后秦,后秦被刘裕灭掉后,他又亡命北魏,其后又曾率兵惹恼刘宋①参见拙作:《陶渊明眼中的刘裕与颜延之—释〈饮酒〉(二十首)其十七的寓意》,见《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五十集》,日本中国学会1998年版。。类似韩延之这样的人物,敢于在刘裕的统治下有所作为,想必也是表现了作者的心情。把这样危险的题材大胆地编入自己的组诗中,诗题的隐微、难解也就显得重要了。
组诗书写了作者的精神探索,表现其取得自信并达到一种自适的境地。《饮酒》其四“栖栖失群乌”、其五“结庐在人境”及其七“秋菊有佳色”所表现出来的飞鸟的形态变化,是这一时期作者在精神上的探索、矛盾并寻求解决的形象展示,它表现了诗人自觉于天命所在、安闲自适的心迹。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周易》与《饮酒》诗之间所存在的极深的关系。
以上所谈,只是一个简单的归纳,详细论述请参阅笔者的其他论文②参见拙作:《从归鸟意向与〈易经〉之关系释陶渊明〈饮酒〉(其五)诗》,见《中国文化—研究与教育》第59号,中国文化学会1999年版。。
[1]陶渊明. 陶渊明集[M].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2]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68.
[3]司马光. 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
[4]程俊英.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498.
[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79.
[8]萧统. 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