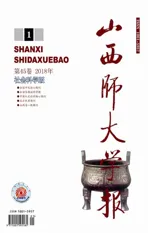语言主观性对语词组合限制的消解与重构
——以“都”“也”为例
2018-04-03储一鸣
储 一 鸣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233030)
语言中语词与语词的组合,一般都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词性的限制,句法结构的限制,语义关系的限制等。限制的存在保证了语言的稳定性。但是,时空的变化总会对语言提出一些新的要求。为了满足这种要求,语言会对原有的某些限制进行一定的修正或突破,以适应新的需要。
从宏观面观察,引起限制被突破的要素是多方面的。有来自语言内部的,如语音、语义、语法的变化;有来自语言外部的,如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变革等。每一次修正或突破能不能变成语用层面的现实,往往需要主体主观认知的参与,经过思维器官的过滤、约定、强化和固化,最终,才能满足表达层面的要求。
主观认知是改变语言原有结构,调整语言适应性的重要力量之一。当这种力量渗透到语言本体结构中,最显著的特征是使语言结构体自身携带上人类思维的“主观性”(subjectivity)。沈家煊把这种力量归结为言语交际中话语里蕴含的“自我”性成分[1]。Benveniste认为“语言如果不以这种方式或方法去构建的话,它究竟还能不能算作名副其实的语言”[2]225。
语言“主观性”介入语言活动,使得言语者在话语表述中,将某些语词原有的组合限制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突破而重新创造出新的表述样式。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语言主观性对语词组合限制的消解与重构。这种消解与重构,既可能发生在深层的语义结构中,也可能发生在表层的形体结构中,它是人类思维的主观能动性在语词层面的表现,对其内部运转机制的认识,能清晰地帮助我们认清语言运行的一些基本规律。
一、主观性到主观化:语词深层语义得以改变
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主体主观性的渗入是一项必不可少、不能忽视的力量。语言作为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和载体,也会遭受主体“主观性”的作用。其表现,Lyons认为是言说者在言说的过程中,表明自己言说的立场、态度或情感。[3]24在实际的话语交际中,话语者的每一句话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体现出自身某种主观性的倾向。比如,“我要去”表明主体的主观意愿;“花是红的”表明主体的主观判断;“你行吗?”表明主体的主观质疑;“你必须走!”表明主体强力的主观祈使等。
这种“自我”性成分,与语言的符号性、系统性、社会性一样,也是语言的一种本质属性,广泛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在语词上最大的表征是,语词除了自身带有与概念相关的理性意义之外,还常常带上附着在理性意义之外的其他意义。比如,色彩意义。它反映的是人或语境赋予词的特定感受,其实质就是人类“主观性”在语词层面的映射。
语词为了表现主体的“主观性”,也会相应地采用一些新的语音、语义或结构形式,并且经历相应的演变来配合。这一过程实质是语词被“主观化”的过程。其直接表征是:语词深层语义在主观化的促动下发生一些修正或改变。比如,汉语里的“都”字,《说文解字》“邑”部解释为:“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从‘邑’,‘者’声。周礼:距国五百里为‘都’。”可见,“都”字在产生的初期,记录的是汉语言背景中的实体性事物,是客体的代称。随着时代的更替,语用的发展,人们主观认知的逐步介入,这种概念性语义特性开始被主观化,深层语义开始发生转移,出现了主观性较强的副词性语义特征,常呈现于“S(O)P+都+VP/NP”的句法格式中。如:一桌子饭菜都凉啦!|我们都去北京。|他连话都不想说了。|都大学生了,还不知道这个。吕叔湘先生概括其句法语义为:(1)表总括全部;(2)“甚至”解,“都”轻读;(3)“已经”解,句末常用“了”。[4]201近年来学者进一步探索,又发现了诸多新的语义情况。Li认为“都”可以激发它左侧的复数 NP 的全称量化。“都”左边的疑问词短语可以被“都”允准为量化词并获得全称解读[5]。潘海华在蒋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都”作为全称量化算子总是约束限定部分(量化域)的自由变量。可以通过话题规则、焦点规则来确定,且后者具有排他性。[6]163—184这些新的语义特征与起始义“都邑”相差甚远。综合观之,“都”字的语义存在一条演化链,表现为:“有宗庙的城市”→“国都”→“汇集 、 聚集” →“总括、 全部”(范围)→“强调和比较”(语气)[7]。在这条语义演化链上,“都”字语义的主观化特征日益显性化,体现为“客体存在(都市)→主体活动(汇集)→主体认知(总括)→主体情感(语气)”。可见,在主观性作用下,“都”字在语用上逐步被人们主观化了,深层语义逐步由实词语义向虚词语义转换。这种语义转换,引起了“都”字代表的词的性质上的变化,即名词性质被副词性质代替,这势必导致原有组合条件的消解而重新构建新的条件,以适应新的性质变化的需要,产出新的表述体(具体内容后节专说)。
E.C.Traugott在研究语言“语法化”现象时认为:“语法化使得语言的意义变得愈来愈依赖言说者对命题内容的主观信念和态度,通过非语法成分的演变而逐步形成语言中可识别的表达主观性的语法成分。”[8]31—54这在汉语史上是普遍现象,也是语词添加新义的重要手段之一。副词“也”的诸多语义,大体就是在人们主观作用力的驱动下,借助多种途径或手段,将非语言或语法性成分转化成了句法或语义性成分,实现自身的语义改变,最终完成原有组合限制的消解,从而实现新表述样式的重构。如下例:
(1)李嘉诚自知如果要在香港安身立命,并想有更大的发展,无论如何[也]要学会英语。(窦应泰《李嘉诚家族传》)
(2)臭虫的寿命一般不到两年,但它空腹一年多[也]不会饿死。(当代应用文自然科学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这两例中都蕴含了“也”字小句,其表述视角是不同的。一般意义上说,视角是言说者在话语表述中必不可少的非语言性成分,是发话时选定表述角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往往因人而异,在语句中多以隐含的方式存在。在实际的话语中,这种视角性非语言成分可以借助语言性成分将句法关系嵌入语词的语义成分中。上例(1)(2)的“也”字句,言说者的视角存在两种情况:例(1)中的视角是言说者借用文本主体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句外言说者与句内文本主体假言性重合,即“李嘉诚”和言说主体重合,句内文本主体是以言说者为参照的个体或集体,其视角显性化,言语接受者易于感知,这种情形可以称之为“重合型视角”;例(2)的视角,句外言说者在句内没有或补不出类似言说者的文本主体,纯粹是言说者的场外叙说。其特征是言说者在句内没有任何被代之的成分,其身份隐匿。言说者与文本主体是分裂的,这种情形可以称之为“分裂型视角”。因视角的不同,言说者选择了不同的句法表达方式。例(1)采用了任指型句式,凸显了外语在香港立足中的重要性,其语用关系为“强调”;例(2)为了表达臭虫寿命虽然短暂,但生命力极强,采用了让步句式,其语用关系为“转折”。这种“强调”“转折”的语义特征是整个句义特征的综合体现,但在实际的句法意义归总时,人们习惯主观上将这两种关系意义归结为是副词性“也”字的意义,实质上并非“也”字自身所携带的意义,而是人们主观上将整个句法意义强加于“也”字的结果。原因出在两句中都以“也”字为显性形式标志。马清华先生认为:“一个词经常用在某种句子环境中,可携带上这种句子的特有特征。”[9]她把这种现象叫“感染”。美国学人J.Bybee,R.Perkins和W.Pagliuca等人在阐述他们的语法化理论时曾言:“吸收是跟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平行的五种虚化机制之一,是指标志词吸收所处的上下文的意义,即狭义的语境意义。”[10]28—39我们也认为一个语言成分长期处在某种固定的语境当中,因语境的浸润作用和语言成分自身的吸附能力,必然会使该语言成分习染该固定语境的语义特征。
可见,在语用过程中,言说者主体可以通过主观认知,利用视角转换、情感表达、认知解读等非句法成分将语义内涵、句法关系等固化到语词“也”字身上。一旦语言手段或非语言手段的成分或关系,在人们思维主观性的作用下,经历约定俗成的固化,就有可能转化为语词蕴含的意义,这种新的意义会推动语词功能的改变,最终导致语词组合限制的改变。下面,我们进一步解析语词功能的改变。
二、深层语义的改变:促动语词功能的转移
主观性而导致的语词被主观化,使得语词深层语义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一旦这种改变带来语词性质的变化,其功能就会发生相应的转移,这是语言运作中重要机制之一。
从历时角度观察,汉语“也”字的深层语义曾发生过两次大的变动。第一次,在上古时期。黄德宽先生曾考证“也”字最早出现在西周中晚期大盂鼎中(学界基本认同),原文“古(故)丧师也。”[11]827其意义《说文5乙部》曾言:“也,女阴也。象形。”不过,这种解释后世颇多微词。如容庚先生就认为:“《说文》‘也,女阴也。’望文生训,形意俱乖。”[12]875谷衍奎认为甲骨文中的“也”字蛇形,金文中的“也”字象突出头部,拖着尾巴游动的蛇形。[13]48—49至于“也”字象什么形的问题,学界多有争论,的确是一个难题,且在当前语料下难以证伪,但若抛开争议寻求共同,却能得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也”字是一个“象形字”。既然是“象形字”,根据造字法的原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断:在最初造字时,“也”字是模仿某种实体性事物而来。从词汇学角度观察,它是具备词汇语义的,即某种概念意义。因为,人类语言中的象形符号所蕴含的原始词汇意义基本上是它所模仿的事物的抽象指代意义,这种抽象的指代意义就是其词汇本义。
但是,从现存文献来看,“也”字作为一个词语已经不具备词汇意义。“也”字大量运用的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段玉裁曾言:“古尚书周易无‘也’字,毛诗周官始见,而孔门盛行之。”(《诗经小学》“鄘风其下翟也”下)语料库统计数据也可以印证,《论语》共469次,《诗经》共90次,《庄子》共1469次。这一时期“也”字用法,《经传释词》列有“犹焉也”“犹矣也”“犹者也”“犹耳也”“犹兮也”“犹邪也”。王力先生概括为不外二端:“句末表确认”和“句中表停顿”[14]249—251。文献考察,结论也的确如此。可见,在上古时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资料不足,有待探索)“也”字作为一个词,在语用上已发生过一次大的转换,即实词转向虚词。该转换过程中,其指称所代表的概念意义已经消失,而被新的表示语气的句法语义所取代。深层语义的转换,语词性质的变化,“也”字的功能就不以承担句子实体性成分为主体,而以建构句法关系、句法语气的作用为主体。原有做实词的结构关系、结构条件被迫改变,新的语气词重构出新的句法形式。如:墙有茨,不可扫也。(周诗经)在这种结构体中,“也”字变成了一个与判断词“唯”“是”相对立的,自足的语法要素,主要功能是表示判断。
“也”字第二次转换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副词性用法。例如:
(1)不能片时藏匣里,暂出园中也自随。(北周,庾信镜赋)
(2)自知费天下,也复何足言。(北周,庾信诗)
(3)那知不梦做,眠觉也横飞。(梁,徐防诗)
(4)贞女信无矫,傍邻也见疑。(梁,沈约诗)
(5)庭草何聊赖,也持春当春。(陈,何揖诗)
(6)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陈,后主诗)
(7)莫轻小妇狎春风,罗袜也得步河宫。(陈,江总诗)
以上例句是“也”字作为副词用法的最早案例。该组案例中,“也”字寓于七言诗句或五言诗句中,七言诗节律是“二:二:三”式,五言诗节律“二:三”式。根据古体诗歌节律要求,语符“也”当且仅当只能跟其后成分“自随”“复”“横飞”“见疑”“持”“去”“得”组配成一个三言或二言节律。这样,“也”字就摆脱了早期附着于主语的结构限制,即“【X也】Y”结构的限制。当“【X也】Y”结构变成了“X【也Y】”结构时,“也”字完成了语气词向副词的转化,其功能也开始发生转换,附着性丧失,从句中冗余成分变成一个有独立位置的成分,在以往语表形式黏附于主语部分,而现在,只能与句中谓词发生关联,句位重心得以后移。表面上看,表层显性结构,即线性系列没有发生变化,但深层句法语义关系却发生了动摇,过去的虚体性成分转化为实体性成分,并在语境的作用下,获得了较充实的意义,经过重新分析,句中发挥小停顿的作用变成了句中发挥修饰或限制的作用。
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语词深层语义的变化所带来的功能转换,往往还伴有语词主观量的变化。“主观量”是汉语量范畴中的次范畴,是语言主观性作用下量范畴主观化的结果。李宇明认为“主观量”就是说话人带有主观评价的量[15]。作为一个计算单位,主观量有“量级”分别,呈梯度特征。其评定以客观现实的存在为参照,可以采取近似值来表征。假设客观量设值为a,以客观量为参照的主观量级大体如下情形:
第一种, ←>a:主观大量
第二种, 0 =a:主观等量
第三种, a<→:主观小量
第一种“主观大量”是指语言表达的主观性要高于现实的客观量的标准,其近似值有趋大的倾向性;第二种“主观等量”是指语言表达的主观性近似等同于现实的客观性;第三种“主观小量”是指语言表达的主观性要低于现实的客观量的标准。由此可见,主观量的数值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呈现为“连续统”的状态。假设A和D是一个语言项目表达主观性强弱的两级,在实际语用中,该语言项目表达主观性的量级变化是在AD之间变化的。大体可以这样描写该语言项目在表达主观性上的模式:
(1)式:A→B→C→D
(2)式:A←B←C←D
如果A代表强级,D代表弱级,则(1)式表达该语言项目在实际语用中表达主观性是由强势逐步向弱势变化的,BC分别代表这一变化过程的两个节点,即次强、次弱;相反,(2)式则代表该语言项目主观性的变化是由弱势向强势转化的,BC依然是两个重要节点。汉语中主观量级的变化,能带来语词虚化程度的变化。如下面“也”字句:
(8)打吧!我不跑,也不躲!(老舍《龙须沟》)
(9)人固有一死,假使能死在这里,也该知足了!(当代文学《刘心武选集》)
(10)我们外面那个链子都已经锁上了,谁也跑不了。(电视访谈鲁豫有约《沉浮》)
(11)这阵子,他吃饭也吃不香,晚上不知道做了多少的噩梦。(欧阳山《苦斗》)
以上四例句中,“也”字的基本语义为“类同”,主观量级规约在主观等量范畴内,但四句中的“也”字在主观化的进程中的虚化程度不是相同的。例(8)“也”字具有表达实际语义“类同”的功能,虚化程度最低;例(9)“也”字的“类同”意义弱化。与 “假使”配合,转化为表示关联关系,虚化程度得到加强;例(10)“也”字在句中主要是表达语气,主观性明显增大,虚化得到进一步加强;例(11)“也”字演化为话题标记,虚化达到最高值。可见,在主观性作用下,“也”字存在一个虚化量级梯度,其虚化链为“类同→关联→语气→话题或焦点标记”,其强度由低到高,句法功能更倾向于由实体成分向虚体成分转化。
三、语词功能的转移:迫使语词组合限制消解与重构
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言说者为了完成彼此的信息沟通,往往根据自身表达意义的要求,来选择相应的语词进行组合。因此,意义对言语交际中表达形式的选择具有决定的作用。从语词层面来看,一个语词因主观性导致主观化,一旦深层语义发生改变而获得了新的意义,也就意味着它获得了新的组合形式或新的语法、语用功能。一旦语词功能得以转化,势必会导致语词对原有组合限制的消解而重新构建新的句法关系或句法形式。
“都”字语用的历史变化,展示了这一语言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在早期(春秋战国),“都”字是以名词面貌出现的,其组合限制以名词结构句法的方式进行。如下例:
(12)皋陶曰:“都。”(周《尚书》)
(13)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春秋战国《商君书》)
(14)是月,六兒鸟退飞过宋都。(春秋战国《谷梁传》)
(15)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周《诗经》)
例(12)“都”字“独立成句”;例(13)“都”字句中主语;例(14)“都”字句中宾语;例(15)“都”字句中定语。各例词义均含“国都”“都城”“都市”之类的概念特征。组合限制被局限在名词规约范围类,体现出概念语义驱动句法组合的语用状态,句法格局以“都+VP”(如:例13)或“NP+V(VP)+都”(如:例14)为常见形式,这是“都”字早期组合句法的基本特征和条件。随着主观化的推进,该种组合句法的条件、形式被逐步瓦解,出现新的组构样式。
当“都”字语义由静态向动态转化,词性也由名词变为动词,开始突破名词控句条件的限制,在句中可以做谓语。如:
(16)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汉书》)
该例中“都”字词义,虽然还与名词“都邑”相关,但被完全动化了,转为“建都”,且带上地点宾语,占据谓词位置,句法形式为N(O)P+都+NP。
语义由静变动,在语用上,“都”字主观性特征得到加强,语法上的虚化,语用上的重新分析开始出现,原名词结构句法的根基进一步动摇,出现了“都”字的副词性用法。
这种用法是对“都”字原组合限制的第二次突破,也是一次彻底消解原词义的控句基础和方式。当“都”字变成副词时,不仅摆脱了实词位置的限制,而且也能进入虚词位置,发挥修饰、关联、语气等功能,句法格局也随之复杂化,在现代汉语中更加突显。语料显示仅表示周遍性语义的就有多种情形,常见的主要有“什么+(NP)+都+VP”“一+量+名+都+不/没有+VP”“重叠量词+都+VP”等,比如:“什么都做不好!”“一个字都不能改!”“个个都是好样的!”等。与“都”字不同,“也”字语用上,除了存在类似于“都”字那样的虚化现象之外,还有实化的现象(张立昌、秦洪武称为“逆语法化”;注:“都”只有虚化),这两种现象的演化,都从不同角度调整着“也”字原结构的重组。前文已对其虚化现象做了说明,下面,我们重点来说明一下实化的情形。
从大数据库里的语料来看,“也”字实化转换大致产生于六朝时期。六朝以前“也”字做语气词使用,句位形式多处于句末或句中(以句末为主),语用功能限定在帮助句子表示“判断”或“句中停顿”上,是一个完完全全被虚化的句子虚体性成分。六朝时期“也”字,因多方面的原因,出现副词用法,语义上突破语气词只虚不实的情形,出现标示“类同”的语义特征,该语义特征使得“也”字不再依附于句中实体性成分,而变成了句中实体性成分,占住状位,充当状语。[16]如:
(17)自知费天下,也复何足言。(北周,庾信诗)
(18)贞女信无矫,傍邻也见疑。(梁,沈约诗)
副词“也”字突破虚体性成分的限制,且能在话语表述中担任实体性成分后,其语用上出现了更加多样的句法形式。比如:重动形式(V也VP):
(19)坐也坐不定。(《宋·王安石诗》)
(20)死也死得瞥脱。(《大慧普觉禅师书》)
叠用并存形式(也p,也q):
(21)我是个乐家,也不向买主,也不向卖主,我只依直说。(《老乞大》)
(22)你这布头长短不等,有勾五十尺的,也有四十尺的,也有四十八尺的,长短不等。(《老乞大》)
复合关系框架形式(即/即使/虽然/因为p……,也q):
(23)虽然不及相如赋, 也直黄金一二斤。(隋唐五代《北里志》)
(24)即使明天下雨,也得去。(日常口语)
语气功能形式:(连/一……也……)
(25)刘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闷过日子,连那泰山的寿诞 [也] 都忘了。”(宋《话本)》)
(26)众人那里肯听他分说,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贯钱,一文 [也] 不多。(宋《话本)》)
这些组合形式,是对“也”字语气句法限制的一次消解与重构。从实例中,可以看出,“也”字虽然失去了句末位(现代语料中还有少量仿古用例),但在语义上得到补偿,功能上得到拓展,这是语言变化中的平衡法则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类主观性思维给予语言适应表达需要而自我调整的结果。语词深层语义改变,功能的转移,以致其组合限制的消解与重构,最终转化成语用层面的现实,都是这种力量作用体现。可见,这种力量在生成、理解语言的意义以及语法结构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丰富了语词的内涵,加强了语词的表现力和适应力;另一方面使一些不可理解的句子可以理解,一些不可接受或不自足的句法结构可以接受。换句话说,主观性而导致的主观化,使得语词组合更加灵活,句法功能更加多样,句式选择更加适切,大大丰富了语言的表达形式,使得语言在语用道路上越走越宽广,更能有效地适应和满足时代、社会、思维的发展变化。
四、结语
“主观性”涉及语言的性质,反映研究者如何看待语言的本质,关系到语言单位、结构体如何组织和运行的理解和操作;“主观化”是体现这一本质问题的过程或结果,两者相互关联、交织,不可分割,共存于历时和共时的层面上。语词的研究或其他语言现象的研究,不能忽视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在现实的言语交际中是蕴含性的存在,借助主体表达的视角、情感、认知等方面的变化得到体现。在语用需要的促动下,非语言成分经过人们约定俗成的规约化可以转化为语言成分,保证语言“生命体”的新陈代谢。
语词作为语言“生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受这种条件的制约和管控,是顺应语言发展的自然规律。在“主观性”主导下的“主观化”的过程中,语词原有组合阈限得到拓展,语义得到增量,主观量级得到变更,原有结构得到调整,在瓦解与重构中,语词保证着自身的活力,也最终满足了时代变化对语言结构体提出的各项要求。
[1] 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外语教学研究,2001,(4).
[2] Benveniste E.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M.E.Meek.Coral Gablres,FL:University of?[M].Miami Press. 1971.
[3] Lyons J. Deixis and subjectivity:Loquor, ergo sum ? In R. J. Jarvella & W.Klein ( eds. ) Speech, Place, and Action :Studies in Deixis and Related topics[M]. Chichester and New York: John Wiley, 1982.
[4]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 Li Jie. Dou and wh-ques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995,(4).
[6] 蒋严.语用推理与“都”的句法/语义特征[J].现代外语,1998,(1).
[7] 潘海华.焦点、三分结构与汉语“都”的语义解释[A].中国语文杂志社.语法研究和探索[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8] Traugott E. CSubjectivityand Sujecivisatin:Linguistic Perspective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9] 马清华.语义共振:突变式吸收的意义条件[J].汉语学习,2004,(5).
[10] Bybee R Perkins, W Pagliuca.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M]. C 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1] 黄德宽.说也[A].张光裕.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97.
[12] 容庚.金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 谷衍奎.汉字源流词典[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
[14] 王力.古代汉语(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5] 李宇明.数量词语与主观量[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报),1999,(11).
[16] 储一鸣.“也”类同作用的获得与语用占位[J].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