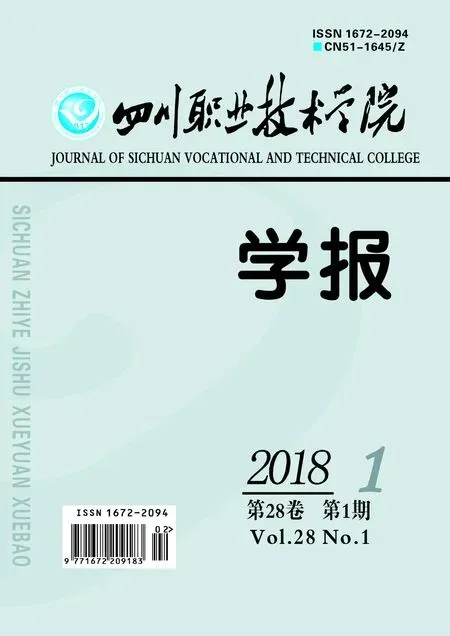高空坠物致人损害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的困境及出路
2018-04-03金富文
金富文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从高楼上抛掷、坠落下来的物品致人损害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前有重庆烟灰缸案、重庆花瓶砸伤案、南京砖块砸伤案、北京玻璃砸伤案等,最近又有安徽芜湖绿地伊顿公馆小区,一骑电动车男子被空中坠落的红砖砸中后脑勺死亡案。对这些案件的受害者,我国均有相应的法律来救济,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前,法官依据《民法通则》第126条来保护受害者,《侵权责任法》出台后,第87条对从建筑物中抛掷物或从建筑物上坠落物有专门的规定。无论是《民法通则》126条还是《侵权责任法》87条,均是一种过错推定责任,即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者被告不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均要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司法实践中,法官依据这些法律作出的裁判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甚至成为一纸空文。重庆烟灰缸案,渝中区法院判决24家住户分担受害人17.8万元的损失,每户赔偿8101.5元,执行过程中,两人做出了全额赔偿,分别是沙坪坝区的一名人大代表魏茂和一名公务员吕春涛,还有一个被执行人给了1000多元,其他被执行人分文未给,以至于法院不得不中止执行。作出赔偿的两人说是碍于公务员和人大代表身份才赔偿,其他未赔偿的人理由大都是自己根本不是侵权人,从来没有丢过烟灰缸,凭什么要赔钱。[1]重庆市三中院曾对高空坠物案做过一个调研,调研结果显示,92﹪的人会对这类案件上诉,愿意执行裁判的人不到2.8﹪,不服裁判选择信访的人为35.6﹪。[2]从这样的实践情况来看,当事人对裁判并不满意,这并不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反而还会损害司法权威,让我们生效的裁判文书得不到执行。
但依禁止向法外逃逸原则,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无权拒绝适用现行法,同时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于2010开始施行,至今才刚刚七年时间,从保持法律的稳定性方面来说,短期内也不可能修改《侵权责任法》。那么让《侵权责任法》第87条更好的得到落实,同时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需要我们做出个方面的努力。
二、《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不足之处
为什么法官依据《民法通则》126条、《侵权责任法》87条作出的裁判人们如此不信服呢。除了老百姓法律意识淡薄等外在原因外,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侵权责任法》87条有诸多不足之处。
(一)《侵权责任法》87条赞成理由之不足
赞成《侵权责任法》87条代表性的理由主要有:损失分担、预防损害、真实发现。[3]笔者认为这些理由有其难以自圆其说之处。虽然现代《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趋势是以强化保护受害人为中心,法官不应过多注重过错的可归责性,应当考虑在行为人和受害者两者之间由谁分担这个损失更为公平,更为合理。但是让一个从来都没有实施过某一行为的人来承担责任多少是与法律内在的善相违背的。马克思曾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行为就是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行为就是为之要求的生存权利,并且要求实现权利的唯一,因此受到现行法的支配。[4]救济受害者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应以牺牲无辜第三人的利益为代价,否则救济了一个受害人的同时,我们又人为的新增了许多个受害者。预防损害理论认为,高空坠物所在小区的业主最接近危险源,让业主来承担责任,可以让他们因害怕承担责任从而从源头上切断高空抛物、坠物事件。[5]但有时高空坠物非人力所为,是自然力所致,比如大风将花盆吹落下来,这样让高楼住户均承担赔偿责任于事无补。还有,有时加害人基于损失均摊,心存侥幸,从高空抛物并不一定会被发现,就算赔偿,那么多人分摊损失,自己也赔不了多少的心理,从高空抛物,那么损失预防理论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真实发现理论认为,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责任,有利于找到真正的物品所有人。物品毕竟是从高楼中抛掷或坠落下来的,与楼的所有人和使用人有一定的联系,尽管绝大多数业主不清楚损害是如何发生的,但毕竟损害的发生是业主中的某一个,因此由业主来举证证明自己不是具体的侵害人有利于事实真相的发现。[6]姑且不论这种“连坐”是否合理,让一个人来证明自己没有做过某事这是何其困难,让一个人来证明自己做过某事还好一点,因为这件事毕竟客观存在过,总会留下一些客观痕迹,反之,一件事情自己根本没有做过,自己并不清楚它,让人来自证清白是很困难的。那么终究谁是具体的加害人还是查不清楚。
(二)《侵权责任法》第87条内在逻辑上的不足
《侵权责任法》第87条内在的逻辑是,只要发生了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坠落物品并造成他人损害这一事实,就推定整个建筑物中的人都是可能侵权的人,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就由所有可能侵权的人承担补偿责任,除非可能侵权人能够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适用这一内在逻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悖论:如果某晚在广场发生一起强奸案,没有查出犯罪嫌疑人,就可以处罚所有案发时间身处广场的14岁以上的男子,因为他们都可能作案。[7]任何一个理性人都可知这是一个荒诞的逻辑,若坚持用这样荒诞的逻辑来制定我们的法律,那么该法也非良法。
(三)《侵权责任法》第87条外在逻辑上的不足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也就是说,不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可能加害人将要承担补偿责任。这是一种概率意义上的加害人,在87条语境下仍是侵权人,需要承担补偿责任,即87条规定的是侵权人承担补偿责任。但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5条可知,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无承担补偿责任这一方式。根据第23条的规定,可知承担补偿责任的主体是无过错的受益人。也就是说侵权人承担的是赔偿责任,无过错的第三人承担的是补偿责任,但第87条却规定的是侵权人承担补偿责任,该立法上矛盾之处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境况:人们基于对赔偿和补偿的朴素理解,被判决承担补偿责任的被告会认为,我又不是加害人,凭什么要“可怜受害人”给予他补偿,真正的加害人认为,我只是承担补偿责任,并不是承担赔偿责任,说明我没有做错,只是“可怜人家”才给点补偿。这样作出的判决往往得不到执行,其法律规范的指引作用会被扭曲,最终司法效果也是很差。
(四)《侵权责任法》第87条概念上的混淆
《侵权责任法》第87条对抛掷物品和坠落物品不做任何区分,均适用同一责任,明显是混淆了抛掷物和坠落物的区别。抛掷物顾名思义是由他人抛掷出来的,也就是该物品受到人外力作用,才被从高楼中抛掷出来。对抛掷物进行法律分析可知,其是在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况下被抛掷出来,行为人对物品被抛掷出来是有过失的。行为人应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某中危害结果,其对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要么持希望、要么持放任的态度,或者行为人过于自信,认为危害结果不会发生,或者行为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故抛掷物是行为人在有过错的情况下作出的积极行为。坠落物,是物品在没有受到人为外力作用下,仅受重力和空气阻力的作用从高空中下落。坠落物坠落的原因是自然力的作用,比如大风,大的震动等,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的积极行为,至多可能会有人的消极行为参与其中,比如物品坠落前“行为人”将花盆放置在阳台上没有及时搬回室内。对坠落物进行法律分析可知,“行为人”对坠落的坠落是没有故意的,至多可能存在过失。但这种过失一般是社会能够容忍的,不能与抛掷物的过错划等号。
综上,抛掷物与坠落物在主观上的区别是,抛掷物的行为人主观上是有过错的,这种过错包含故意和过失,坠落物的“行为人”主观上至多存在过失。二者在客观上也有区别,抛掷物是行为人的积极行为,坠落物至多存在“行为人”的消极行为。基于最朴素的观念,“故意犯”的社会危害性高于“过失犯”,对“故意犯”的处罚力度也应大于“过失犯”,所以抛掷物与坠落物不应适用相同的责任。
三、《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具体适用
适用现行法是法官的义务,尤其是现行法对某一问题有具体的规定时,法官不能向法外逃逸,即使该法律条文有不完善之处。但法官适用该条文时,可运用一些司法艺术,将该条适用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甚至软化该法条,为以后的修法做准备。
(一)法官依职权取证,尽量避免该条的适用
在高空坠物案件中,当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时,根据现在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由可能加害人承担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举证责任。然,可能加害人只是普通公民,其举证能力有限,常查证无门,手足无措。但如果在这类案件中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情况势必会好很多。
当受害人被从高楼上落下的物品伤害时,必定会留下伤口或其他痕迹。医生或者法医可以及时记录下这些痕迹,比如伤口的角度、长度、深度等,再查看“作案工具”,看“作案工具”的长度、质量、形状等,再综合相应的力学原理,G=mgh等,再作相应的“侦查实验”,来测量从哪个角度,什么高度掉下来的物品才可能造成受害人所受的伤害。这个发现“真相”的过程如果由法官来组织,必定会减轻当事人的许多负担,也比现在许多判决所判的由二楼以上住户来承担补偿责任要让人信服的多。同时现代小区到处都遍布摄像头,普通公民并不一定能接触到监控录像,如果由法官依职权调取这些监控录像,对查找到具体的加害人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降低“自证清白”的证明标准
《侵权责任法》及民诉法司法解释等法律并没有对《侵权责任法》第87条有特别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该条的证明标准就是民诉法中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即可能加害人要对自己不是侵权人证明到存在高度可能性时,才能不承担补偿责任。
笔者认为,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对可能加害人来说过于苛刻。这是因为,由可能加害人来自证清白就是一种政策上的考量,这与最朴素的“谁主张谁举证”相违背,同时,可能加害人也并不比受害人更容易举证,所以在规定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方面已经是立法者在遵循侵权法保护弱者这一原则下做出的妥协。又基于普遍的常识,我们知道,证明是对过去发生的事实的再现,往往很难证明到客观真实,何况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做的事。所以笔者认为可能加害人“自证清白”的证明标准为优势证据,即可能加害人不是侵权人的可能性大于其是侵权人的可能性。降低“自证清白”的证明标准,能够减少“连坐”的范围,让《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减少上诉案件的数量,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能减少因判决让其承担责任而产生不满的人数,防止增加不稳定因素。
(三)责任形态应为按份责任
关于《侵权责任法》第87条所确定的补偿责任之责任形态有“连带责任说”和“按份责任说”两种观点。连带责任说认为,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救济受害人最有利。而且,难以确定具体的加害人,也就无法确定具体的份额。[8]
笔者认为,赞成连带责任说的理由不可取。《侵权责任法》第87条所确定的补偿责任根本就不是一项侵权责任,而是一种出于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的损害嫁接机制。这一制度几乎不能体现侵权责任法应有的任何一项功能,诸如救济损害、惩罚过错、阻却不法、警示教育或者平衡利益等等。[9]如果采用连带责任说,看似方便了救济受害人,实则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受害人向某一加害人主张全部损害,而其并非实际加害人,让他承担全部的补偿责任是不公平的,一来真正的加害人并未受到处罚,二来该承担全部补偿责任的人心有不甘,可能不会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责任,导致执行难。如果采用按份责任,真正的加害人或多或少被判令补偿一部分,这也算是对他的交轻微的惩罚,也可以避免判令某个人承担责任而执行不能时受害人救济目的的落空。
四、高空抛掷物、坠落物致人损害的救济展望
由于《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有诸多不足之处,在现在的适用阶段和以后的法律修改过程中我们必定要对这种责任承担方式进行一些限制和改进。
(一)区分抛掷物、坠落物,确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关于抛掷物与坠落物的区别上文已经论述,在此不予赘述。笔者认为,对于坠落物,可由可能加害人承担补偿责任;对于抛掷物,无论有没有受害人,我们都要尽力查找具体的抛物人,根据危害结果的大小令其承担侵权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是因为高空抛物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危险的行为,我们要让行为人承担与其行为危害性相适应的责任,才可能减少甚至避免高空抛物行为。至于抛掷物和坠落物的区别可由法官根据具体的物品并结合案情来判断,比如烟灰缸,依据生活常识我们可知这就是一个抛掷物。
(二)设立意外救济基金、鼓励群众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我们应该始终牢记,侵权法所起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侵权法不应该是解决意外伤害的唯一机制,私法无法为人们擦去眼中的每一滴泪水。[10]这也是法律并不是万能的体现,我们要摒弃法律中心主义的看法,认为法律是无所不能的,其实法律也有其调整的空白点。在高空抛掷物、坠落物伤人案件中,当穷尽一切办法都找不到具体的加害人时,寻求法外途径来救济受害人未尝不可,既能救济受害人,也能不增加其他人的负担,不影响我们裁判的执行力,从而不伤及司法权威。
有学者主张,可以借鉴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的经验让高楼住户来购买强制责任险,当发生高空抛掷物、坠落物伤人事件而又找不到具体加害人时可由保险公司来理赔。[11]笔者认为该做法不可取,交强险的法理依据在于驾驶机动车是一种危险行为,其在道路上的行驶对他人来说增加了受伤的风险,当加害人驾驶机动车造成他人损害时,其未必有充足的财力来承担赔偿责任,通过交强险可以分散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交强险的前提是驾驶机动车是一项危险行为,增加了他人的风险,但是业主住在高楼这一行为并不是一项危险行为,让业主购买强制责任险就显得强词夺理了。
笔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意外事件经常发生,难免哪天意外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是值得鼓励的。目前我国的意外伤害保险项目包含了一般意外身故、意外伤残等,即从高楼中的抛掷物、坠落物伤人的可以适用意外伤害保险来救济保险受益人。当然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只是公民个人一种道义上的义务,并不能强制其购买。当公民个人并未购买强制责任险时,这时可由社会承担道义上的补偿来救济受害人。目前我国有交通事故社会救济基金,之外并无其他社会救济基金,我们国家可以设立意外救济基金,当发生高楼抛掷物、坠落物伤人事件时,找不到具体的加害人,受害人又未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此时可以由意外救济基金来承担补偿。
[1]重庆烟灰缸案已过14年22名被告仅3人赔了不到2万[EB/O L].成都商报(电子版),2014-5-13(11)[2017-08-24].ht tp://e.chengdu.cn/ht ml/2014-05/13/content_469047.htm.
[2]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权衡与博弈: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路径选择——兼评《侵权责任法》第87条[J].法律与适用,2012,(12).
[3]王利明.抛掷物致人损害的责任[J].政法论坛,2006,(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17.
[5]王利明.抛掷物致人损害的责任[J].政法论坛,2006,(6).
[6]王利明.抛掷物致人损害的责任[J].政法论坛,2006,(6).
[7]周永坤.高楼坠物案的法理分析——兼及主流法律论证方法批判[J].法学,2007,(5).
[8]吴煦,逯笑微.高空抛物责任承担的经济学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5).
[9]韩强.论抛掷物、坠落物致损责任的限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困境及其破解[J].法律科学,2014,(2).
[10]张铁薇.侵权法的自负与贫困[J].比较法研究,2009,(6).
[11]郭霓.高空坠物中多元化保护救济受害人的反思[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