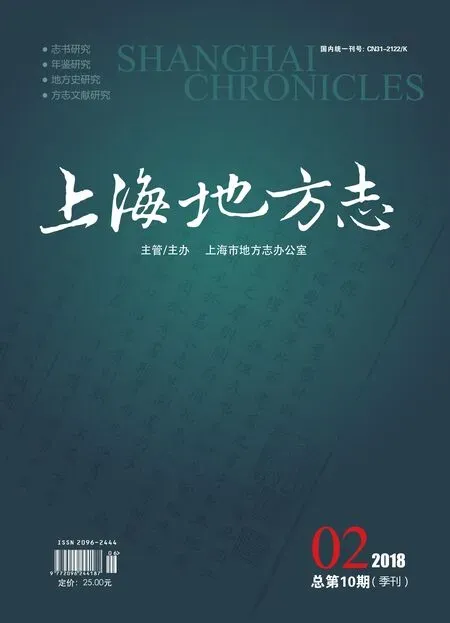方志对嘉定竹刻的书写与塑造
2018-04-02刘芝华
刘芝华
清人金元钰在其所著《竹人录》的凡例中称:“雕竹有二派:一始于金陵濮仲谦,一始于吾邑朱松邻”,最早提出了竹刻的分派问题。褚德彝在《竹人续录》中虽未明言分派,但指出当时存在着两个地域的竹刻,即金陵与嘉定,称“金陵濮、李,嘉定朱、侯,名擅雕镌,咸称绝技”。王世襄先生因传承性问题基本否定了金陵派的存在。①王世襄:《论竹刻的分派》,《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3期,第15—17页。嘉定派的存在成为一既定事实,且朱鹤成为了嘉定竹刻的创始人物。但这一既定事实是经由清代志书对嘉定竹刻的书写与塑造才得以形成的。本文尝试对这一过程作一考察。
一、志书对嘉定竹刻的书写与塑造
作为工艺类别之一种的竹刻,在地方志的记载中是作为物产出现的。万历年间编撰的《嘉定县志》在有关物产的记载中尚未出现竹刻的字眼,在叙及朱缨时,亦仅是指出朱缨“雕镂牙檀仙佛笔筒簪佩之属,俱为世珍重,几不可得”。②韩浚、张应武等纂修:(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物产,《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8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776页。这一时期嘉定竹刻尚未形成派别,且朱缨尚未被塑造成嘉定竹刻的创始人物,甚至竹刻在朱缨的作品中不占据主要部分。这一情形在康熙年间编撰的《嘉定县志》发生了转变。康熙年间编撰的《嘉定县志》在物产中称“雕刻竹器始于朱小松,制作精巧绝伦,为世所珍,后之袭其技者,实繁有徒”。③赵昕修、苏渊纂:(康熙)《嘉定县志》卷四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513页。竹刻开始被认为是嘉定的物产之一,朱小松则被塑造成竹刻的创始人物。
竹刻被认为是嘉定的物产之一,可能跟竹刻作为一种营生手段有关。康熙《嘉定县志》的编撰者之一赵昕认为:“物产记土之所生也。然人工所出,亦以物产名之。太史公云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故不独布之出于木棉者,有斜纹、药斑等之殊名,即耕织之外,或镂刻以为业及结草成靸,极其擘练纂组之工,所行甚远……”。①赵昕修、苏渊纂:(康熙)《嘉定县志》卷四物产,第514页。蒲鞋亦为嘉定物产之一,“出新泾镇,其居民取黄草、菅草织之。无论男女皆习以为业。又有凉鞋,则夏天鬻之,坚致精巧,用以馈远。四方来游者,必市之以归。”②赵昕修、苏渊纂:(康熙)《嘉定县志》卷四物产,第513页。竹刻亦是如此,“争相技摹,资给衣馔,遂与物产并著”。③赵昕:《竹笔尊赋》,(康熙)《嘉定县志》卷二十艺文,第846页。
在竹刻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进入物产之列之时,三朱的作品已为世人所珍。如朱缨的作品,被认为“制作精巧绝伦,为世所珍”;朱稚征的作品,被“邑好古士大夫家所藏”,则“重如拱璧,不轻馈人”。
正因为后人认为三朱的雕刻达到了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三朱开始被塑造成嘉定竹刻的创始人物。关于嘉定竹刻的创始人物,当时至少存在着两种看法:一是以朱鹤为始;一是以朱缨为始。康熙年间编撰的《嘉定县志》以朱缨作为竹刻的创始人物;乾隆年间编撰的《嘉定县志》则以朱鹤为始,在物产之竹刻条称“始明邑人朱松邻,其子小松,孙三松益精其技,以画手行刀法,朴老可贵”。④程国栋纂修:(乾隆)《嘉定县志》卷十二物产,乾隆七年刻本,5页。陆廷粲的《南村随笔》、王应奎的《柳南续笔》亦是将朱鹤作为竹刻的创始人物。《南村随笔》称:“疁城竹刻自明正嘉间高人朱松邻鹤创为之,继者其子小松山人缨,至其孙三松稚征而技臻极妙”。⑤陆廷粲:《南村随笔》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16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13页。《柳南续笔》称:“嘉定竹器为他处所无,他处虽有巧工,莫能尽其传也。而始其事者为前明朱鹤,鹤号松邻,子缨号小松,孙稚征号三松,三人皆读书识字,操履完洁,而以雕刻为游戏者也”。⑥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62页。《南村随笔》刊刻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柳南续笔》刊刻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年代上都晚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编撰的《嘉定县志》,与乾隆七年(1742年)编撰的《嘉定县志》的年代更为接近。这可能是《南村随笔》、《柳南续笔》与乾隆年间编撰的《嘉定县志》的观点一致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对三朱身份的塑造。
万历年间编撰的《嘉定县志》将朱缨列入方技类。康熙年间编撰的《嘉定县志》将朱鹤、朱稚征列入方技类,朱缨无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编撰的《嘉定县续志》补遗,将万历年间编撰的《嘉定县志》中有关朱缨的记载补录,值得注意的是将朱缨列入隐逸类。乾隆年间编撰的《嘉定县志》随之将朱缨、朱稚征列入隐逸类,有关朱鹤的叙述夹杂在朱缨的传记中,未单独列出,可能将朱鹤与朱缨、朱稚征同等对待,都视为隐逸者。也就是说,嘉定竹刻的创始人物的认定与三朱的身份塑造是息息相关的,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是朱缨。这得益于明代嘉定本土士人对朱缨“隐者”身份的塑造。
二、明人对朱缨“隐者”身份的塑造
朱缨(1520—1587年),字清父,号小松。明代先后有四人为朱缨写作传记性文字,即徐学谟(1522—1593年)、丘集(1524—1603年)、徐允禄(1563—1625年)、娄坚(1554—1631年)。从四人的生卒年代来看,徐学谟、丘集与朱缨是同辈之人,徐允禄、娄坚则为晚辈。四人为朱缨写作的传记性文字,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目的。徐学谟的写作纯粹是墓志铭以及祭文。丘集的《书朱清父墓志后》与其说是针对朱缨的写作,不如说是针对徐学谟撰写的朱缨墓志铭。娄坚的《先友朱清甫先生传》写于朱缨逝世后三十年。据娄坚所言,《先友朱清甫先生传》的写作可能缘于对世事变迁的慨叹,称“每叹世道交丧,日趋浮薄,正犹狂澜横流。而前哲之遗范,遂同潦水之归壑,几无复存者,盖不胜今昔之感焉”。①娄坚:《学古绪言》卷四先友朱清甫先生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8—49页。娄坚通过传记的写作来缅怀先哲的风采,同时也是对昔日素朴、多贤君子以及隐士的风气的追念。朱缨只是其中一人,在朱缨之外,娄坚还列举了王翘、唐钦训、宣应辑、丘集、张应武,“此数公者,或颀然严重,或坦然恬夷中,或退然而勇于为义言,或呐呐然而叩之不穷,行修而识明,论议皆依于忠厚,而确然有所不可夺,非世俗之君子也”。娄坚列举的人物中,王翘和朱缨是徐允禄《独行传》的写作对象。《独行传》的写作,目的与娄坚类似。据徐允禄称“今夫睂山俗乱起于一人,颍川多贤成于四长,故嚣陵诟谇之。为俗即有大人显者,方且茅靡,尔波流尔。而乃有独行隐君子之德,信古执礼,踽踽凉凉,年暮而名彰,棺盖而论定,没世之下,犹能令闻者啸歌感悼,不能自已。而曩所谓大人显者,声销景灭,富贵尽于一朝,顽誖留于人口,此亦足以为诚不以富之证。而敝俗或有反辕之日也。吾祖幽贞先生寔弘此道。嘉隆以来隐者繁称于邑中,而朵颐盰豫至有随俗雅化者焉。吾取其贞而不污,醒而能全者,得二人为之作传。”②徐允禄:《思勉斋集》卷九独行传,《四库禁燬书丛刊》集部第163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92—293页。《独行传》写作于世风日下之时。徐允禄将“大人显者”与“独行隐君子”作一比较,认为“大人显者”是俗乱的源头,从而寄希望于“独行隐君子”,期望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徐允禄选择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为画家,一为工匠,二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同一性质的人。今已无从知晓徐允禄选择王翘的原因,据徐允禄所言“不识其人,且闻其事不多”,但可能接触过王翘的作品。而对朱缨的选择,可能得益于徐学谟对朱缨墓志铭的撰写。
四人对朱缨的书写,虽出于不同的目的,但四人所塑造的朱缨形象却呈现出一致性。朱缨在世人的眼中,可能以擅长雕刻不同材质的作品著称,正如万历年间编撰的《嘉定县志》对朱缨的记载。但四人对朱缨的书写都强调朱缨在技艺之外的所为,更注重的是朱缨的为人,特立独行,不为势所屈的个性以及对待技艺的态度。如徐学谟在墓志铭中称“君之名几满天下矣,顾不知君者,谓君以技重。而知君者,则为技以君重”。娄坚则强调朱缨多能,并不局限于雕镂,称“先生少而多能,博涉有余力。而世或重其雕镂,几欲一切抹杀则过矣。其书工小篆及行草,画尤长于气韵,长卷小幅各有异趣。不多为诗,而间一书,其中所欲言,悠然之味,常在言外,庶几香山击壤之遗音焉。良由胸怀洒脱,有所自得于贫贱,故绝不同于俗耳”。③娄坚:《学古绪言》卷四先友朱清甫先生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95册,第49页。据娄坚所言,诗、书、画亦是朱缨所能。在诗歌方面,朱缨曾有《小松山人诗稿》传世,今已佚。在书法方面,朱缨工小篆,可能跟印章的篆刻有关。朱守城墓出土的“刘阮入天台”香筒,在洞门门楣处浅浮雕篆书“天台”,后有阴文“朱缨”和阴刻方印篆文“小松”。在绘画的运用方面,朱缨拓展雕刻作品的题材,出现花草、人物以及故事等题材,而且朱缨模仿绘画中的山水布景并运用到盆景的栽培上,徐允禄称“又间仿王摩诘诸名家所画山麓云树就盆景中,极其神理,其所纡曲盘折,尽属化工,他人即竭心力效之,终不能及”。④徐允禄:《思勉斋集》卷九独行传,《四库禁燬书丛刊》集部第163册,第293页。朱缨在诗歌、书法、绘画上的修养,并非与其雕刻作品无涉,而是将之融会贯通并运用到作品之上。在四人的书写中,只有丘集对朱缨的雕刻作品略有微议,认为朱缨的雕刻作品“徒为玩好,以娱时人耳目,莫能用之为典章法物,以传于后”。⑤丘集:《书朱清父墓志后》,韩浚、张应武等纂修,(万历)《嘉定县志》卷二十文苑,第176页。丘集曾在张应武的筵席上,劝朱缨说“君之艺,固世所罕见,惜枉用之。今将老矣,何不以吴产黄杨木刻一先圣古衣冠燕居席地危坐象,俾流传为儒林大宝乎”。但丘集仍肯定朱缨“能工于艺而有士行”。
虽四人对朱缨的书写更加强调朱缨在雕镂之外的修养和士行,与世人眼中的朱缨保持一定距离,但朱缨以雕镂为业这一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因此,朱缨对于雕镂的态度,成为形塑朱缨形象的关键。徐学谟认为朱缨的雕镂是“聊以寄情”,因此常常是“兴至始一运斤,主于自适而已。即所制器,非经岁月不能得”。这种“游戏”的心态正是后人强调三朱不同于将雕刻作为营生手段之人的地方。但这一说法过于强调三朱“脱俗”的一面,恐非事实的全部。据载,朱缨好饮,雕刻的作品多半换成酒钱,“以艺事之精绝,而强半入于酒家”。
总而言之,四人对朱缨的书写强调朱缨以“游戏”的态度对待雕镂,而且雕镂不是朱缨技能的全部,诗、书、画亦朱缨所能,在雕镂之外,朱缨的为人与个性更为重要。通过这些传记性文字的写作,将朱缨与职业匠人的形象区别开来,将原本作为营生手段的雕镂妆点成一种业余爱好,用以寄托情怀。这些书写塑造了朱缨作为文人工匠的形象。
徐学谟等嘉定本土人士进而将朱缨置于嘉靖、隆庆以来嘉定一地“好古”“近古”的士风之下予以肯定。明代晚期,嘉定一地风俗日趋奢靡,世风日下。徐学谟所塑造的朱缨“隐者”形象,以及以朱缨为代表的逝去的一代人的士风,成为嘉定本土人士缅怀的对象。嘉定本土士人通过这种文字性的书写,试图力挽狂澜,提倡“近古”“好古”之风。
总而言之,明代嘉定本土人士塑造朱缨的“隐者”形象,同时与世人眼中作为匠人的朱缨保持距离。这从万历年间编撰的《嘉定县志》将朱缨列入方技类以及丘集的微词亦可见一斑。也就是说,明人对于朱缨的身份认知存在着两重性,即作为隐者的朱缨与作为匠人的朱缨。这种二重性的身份认知在清代志书的写作中逐渐统一,这不仅牵涉到清人对竹刻与三朱认知的转变,而且牵涉到竹刻收藏者身份的转变。
三、竹刻收藏者身份的转变
明代嘉定本土士人对朱缨的书写,尽量将作为隐者的朱缨与作为匠人的朱缨区分开来。这可能跟当时竹刻的主要收藏者不是文人有关。朱守城墓出土款署“小松”的竹刻香筒,但因无墓志铭的出土,对于墓主人朱守城的身份一直停留于猜测阶段。笔者在阅读之余,收集到一条跟朱守城相关的资料。徐学谟曾为朱守城的儿子朱显卿撰写墓志铭,在墓志铭中提到朱显卿的“父铃,号守诚公者,以农起家,颇积高赀”。①徐学谟:《海隅集》卷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4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602—603页。可知,朱守城名铃,守城是其号,是一名富农。此外,嘉定竹刻在晚明的兴起,跟晚明折扇的风尚变迁有关。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称“今吴中折扇,凡紫擅、象牙、乌木者,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663页。这一折扇风尚的变迁是折扇的消费走向大众化、普及化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竹刻扇骨为时所尚。从朱守城墓的竹刻香筒以及竹刻扇骨的情形来看,当时竹刻的消费者或者收藏者不是文人。
但这一情形随后发生了转变,明末文人也参与到这种时好的消费与收藏中去。袁宏道注意到“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其事皆始于吴中,獧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然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千百年后安知不与王吉诸人并传哉?”③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31页。这类时好的消费与收藏不同于书画作品,不是自上而下从士大夫阶层逐渐波及到其他社会阶层,而是相反。这可能跟这类时好也寻求士大夫阶层的认同有关,甚至以士大夫阶层的品味为导向。正如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称“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①张岱:《陶庵梦忆》卷一,中华书局2007年,第20—21页。嘉定竹刻亦是如此。三朱的作品“在明末即已宝重,至今日则可遇而不可求矣”。②陆廷粲:《南村随笔》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16册,第313页。入清之后,三朱的作品成为文人收藏与吟咏的对象。如赵昕的《竹笔尊赋》、汪价的《竹笔斗赋》。通过这些文人的收藏与吟咏,朱缨在明代作为隐者与作为匠人的二重身份得到了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以竹刻作品为主题的赋中,笔筒成为争相吟咏的对象。如赵昕在《竹笔尊赋》中称“疁以竹刻名,器则为酒觚,为诗筒,为书尺,为楸奁;人则仙释;物则为蟹,为蟾蜍。因竹肖撰,恍惚海上鬼工矣。而笔尊尤精绝。一尊之周,写形造境,无美不出。漥隆浅深可五六层,漏沉其次也。镂法原本朱三松氏,朱去今未百年,争相摹拟,资给衣馔,遂与物产并著”;③赵昕修、苏渊纂:(康熙)《嘉定县志》卷二十艺文,第846页。汪价亦称“竹刻之器皆称绝,笔斗尤为通俗”。④闻在上修、许自俊等纂:(康熙)《嘉定县续志》卷四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1085页。此外,乾隆御制诗中涉及三朱的作品都是笔筒,无一例外。⑤《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六十一、卷七十三、卷七十五,《故宫珍本丛刊》第562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45—146、310、343页;四集卷八十一、卷八十二、卷八十五,《故宫珍本丛刊》第563册,第15、23、70页。暂不论这些三朱作品的可靠性如何,但这一现象说明清代文人将笔筒这一文房用具塑造成三朱的代表性作品。清代文人为什么选择笔筒这一器物类型?
据扬之水的研究,“笔筒”一词虽早在三国已经出现,但宋以及宋以前所说的“笔筒”是指收笔之用的笔套。⑥扬之水:《笔筒、诗筒与香筒》,《终朝采蓝》,三联书店2008年,第133页。作为收纳笔之用的笔筒,可能出现于明代晚期。在竹制笔筒流行之前,笔筒可能由其他材质制成。如严嵩籍没的财产清单中出现了象牙牛角笔筒的字眼。⑦无名氏:《天水冰山录》,《明太祖平胡录(外七种)》,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0—191页。作为明代新出现的文房用具,笔筒与竹节之间在造型上有着相通性,竹节被制作成笔筒是水到渠成之事。汪价在《竹笔斗赋》中称“制为笔斗,实疁创闻”,也就是说,笔筒是嘉定竹刻的首创。而且,书房空间是文人安身立命之所,文房用具也成为文人品质与追求的一种表征。笔筒,中空外直,襟怀若谷,这是文人的精神追求。清代文人将笔筒塑造成三朱的代表性作品,可能跟两方面原因有关,一方面可能跟笔筒是嘉定竹刻的首创有关,成为嘉定一地富有特色的物产之一;另一方面可能跟笔筒使用者的身份有关,其象征意义不容忽视。
四、结 论
嘉定竹刻始于朱松邻,这一表述是清代志书对嘉定竹刻的书写与塑造所造成的结果。嘉定竹刻在清代进入物产之列,且嘉定竹刻的创始人物的认定与清代志书对三朱的身份塑造保持一致,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朱缨。这得益于明代嘉定本土士人对朱缨“隐者”身份的塑造。但明代嘉定本土士人对朱缨“隐者”身份的塑造有意识地将之与作为匠人的朱缨区分开来。朱缨身份在明代的二重性在清代志书的书写中逐渐统一起来,一方面跟清人对竹刻和三朱的认知发生了转变有关,另一方面跟竹刻的收藏者身份发生了转变有关。竹刻的消费者或收藏者最初可能不是文人,随后文人也成为了竹刻的收藏者。进入清代,嘉定三朱的作品更是文人争相收藏的重宝并成为吟咏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笔筒被塑造成三朱的代表性作品。这一方面跟笔筒是嘉定竹刻的首创有关,另一方面跟笔筒的使用者身份及其象征意义密切相关。